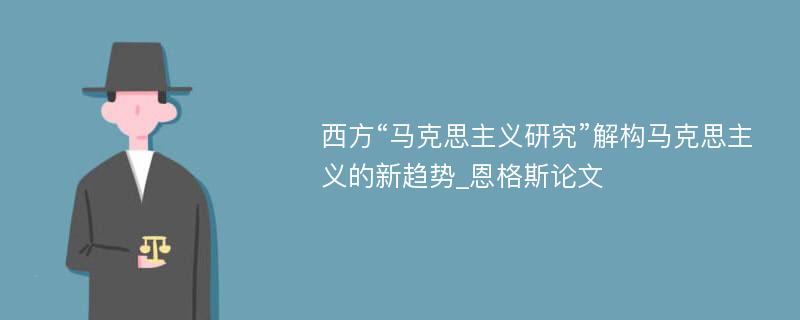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是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为此,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采取了“二分论”或“对立论”的立场:把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企图用青年马克思打倒老年马克思,用马克思打倒恩格斯。然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西方“马克思学”中出现了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这就是从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的“对立论”转向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一致的“同质论”。以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反思和批判“对立论”的不足与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同质性。批判性地分析“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构,揭示其实质,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批判
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构,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长期以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学”的主流学术观点是“对立论”。然而,“对立论”也遭到了部分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当诺曼·莱文极力用所谓“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全面对立”代替早期马克思主义解释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的立场时,洛弗尔就指出:“在重新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时,我们不应当简单地用一种相反的极端来纠正早期的极端立场”。(Lovell,David W.From Marx to Nenin:A Evaluation of Marx's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cityPress,1984.73.)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德纳尔在《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进行了专门批判,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有重要差别,但他们在技术观、社会发展道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践概念等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英国学者约翰·奥内尔既不同意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晚年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对立起来,也不赞同大部分“马克思学”学者编造的所谓恩格斯的“教条的、粗陋的、非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开放的、精致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故事,认为这种简单的“对立论”毫无意义,“既不能明确表达我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解,也不能明确显示马克思思想中的优点和缺点”。(Arthur,Christopher J.ed.Engels Today:A Centenary Apprecia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49.)比较全面系统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应该是亨勒和利各比。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一种再评价》一书中,亨勒详细地考察了“对立论”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着重从理论的性质与特征方面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诸如反映论、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决定论等方面的根本一致性、同质性。利各比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一书和《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历史》一文中,着重从理论的内容方面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以及与黑格尔关系等问题上的根本一致性、同质性以及各自所包含的所谓“内在矛盾”,分析和批判了“对立论”的主要观点及其错误。亨勒和利各比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批判和“同质论”的论证,影响很大,以至于持“对立论”立场的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卡维尔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部分学术研究又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传记作家的“一致论”的立场。(Steger,Manfred B.and Carver,Terrell,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6.)
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对“对立论”反思和批判的基本思路是:证明“对立论”所贬低和批判的恩格斯的思想也是马克思所具有的,也就是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根本一致的、同质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对立论”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特征。
第一,把马克思的思想设想为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整体”。大部分“马克思学”学者在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时,把马克思的思想想象为一个连贯的统一整体,否认其内在冲突与矛盾。为此,二分论者必然把马克思加以“纯化”:要么对马克思的著作“有选择性地加以引用”,对相反的观点视而不见;要么把马克思主义中的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内容归结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背离和歪曲。在利各比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比二分论者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们各自的思想不仅前后矛盾,即使同一时期的观点也彼此不同。“在他们每个人的著作都如此具有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是无意义的。”(Rigby,S.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236.)
第二,“马克思,好;恩格斯,坏”的绝对对立的价值评价方式。二分论者不仅要肯定马克思的思想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而且要维护“纯化”了的马克思的思想的地位。为此,他们一方面把马克思“当代化”,用各种当代哲学和社会学思潮解读马克思的思想,让马克思披上了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时髦外装;另一方面矮化恩格斯,把恩格斯看作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根源,企图通过贬低恩格斯的思想价值彰显马克思的地位。这样一来,“一位喜爱辩证法的作者会赞扬马克思辩证法的精妙;相反,一位厌恶辩证法的作者会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归因于恩格斯的形而上学的阴影”。(Arthur,Christopher J.ed.Engels Today:A Centenary Apprecia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xxi.)
第三,二分论者“彼此相互矛盾,有时自相矛盾”。不同的二分论者视野中有不同的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或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或与黑格尔主义决裂者,晚年马克思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或从来就不是实证主义者。更严重的是,二分论者往往自相矛盾,例如约丹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进化》一书中,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恩格斯式的形而上学者,同时又说马克思有一个“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因果关系理论”。(Hunley,J.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62.)
第四,寻找“真正马克思”或“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情结。“对立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情结是对“真正马克思”的寻求。在二分论者眼中,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起源于恩格斯并被列宁和斯大林所歪曲发挥了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恢复和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必须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恩格斯的思想中分离出来,回到“真正马克思”。在这场寻找“真正马克思”的运动中,“既诞生了不加批判的英雄偶像,又产生了无足轻重的‘替罪羊’”。(Gouldner,Alvin W.The Two Marxisms: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Development of Theory.New York:Seabury Press,1980.253.)青年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被置于“真正马克思”的崇高地位,而恩格斯也就成为二分论者所厌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替罪羊”。
二、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及其特点
在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不像二分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立的,相反,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具有一致性、同质性,这就是都存在着“内在张力”或“内在矛盾”。二分论者的错误不在于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重要差别,而在于只是把他们两人各自思想的“内在矛盾”化为所谓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外在对立”,企图以此消融马克思的思想本身的问题。利各比指出,要走出“对立论”的理论困境,必须根本转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解读方式,从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统一转变到强调其内在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性质的认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才能正确对待各个解释者的解释,才能消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真正马克思”的企图,真正从现实需要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
可见,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思想和恩格斯一样,也具有内在矛盾性。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对“同质论”的论证,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所谓“内在矛盾”的发掘。
第一,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矛盾。古德纳尔通过考察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趋向,集中探讨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张力,并认为这种张力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既是理性理解,又是政治实践;既是关于世界的叙述,又是改变世界的行动‘命令’。”(Gouldner,Alvin W.The Two Marxisms: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New York:Seabury Press,1980.34.)据此,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亨勒分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证主义因素和人道主义因素,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比他们的大多数学生所愿意承认的更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Hunley,J.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145.)利各比则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呼吁”,要么“成为各种多样的纯学术性社会理论”。如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追求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结合,不仅“动摇了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而且损害了所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Rigby,S.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234.)
第二,经验论因素与唯理论因素的矛盾。利各比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从具体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经验方法,同《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强调概念、理论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总体性方法是不协调的。亨勒声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论中,简单化的经验主义与精致的抽象方法是相互矛盾的。(Hunley,J.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69.)
第三,人类中心论历史观、实用主义历史观与法则学历史观的矛盾。利各比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着三种历史观的对立和冲突,也就是把历史看作人克服自身的异化而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质的过程的“人类中心论历史观”、把历史看作在一定条件下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实用主义历史观”、把历史理解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所支配的自然过程的“法则学历史观”的矛盾。(Rigby,S.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
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95.)
第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的决定论与渗透论的矛盾。利各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论断,但同时又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的观点。这必然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现实中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活动”。把经济从社会整体中抽象出来并宣布它是现实的“基础”,这“似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曾经正确地谴责为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例子”,使“对社会的最唯物主义的分析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个真正的辩证讽刺——成为纯粹的唯心主义”。(Ibid.,133—134.)
第五,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古德纳尔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矛盾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的革命策略中也存在革命和改良的“张力”。在他看来,马克思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变化概念,一是逐渐的、进化的和连续的,另一个是不太连续的、突发的、灾变的。前者与达尔文主义相一致,后者在黑格尔著作中找到根据;前者可能通向“仪式主义”或“修正主义”,后者通向“冒险主义”或“革命救世主义”。利各比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原则,反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为工人阶级中的持续的改良主义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Ibid.,214.)
应该说,当代的二分论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内在矛盾,但大部分人把这归因于恩格斯,用青年马克思解释和统一马克思的思想。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立论”打着“回到马克思”的旗号,用歪曲了的马克思来反对歪曲了的恩格斯;“同质论”则打着“中立、公正”的旗号,在歪曲恩格斯的同时,重点反对马克思。第二,“对立论”把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他们所不喜欢的观点归结为恩格斯的歪曲,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同质论”则企图证明恩格斯的缺点同样存在于马克思著作中,从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外在矛盾”“还原”为各自思想的“内在矛盾”。第三,“对立论”坚持马克思的思想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并把这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作为当然的前提;“同质论”则企图破除马克思思想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假设,证明不仅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不一致,而且同一时期的思想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第四,“对立论”在解构马克思主义时,仍然保留了被“纯化”和“当代化”了的马克思,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工具;“同质论”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打倒,企图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第五,从历史背景看,“对立论”主要是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同质论”主要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巨变的理论回声。
三、“同质论”解构方法批判
以亨勒、利各比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批判,对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的论证,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伙伴论”或“一致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的早期解释者一般持这种观点。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卢卡奇、科尔施,在指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方面与马克思不同的同时,也肯定了二人思想整体上的一致性。二是“二分论”或“对立论”,利希特海姆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确立并成为西方学术界主导性观点的标志。三是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同质论”。“同质论”学者的学术贡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一片鼓噪声中,他们敢于逆潮流而动,公开批评二分论者观点的片面性和方法的非科学性,系统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内容和理论特征、理论性质上的根本一致性,为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推动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也为我们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启示。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部分西方学者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根本目的,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早期解读者那样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而是要从根本上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巨变,已经在实践上完成了解构马克思主义,但在理论上的解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构是“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主要任务,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采取的解构方法不同。从制造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到用早年马克思解读晚年马克思,再到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分裂与对立,捏造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峙,这是“马克思学”学者解构马克思主义先后使用的手法。然而,在利各比看来,以前的“马克思学”学者为解构马克思主义而对它的批判,都只是“外在批判”。各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外在批判”的典型。然而,“正如基督徒不可能因为受到如印度教的批评而动摇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受以外在于它的理论为根据的批判的影响。”(Rigby,S.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236.)在利各比看来,要彻底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样只能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批判马克思主义。他自己的任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内在批判”,即通过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内部,发现其内在矛盾,证明其不具有科学性,从而把它彻底颠覆。
如果说利各比等人用“同质论”批判“对立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他们企图通过发掘所谓“内在矛盾”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则充满了主观主义的想象和资产阶级的偏见。
第一,“中立”立场不中立。虽然利各比等人标榜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来著书,也不是作为一个职业马克思学家来立说,而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来进行客观的公正的研究,但实际上,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欲盖弥彰。他们批判“对立论”,不是因为“对立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不公正,而是其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方法的不正确。在他们看来,要完全彻底地解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用早年马克思反对晚年马克思或用晚年马克思反对早年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唯一的方法就是像反对恩格斯一样彻底抛弃马克思。这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进行“公正”、“客观”的研究,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批判。
第二,“内在矛盾”论的非客观性。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企图通过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所谓“内在矛盾”来解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说的“内在矛盾”纯粹是自己的主观臆造。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致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在科学地“解释世界”基础上能动地“改变世界”时,不仅不是对其科学性或批判性的损害,反而是对其的检验和证明。这里根本不存在古德纳尔等人所说的“内在矛盾”。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性质。它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又认为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是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而存在和实现的。这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利各比不懂得社会历史的这种辩证性质,把历史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人为地对立起来,从而制造了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中的“实用学历史观与法则学历史观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的统一。它认为,虽然现实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各个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总体性的复杂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科学的抽象对这个现实的社会总体进行逻辑分析。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大量的经验材料运用逻辑方法从混沌的感性社会总体中抽象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并揭示了经济在历史过程中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时,他不是从唯物主义转变为所谓“纯粹的唯心主义”,也没有陷入所谓“经验论因素与唯理论因素的矛盾”,而是找到了唯物辩证的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在革命实践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也不存在所谓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革命家,一生始终坚持革命的信念,从未与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妥协过。同时,他们又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灵活地运用改良策略,把改良作为宣传发动群众和积蓄革命力量的准备。这体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的统一。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形式或手段,都必须以对社会历史规律和具体的革命形势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古德纳尔等人从马克思主义中的所谓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矛盾中引出所谓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只能说明他们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无知,要么是出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总之,“同质论”者由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需要和不懂辩证法,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重点论与全面论的统一看作相互矛盾,似乎强调了科学性,就不能坚持批判性;强调了反映论,就不能肯定主体能动性;坚持了经济决定作用,就不能有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坚持了革命原则,就不能选择改良策略,如此等等,否则就陷入了所谓的“内在矛盾”。这样纯粹主观的“内在批判”,解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质论”本身。
第三,“解构”目的的非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深深根植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实践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的本质。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企图通过理论的批判来解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其致命缺陷在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脱离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从而一方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或那个思想观点与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以为通过批判马克思就可以彻底驳倒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封闭的纯粹理论,以至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最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被置于理论视野之外。这种非实践的纯粹理论批判,虽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增添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不可能达到所谓“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