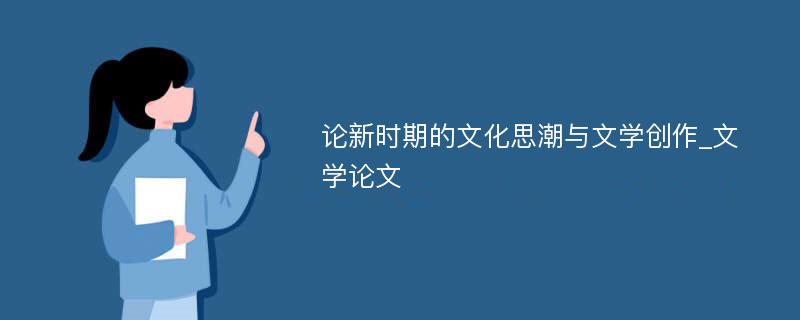
论新时期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0)04-114-(09)
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存在”的命题,认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由文化所产生的,文化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谈到文化变革的原因时,西方的学者各有不同的见解:怀特将技术发展看作是文化变革的基础;斯图尔德强调生态学的重要作用;韦伯偏重于宗教意识在重要性;华莱士注重心理学方面的因素。然而,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文化变革的终极阐释,文化的变革总是离不开经济。文学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制约着文学的表现与发展,文学则反映着一定时期的文化特征,这在1985年至1990年代表现得十分突出。
一
1985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拓展深入,西方文化介绍引进也加大了步伐,各种哲学思想大量地被翻译进国内:克罗齐、叔本华、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思想;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弗洛姆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海德格尔、雅斯贝尔士、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维特根斯坦、赖尔、布莱克的日常语言哲学;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等等,都先后成为中国理论界热衷的话题。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诸多代表作家先后被介绍进来: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象征主义文学家里克尔、勃洛克、艾略特、瓦雷里;荒诞派大师卡夫卡、贝克特、尤奈库斯;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梅尔勒;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鲁尔弗,他们成为中国作家仰慕借鉴的对象。西方当代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也被大量介绍进来:语义学与新批评派,人类学与原型批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批评,接受美学与阐释学批评,后结构主义理论与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理论与文化诗学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评等,构成了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热”。虽然在文学批评界一度形成了新名词、新术语满天飞的局面,为人诟病,但毕竟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角,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1985年至1989年间,中国的文化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指归的现象。由于西方思想与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大都以中国知识界的召唤与行动为前提,追慕新奇排斥平实、推崇经典关注精致,使国内此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精英文化的意味,文学创作也形成了别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
在观照80年代的文学创作时,李洁非说:“80年代中期后,随着‘西方’文学价值禁忌的实际上的解除,‘西方化’的呼声开始变成了一场竞赛,其疯狂程度可与冷战时期的国际军备竞赛相媲美。”(注:李洁非:《实验和先锋小说》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理论批评》281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这说出了在1985年以后的中国,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以西方当代文学为模本,显示出中国作家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统天下的的不满,他们努力追踪模仿域外文学新的艺术手法、渴望赶上世界文学潮流。无怪乎作家邱华栋曾经这样说:“从某种程度上讲,1985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被影响下的当代西方的汉语文学的变种文学,1985年以后中国作家们的很多努力,在今天看来更多的应该算是在西方大师的阴影下的匍匐前进的现实,几乎每一个中国‘走红’的‘现代派’、‘笑脸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的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见邱华栋《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版。)邱华栋将文学的这种模仿化追求称为“一种当代文学的侏儒行为”,这种评说虽然有偏激之处,但也道出了1985年以后西方当代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之深与广。寻根文学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迪,王安化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老井》、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等,都是例证,而在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寻中,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对于传统的解构与批判。被称为“荒诞派”小说的创作承继了欧美“黑色幽默”创作的衣钵,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陈染的《世纪病》等作品,都以一种对于传统反叛的姿态,刻画了一群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中国当代“嬉皮士”形象,表现出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不满与颠覆。在现代主义戏剧的实验中,可以见到西方现代派戏剧的濡染,高行键的《野人》、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陶骏、王哲东等的《魔方》、魏明伦的《潘金莲》、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朱晓平等的《桑树坪纪事》等剧作,都透露出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探索意味。“第三代诗歌”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诗群、“整体主义”诗群、“非非”诗群、“新传统主义”诗群、“海上”诗群等,都以反传统、反崇高、反文化的姿态,在对传统的文化解构中建立他们的价值系统与文化观念。
由于80年代中期后对于域外文化的热衷、对于西方当代文学的追慕,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呈现出对西方当代文学的模仿借鉴的趋向,也展现出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建的姿态。
2.以探索创新为目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
自1985年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拓展深入,由于解除了诸多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追求探索创新的风气。在谈到此时期的历史时,孟禄丁说:
一切定论对青年来说都是有疑问的。时代的压力迫使我们对以往进行反思。原有的秩序对我们来说越来越不适应。我们不满足于过去,要求进一步开拓、发展。发展意味着打破,打破意味着创造,不断地创造,推动人类文明的延展。
“创作自由”使我们振奋,驱使我们勇敢地对原有艺术模式和框框作出新的评判。
新时代、新观念、新意识无时无刻不冲击着我们的头脑,逼使我们从根本上更新艺术的观念,去探索艺术的新途径。(注:见李一:《走向何处》,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中,以新的艺术观念去探索艺术的新途径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构成以探索创新为目的的文坛新景观。这正如李洁非所说:“总之,自那时候起,文坛完全被‘新’字所左右,使这样一个按照中国传统趣味来说偏于贬义的字眼大行其道。被冠以‘新’字的作家作品扬眉吐气,尚不够‘新’字的作家则拼命想挤进这样的行列,而那些显然毫无可能的作家则抬不起头来只得徒劳地发出一些抱怨。……正是从1985年开始,‘标新立异’取代了其它一切而成为作家从事写作和取得成功的佳径,一个作家从默默无闻到顷刻名播遐迩确实变得容易多了,只要他的小说够得上‘新’字,成功就基本上有保证,反之,如果失去了‘新’字的眷宠(即便曾经‘新’过)则很快会被淘汰。”(注:李洁非:《实验和先锋小说》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理论批评》256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在文学创新的过程中,新潮小说以其别样的风采为文坛所称道,莫言的小说以细腻生动的生命体验与感觉、奇特的想象与奇诡的潜意识、色彩缤纷充满张力的语言等,构成了他的小说创作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风范。《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金发婴儿》等作品,使莫言成为80年代站在创新前沿的小说家之一。残雪的小说用梦魇般的笔调描写荒诞社会造成人们的丑陋人性与变态心理,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荒诞变形的描写手法、敏感细腻的感官表述、阴湿闭塞的环境描写、阴鸷变态的性格刻画等,都使她的小说呈现出独异的个性。《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污水上的肥皂泡》、《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旷野里》、《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等作品,都显示出残雪求新求变的创作姿态。王朔以一种独特的玩世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他将愤世嫉俗的心态用调侃、嘲讽、挖苦等语态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颠覆与反叛,塑造了一些处于社会边缘与底层的顽主形象。漫不经心的叙事方式、调侃反讽的机智语言、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形成了王朔小说独有的意味。《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等作品,都呈现出王朔小说新颖的谐趣味。
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以丰富的想象、独特的叙事,将历史与现实、记忆与当下相互渗透,使历史小说成为作家们“随意搭建的宫廷”,如作家苏童所说的“是我按自己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注:苏童:《后宫·自序》。)。周梅森的《军歌》、《国殇》、《孤旅》,叶兆言的《追月楼》、《状元镜》,苏童的《红粉》、《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余华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作品,都呈现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色彩。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续到90年代,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叶兆言的《花影》、《1937年的爱情》等作品,使按自己方式勾兑历史的创作方式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三代诗歌”创作中,以“带着个人的独创性加入传统”的方式(注:石光华:《企及磁心·代序》,见《磁场与魔方》第13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进行诗歌创作,主张破坏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强调对于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张扬,有的打出了“新传统主义”的旗号,宣称:“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和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注:《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展览》《诗选刊》1987年第1期。)宋渠、宋炜的《大佛》、廖亦武的《情侣》、《巨匠》、西川的《读1926年的旧杂志》、《近景和远景》、钟鸣的《树巢》、李亚伟的《旗语》、海子的《土地》等诗歌中,都展示出新一代诗人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
1985年以后,中国作家们各显神通地变换着手法进行各自的文学探索与实验,在不满传统中求新求变,在求新求变中努力超越世俗,使中国文坛奇芭缤纷。但是,也有人对于这样一味以新为贵的风气表示了不满。
3.以形式的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
新时期文学在创作与评论中都注重文学的本体,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看重作品的思想内涵而忽视文学特性的偏向。在文学创作中,自1985年始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成为诸多作家努力的目标。早在1982年,敏锐的文学批评家李陀就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里,这决定我们的文学必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有一个新的文学时期。这个文学时期的光辉,也许将能与唐诗、宋词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阶段相互映照。那怎么能设想出这样一个新的文学时期会不探索、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文学形式呢?怎么能设想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会不发生重大变革呢?能想象吗?反正我不能。因此,我至今坚持,就艺术探索来说寻找、发现、创造适合表现我们这个独特而伟大时代的特写内容的文学形式,是我们作家注意力的一个焦点。不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必定会辜负我们的时代。”(注: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李陀将“寻找、发现、创造适合表现我们这个独特而伟大时代的特写内容的文学形式”看作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义务。80年代初,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舒婷、顾城等诗人的朦胧诗、宗璞、谌容的荒诞小说都体现出作家们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关注,但是真正在中国文坛展开文学形式实验的还是到1985年以后。
诗人徐敬亚在1986年指出:“1986年——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把80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一个新的潮头。”(注:《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26日。)在这样的艺术探索中,对于艺术形式的实验与迷醉成为诸多作家的执著追求。有人将马原在1985年、1986年的异军突起视为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革命性的事件,认为马原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喜马拉雅古歌》、《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虚构》、《大师》、《游神》、《战争故事》、《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上下都很平坦》等作品,都被视为小说形式实验的佳作,他受到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略萨等文学大师的影响,倾慕于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西方新小说的审美原则,他的小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迷宫与叙事圈套,推翻了传统的叙事秩序与方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或频频变换叙事视角和身份,或执意颠覆叙事的逻辑结构,在奇幻无比的故事空间里,在亦真亦幻的情节片段里,形成了独特的形式魅力。受到马原的影响,洪峰的小说也努力进行着形式的探索与实验,从《奔丧》开始,他执意作着小说形式的探索,在叙事策略上,他故意将原本完整的故事叙述得零零碎碎扑朔迷离,努力寻找生命本体的奥秘。《翰海》、《极地之侧》、《湮没》、《离乡》、《重返家园》等作品中,都可见到特异的叙事形式。
在话剧创作中,高行键的《野人》、《彼岸》参照西方当代戏剧家的探索,不受实在的时空的约束,表现出其对于话剧形式与表现手法的探索与实验。陶骏等创作的《魔方》运用象征隐喻手法,以拼盘式的戏剧结构,在反讽、荒诞、谐谑、夸诞等手法中,净当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状态生动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导演王晓鹰说:“《魔方》将我们惯常遵循的戏剧创作规范通通置于脑后,真个是‘无法无天’了。”(注:王晓鹰:《〈魔方〉导演阐述》《探索戏剧集》第4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魏明伦的《潘金莲》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将中外古今诸多人物搬上同一舞台,互相自由对话,体现出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别出心裁。锦云的《狗儿爷涅槃》引进了小说的叙事手法,让狗儿爷作为舞台上的叙事主体,并按照人物的意识流动安排戏剧结构,突出对于人物心理的表现,体现了该剧运用现代意识表现农民心灵史的独特尝试。朱晓平等的《桑树坪纪事》以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主要人物的故事形成剧作的结构框架,生动地展现了黄土高原农民的坎坷命运惨烈人生。
在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成为众多作家们的执著追求,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学的不满与新的文学观念的深入,也展现出此时期文学创作的多姿多采,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由于过度热衷于形式的实验,一些作家因此而忽视文学的内容,以至于使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技巧的玩弄,使文学逐渐脱离了读者。
二
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精英文化逐渐失去了市场与活力,而大众文化成为90年代具有很大覆盖面的文化。
1.中国90年代的大众文化有它的特性:
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指归。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常常强调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职责,或强调伦理的教诲,或突出道德的意义,或追求政治的目的,文化常常显得分外沉重,有时甚至有些不堪重负。90年代的大众文化将消遣性娱乐性置于首位,在快餐式的文化读物中,在轻松惬意的影视片中,在具有刺激性的电子游戏中,消解现代社会工作中的紧张心理与情绪,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虽然大众文化的文化品位与审美格调极需提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化的政治的功能、道德的说教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大众文化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
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浓郁的抑商扬士的色彩,而90年代的大众文化是商业性的,它与商业赢利几乎难以分开,因而“包装”成为一个流行甚广的词。大众文化往往成为一种流行商品迅速为大众所接受,而这种流行又常常与时尚性难分伯仲,追逐时尚、追求时髦成为诸多大众的生活乐趣,甚至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固然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它带着过多的实利色彩,它的时尚性使它往往呈现出庸俗的一面,但却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的模式,呈现出横向移植与模仿的特征。
大众文化以现实性、及时性为内涵。
中国文化历来充满着英雄色彩与隐士意味的两方面,或以铁肩担道义式的崇高使命感规范自我的责任,或用隐匿山林放纵自我的绝对自由寻找人生的独立。90年代的大众文化回避抽象的崇高,也不崇尚天人合一式的隐士风范,而转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甚至表现出一种“去理存欲”及时享乐的生活态度,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虽然大众文化中透露出浓重的拜物情绪,但大众文化的现实性及时性使它洋溢着一种生存的愉悦与生动。
2.中国90年代的文化转型必然也影响着文学的转型,这使90年代文学呈现出与80年代迥异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使90年代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
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忽视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
新中国文学大都致力于对于时代英雄的讴歌与描写,而往往忽略了平凡普通百姓生活的观照,80年代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也大都如此,90年代文学却突出了对于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进入90年代后,新写实小说作家仍然循着80年代末《烦恼人生》、《风景》等作品的姿态,方方的《落日》、《结婚年》,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官人》等,都以社会下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为内容,“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实相呈现在读者面前”(注:曾卓:《太阳出世·跋》。)。1994年《北京文学》推出的新体验小说倡导作家“率先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躬行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深切体验,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注:《本刊'94推出新体验小说》《北京文学》1994年第1期。)。作家们深入下层社会,真切地反映下层社会的庸常人生,或描写板儿爷的生存状态(袁一强《“祥子”的后人》),或勾画换房人的人生(王愈奇《房主》);或讲述丧葬工的生活(齐庚林《殡仪馆里的故事》),或记叙小酒馆里的故事(毋国政《在小酒馆里》),作家们大都亲历现实生活,在亲身体验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中,对“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注:毋国政:《回避“深刻”》《北京文学》1994年第4期。)作生动真实的描绘。1994年《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倡导的新市民小说,观照“在世俗化的致富奔小康的利益角逐之中”的市民人生,新市民小说也大都描写城市中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或描写都市闯入者的奋斗挣扎(邱华栋《闯入者》),或坦现市民社会中的性爱欲望(张欣《爱又如何》),或揭示都市生活中的阴暗丑陋(孙春平《放飞的希望》),总之市民社会中种种庸常的生态成为作家们关注与描写的题材。新现实主义作家直截了当地提出“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注:谈歌:《小说与什么接轨》《小说选刊》1996年第4期。),站在大众的立场,关注大众的生活状态,为大众代言,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的创作追求。他们或写出社会转型期中企业、乡镇的经济困境(谈歌《大厂》、关仁山《破产》、何申《穷县》),或揭示改革实施的艰难(关仁山《大雪无乡》、何申《村民组长》、刘醒龙《菩提醉了》,或揭露基层政权的腐败(何申《信访办主任》、关仁山《九月还乡》、刘醒龙《去老地方》),新现实主义作家们都将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为使命。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关注当下、关注自我,“是为关心灵魂和人的卑微处境的人写的”(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他们或描写现代人的欲望追求(朱文《我爱美元》、韩东《为什么?》、李冯《多米诺女孩》),或揭示现代人困惑的心理(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刁斗《状态》、刘继明《浑然不觉》),或展现现代人的奋斗挣扎(刘继明《可爱的草莓》、毕飞宇《生活边缘》、朱文《因为孤独》),新生代作家大都以其自我的生活与体验为题材,却也写出了社会卑微处境中人们的生活与心理。9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以写实为主的风范中呈现出对于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而忽视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这与文化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
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忽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
新中国的文学历来关注具有史诗意味的题材的描写,在对于崇高的美学境界的推崇中,追求史诗性的宏大叙事。80年代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大抵如此。90年代的文学却突出地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这与大众文化的兴盛有着直接的联系。大众文化对于现实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都使文学创作呈现出独特的追求。新写实小说大都以“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它那既有故事、又没有故事模式,让主人公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自由行动”(注:《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新写实小说这种以生活流式的叙事方式结构作品,在平凡、琐碎、偶然的日常生活琐事与细节的描写中,展示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新体验小说将作家的亲历性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体验普通人的生活中描写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创作常常“没有通常的故事和人,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段像浮冰漂动着”(注:毕淑敏:《炼蜜为丸》《北京文学》1994年第3期。),在充满着日常人生情趣的琐碎生活的描写中,真切地展示普通人的生活与心态。新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常常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困境,但创作大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以女性意识进行写作,用私语化的叙事方式叙写女性的私人生活,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私人生活》等,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回廊之椅》、《一个人的战争》等,努力对女性意识和欲望作细腻的展示与解剖,而忽略对于历史场景、社会生活的描写。新生代作家韩东曾说:“我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无法真正屏弃,并不虚无。”(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面对当下人生碎片的写实色彩,把对于真实生活与感受的叙写置于首位,不追求创作的史诗意味,不营构作品的宏大构架,常常在人生碎片的真实叙写中展示当下人生。在散文创作领域中,以素素、黄爱东西等为代表的小女人散文也以琐琐碎碎的生活为题材,忽视重大题材的叙写,而将个人的微妙情感与琐碎生活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90年代文学对于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使文学充满了独特的生活情趣,展示出现代人新的生活观念。
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视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
新时期作家大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语言意识,努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90年代文学创作更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而反对新潮创作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探索与追求,不满于先锋文学追求语言的雅化。新写实作家常常“关心的是把生活变成自然的、有滋味的语言”(注:《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他们的创作常常注重语言的本真色彩,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语、世俗之见,以俚俗之语描写凡俗场景、世态人情,在近似于老妪都解的生活化世俗化的语言中,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地叙写平平常常的现实人生。新体验小说创作“注重语言的生活化,口语化,平易近人,与纪实性的内容谐调”(注:赵大年:《几点想法》《北京文学》1994年第2期。),新体验小说以它的描写世俗的题材、如诉家常般的叙事语调、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体现出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平易性的审美风范。自然平和中叙说其接触的人生故事,大多没有剑拔弩张式的骇人听闻;絮絮而谈里透露其体验的甘苦酸辛,大多没有九曲回廊式的跌宕曲折。新现实主义作家以小说是一门面向大众的世俗艺术的观念从事创作,他们“努力放下文章腔来说话,说得自然流畅”(注:何申:《往事如烟几十秋》《小说家》1996年第5期。),努力以公共话语发言。他们努力以生活化世俗化的语言写作,不雕琢不粉饰,不拿腔拿调,不追求典雅精致,而崇尚朴实畅达,不信奉曲折含蓄,而追求晓畅平实,不回避俗语俚语,而注重真实生动,使创作充满了生活的生动与丰厚。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在追求语言的精确中,努力使语言自然生动。他们克服了新潮作家对于语言陌生化游戏化的追求,而努力以反朴归真本色的语言进行叙事,关注对于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以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叙写作品,不哗众取宠,不故作艰深,使他们的作品洋溢着一种自然真切的世俗化意味。
3.90年代文化的转型必然影响了文学创作,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历来过于沉重的政治的、文化的负载,回到其原初的消遣娱乐的状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解放。文学创作对于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使文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的演说,不再充满了贵族气息,而呈现出以一种与民众平等的姿态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使90年代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平民精神。由于大众文化的过于强调消遣性娱乐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文化中的精神与理想的追求。文学创作在对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中,也往往忽略了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精英人物与境界的描写,它在对现实生活“真”的反映中,常常忽略了“善”,甚至忘却了“美”。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时尚性的特征,也使90年代文学突出了其商品的性质、时尚的意味,在作家——作品——读者的关系链中,读者被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文学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就考虑到读者,在作品被推向市场的过程中,种种的商业宣传成为让文学作品被读者所接受的重要手段。摸准文学市场揣摩受众心理也成为文学策划者与创作者重要的一环,文学也就常常成为一种社会的时尚之一。在这样的状态下,文学创作有时就往往存在着迎合读者迎合市场的倾向,作家的创作也大都没有了“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仓促草率,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淡化了,更别说经典意识了。虽然文学的时尚意味使有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发行量,但有时只是过眼烟云,常常成为一种精神快餐。
大众文化的现实性及时性使人们不再将渺茫的理想、空幻的崇高作为精神的支柱,而是努力关注现实生活当下人生,90年代文学的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也与大众文化的这种特性一脉相承。对于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的关注,将普通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生动细致地描写出来,使文学充满了人生的趣味与生活的生动,摆脱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概念化的倾向。在对于偶然性、零碎性的人生琐碎生活的描写中,常常使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显得过于琐碎平庸,作家甚至有时将自己生活中的琐碎经历写进作品,使创作缺乏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作品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固然使作品贴近了生活,但有时也使作品显示出粗俗化的色彩。文学在关注世俗的同时,忽视了文学的典雅。
90年代文化的转型与文学的转型是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的世俗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看待90年代的大众文化,如何看待90年代文学的世俗化,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收稿日期:2000-01-07
标签:文学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北京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