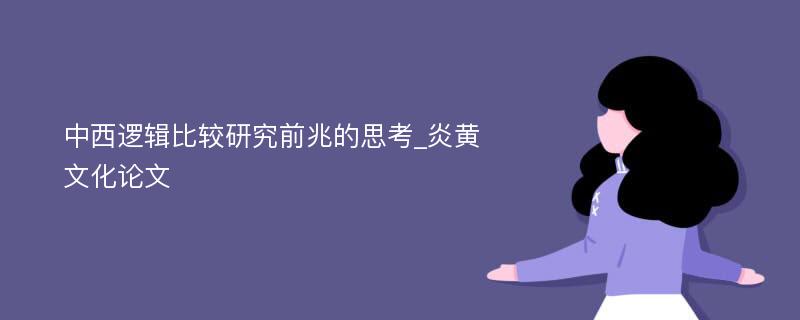
反思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性问题论文,逻辑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769(2004)05-0040-05
一、为何要提出“前提”性问题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不应只是表面地讨论各自的“异同”或熟优熟劣,事实证明这样的讨论于事无补;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去探讨各自的研究对象、个性与“长短”,发现与评价中西逻辑的人类性价值,寻求中国新文化建设以及人类知识创新、思维方式革新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对于中西逻辑比较研究问题,尽管学者们会采用不同的理论观点作出回答;但是,无论从何种视角回答这一问题,都应对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自觉的意识。这既关乎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立论依据和展开方向;也是我们研究者审视以往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目的、主题、方法及得失的依据。
理论研究中,“前提”是必须拥有的真实根据。它是生成思想的理论根据与“硬核”,是尚未展开的逻辑起点,蕴涵着逻辑的全过程及其终端。作为思想根据的“前提”,虽然是以“假设”的形式提出,但这种假设作为“理论硬核”在内容上必然是具体的——由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1]选择什么样的前提,就会有什么样的研究出发点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因此,理论研究的“前提”是研究的关键所在,是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大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自梁启超开启墨家论理学研究以来,我国几代学者对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和理论成果上都是颇有建树的。然而,一直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的争论。尤其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延续至今的这场争论,出现了诸多挑战传统观念的观点,如: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自然语言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辩逻辑”、“内涵逻辑”、“逻辑指号学”、“古汉语的语义学”,等等。主要聚焦在是否存在“名辩逻辑”的问题上。这场争论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对“中西逻辑”进行合理的比较研究。要摆脱这种困扰,惟有反思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二、前提性问题
问题之一: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19世纪中叶以前,中西两种文明、文化总体而言是彼此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没有进行比较研究的机缘和必要。中国人对中西文明、文化的比较研究,根本起因于鸦片战争为始点的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和交锋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民族生存的巨大压力和强烈愿望迫使中国人去审视自己,去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这种比较研究,“其过程总体是按照军事、经济、政治之比较,然后是文化之比较,再后是中西哲学(包括中西逻辑在内。笔者加)之比较的次序进行的。”[1]这个次序表明:中西比较研究是从根本上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路径。[1]甲午战争的惨败,使近代“西学第一人”、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的富强要靠‘实学’,要靠掌握真理,进而思考如何去求取真理的‘思理’——思维术的问题,开始注意于方法论。”[2](p242)他认为,逻辑学(名学)是西学的“命脉”,“其理有以统诸学”,[3](p3)即:“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集中总结了科学思维的方法和体现了“黜伪而祟真”[4](p2)的科学精神。严复着力翻译、介绍西方近代逻辑学,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则进一步把中国的墨辩与西方的形式逻辑(甚至印度的因明)作比较研究。他们借鉴西方近代的科学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的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为的是从根本上救治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未经分析的整体直观思维,实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重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最缺乏的是西方的那种逻辑分析方法——“缺少分析乃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缺陷”,[5]要重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就必须吸收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严复指出:“名学(逻辑学)固无待于理学(哲学),而理学欲无待于名学(逻辑)则不能也。”[6](p12)胡适说:中国人对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感到陌生,要最有效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促使其融入中国文化并发展中国自己的固有文化,单纯地依靠翻译西方逻辑著作决不能达此目的,而必须通过比较研究中西逻辑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才能成功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佳成果”。[7](p9)“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7](p7)他借鉴西方逻辑的分析方法,重新梳理中国哲学,著成全新面貌的时代性佳作《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冯友兰也深刻认识到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就是“缺少分析”,而且还努力借鉴西方逻辑分析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他说:“历史上中国哲学所最缺乏者,就是西方哲学那种‘理性主义的训练’,而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就是逻辑分析方法。”[8](p297)并引用“点石成金”的故事明确宣称:“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9](p379)冯友兰主张吸收、消化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并用它来重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并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一大学派。
可见,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一开始就是为了救治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帮助中国人吸收和消化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并使之成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自身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重塑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问题之二:为何必须置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去比较研究?
张东荪最早提出:“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逼出来的”。[10](p59)这是很精辟的。因为逻辑是文化有机整体中深层而本质的东西,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中所孕育的逻辑必然会反映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或烙上其文化传统的“印记”。欧洲逻辑史家安东·杜米特留(Anton Dumitru)说:“我们已经论述了二千五百多年的逻辑史,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构想和阐述逻辑学。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逻辑演变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11]刘培育先生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逻辑思想,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发展历史,它总是这样那样的受到一定时候的政治、经济、科学的影响和制约。”[12]孙中原先生针对中国古代逻辑的代表即墨家逻辑强调:“墨家逻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先贤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的必然产物,是百家争鸣伴生的名辩思潮的总结与升华。”[13]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创制了求取科学知识的思维工具——三段论。它以“求知”为直接目的,以“求真”为根本任务。三段论之所以是形式的、演绎的、用于科学证明的,主要因为:(1)古希腊哲学从寻求宇宙本原出发,确认了存在论、逻辑学和语法学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领域,即:“思维的形式反映着存在的结构,而语言的表达是以思维形式为基础来进行的。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的结构、逻辑的形式和语法的形式之三者之间,可以看作是对应的并行关系。”[14](p88)(2)在西方逻辑史上,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第一次应用了“公理化”方法,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古希腊人的演绎系统结构的典范——几何学的发展。数学史家M·克莱因说:“希腊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定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科学”。[15](p39)英国逻辑史家威廉·涅尔夫妇说:“……只有数学符合于亚里士多德关于证明的论证的描述,而且数学为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对证明所做的大部分解释。……最早的逻辑研究多半是由这种推理的考察所引起”。[16](3)古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探究世界整体的本原和万事万物的本质、原因。三段论体现了古希腊的分析理性和科学求真精神——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三段论追求结论的“必然得出”,这跟古希腊知识论(认识论)所持的信念——“知识就是必然性的东西”相一致。
然而与古希腊文化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古代文化,则以政治伦理实践、社会人事为核心,注重从具体的现象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亦即用“关联”思维)来揭示道理,而不注重事物的结构、要素分析,表现在语言面就是重“语义”而轻“语形”——不关注通过语言的结构来显示思维的结构,也没有发展出以“形式结构”的演绎推理为特色的几何学。再者,中国哲学属于“义理化”哲学而不是以概念分析为特色的系统化理论,一个“道”贯穿其中,一切都处于融通的关系之中,诚然,中国古代的推理论证也偏向“义理化”而不是形式化。这样,就不可能发展出“形式”的逻辑学。张岱年先生说:“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祟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17](p208)建立在“类”观念基础上的“推类”就是中国古代广泛使用的推理论说的方法,而在推类的诸方式中又以譬喻推论为基本推理形态,刘培育先生说:“中国人民的逻辑思维传统不同于西方,它以譬喻推理为基本推理形态,往往用具体形象的个例‘代替’一般,用譬喻进行推论。”[18]所谓墨家逻辑,应当是“推类”逻辑。因为墨家以“推类”为称谓,概括出了“推类”逻辑原理——“故”、“理”、“类”,并具体提出了“推类’,的方法——“譬”、“侔”、“推”等,还总结了相关的谬误理论等。
事实证明,脱离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中西比较逻辑研究就会失去“基本依据”;如果不从中西文化各自的背景去透视中西古代逻辑,而是只管拿西方某种逻辑的术语、理论来对号入座或妄加评论,那么,就很容易陷入片面“求同”或片面“求异”的泥潭,中西逻辑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正确解答,各自的长短及其价值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评价。崔清田先生强调说:“只有把不同的逻辑传统置于它们所由生成并受其制约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进行分析和诠释,我们才能认识这些不同逻辑传统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才能对它们的异同作出合理的比较和说明。”[19]既然中国文化、文明有自己的传统,有独特的逻辑推理类型——“推类”,那么,在参照西方逻辑的基础上,就应遵重中国文化传统,发掘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推类逻辑”。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人从先秦直到宋明对“推类”逻辑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演化规律作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的考察。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研究空白。因为要搞清楚具有中国特质的“推类逻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考察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应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推类逻辑”作一个完整的考察。(注:本人正在导师崔清田教授和刘培育、董志铁教授的指导下做这项研究工作。)
问题之三:究竟应以怎样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来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思想倾向。一种认为逻辑是“共同”的,只能按照西方的某种逻辑样式来裁剪和改铸出中国古代逻辑。从心态上说,无非是要维护“西方有的,我国‘古已有之’”的脆弱的民族自尊心;从思维方式上说,这是单一的“求同”。这种比较研究事实上是以抹杀中国古代逻辑的“个性”为前提,使中国古代的名学、辩学成了西方逻辑的“复制品”,失去了其文化特质、价值和意义,消解了比较研究的正确思路和方法,远离了比较研究的真实主题和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实质上是以西方逻辑研究取代中国逻辑研究。另一种认为逻辑是“超验”的、“一元”的、“形式结构”的、“必然得出”的东西。于是,极力“挑”出名学、辩学与西方逻辑的种种“不同”,借此以否认“名学”、“辩学”中有逻辑,进而得出中国自古无逻辑的结论。这是一种“傲视”心态,其思维方式是片面的“求异”。这两种心态和思维方式的产生,关键在于其“前提”的不真实和不充分。我们应当认真检视和彻底质疑这两种比较研究的心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刘培育先生指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必须借鉴外域逻辑研究的一切经验,以任何借口拒绝外域经验的想法和作法都是不对的。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抄照搬,不是硬套。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曾经有过、现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用西方逻辑的模式看待中国古代逻辑,用西方逻辑史的模式编写中国逻辑思想史的一种倾向。这样做是十分有害的。有的人,用西方逻辑体系衡量我国古代逻辑,得出了‘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荒谬结论。有的人,以西方逻辑为标准模式,对中国古代逻辑或削足适履,或画蛇添足,或无类比附,使中国逻辑成为西方逻辑的翻版,抹煞了中国逻辑及中国逻辑史的特点,歪曲了中国古代逻辑的面貌。”[20]应当认识到:西方逻辑是“已成”的或“现成”的东西,而中国古代逻辑是“未成”的或“特定”的东西。“已成”的不同于“未成”的。“未成”的是要选择的,所以,决不能用“已成”的代替“未成”的。按照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逻辑看作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世界;但应当选择其中“最好的可能世界”。
此外,有学者认为,应当用“现代逻辑”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惟有这样才能“创新”和取得“更大的成果”。这里有个“假设”,即:中国古代逻辑应当等同于西方的某种现代逻辑,这跟传统上假设中国古代逻辑类同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那种片面“求同”的思维取向并无二致。诚然,比较研究应该了解现代逻辑。但是,应当搞清楚:中国古代逻辑能否化归为西方的某种现代逻辑类型。王路先生说:在借用某种现代逻辑(如:自然语言逻辑等)之前,应当首先搞清楚它是什么样子的东西,这是进行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前提”;而随便套用是不可能把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提高一步的。[21]
三、结语
高清海先生针对中国哲学研究指出: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是谁”。“凡是西方好的、有用的都应该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由此丢弃了我们的‘自我’,失去了我们自我的根基,忘记‘我们自己是谁’,那恐怕就要成为民族罪人了。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标志文化特质、体现文化灵魂的哲学思维传统,历史证明,那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终究要被淘汰出局的。”“在这许多思想框框中,在我看来,头一个致命的框框就是:不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具有自我个性的独立哲学形态,我们总是用西方的眼光看自己,以西方哲学为模式去硬套我们的理论,经过这样改铸、裁剪的结果,我们的哲学不仅面目全非,而且完全失去了我们自己所特有的哲学思维的意义和价值。”“从今天来看,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哲学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灵魂,如果承认文化有民族文化差异,就应该承认哲学理论特别是它的思维模式也是有民族差异的。”“我们从事实来看,哲学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22]这些话同样适合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
中国哲学要注重“自我个性”,中国古代的逻辑也要注重“自我个性”。随便拿西方的某个逻辑来套释中国古代逻辑的做法,即:抹杀“自我个性”的做法,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本民族特质的逻辑,才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才是对人类逻辑学的真正丰富。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自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变革思维方式、有效吸收西方文化的基本路径。我们只有以平和、公正的心态对待自己与他人逻辑的传统、特点、内容、价值和长短,才能顺利地推进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反思上述前提性问题,就是为了解决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心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合理的逻辑观来进行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合理的逻辑观”,其要旨与实质就在于充分肯定人类的一切逻辑成果;既充分尊重和学习西方逻辑的精华,又坚定地保持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立与个性,批判和超越中西逻辑各自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促成中西逻辑的互补,生成人类性意义的全新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