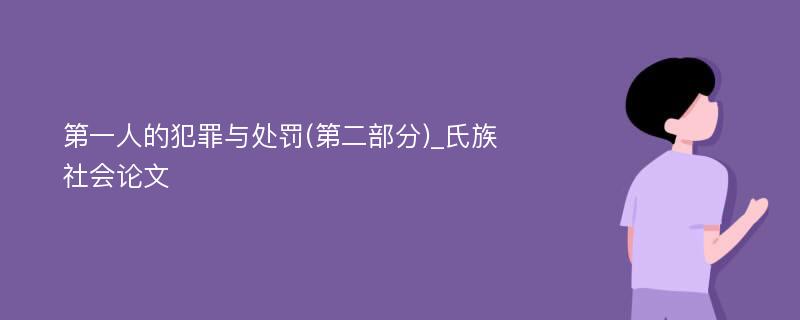
初民的犯罪与刑罚(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民论文,刑罚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彼此冲突的法律制度
初民法并非一种纯然有序、完全统一的规则体,不是奠立于某一原则之上,进而生成、演进而成的一种协和自足、圆融无碍的体系。这是我们从对于特罗布里恩岛法律事实的上述查研中已然确知的。相反,凡此种种初民法律,均多少各成独立体系,彼此略有调适而已。其中,每一种——母系制、父权、婚姻法、头领的特权和义务,等等——各有一己特定而自足的畛域,却又能越出法域,干犯他类。这便造成了一种偶有失衡的充满张力的平衡状态。法律原则间的此类冲突或隐或显,对于此种冲突机制的研究,极具启迪价值,它向我们昭示出初民部落中社会组织的真切特性。这里,笔者就其中一、二项作一描述,进而再予阐释。
我首先描述一个典型事例,此例说明初民法的主要原则的母权,与人类最为强烈的情感之一的父爱之间的冲突,围绕于此,产生了虽然实际上与法律相抵触,却为习俗所容纳的诸多惯例。
母权与父爱这两项原则,分别最为集中地关涉一个男子与他的姐妹的儿子和他自己的儿子的各自的关系。他的外甥乃为他最亲近的亲属,是他所有尊严与职务的法定继承人。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儿子却不被当作亲属;从法律来说,他与父亲没什么关联,乃父与其母间的婚姻这一社会身份,是两个男人间的唯一纽带。(注:参阅“初民心理学中的父亲”(1926),最早刊发于是年《心理学》杂志第4卷第2号。)
不过,在实际生活现实中,父亲对于乃子的舔犊之情总是超过对于外甥的,父子间存有永恒的友情和个人的依恋;舅甥间团结和谐、同心同德的理想,则常常被内在于任何后裔间的竞争和猜疑所破坏。
因此,母权作为一项权威的法律制度,却只与一种微弱的情感相连,而父爱虽则在法律上无足轻重,但却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个人情感的支持。对于一个掌有相当权力的头领来说,个人的影响超过了法律的规范,乃子的地位同乃甥一般坚不可摧。
这有一个例子,发生在奥马拉卡纳的中心村庄,第一头领的驻地。这位头领的权力广被整个地区,影响达于诸多岛屿,在整个新几内亚东部声望隆著。我不久发现,其子与他的外甥长期不和,表现为受宠的儿子纳姆瓦纳·盖伊(Namwana Guya'u),与次甥米塔卡塔(Mitakata)之间常常激烈争吵。
在一场提送该区政府官员的讼争中,头领的儿子严重伤害了外甥,至此,冲突终于爆发了。事实上,外甥米塔卡塔被判有罪,在狱中羁押了约一个月。
消息传到村里时,纳姆瓦纳·盖伊的支持者们于短暂的狂喜之后,立刻陷入恐慌,因为大家都感到事态到了危急关头。头领将自己关在他的屋中,他的爱子的所作所为,被认为粗暴践踏了情感,严重违犯了部落法,对于爱子的种种后果,他心中充满不祥之兆。被监禁的年轻的头领继承者的亲属们,其压抑的满腔怒火和义愤达到了顶点。夜幕降临时,克制着的村庄渐渐平静下来,安宁享受晚餐,家家专注于各自的佳肴。村庄中心地带阒寂无人——没人看见过纳姆瓦纳·盖伊,头领图努瓦(To'uluwa)将他藏在家中,他的大部分妻子和家人也在屋中。突然,一阵喧哗划破寂静的村庄,被监禁的男子的长兄巴格多(Bagido'u),肖似乃弟,站在头领的屋前,高声大气地称他的家人为罪犯:
嗟乎冤家,汝乃祸根!
吾人慈悲,谓“塔巴鲁”,
容汝于邦,以沫相濡;
汝有足粮,复魇吾厨,
鱼豕佳馐,原本馈礼,
吾侪既得,慷慨施汝;
刳木成舟,供汝远航,
汝屋汝厦,岿然吾土;
汝今害吾,复谎弥天。
米塔卡塔,身陷囹圉;
吾愿汝去,此乃吾邦,
汝乃生客,命该黎黍;
驱之逐之,汝速远吾,
汝速远吾,此乃吾土!
此乃吾土,此乃吾土!!
语声高昂激越,因异常激动而颤栗,短句间稍作停顿,句句都象飞弹,穿过寂静的空际,直射纳姆瓦纳·盖伊正颓然跌坐其中的小屋。继这个青年之后,米塔卡塔的姐姐也站起来数落一通,然后是一个年青小伙,头领的外甥之一。他们的话与第一个人的内容几乎一样,主要意在将人赶走,即象征性的驱逐(yoba,“哟罢”)。他们的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传遍全村。村中并没发生什么骚乱,但是,在黑夜结束之前,纳姆瓦纳·盖伊却永远地离开了奥马拉卡纳。他永辞该村,回归几里之外的奥萨珀拉村(Osapola),从母亲处外出的自己的村庄。连续几周,他的母亲和姐妹为“死者”悲伤举哀,放声痛哭。头领在屋内呆了三天,当他出来时,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被悲痛折磨得身心交瘁。他的所有关怀和慈爱当然都倾注在爱子身上,可他也爱莫能助。他的亲属们是完全根据他们的权利,根据部落法行事,他不可能割断自己与他们的关系。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改变放逐的判决。一旦宣布要他“滚开”(bukula),“我们要将你赶走”(kayabaim),此人就必得离开。这些话绝少以绝对严肃的口吻说出,可一旦某地的居民反对某个外来户而作出这一宣布时,它就具有强制力和几乎典仪般的权威。如果某人试图铤而走险违犯它们,不顾一切地留在他们中间,他将会蒙受终生耻辱。事实上,对于一个特罗布里恩岛居民来说,除了绝对恭奉典仪的要求行事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
头领对于亲属们的敌意深沉而持久。起初,他甚至不和他们说话。大约一年,没有一个人敢于请求他带领进行对外贸易,尽管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两年后的一九一七年,当我重返特罗布里恩时,纳姆瓦纳·盖伊还住在另一个村中,远避乃父亲属,离群索居,虽然他时常去看看奥马拉卡纳以便看一眼自己的父亲,特别是当图努瓦出国时。纳姆瓦纳被逐一年不到,他的母亲去世了。正象初民们描述的那样:“她不吃不喝,只是一个劲儿啼哭,后来便死了。”两个劲敌的关系完全破裂,曾被监禁过的年轻头领米塔卡塔已将自己的妻子赶走,她与纳姆瓦纳·盖伊同属一个亚氏族。特罗布里恩的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分裂中。
此事不过是我在特罗布里恩所目睹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笔者之所以详予叙说,不避冗繁,乃因其清楚地说明了母权,说明了部落法的权威,展示了人类情感的力量。
这一特具典型、颇能说明问题的案例,绝非罕见的异数。每个村庄中都有个高贵的头领、声威赫赫的名人显要或有权有势的巫师,宠爱自己的儿子,赋予他们严格说来并不属于他们的特权。通常,这不至于导致村社内的敌意与纠纷——当儿子和外甥都很温和持重而又圆融老练时。凯莱(Kayla'i)是新近故世的卡萨奈(Kasanai)最高头领马塔巴努(M'tabalu)的儿子,他一直住在父亲的村中,负责大部分的村社巫术事务,与乃父继承人相处极洽。在司纳凯塔彼此相邻的若干村庄中,居住着好几个上层头领,他们的爱子有的与合法继承人是好朋友,有的则表现出明显的敌意。
在毗邻教堂和政府大厦的卡瓦塔尼亚村(kawataria), 末代首领的儿子戴波亚(Dayboya )在自然是力主父系诉求的欧洲势力的支持下,完全取代了真正的主人。而且,由于这种做法现在得到了白人的必然支持,而使得冲突愈益尖锐,继续按照父系原则行事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其间冲突的深沉如同神话传说一般悠长而古老。许多逗乐的说唱故事中都讲到这一冲突。说的是在库夸纳布(Kukwanebu), 首领的儿子拉图拉· 古亚(Latula guya'u),一个典型的狂妄自大、娇生惯养而又夸夸其谈之徒,常常成为恶作剧的笑柄。在严肃的神话传说中,他有时是个恶棍,有时却又成为一个好斗的勇士——但此二者的对立在故事中乃泾渭分明。但是,有关此一冲突的时代和文化深度的最令人信服的事实,是这一冲突依然积淀在我们马上将要研究的许多氏族制度中。在低层社会成员中,母权与父爱的对立同样存在,它表现为父亲愿在损害外甥利益的情形下为乃子竭尽所能。另一方面,父亲死后,儿子实际上必须返还合法继承人其父健在时他所获得的一切利益和财物。这自然会造成许多不满、摩擦,以及臻达圆满解决之境的迂回曲折的方法。
这样,我们便又直接碰到了法律理念与其实现程度、正统观念与实际生活实践之间的脱节这一问题。在论述异族通婚、反巫术制度、妖术与法的关系,实际上,在论述所有民法规则的伸缩性时,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这里我们发现部落基本结构的真切基础受到了与之全然捍格不凿的另一倾向的全面挑战和蔑视。如我们所知,母权是最重要、最具综合性的一项法律原则,渗透、内化在所有的习俗和制度中。他规定亲属关系只能根据女方来确定,一切社会特权归属母系。这样,它便排除了父子间的直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派生、衍化的其他一切关系的法律效力。(注:正如我在上引“初民心理学中的父亲”(1926)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初民不了解生理上的父亲身份这一事实,而赋予出生原因以一种超自然的解说。男子与他的妻子的孩子之间,没有任何直观有形的身体上的联系。但是,父亲从孩子出生伊始便爱他——至少他象一个通常的欧洲父亲那样去爱。既然父爱不能被归结为因着孩子是他的后代所以才爱他们等等观念,那么,它就必须被看作是人类某些本能的倾向的结果。在男人一方,他感到与自己性交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与自己具有某种联系,因为他与她长期生活在一起,并在她怀孕期间一直观察、照顾她。这向我们展示了对于“血缘的呼唤”的唯一可能与合理的解释。“血缘的呼唤”表明社会移情于宗法制度准允的人选,但却对血缘上的父亲身份一无所知;这一使得父亲虽然不知就里,但却爱着生理上属于他的孩子,也爱他的私生子。这种倾向对于物种具有伟大的价值。)基此,尽管父亲永远爱自己的孩子,但法律对这一情感只给予有限的认可;丈夫具有作为妻子的孩子的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然,此乃这一文化中的法律所能赋予父亲与婚姻的唯一的关系。既然幼小的孩子无法与母亲分离,既然她必须与丈夫在一起而常常远离自己的族人,既然她和她的孩子身边需要一个男性监护人和保护者——而丈夫则恰恰必须履行这一职责并根据严格而正统的法律实际这样做了。不过,同一法律只要求男孩——而不是可以与父母一起生活到结婚的女孩——在成人时离开父家,迁居母亲的村社,接受舅舅的监护。总的来看,这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也违背了儿子本人及其舅舅的意愿——职是之故,三位男子对于愈来愈多的倾向于延长父系权力,并在父子间建立起更多的联系的惯例的结果,自表关切。严格的法律规定,儿子是母系村社的居民,在他父亲的村中,他只是一个外来的陌生人(tomakava)——而惯例则允许他留在那里并享有大部分的居民权。出于礼仪需要,在葬礼或哀悼仪式上,在宴飨筵席上,通常,还有在战斗中,他都与舅舅并肩比立。而在日常生活的十分之九的事务和利益方面,他却与自己的父亲休戚与共。
使儿子在成年之后,常常是在结婚之后,还可以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惯例,乃为一项常规的制度:它有一定的措置以为安排,根据严格的规则和一定的程序进行,这一切使得此一惯例根本不是偷偷摸摸的和逾常无效的。这得益于这样一个借口:儿子留在那里有利于更好地帮助父亲种植粮食,而这一切又是以舅舅及其继承人的名义进行的。同样,如果头领据有某些职位,他考虑最合适的还是由自己的儿子来担任。后者结婚时,他就在父亲的住地盖一幢房子,靠近父亲的住宅。
儿子当然也有衣食之需,所以他必须去田园耕作并从事其他事务。父亲从自己的土地上分给他几小块“扒拉口”(baleko,营造田园的土地),给他一方置独木舟处,予其捕鱼的权利——狩猎在特罗布里恩并不重要——为他置备一些工具、鱼网以及其他鱼具。通常,父亲所做的还要多。他赋予乃子某些特权,并馈以礼物,按理说,他应该将这些保留起来传给他的合法继承者。 的确, 如继承人经由称作“泡汤啦”(pokala)的一笔给付而请求馈予这些特权和礼物时,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将这一切给他们,他甚至不得拒绝这项交易。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弟弟或他的外甥实际上已经为土地、巫术、“库拉”(对外贸易)权利、遗传动产或在舞蹈与礼仪中的“统治权”付出了代价;即便如此,它们按理还应属于他,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继承这一切。既有的惯例准允男人将这类贵重物品或特权免费给予儿子。因此,此一惯例虽已成既定事实,却是非法的,不仅全然无视法律,且因赋予篡位者以诸多利益,而在予合法所有者伤害之外复加侮辱。
使暂时的父系纽带得以偷梁换柱地渗入母权的最重要的措置,乃是表兄弟姐妹间的互婚制度。在特罗布里恩,一名男子有个儿子,而他的姐妹却生了女儿,则他有权要求这个女孩与其子订婚。这样,他的孙辈乃是他门族中人,乃子则成为头领地位继承者的姐夫或妹夫,因而,继承者必须担起向其子家庭提供食物的责任,而且,一般说来,他是他姐夫或妹夫的合作伙伴,是他姐妹家庭的保护人。职是之故,真正的男人,如果乃子可能侵犯他的利益,他不以为忤,事实上,他视此为乃子的特权。在特罗布里恩,表兄弟姐妹间的互婚,是一项使得一个男人通过特殊的母系婚姻,确保其子虽然间接,但确实留在父亲村社生活的权利,并使他几乎享受一个合法居民的一切权利。
围绕父爱这种感情,产生了这些被传统所认可和约束,并被村社视为最自然不过之事的既定的惯例。但是,它们是严格的法律的对立面,涉及诸如母系婚姻这种特异而反常的行为,如若受到以法律名义所进行的抵制或反对,就得向其屈服。已然载述的情况是,即便儿子是与乃父的甥女结婚,他也得离开村社。情况常常是,继承人通过向舅舅索要他准备给予其子的“泡汤啦”来中止其非法的慷慨。但是,任何这类对立行动都会冒犯掌权者,挑起敌意和摩擦,故尔只在个别情形下才会发生。
四、使一个初民部落具有社会凝聚力的诸因素
在分析母权与父爱的龃龉时,我们曾将注意力集中在男人与其子暨外甥各自的个人关系上。然而,整个氏族的团结和谐亦为问题所在。由掌权的男子(不管他是氏族头领、显要、村社头领或巫师)及其继承人二者所构成的集团,乃是母系氏族的真切的核心。较诸此一核心,氏族的团结一致、协调有序以及同源同种同质,亦相为逊。而且,因着我们发现这个核心有隙,两个男人之间通常存有紧张和敌意,故尔,我们便不能接受氏族乃一圆融无碍的整体这一公设。 不过, “氏族信条”(clan—dogma)或“血亲信条”(sib—dogma), 援用洛伊博士精当的措辞,亦并非无稽之谈,虽然我们已经指出,在最核心处,氏族是分裂的,并因着外族通婚的缘故,氏族亦非同源同种同质,但是,这却更有利于确切地展示所谓氏族团结和谐的论点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
这里,不妨即再指出,人类学已因信奉有关初民生活的什么正统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于表层价值上接受了有关他们的法律状况的想当然的“法律神话”,误将法律理念当作部落生活的社会学现实而备受欺弄。在此一事上,初民法的意思其实确定而明晰。经由将母权当作亲属关系中排他性的唯一原则,并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施行,初民据此将一切人类分为因母系纽带而与自己相联、称为“亲属”者(veyola,“维约拉”),和无此关联、称为“陌生者”(tomakava,“托马卡瓦”)。此一信条与“亲属关系分类原则”相结合,不惟完全决定着日常的语汇,即对法律关系亦有真切的影响。母权和分类原则进而与图腾崇拜制度相连,据此将一切人类分为四大族类,并再细分为若干亚类。职是之故, 一名男子或女子, 便是“马来西”(Malasi )、 “奴苦吧”(lukuba )、 “奴克瓦斯斯加”(Lukwasisiga )或“奴克拉布塔”(Lukulabuta)等诸如此类的亚类,此种图腾崇拜位格就如性别、肤色或身材的高矮胖瘦一般,确然不易;它不因人的死亡而消失,保存着它之为它的一切;它先于人的出生而存在,“魂灵之子”早已是某个氏族和亚氏族的成员。这一亚氏族成员资格,意味着他们有着同一个女性祖先、同一亲属关系及在当地村社中的同一居民身份,还意味着他们对于土地的共同所有权和在诸多经济事务与一切礼仪活动中的互助合作。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意味着他们具有共同的氏族和亚氏族名称,共同的血族复仇(lugwa,“怒格瓦”)责任和异族通婚的规则,最后, 它并意味着我们所想象的初民对于彼此利益的强烈关注这一神话。职是之故,某一亚氏族的消亡,一定程度上也就等于氏族的毁灭,为此而施行的整个丧悼仪式都得与此传统观念若合苻节。而且,氏族的团结和谐与亚氏族更为稳固紧密的团结和谐,经由盛大的节庆分配仪式而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同一图腾崇拜的集团上演着仪式性的经济上的予、取游戏,他们便在诸多利益与活动,必然的,还有某些情感方面,达致一种真正多元纷呈,确然协和的团结一致,进而将人们联结成为一个亚氏族,各亚氏族再合成一氏族,氏族的诸多制度、神话传说、日常语汇、流行的谚语和传统的箴言,均对此言之凿凿、强调再三。
但是,此一图景尚有另外一面,我们虽曾明确指出过,但必须再予简扼阐述。 首先, 虽然所有关于亲属关系、
图腾分支(totemicdivision)、财产共享以及社会责任等等事务的观念,都格外重视“氏族信条”,但并非一切情感均循此而生。在任何社会、政治或礼仪的竞争中,因着抱负、自尊和乡土情怀,男子总是站在母系亲属一边,在一般的现实生活中,柔情蜜意、醇厚友谊以及依恋心理,使得他常常为了妻子儿女和朋友而将氏族撇在一边。 从语言学来说, “为伊若”(veyogu,“我的亲属”)一词烙有冷冰冰的义务和自尊的色彩;另一方面,“奴般苦”(lubayku, “我的朋友和我的情人”)一词却明显更含温馨、亲昵的音调。他们对于死后世界的信念——较少正统色彩而更多个人信仰的意味——也认为,两情缱绻、忠贞不渝的爱,夫妻间的依恋和友谊,确保他们进入灵魂的域宇,如同图腾位格一般,恒久不朽。
至于氏族的特定的责任,人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规避和违犯其规则,在异族通婚一例中,我们已进行了详细考察。在经济事务中,如我们所知,因着父亲对其子的态度和让他参与氏族事务这一事实,氏族的互助合作的排他性便变得漏洞百出。“怒格瓦”(血族复仇)虽有,但很罕见;“掳勒”(lula,“血腥钱”)的支付(缔造和平的代价)是一种实为逃避更为苛重的责任的传统赔偿形式。在情感上,较诸死者的亲属,父亲或寡妇常常更加关注为被杀者之死复仇。在礼仪性的财物分配过程中,氏族始终是以一个经济单位的面目出现的。只是在相较于其他氏族时,它才显出自己同源同种同质的特性。组成氏族的各亚氏族,亚氏族内的个人之间,在经济往来中均实行严格的有偿核算。因此,一方面,各亚氏族及其成员确乎团结和谐,另一方面,与此并存的是,他们各自域界分明,对于自己特定的私利紧盯不舍;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团结和谐中也不乏全然商业性的猜疑、妒嫉以及卑劣行径。
如果我们对亚氏族内的人际关系作一具体考察,绝对不难发现,我们在奥马拉卡纳所曾看到的那种舅甥间的紧张而直接的不友好态度,也同样存在着。兄弟之间有时保有真正的友谊,就象米塔卡塔与他的兄弟纳姆瓦纳·盖伊昆仲一样。另一方面,强烈的憎恶、暴力和敌意,在传说和现实中均不乏其例。现在我举一个本应成为氏族核心的一群兄弟之间决绝性的不和的具体例子。
距我当时安营处很近的村中,住着昆仲三人,老大是氏族头领,目盲。老小常常从长兄的残疾中渔利,甚至在槟榔尚未成熟时就先行采摘。盲兄因而被剥夺了应享的份额。一天,当他再次发现自己应得的一份被骗取时,勃然大怒,夜色苍茫中,手提利斧,闯进三弟家中将其砍伤。负伤者仓惶逃走,躲到老二家中。二弟愤愤于兄长对于幼弟的伤害,操起鱼叉杀死盲兄。悲剧以杀手被治安法官判处一年监禁而不了了之。若在过去,他非得自杀不可——我的所有向导对此均毫无异议。
本案中,我们碰到了两种典型的、彼此关联的犯罪行为:盗窃和谋杀。对此,不妨多说两句。在特罗布里恩的初民生活中,上述两类违法行为均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罪行。指称盗窃的有两个概念;“苦娃怕捕”(kwapatu,意谓被抓获),该词指谓非法盗用他人所有的物品、 工具和贵重物件;“喂肚”(vayla'u),一个特殊的词汇, 意指从菜园或粮仓中盗窃蔬菜类食品,也用来指偷窃猪或家禽。人们认为盗窃私人财产危害更大,但同时却视盗窃食物更为卑鄙。对于一个特罗布里恩岛民来说,没有什么比没有食物、食物匮乏或乞食更丢脸的了。一个人陷入这一困境以致铤而走险而行窃这种劣行,将会使他蒙受所能想象的最大的耻辱。而且,既然因着贵重物品都有标记,(注:参详笔者上引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因而它们几乎不在窃贼的犯意指向之内,那么,盗窃私人财物便也就不可能给合法所有者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失。在每一案件中,刑罚涵蕴于对于犯罪千夫所指的差辱和嘲弄中。的确,所有引起我注意的盗窃案都是由低能者、社会的弃者或未成年人实施的。攫取白人小气巴巴地深藏密锁而不使用的余财,诸如用来贸易的商品、罐装食品或烟草,这些东西对于初民来说已别属另册,很自然,初民们并不认为违犯了法律、道德或礼仪规范。
谋杀是极其罕见的。事实上,除了刚才描述的案件外,在我逗留期间只发生过一起;一个臭名昭著的巫师,在夜间鬼鬼祟祟地走近村庄时被人杀死。一名夜间不时在此巡视的武装卫兵,为了保护巫师的被害人,一位病人,乃将巫师杀死。
在我所听说的几起案件中,杀人是作为对于当众抓获的通奸、冒犯上层人士、吵架和小打小闹行为的一种惩罚。当然,通常的战争中亦发生杀人行为。在所有案件中,一旦一名男子被另一亚氏族的人杀害,则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义务同时产生。在理论上,此一义务乃是绝对的,而在实践上,则只在被杀者系具有一定地位或重要性的成年男子时,才被看作应尽的义务;而当死者是明显因为自己的缺失而送命时,这甚至被认为是多余的。在其他案件中,当亚氏族的荣誉显然要求必须进行血亲复仇时,也仍然可以通过“血腥钱”(lula,“掳勒”)的替代来逃避这一义务。战后,为对方每一被杀死、伤者予以赔偿,乃为缔造和平的一种常规措置。而且,如果实施了谋杀或杀人行为,“血腥钱”将会使幸存者免除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义务(“怒格瓦”)。
我们不妨回到氏族的团结和谐问题上来。上引一切事实均表明,氏族的团结和谐既非只是人类学捏造的神话故事,也不是初民法的一条和唯一的真正的原则,这是解开它的所有谜底和困惑的关键。由于理想及其实现程度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由于对本能的人类倾向与严格的法律之间调处失当,而使得要完全看清和彻底理解内在与外在均矛盾重重、冲突迭起的事物的实际状况,变得难乎其难。氏族的团结一致只是一个法律神话,它要求——表现在所有的初民信条中,就是说在初民的所有的表白、陈述和格言谚语中,公开的规则和行为模式中——绝对服从他人利益,使自己的一切隶属于氏族的和谐有序,与此同时,事实上,氏族的和谐有序总是遭到违犯,在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在上述初民生活的一切礼仪方面,氏族的团结一致压倒一切,如果个人一己的考虑和缺失、陋习与此发生明显的抵触和公开的冲突,那么,它将否定通常情形下肯定支配个人行为的这些考虑和缺失、陋习。因此,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如果意识不到这两方面及其互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初民的制度、习俗和倾向,以及初民生活中的大部分重大事件。
为什么人类学只注意到此一问题的一方面?为什么人类学将严格然而却是虚构的初民法的信条当做全部真实呈现给世人?明白这一点亦非难事。因为这一信条反映了初民态度中智识的、表面的和充分习俗化了的一面,它被人们清晰地予以阐述,并被置于一个既定的法律构架中。当初民被问及在此种或彼种情形下他将做什么时,他回答说他应当做什么;他选择具有最佳可能性的行为模式。当他作为一名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的向导行事时,讲述初民法的理念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在现实生活中,他不仅对他人的过错和缺失保持容忍,他同时还保持着自己行为的情感、癖好、偏见和恣意任性。即便此时,虽然他如此行事,他却常常不愿承认他的行为低于法的标准。另一方面,有关行为、规避、妥协和非法律性质的惯例这些自然形成并自发起作用的规则,只会向田野调查者展示,他们对初民的生活进行直接的观察,采撷事实,与他的“材料”起居贴近,鸡犬之声相闻,以致于不仅理解他们的语言和表述,而且洞悉其行为背后的隐蔽动机以及几乎捉摸不定的行为的本能的特性。“道听途说的人类学”(Hearsay Anthropology)总是面临着无视初民法的阴暗面的危险。这一阴暗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客观存在的,其之长久不被正视,一如之被长久容忍,换言之,人们从不曾就此作过公开指陈,因而对之提出疑议。这或许可以对“自由自在的原始人”这一陈腐理论作出某些解释。该理论认为,初民没有什么习俗,其言谈举止亦愚蛮不堪。给我们这一理论的权威们清楚地知道根本不曾遵循严格的法律的初民行为的错综复杂性和不规则性,同时却对初民法的基本原则和信条的结构熟视无睹。现代田野调查工作者根据当地向导的陈述,可以毫不费力地构筑起这一理论,但他对于人性施诸这一理论建构之上的种种缺失,也就同样昧于自知。因此,他对初民进行了重塑与再造,将他们置于一种他所体认的法制模式中。事情的真相是,上述理论与我们有关于此的知识两相结合,表明或新或旧的这些主观臆断只不过是对极其复杂的事物状况的一种无效的简化。
这一点,如同人类文化现实中的其他一切一般,并不是一个自我圆成的协和的逻辑结构,而是一个各种彼此冲突的原理原则纷纭错综、沛然生动的混合体。其中,母系与父系的利益冲突恐怕是最重要的。崇拜同一图腾的氏族的团结和谐与家庭或治者的私利的约束的冲突,则居其次。依据个人的才干、经济成就和巫艺等分级的继承原则的斗争,亦很重要。因为巫师常常是头领或首领的令人生畏的竞争者,所以,作为个人权势工具的巫术,亦颇值得一提。如若篇幅允许,笔者或可举出一些其他冲突的例子,它们更为具体,更具随机偶然的特性。从历史上“塔巴鲁”(属“马来西”氏族的亚氏族)政治权力有迹可循的广被中,我们可以看到,森然有序的当地居民身份是建立在神话诉求和母系继承权基础之上的,而等级原则对此法律的合法性,则根本熟视无睹。或者,我或可描绘“塔巴鲁”和“托利瓦根”亚氏族(Toliwaga,属“奴克瓦斯斯加”氏族)之间的世俗较量,在这场争夺中,前者拥有等级身份、声望和既有的权力,后者则有更为强大的军事组织、好战性格,并在战争中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在我们看来,在此社会原则的冲突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它迫使我们对有关初民社会法律与秩序的传统概念予以彻底的重新检讨。现在我们必须绝对抛弃从外强加于整个部落生活表面的刻板、僵硬的“面包皮”或“习俗燕麦饼”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法律和秩序确乎渊源于它们施治的程序。但它们并不是呆板僵硬的,也不是生气了无、惰于应变的,或有什么永恒不易的模式。相反,它们是永恒冲突的结果,这不仅指人的情感抗拒法律,而且包括法律原则彼此间的冲突。然而,此一冲突不是毫无规则的混战:它必须服从一定的条件,只有在一定的限制内,并置于一种公开的状态,才能进行。一旦有人对此进行公开的挑战,则认定严格的法律优先适应于法律化的惯例或具冲突性的法律原则,而由关于各项法律制度的正统的梯阶划分进行调控。
此种严格的法律与法律化的惯例之间的冲突,如我们所见,乃是因为前者的背后拥有更为稳固的传统的力量,而后者则附势于个人的爱好和实际的权力,因而,其间冲突的发生自是可能的了。因此,在这一法的统一体内,不仅有不同的类型,如准民法、准刑法或有关经济贸易、政治关系等法律,而且其正统性、严厉性和效力亦存在着程度之别,使各项规则形成为从有关母权、图腾制度的主要法律,逐次递降到调节秘密规避法律和公然违法与教唆犯罪的传统手段的梯阶。
至此,我们对于特罗布里恩诸岛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考察已近尾声。在此考察过程中,我们曾就下述问题得出了若干结论:初民社会存在着积极的、具有一定伸缩性,但却具有约束力的各种义务,它们相当于那些更为发达的文化中的民法;这些义务的互惠性、履行的公开性、周密性,乃为这些义务的效力源泉;我们发现,消极的法律裁判、部落禁令和图腾禁忌,虽与积极的规范功能不同,但具有同样的伸缩性和适应性;我们还就习俗规范与传统规则试予新的分类;重予订正的法的定义将法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习俗性规则,进而揭示出法律统一体本身的各项子类。在这方面,除了准民法和准刑法这两种主要类型外,我们发现,还须对各种梯阶的法律作一区划,而形成一个从由主要的正式的法律所构成的成文法、被法律所完全认可的惯例,到各类规避制度和违犯法律的传统方法的梯阶。我们还必须对由诸如母权、父爱、政治组织和巫术的影响等构成部落法统一体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区分,这些制度不时发生冲突,又达成妥协,并重新彼此调适。上述种种,无需再予详述,我们的结论,因具有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缜密的理论论证,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有必要再次认识到,综观我们的整个研究,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非惟对于这些规则的单纯的列举,而在于对其爬梳提抉的方式和手段。我们发现,对于我们的研究最具启发性的是,初民社会中吁求具有既定规则的具体生活情境、置身此一情境中的人们习常的行为方式,社会通常对此所作的反应,以及循奉还是疏忽此一行为方式的结果。所有这一切,或可被称作原始规则体系的文化背景,较诸根据田野调查中道听途说的方法,作为问答结果,而纂记于人种学者笔记本中的那些虚幻兮兮、一鳞半爪的初民“法律集成”,如果不是更有价值,至少也是同样重要。
为此,需要一种新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经由对于正在实际生活中运作的习俗规则的直接观察来进行研究。这类研究表明,法律权威与习俗的权威原本相连,并非判然两分;它们的真切的本质涵蕴于它们伸向具体社会生活的诸多触须中;它们仅仅存在于自身亦不过乃其中一环的社会生活的长链中。我坚认,大部分对于部落生活的阐述,之所以鸡零狗碎,捍格不凿,乃系研究资料疏缺的结果,此种阐述方式,与人类生活的一般特性和社会组织的谨严本身,事实上颇相捍格不凿。而一个由各不相关、了无生气的人为虚构的习俗所构成的法典来支配的初民部落,显而易见,将会土崩瓦解。
我们只能借口说人类学因完全缺乏实际考察得来的有关习俗和行为规则的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学只能用第三手材料进行研究,才使得其结论不着边际。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因此将只能写下使我们人类学家发傻,而初民则觉得滑稽可笑的,启应祷文(litany)般的冗长琐屑的絮絮叨叨。鄙意是指将会造成下述这类对于事实的冗长叙述,例如:“在巨人国的居民中(Brobdignacian),女婿遇到岳母时, 俩人便相互辱骂,然后鼻青眼肿地各自打道回府”;“当一个巨人遇到一只北极熊时,他会撒腿就跑,有时熊会紧追不舍”;“在过去的喀里多尼亚,一个土著发现路旁有一瓶威士忌,他会一饮而尽,然后立刻再去寻找另一瓶”,等等。(我就记忆所及写下这些,所以它们虽然听起来若有其事、振振有词,但实则可能只是个大概意思。)
不过,嘲笑“启应祷文”方法固然容易,但这正是田野调查者的真正职责所在。几乎没有什么田野调查记录材料,其之大部分叙述,一如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而不只是它们应当或传说的那样。过去的许多研究,以损害初民为代价,竭尽耸人听闻、哗众取宠、消遣娱乐之能事,好在这一局面现已得到扭转,但却又易使人类学家罹受滑稽可笑之害。对于旧日田野调查材料的记录者们来说,他们真正重视的是初民习俗的奇异处,而非习俗本身。现代人类学家借助一名译员,通过问答的方法,也只能收集到一些零散的看法、一般性的泛泛之论和未经加工的访谈材料。他给予我们的不是初民社会的现实,因为他从未亲睹这一切。大部分人类学著述之所以荒谬不经,乃因其对本已割裂生活语境的访谈材料复进行了人为的加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要研究人类生活是如何服从规则的——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问题乃是这些规则是如何适应人类生活的。
至于说到我们的理论收获,则对于特罗布里恩法律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建立在集团内部团结一致并尊重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初民社会的凝聚力的图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个人主义和追逐私利相对立的初民的“集团情感”、“共同人格”(joint personality )和“氏族兼并”,在我们看来,纯属虚构,于初民社会本身,亦为枝蔓末节处。没有任何社会,不论是初民社会还是文明社会,能够凭空建立,或建立在人性的病态发育的基础上。
本文的结论更多地指向道德诉求。虽然原则上我主要将自己限于描述和指陈事实,但一些描述却使笔者自然而然地渐臻于更为一般的理论分析,而于所论事实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不过,凡此种种,并非意味着必须再度借助什么假设,或进化论的、历史的重建来进行。此处所作的这些解释,涵蕴于将一定事实简化为有关因素并追溯各有关因素间关系的分析之中。否则,便不可能将文化的各个方面联为一体,以揭示文化综合体中的诸多因素各有何种功能。母权与父系原则间的联系及其部分的冲突,正如我们已然看到的,对诸如表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继承和经济贸易的类型,父、子和舅舅这些典型人物的名分大义,以及氏族制度的某些特征等等一系列相互妥协的产物都系极好说明。(注:关于母权与父爱的关系,在上引《初民社会中的性及其压抑》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特罗布里恩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性、互惠义务的链条、对于义务的礼仪性履行、若干彼此独立的贸易活动联结而成一种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已经藉由自身本有、而给法律提供了强制力的功能而获得了解释。在特罗布里恩诸岛,巫师世袭的威望和权力与个人成就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各自发挥作用的每一文化因素而得到解释。只要我们严格坚持经验研究的立场,我们便能阐明所有这些事实和特征,揭示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和结果,从而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解释它们。此类解释绝不排斥对于这些习俗的演化水平或它们的历史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这既是科学的用武之地,也是文物研究的兴趣所在,但后者不应诉求作为人类学唯一的甚或绝对的内容。是时候了,关注人类的人类学研究者应该作出下列宣告:“需要假设,但不是想象”(hypothese non fingo)。
* 本文是布·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名著《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初民的法律与秩序”已在本刊上一期登载。本书根据英国ROUTLEDGE &KEGAN PAUL,LTD.1978年第10次印刷本译出。本刊得以刊登此书, 应感谢该书的版权授权者和译者。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