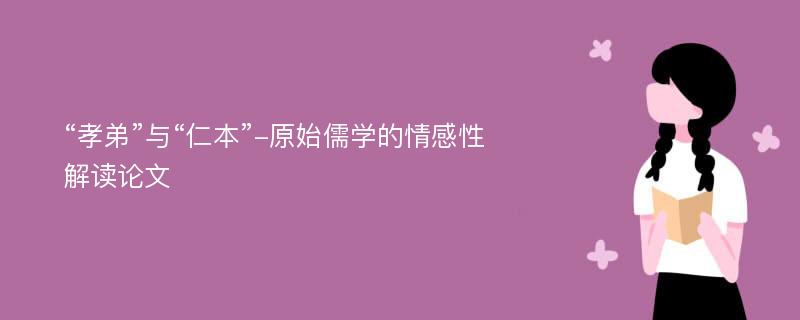
“孝弟 ”与 “仁本 ”
——原始儒学的情感性解读
吴先伍
[提要 ]孔子将“孝弟”当作仁本。过去人们过分地重视“孝弟”的行为性和规范性,而忽视了“孝弟”的情感性,从而使得儒学的发展走向教条化,逐渐背离了原始儒学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仁作为原始儒学的核心,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它是一种敢爱敢恨的情感。“孝弟”同样具有高度的情感性,是人们对于父母兄弟的爱敬之情。由于这种情感具有原初性、炽烈性等方面的特质,具有可推扩性,所以,它被看作仁本。由于原始儒学就是仁学,所以,“仁”与“孝弟”的情感性,也就决定和反映了原始儒学的情感性,历史上有关儒学冷漠无情的判断都偏离了原始儒学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孝弟;仁;原始儒学;情感性;《论语》;本体;爱
《论语·学而》第二章中记录有子的言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P.2)《论语》以孔子语录开篇,有子言论继之,此段言论之所以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乃在于其论述了“为仁之本”,而儒学本身乃是仁学,因此,它涉及了儒学的根本。后世学者正是有见于此,纷纷对此段言论展开论述,希望通过此举来破译儒家思想的奥秘。综观前人的解读,由于过度地强调“孝弟”之行与“孝弟”之行的典范性,忽视了“孝弟”的情感性解读,因而扼杀了原始儒学的勃勃生机,导致儒学逐渐走向僵化。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孝弟”的情感性解读,呈现原始儒学的情感本性。
将缓冲器轴向力减去阻尼力,获得气弹力和摩擦力;绘制“缓冲系统行程—气弹力和摩擦力”曲线,与静压曲线进行对比,根据两条曲线的差异情况确定起落架缓冲功能是否异常,如果异常,根据异常出现的起始点确认异常时的缓冲器行程,并记录起落架载荷。
一 、“仁 ”的情感性
按照现代诠释学的理论,理解并不是经由部分通达整体的单向直线式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整体作为开端,经由部分,再达到作为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整体的圆圈式发展过程。因此,理解乃是一个诠释循环,我们只有在此循环当中,才能对部分与整体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当中,“孝弟”与“仁”之间就存在着树根与树木、地基与大厦这样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我们要想了解“孝弟”以及以“仁”为核心的原始儒家的思想学说,必须从“仁”出发。
早在先秦时期,《吕氏春秋·不二》就以“孔子贵仁”来概括孔子的思想学说,突出“仁”在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中心地位。现代哲学家贺麟则将其推扩到整个儒学,认为“仁乃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2](P.9)陈来更是在其《仁学本体论》中,力图将儒家的仁论演化为仁学本体论或仁学宇宙论。由此可见,“仁”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说:“仁者,人也。”[3](P.784)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4](P.329)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那里,仁实际上就是人之为人的问题,就是人道问题,仁与现实之人具有密切的关联。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仁越来越形而上学化,越来越脱离现实当中的人,变成了天道、天心、天理。董仲舒说:“仁,天心,故次以天心。”[5](P.161)他认为天以仁为心,因此根据他的“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说,人之仁乃是对于天心的效法模仿。程明道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6](P.424)因此,程朱理学将仁与天理结合起来,指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认为仁就是天理、天心,所以为仁成仁就是要遵守天理,克尽人欲。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化的过程中,仁慢慢失去了内在的人性根基,离现实之人越来越远,变成了现实之人的一种外在规范、文饰,甚至是外在压制,而这也致使儒家思想学说在近现代中国受到了强烈批判。
儒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我们不能将后来经过发展演化的各种儒学等同于原始儒学。朱熹在《答陈同甫书》中曾经说过,自从孟子殁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7](P.1583),就已经明确感受到了儒学的发展偏离了原始儒学的本来面目。虽然朱熹以孔孟传人自居,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但是牟宗三则认为他与原始儒家相去甚远,批评他是“别子为宗”。由此可见,儒学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我们既不能笼统地以儒学来取代原始儒学,也不能以后世儒者所理解的“仁”来代替原始儒学中的“仁”。
在原始儒学中,“仁”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僵化的天理教条,而是生动活泼的“人心”。孟子说:“仁,人心也。”[4](P.267)因此,“仁”所指的乃是“仁心”、道德之心。仁心实际上就是爱心,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就答以“爱人”,即使是将仁与天理挂钩从而使仁走向形而上学化的宋明理学,也同样承认“仁主于爱”。[6](P.182-183)既然仁是“爱人”,“仁主于爱”,那么,仁就必然带有强烈的情感性,情感就构成了仁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不过,对于像孔子那样坚持“天生德于予”“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者来说,讲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或道德情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既然人类具有天然的道德情感,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忍心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呢?孟子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第一,我们不能以“忍心”来否定“不忍之心”的存在。孟子通过对特殊事件普遍意义的发掘,指出“不忍”这种道德情感具有普遍性:“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4](P.79)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那些在现实当中表现得凶残暴虐之人,其内心当中也会存有道德情感,像齐宣王这样的暴君,也会因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而做出“以羊易牛”的仁义之举。第二,当我们讲仁爱的时候,表达的是一种道德情感充盈成熟的状态,然而问题在于,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并非充盈成熟的,而是处于一种萌芽发端的状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4](P.80)这个萌芽如果得到精心呵护,加以扩充存养,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会枯萎夭亡,自然的道德情感就会消失殆尽,而这也正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不道德现象的原因之所在。
Study on public transit network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layout---A case study of central Qingdao
综上所述,针对行微创手术进行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于治疗期间给予患者综合护理干预有利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具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认同不仅是理智上的,更是情感上的。“孝弟”之所以能够被当作“仁本”,实际上就因为“孝弟”与“仁”在情感上的一致性,或者说“孝弟”是“仁”的情感的发育之根。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孝弟”具有情感性;第二,“孝弟”的情感带有根本性,由之出发可以长成仁德的苍天大树。
本文从业务逻辑的角度出发,初步建立指标体系。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指标是否对个人逾期(在数据集中该指标符号为y)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或者说,这些指标与因变量y是否相互独立,则需进一步验证;若独立,则意味着这些指标无法起到评价个人信用状况的作用。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筛选变量的优点,是可以有效地降低数据集的维度,提高鲁棒性,更多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收集变量数据所需成本的增加、模型运行速度的下降、模型训练成本的增加。
二 、“孝弟 ”的情感性
《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0](P.49),都强调“孝弟”是仁本、德本。何谓本?按照《辞源》的解释,“本”的最原初的意义是草木的根、干,像《诗经》中说:“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11](P.422)这个“本”就是指根,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根基、根本、基本、根据等多层意思。问题在于,在这种衍生的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其本源的意义——根、干。尤其当我们将“为仁之本”的“本”理解为基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将“孝弟”理解成为仁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或者重要的方面,从而使得“孝弟”与“仁”之间由时间上的生成关系变成空间中的展开关系。像马克斯·韦伯说:“同封建制是以荣辱为基础一样,世袭制则以孝为基础,孝是元德。前者(荣誉)是藩臣的封臣忠诚可靠性的基础;后者(孝)是统治者的仆从和官吏服从的基础”[12](P.207),实际上就是把孝当成一种基本的道德,当成中国传统道德大厦得以成立的一个支柱、一块基石。这种理解模式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动态生成性。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机论、生成论的哲学,中国人强调天地万物不断的生成过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仁德同样也处于不断地生成发育之中。如果我们罔顾中国哲学的特点,简单地将“孝弟”看作“仁德”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就会走向僵化的“三纲五常”之论,从而使得原始儒家的仁道思想暗而不明。如果我们回到“本”的根干的本源意义,就能够理解孟子为什么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端”实际上就是草木的根芽,就是草木的萌蘖,为了让这些仁德的根芽长成参天大树,就要像对待牛山之木一样,既要防止牛羊的啃噬和人为的刀砍斧剁,也要加以灌溉施肥,修枝剪叶。
既然“孝弟”“为仁之本”,“仁”是从“孝弟”成长起来的,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仁的情感性,那么,“孝弟”必然也是情感性的,否则就会导致仁的情感性的丧失。在以往的解释中,人们相对忽视了“孝弟”的情感性,而过分地关注“孝弟”的规范性、行为性。像《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0](P.49),“事亲”与“事君”就清晰地表明,《孝经》所强调的是“孝”作为侍奉亲人、君主的行为。自从汉代开始,《孝经》就受到了中国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直到明清时代,都一直被当作儒生的必读经典,是科举取士的重要科目。《孝经》对于“孝弟”的这样一种理解,使得人们赋予“孝弟”之行以崇高的典范意义,像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图》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许多人争相模仿其中的孝行。每一种行动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我们抛弃其特定背景而将其作为行为典范乃至行动指南加以推广的时候,必然会伴随形式化乃至暴力化的风险,要么沦为愚孝,要么成为在上者压制残杀在下者的工具,因而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同,而这也就是中国孝弟之道饱受诟病的原因之所在。
由表8可以看出,逐步回归法作为一种寻找较优子空间的变量选择方法,其可以系统地去除多重共线性,该方法相对于Logistic回归的去重,规避了偶然性和人为主观判断的影响.此外,Logistic模型的整体拟合预测仅为72.1%,而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93.3%,这说明就整体预测而言,逐步回归模型优于Logistic模型.另外,逐步回归模型可以确保所有进入方程的因子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这一点是Logistic模型甚至是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都不能达到的.
讲“仁者,爱人”“仁主于爱”,并不是说一个人要想为仁成仁,就只能有积极的“爱”的情感,而不能有消极的“恶”之类的情感。如果将仁仅仅理解为单一化的爱,那也是一种教条化,表面上是情感的炽烈,而本质上则是情感的麻木。“爱与恨,好与恶,来自同一情感源。唯其有爱,必然有恨。‘仁’以‘爱人’为规定,本身就隐含着并要求着‘恨人’作为补充”。[9](P.18)实际上,当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4](P.80),就已经肯定了爱与恨、好与恶都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情感:恻隐是对他者的爱与怜悯;羞恶则是对于自我与他人之不善的不满。孟子这样一种隐晦的表达,在孔子那里就要直接得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P.35)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是充分表达情感的人,就是一个敢爱敢恨之人。因此,孔子面对弟子的病逝,长吁短叹,嚎啕大哭;面对弟子的不求上进,无情地施以唾骂。
孔子对于仁心的推扩之道就是广为人知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主要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P.6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P.166)以往人们比较关注忠恕之间的区别联系以及推己及人的推扩方式,而相对忽视了“欲”与“不欲”,从而错失了其中的情感问题。“欲”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像荀子说“人生而有欲”,就是肯定情欲的自然性,朱熹就指出“欲是情发出来底”,[8](P.229)他也正是据此将理与欲、性与情对立起来,要求人们存理灭欲,“性其情”。问题在于,孔子并不否定人类的自然情感欲望,只是要在自我与他人情感欲望的满足上达到协调统一。因此,对于原始儒家来说,情感并不与仁相抵牾,反而是仁的题中应有之义,仁不能脱离情感,否则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孟子同样肯定,仁人就是善于推扩情感的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4](P.79)“爱”是情感的充溢,“不爱”则是情感的缺乏,是情感的麻木,是麻木不仁的表现。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是能够将其充溢的情感扩充到对于那些自己原本与其没有直接关联的他者身上,从而对于万事万物都表现出炙热的情感,这也就是所谓的一体之仁。
总而言之,在原始儒家那里,“仁”并非脱离现实人生的天理规范,也非铁面无情的理性,而是一种能爱能恨、敢好敢恶的情感,“仁即天真纯朴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P.9)
按照诠释循环理论,我们已经在分析“仁”之情感性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孝弟”的情感性,实现了从整体到部分的诠释进程,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达到部分与整体的统一,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宏观的整体性认识。这种整体不再是“仁”,而是原始儒家有关“仁”的学说——原始儒学。“孝弟”不仅构成了“为仁之本”,而且也构成了原始儒学之本。原始儒家以“仁”作为核心范畴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到了孔子,则把此一仁字深化,亦即把所以会爱人、所以能爱人的根源显发出来,以形成其学问的中心;孔学即是仁学,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15](P.81)“《论语》一书,应该是一部‘仁书’。”[16](P.232)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不仅能够领会“仁”与“孝弟”的情感性,同样,也能够更加深刻地领会原始儒学的情感性。
正是因为“孝弟”与“仁”都具有深厚的情感性,使得“孝弟”与“仁”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我们能从“孝弟”当中所蕴含的爱亲敬长之情出发培养起仁心的参天大树。不过问题在于,人类的自然情感是丰富多样的,喜怒哀乐都是人类的自然情感,孔子何以要抓住“孝弟”不放,将其当作“为仁之本”呢?其中原因在于:“孝弟”所代表的自然亲情更加具有原初性、根本性、炽烈性。第一,人都是由父母所生,我们的身体当中流淌着父母的血液,我们与父母兄弟之间天然就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亲情。第二,我们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由父母含辛茹苦地抚育培养,直至成人,父母兄弟乃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导师和朋友,因此,我们对父母自然会有一种敬畏感恩之情,这也就是人们在父母去世之后“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的原因之所在。第三,“亲近”“疏远”这些日常生活用语告诉我们,情感的亲疏与距离的远近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在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亲人之间的距离最近,因此,亲人之间的情感必定更加浓烈。正是由于“孝弟”之情这种独特性,决定了“爱有差等”,我们爱自己的父母亲人更甚于爱他人的父母亲人。“仁”并不是要否定对父母的爱,更不是否定爱,而是推广弘扬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正是由于对于父母兄弟的爱显得更为原初、更为根本、更为炽烈,它才最为重要,是“为仁之本”。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3](P.28)孟子说“亲亲,仁也”。[4](P.278)正是因为它最为原初根本,所以它具备了生长发育或存养推扩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重要的提倡,他这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他要让人作他那种富情感的生活,自然要从情感发端的地方下手罢了。人当孩提时最初有情自然是对他父母,和他哥哥姊姊;这时候的一点情,是长大后一切用情的源泉;绝不能对于父母家人无情而反先同旁的人有情”。[14](P.145)
三 、原始儒学的情感性
不仅后世学者往往将“孝弟”当作一种侍奉父兄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这大概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因此,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1](P.14)“能养”的具体表现就是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1](P.15)养活父母当然重要,否则,就会造成“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遗憾,使得我们的孝心无法安放。因此,孔子也反复告诫弟子:侍奉父母,要尽心竭力;要牢记父母的年龄;要守在父母身边等等。虽然侍奉活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孝弟”的根据,不能因为一个人做到了这些,我们就说他符合“孝弟之道”。孔子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P.14)如果我们仅仅将“孝弟”理解为奉养行为,那么人类的孝行就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没有任何差别,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流传着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美丽传说吗?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声称人类超出于万物之上,不能与禽兽为伍——“鸟兽不可与同群”呢?人类孝行与动物本能活动的差别之处,不在于奉养活动本身,而在于奉养背后的情感支撑。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都不过是出于本能,缺乏内在情感的支撑。人类的“孝弟”则不然,它虽然也表现为侍奉父兄的行为,但它背后却存在着深厚的情感支撑,“爱”与“敬”成为“孝弟”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之所以会遵守“孝弟”之道,我们之所以会作出“孝弟”之行,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始终涌动着爱亲敬长的情感,这也就是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4](P.307)
由于两千年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儒学留给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冷酷无情的印象——儒学不仅要求人们灭情窒欲,甚至还对违反者进行残忍的迫害,因此,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对儒学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呼唤伦理的革命。实际上,这里面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对“儒学”和“原始儒学”的混同。儒学作为思想学说虽然具有一脉相承性,但是其间曲折变化甚多,以致在历史上道统中断说层出不穷,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儒学来代替原始儒学,不能以笼统的儒学印象来代替对原始儒学的认知。自荀子把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称作人情,并指出人性(情)本恶,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开始[17](P.434-435),儒学中的情感就开始遭到否定,“性善情恶”“性其情”就逐渐成了儒学的一个发展潮流,从而使得儒学逐渐偏离了情感性的轨道。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原始儒学否定情感。新近出土的文献已经充分地证明,原始儒学不但不否定情感,而且高度重视情感。像《郭店楚简》当中不但出现了大量有关情感的论述,而且把情感提升到人道之基、人道之始的地位,突出了情与性的内在关联:“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18](P.179),认为只有出于自然情感的行为,才能最终符合外在的礼义规范,即使有所偏差,也不会相去甚远,因而符合情感才是难能可贵的:“凡人情为可兑(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之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18](P.181)根据考证,这批竹简的出土年代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其中的14篇儒家经典“正是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儒家早期心性说的轮廓,便隐约显现其中。”[19](P.163)时间上的相近性,学说的同源性,决定了其中有关情感问题的论述应该比较符合原始儒学的本来面貌。
实际上,我们对于儒学情感性缺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古代社会的以礼杀人,像著名的历史人物孔融就因其大胆的言论而死于违反礼教的罪名之下,而中国历史上死于封建礼教的“贞夫烈妇”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意识形态化的礼教中,礼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自然情感根基,奠定在天道、条理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成为人们必须效法遵守的对象。而这与原始儒家所讲的“礼”相去甚远。
虽然原始儒家同样也把“礼”看作国家的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但它不是出自外在的强加,而是出自人的内在道德情感的需求。一如作为中国传统礼仪当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丧祭之礼,就源自于人的自然情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守孝居丧三年,就会觉得情感上过意不去,就会觉得对于父母有所亏欠。因此,“礼”作为一种仪文形式,它所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需求,礼植根于人的内心情感。因此对于礼来说,它必须准确地和人的情感对应起来,力求准确地表达人的内在情感——“礼之用,和为贵”。[1](P.8)这也就是说,对于礼而言,我们不应过分地关注于其所要求的外在形式,而要关注其所表达的真实情感,否则,就会使礼流于没有任何内容的纯粹形式,从而丧失存在的价值,“人而不仁,如礼何?”[1](P.24)“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1](P.34)因此,对于丧祭之礼,“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P.24)正是因为礼奠定在情感的基础上,所以礼不是僵化的、不可移易的教条,它必须随着情感的变动而有所变通,从而寻求礼与情感的统一。就像三年之丧的礼仪规范虽然符合大多数人的情感需求,但与宰我却不相应,宰我不能心甘情愿地居丧三年,不如此也很心安理得。对于宰我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将三年之丧强加于他,而是让他跟着自己的情感走,“汝安,则为之”。因此,原始儒家并不强调死守善道,而是更加重视因权达变。孔子说:“可与立,未可与权。”[1](P.95)“立”是建立起一般性的原则,而“权”则要根据情况进行变通。孔子在这里将“权”置于“立”之上,后来孟子将其概括出执一用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4](P.313)对于原始儒家来说,“礼”这个原则规范应带有灵活变通性,而灵活变动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情感。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4](P.177)面对嫂子落水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要果断地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的束缚,主动“援之以手”,这就是基于我们“不忍”的自然情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由此可见,在原始儒家那里,由于“礼”是以仁心仁情为内在根据的,所以带有形式化特征的“礼”并没有成为情感表达的阻碍,反而构成了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而且情感的贯通不仅使礼摆脱了僵化的教条属性,而且具备了鲜活的生命流动性。
既然在原始儒家那里,就连被后世学者广泛误解的“礼”也与情水乳交融,那么情在原始儒学当中,就无处不融贯,无处不贯通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梁漱溟才会说,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就在于情感,“孔子两眼只看人的情感”。[14](P.145)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情感在思想学说中贯通最终也体现在孔子个人身上,即使被弟子晚生树为大圣,立为后世楷模,但孔子始终并没有将自己修饰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一任情感洒落:孔子经常会被美妙的音乐所吸引而不能自拔,因而才有“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1](P.74)当他看到一些自然景象的时候,也会触景生情,面对奔流不息的大河,他会感叹时间的流逝,面对翔而后集的飞鸟,他也会顾影自怜,羡慕它们适得其时;当他面对学生睡懒觉、不求上进,他也会忍不住厉声责骂;当他面对学生的误解,也会赌咒发誓地为自己辩解;当他面对学生的病逝,他也会放声痛哭,悲从中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思想的情感性在其人生当中得到了落实,而其情感的充盈最终又在学术思想中得到了升华。
“孝弟”之情的根本性,决定了其在原始儒学当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对于人们立身行事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就是对于统治者治国平天下也同样意义非凡:“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在修齐治平当中,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规范的推扩,而是最为切身的“孝弟”之情的扩充。总而言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讲的,并不是要将“孝弟”的行为规范作为行仁成仁的模板,而是要从人类最为根本性的爱亲敬长的自然情感出发,去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怀。因此,对于原始儒学而言,其所追求的不是僵化规范或行为范式的建立,而是情感的融贯,使得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能够得到充分地发育成长,突破家庭阈限向外蔓延,而这恰恰是古人贡献给现代世界的一笔重要的财富。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宋)朱熹.朱子全书(2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宋)朱熹.朱子全书(1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德]马克斯·韦伯.儒家与道教[M].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7]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9]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A]//冯建国.庞朴学术思想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1—006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他者伦理研究”(14BZX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先伍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江苏 南京 210046
收稿日期 2018-11-08
责任编辑尹邦志
标签:孝弟论文; 仁论文; 原始儒学论文; 情感性论文; 《论语》论文; 本体论文; 爱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