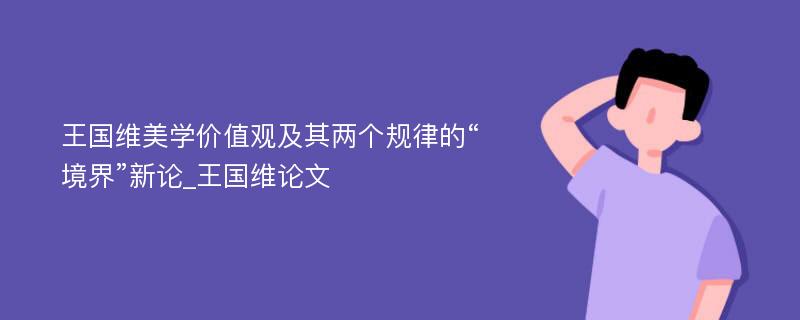
“境界”新论——并议王国维之审美价值观及其二律背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价值观论文,境界论文,王国维论文,二律背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2]07-0115-07
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最后集大成者,王国维以短短一部《人间词话》为我国古代诗学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王国维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排云殿前的昆明湖自沉身亡,则为中国旧式文人的最后结局作了一个注脚。不过,王国维自屈子以降诸多“上下求索”的文人侠士那里继承来的一种人格精神却没有自此而绝,恰如昆明湖中那一圈圈无言之涟漪,久久回荡,在凭吊者的眼里幻为一种遗世之绝美。
王氏个人的人生悲剧与其著作之历史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一个生命之谜和一个审美之谜却同时成为后世文人讨论的永恒话题。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人间词话》于1908-1909年在《国粹》学报连载,1910年9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自此引来了众多的研究者。虽然中间曾因各种社会政治原因而中断,但仍然或早或晚地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综观诸多关于王氏诗学的研究,多从材料的发掘和考证入手,或以王氏本身之经历为参照进行社会历史的或传记式的批评,或从词源学角度对王氏之“境界”理论进行简单的意义阐释,而少有从美学角度对《人间词话》作系统分析和研究的,更缺乏对《人间词话》以其独特之核心概念“境界”为基础建立的内在美学价值观的矛盾及其根源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对“境界”进行重新辨析与界说,在上述方面作一初步尝试。
一、“境界”新解
观《人间词话》64则,加上其“删稿”62则,共126则[1],其核心概念是“境界”一词。“词话”第1则即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第9则又云:“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何谓“境界”?历来论者甚多。有人从诗歌/艺术的形象性本质出发,以“形象”、“意象”或“艺术画面”等作类比性阐释。比如佛雏先生即认为,“王氏的‘境界’(意境),似可初步理解为:诗人在对某种创作对象(自然、人生)的静观中领悟并再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与独创性的一种有机的艺术画面。[2]”有人更直接地把“意境”等同于“境界”,解释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其主要依据是“词话”第6条:“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比如《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3]即如此解释。还有人从主体的审美体验出发,强调“境界”之主观根源,即主体对自然人生之真切感受,有真感受即有境界。如叶嘉莹在探寻“境界”一词的佛学渊源基础上,得出结论说“所谓‘境界’,实在乃是专以感觉经验之特质为主的。换句话说,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在吾人感受之所及。因此,外在世界在未经过吾人感受之功能而予以再现时,并不得称之为‘境界’。”“《人间词话》所标举的‘境界’,其含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但无论如何,却都必须作者自己对之有真切之感受,始得称之为‘有境界’”[4]。
以上种种说法各有道理,但都未能理解、揭示出王氏“境界”之真义。原因在于,诸家均未能充分注意并辨析“境界”一语与传统之“意境”的区别。这一区别未能引起注意,原因又在于王氏在其著作中,的确常以“境”或“意境”替代“境界”一语,从而造成误解,让人以为此三语具有概念的同一性,如前引《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即认为境界一语“单言之则称境,重言之则称境界,换言之又称意境”(第374页),对三者完全不加区分。一般认为,“境”或“境界”之语来自佛家。后经诗人、诗论家们(如王昌龄等)的创造性转换成为诗歌理论及批评术语,但一般都不对“境”、“意境”和“境界”加以细致的区分,常常互换或通用。此种渊源已有众多批评家的研究在前,此不赘述。
既然“意境”理论在王氏之前的中国诗学中,经过历代诗人、理论家的努力已发展得高度成熟,若王氏之“境界”与“意境”一词,语义完全重复,而没有任何新意的话,如此大张其鼓地“拈出”来,就大可不必了。
笔者认为,“境界”并不等于“意境”。“境界”之“境”即相当于一般所谓“意境”;“境界”之“界”则另有深义,实乃体现了王氏在同一个词的内部对“境”(即“意境”)的审美价值域的某种要求和限定。就词的结构来讲,“界”并不是“境”的同义反复。固然,“界”字与“境”字有一致的字源和内涵,《说文解字》就解释:“界,境也。”但另一方面,“界”也有与“境”不同的意义,《康熙字典》载《增韵》解“界”为“分画也,限也。”《辞海》解释“界”也有这样的词条“地域的限隔”,“引申为极限”,并引证《几何原本》:“点为线之界,线为面之界……”这样问题就清楚了,“境”主要指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具有实体性;“界”主要为“境”之界限(线),它限制了“境”之空间(三维)大小。就如“深度”一词之“深”与“度”,前者为“本”,后者是对前者的程度说明与限定。可见,“境界”一词,“境”为本,实可大致等于通常所谓“意境”即诗歌(艺术)作品所表现的艺术世界(但也可离开艺术作品而指客观自然之景,或者主观内在之情,参上引“词话”第6则及《清真先生遗事》一文对“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区分[5]。);“界”则亦实(指界线)亦虚(指量度、程度等),对艺术境界而言则指其审美价值之大小高低。“词话”第8条“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既然如此,“界”就不是指“境”的实际的空间之量,而是指“境”的审美价值之质。
这样也可以解释王氏为何在许多地方都不言“境界”而言“境”或“意境”。既然,“境”为“境界”的主体(本体),即可单言之,方便用其它概念对其进行价值区分或类型区分,如写境/造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辨析清楚了“境界”的概念结构和涵义,我们就可以说明它在王氏诗学、美学中的地位了。笔者听北京大学刘烜教授讲课,言道“境界”是一个纯美学概念,指“抒情诗的美的特质”,是“读者阅读抒情诗时感悟到的内在的艺术世界”,深以为然。这就是说,“境界”乃诗美之本质或本体,是一首诗、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是否真正的艺术的基本前提。诚如王氏所言,“探其本也。”陈良运先生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王氏拈出“境界”二字,“好象‘境界’二字是他的发明。以他的学问而言,当然不会不知道‘境界’说由来已久,大概是他认为历来诗人和诗论家所讲的‘境界’或‘意境’,都不过是一种审美形态的表述,而没有认识其作为审美本质的意义,所以,他要重新建构并阐释自己的‘境界’说。”[6]惜乎陈先生只是看到了“境界”在王氏诗学中的审美本质之意义,而没有对“境界”一词和“意境”的概念结构和审美内涵加以区分,仍把二者对举。
综上所述,王氏“境界”一词,既为诗(艺术)之为诗(艺术)作了审美规定(诗须有“境”即“意境”),又预设了其审美价值的区分(“界”之所指),这两个方面都是独创性的。“境界”是一个十分完满的美学概念(甚至可上升为范畴),它为王氏从各方面阐述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人间词话》美学体系及其审美价值观的矛盾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为诗美的特质,从它出发构筑起自己的诗歌美学体系,并从不同侧面展示出自己的审美价值观。
其一,从审美创造主体的角度,王氏把诗人(艺术家)分为“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词话”第17条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关于两种诗人的内在个性特征,可参照下面有关审美创造方法和艺术作品之不同审美特质的论述来理解。
其二,从审美创造方法的角度,王氏分为“造境”与“写境”两种方法。“词话”第二则“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派之所由分。”“造”与“写”是两种不同的创境方法。造,即依理想之要求,想象虚构而成;写,即依社会人生之客观真实摹写而成。用现代术语说,一表现,一再现。王国维通西学,此一思想显然来自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区分,较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两种方法,大致上为两种诗人所用,即上述“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那么,两种诗人、两种方法在王氏美学观念中有没有价值高低之别?表面上看来没有,“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词话”第2则)”第5则又说“……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在“大诗人”那里,也可理解为在最高的审美形态中,二者是可以统一的,好象不应有审美价值高低之别。然而,若参照王氏之整体的文艺观和个人人生观,可知王氏实际上是更推崇主观之理想主义的。另一方面,王氏在实际的审美操作中,又希望艺术对血写的人生进行再现,显示出了深刻的矛盾。此一问题,留待下文探讨。
其三,从诗歌(艺术)作品的内在美学特质这一角度,王氏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艺术境界之高下,即审美价值之高低由此而分。《人间词话》第3则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在王氏的所有概念中,只有这一组阐释得最多,也最为清楚。可见,他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是极为重视的。因为这一组概念直接指涉了“境界”之价值取向,即王氏之审美价值观。同时,上述“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造境”与“写境”的区分也只有到这里才显示出审美创造的实际效果,否则这些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
所谓“有我之境”,类似西方人所说“反映论”,是主体观照客体的结果,两者处于对立状态。最好的效果也就是主体之人格力量“对象化”或曰“移情”,即创作主体通过审美实践,使审美客体烙上主体之主观情感的印迹,所谓“物皆着我之色彩”。但这不是审美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无我之境”。
所谓“无我之境”,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物我两忘、物我同一之境。要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在于主体的状态。此时的主体应该处于佛家所谓“四大皆空”,道家所谓“坐忘”状态,西人叔本华又称之为“纯粹的主体”,即完全超脱于生死之欲、取消了个体意志的主体。只有取消了个体意志,才能取消主客对立,实现物我同一。此时的审美观照就是“以物观物”,等价于“以我观我”,两者并无区别。
主体要达到无知无欲的“纯粹”,就必须超脱于现实。这样,执著于现实的“客观之诗人”是做不到的。那么要创造出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级艺术精品,也非“写实”的方法而能为之了,只有通过冥想或审美的直观超越现实(哲学之谓现象界)的“主观之诗人”才有可能以想象和虚构而“造”之。这时,我们可以反观王氏在所谓“造境”与“写境”的背后隐藏着的审美价值取向了。《词话》第4则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静之动时得之。”“静”即无知无欲无主观意识的玄想状态;“由静之动”,即由实践的现实趋归冥想的途中。所以,即是“写实”也不能在“动”(实践行动)中完成,还须借以“静”(沉思、冥想)的观照。因而没有纯粹的“写实”。或许他进而认为,写实主义文学之所以还有价值,正在于它必包含有沉思和冥想的超脱因素。虽然王氏并未言明此点,但上述推断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其四,从作品所呈示的美感范畴看,有“优美”和“壮美”之分。“词话”第4则“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结合上文,王氏是更欣赏“优美”的境界的。“优美”与“壮美”,本是西方人的概念,许多美学家都有论述,王氏拿它对应于自己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多少有些牵强。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之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紧接着,他却又肯定“壮美”之价值,说“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7]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下文再做探讨。
其五,从鉴赏主体的审美实践效果,如何判定“境界”之高下,王氏用“隔”与“不隔”作为标准。“词话”第36、39、40、41则都是讲“隔”与“不隔”的问题。撇开对具体词人的评价,概括地说,“雾里看花”曰“隔”,“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这里的“雾里看花”,不可误解为传统诗学中“含蓄”美的概念,王国维也是推崇诗歌的含蓄之美的,比如“词话”第42则评价姜白石之词“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其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王氏所谓“雾里看花”,实际是指审美主体与客体尚有距离,因而尚为对立状态,不能达到“以物观物”的物我同一。而“语语都在目前”的审美效果才是理想的“无我之境”。
由此观之,王氏所用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似的审美概念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在一致性,它们以“境界”为理念的和价值的逻辑核心,构筑起一个相当完整的美学体系:
创造主体: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
创造方法:“写”境——“造”境
作品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美感范畴:宏壮——优美
审美效果:隔——不隔
审美价值:低——高
但是,上面的分析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单就审美价值观念而言,王氏实际上还有另一方面,与上述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
一方面,王氏称“主观之诗人,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第17则),“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前,是为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16则)这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赤子之心”即李贽之“童心”,未受俗世污染之心。怎样才能不受污染,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永远远离俗世。诗人、艺术家的创作只能出自“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因为“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删稿”第48则)所以,王氏坚决反对“美刺投赠之篇”(“词话”第57则)和词之沦为“羔雁之具”(“删稿”第4则)。王国维从审美的角度推崇具有赤子之心的“主观之诗人”和艺术的“无我之境”概源于此。
另一方面,“词话”第18则称:“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不难看出,王国维在推许纯艺术之“优美”的“无我之境”的同时,似乎更对“担荷人类罪恶”的“宏壮”之举充满敬意,他认为这样的诗人与“自道身世之戚”的诗人“其大小固不同矣”。“词话”第26则概括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三种之境界”,也包含有对人的生存进取之心的肯定。这一层对现实的观照之意最集中地表现在《论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其中有两段话最值得深长思之:“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遂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8]王国维既看重北方人改作社会之“强毅之气”,亦欣赏“南方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伟大的诗歌,只能是二者的结合,即以“想象的原质”,植于“感情”之“素地”[9]。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感情”非今人谓之纯粹主观之感情,实乃“改作社会”之理想与实践经验的全体。
由此看,改造社会亦是诗人之责任,能否“担荷人类罪恶”也是判断诗人之大小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诗人必得“多阅世”才有深体会,对人世有了深体会,才可能但此大任。因此,“词话”第25则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又要忧生,又要忧世,还如何能够做到超脱尘世,无知无欲,“造”出“无我之境”?
以王国维所论李后主为例,即明显前后矛盾,既以之为“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主观之诗人”的典范,又把他指认为“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血书”的榜样。而事实上,后主之词,举凡优秀者,多为遭遇国破家亡之后的感时忧世之作,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岂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没有任何人世沧桑之体验的诗人所能作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真的担当起人类的苦难,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脱,哪里还会有什么“无我之境”!“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被王氏誉为“无我之境”的典范。诗句出于元好问《颖亭留别》,全诗如下:“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诗歌理论家陈良运先生指出:“这首诗从整体观,我认为实在够不上‘无我之境’,王国维引以为据的只是其中两句,而这两句恰恰是作为‘怀归人自急’的情绪对照而出现的,以物态‘闲暇’反衬人生存奔波于尘土之中‘足悲咤’,‘无我’之‘优美’与‘有我’之‘壮美’相互衬托,映发而构成深邃的情境。”[10]另外,还可以王氏甚为自得的《人间词》加以印证。《人间词(乙稿)》中有一首《蝶恋花》,王氏最为满意,曾假托樊志厚称许其“意境两忘,物我一体”[11]。全诗为:“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知昏和晓。独倚栏杆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台,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陈良运先生分析说:“上阙尚可称‘无我之境’,‘闲中数尽行人小’有‘意境两忘’之妙,但当‘一霎车尘生树杪’,眼前‘优美’之境即刻发生变化,倚栏之人从‘闲中’观物转而为‘深观其物’,于是有‘都向尘中老’这样‘有我’的慨叹……从而以‘伤流潦’终其篇,入‘壮美’之境。”[12]
《人间词》中,无论是“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浣溪沙》),还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等,不仅没有能够“忘我”,相反统统都“有我”,都是“我”在人世沧桑中的孤苦、漂泊,灵魂的无所归依。王国维一生自负其才,对自己的词作极为看重,但是他的作品不仅没有达到他理想的“境界”,反倒证实了这种理想之几乎不可能。
三、王国维美学价值观念之思想根源及其二律背反
王氏这样的旧式文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当然是极深的。儒家要求“文以载道”,道家却主张“无为”,在艺术上则提出“坐忘”、“心斋”。王国维的艺术理想显然是倾向于后者,集中体现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的《红楼梦评论》开篇,即引老、庄之语“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老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庄子),说明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有“身”与“生”。但是,王国维毕竟是一个传统文人,要完全摆脱儒家的束缚是不容易的,他后来走的人生道路(应召做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虽为逆潮流之举,却并非不可理解,正是因为如此他要求诗人“忧生”、“忧世”。
这种思想根子上的矛盾,同样体现在他对西学的认识上。一般认为,王氏思想受叔本华影响最巨。上述奠定王氏一生思想基调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中许多重要观点几乎就是叔氏思想的中国版本。“夫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13]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欲望不得满足就是痛苦,故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而人的知识也是为了帮助人“趋利避害”,摆脱痛苦。“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14]
生活的本质是痛苦的,人必想尽办法解脱痛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非美术(即艺术、诗歌)何足以当之乎”。可见,王氏之人生观曰痛苦;王氏之艺术观曰超脱。而文艺之所以能够使人从痛苦中超脱,是因为它“非实物”因而“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即文艺是非功利的。由这种非功利的超脱文艺观,当然不难生发出对“主观之诗人”的“赤子之心”、对“无我”的艺术“境界”、对静谧之“优美”、对物我两“不隔”的审美人生的强烈价值趋向。
可是,王国维并不相信人能够真正的解脱。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对叔氏之思想深表认同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正是从质疑中,王氏开始称引尼采。
“然事不厌其求详,姑以生平可疑者商榷焉: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得而拒绝。何则?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别,仅由于吾人知力之形式,故离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观之,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则拒绝吾一人之意志,而姝姝自悦曰解脱,是何异蹄涔之水,而注之沟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者哉!佛之言曰:‘若不尽度众生,誓不成佛。’其言犹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观之,此岂徒能之而不欲哉!将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15]
“然叔氏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然则所谓持万物而归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欤?抑徒沾沾自喜之说,而不能见诸实者欤?果如后说,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16]王国维先从逻辑上指出叔本华思想之矛盾,进而对“解脱”之可能性提出怀疑,甚至对佛祖和基督自身之解脱也不相信,况平常之人。
尼采也看到了叔氏哲学的困境,认为取消意志是不可能的,因而反过来强调意志,主张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哲学,在艺术上则崇尚天才的创造。正是在肯定人的现实奋斗精神方面,尼采哲学获得了合理的内涵。它跟中国儒家的“入世”精神具有某种一致性,不过一个强调个人主义,一个强调内圣而外王。王国维因此而推举尼采“以血书”的艺术精神。以致于认为,“忧生”、“忧世”乃是诗人的天职。
但即使如此,王氏思想的这一面也不可夸大,因为非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和美学观才是王氏思想的主流和本质。王国维曾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宣扬康德:“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德(康德),以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17]类似的言论在王氏著作中经常可见,如《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18]
实际上,王氏在怀疑叔氏之绝灭意志的“无生主义”的同时,也对肯定意志、积极入世以“改作社会”之“生生主义”提出了同样的怀疑:“今使解脱之事,终不可能,然一切伦理学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矣?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则大不可解者也。”[19]无生主义也好,生生主义也罢,终归是不可实现的理想,而人能够完全没有理想吗?王国维在此陷入了困惑。
最后,王氏选择的依然还是“解脱”。不过此“解脱”非彼“解脱”。王国维不再认为最杰出的诗人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完全不谙世事的“赤子”,而是“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词话”第60则),只有经过人事沧桑的艰苦磨砺,然后超脱出来,才是真正的超脱,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创造出大境界的作品。所以王国维总结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词话”第26则):“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执著于现实人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奋斗于现实人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超脱于现实人生。这中间已有“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这时,王国维的审美价值理念与其说是“解脱”或“非功利”,不如说是一个“真”字,“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词话”第6则)。这与前述反对政治直接入诗,反对“美刺投赠之篇”和“羔雁之具”是一致的。即使是“鄙”词、“淫”词,只要不失其“真”,就仍不失其价值(“词话”第62则),最等而下之的是对人对事对物皆不“忠实”的“游词”(“删稿”第54则)。由此他又反对写作者不去感受真实的人生,而被“习惯”所支配:“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删稿”第14则)
由此观之,王氏欣赏李后主,非为其入世之浅,实为之真;欣赏《红楼梦》,非为其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实为之真。所以王氏赞赏贾宝玉出家,反对金钏、司棋自杀,因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前者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的真解脱,后者“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20]。境界之高下立判。具有悲剧意味的是,23年之后,王国维走了他曾反对的道路。个中原委,难道不跟其思想一样,值得深长思之?“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入“无我之境”,何其难也!
借一“真”字,“优美”与“壮美”的美感范畴在王氏审美价值观中最终统一起来:“……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21]只要是“真”,文学艺术就可以发挥出其“无用之大用”。可见,王国维审美价值观的矛盾,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康德式的二律背反。
标签:王国维论文; 有我之境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艺术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文化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诗歌论文; 意境论文; 王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