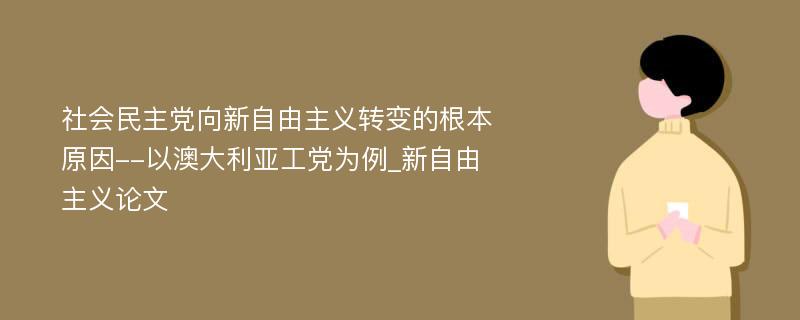
社会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为什么澳大利亚工党支持“经济理性主义”,很多国际文献作出的解释大都围绕着意识形态潮流、全球化趋势和选举动机这三大因素。这些解释并非毫无价值,然而更重要的因素在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战后经济繁荣结束,工党此前奉行的干预主义政策几乎失去了财政来源。由此工党才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
澳大利亚工党与经济理性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工党采取经济理性主义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霍克和基廷执政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代表了工党与以干预主义和公共部门为中心的前惠特拉姆(1972年12月上台执政)工党政府的彻底决裂。惠特拉姆政策的核心部分是庞大的包括卫生、教育、城市和地区发展的联邦政府公共开支。
1983年在工党重新执政之前,工党领导层总结出,惠特拉姆政府垮台部分要归因于政府试图做得“太多,太快”而导致的经济问题。1983年以来,在霍克及基廷的领导下,工党依循经济理性主义制定了许多政策,包括削减关税、澳元汇率的浮动、主要政府设施的私有化、财政紧缩、外国投资制度的自由化和对获得福利的严格控制。
人们普遍认为工党在霍克和基廷领导下采取经济理性主义,起因于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日益得势。这个观点最具影响力的阐释者——迈克尔·普西认为是“联邦政府机构里的经济学家们把霍克工党政府引向经济理性主义。普西的说法虽然受到批评,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即意识形态的转变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党走向经济理性主义产生了重要作用。
也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工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策上的右转,部分地是出于选举的动机。廷施认为,工党的基础蓝领工人发生动摇及社会的资产阶级化导致工党作出调整,斯坎伦认为工党的政策调整是为了回应公众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策支持的逐渐降低。
在国际文献中,评论家有一种倾向,把工党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退却归因于全球化限制了国内政策实施的效果。工党政治家也这样解释新自由主义。这一立场获得了其他作者的支持,如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记者保罗·凯利。
其他一些经济因素也被视作影响工党政策的转变的力量。例如,斯坎伦不同意是意识形态引起的转变,他认为是“管理超负荷”使政府陷入窘境,政府负担过多导致资源的增长不够所需。商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和对外贸易对澳大利亚不利等因素导致了霍克政府的“手段受到限制”。曼因提到70年代产生的“经济和文化的悲观主义情绪加深”的影响。同时,伊斯顿和格里特森猜测工党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对正在改变的国际经济政策议程的回应”。他们认为该转变是为了适应“更具弹性”的外部环境,“国际化的需要”促使政策转变。
这些不同解释的共同缺点在于他们都没有强调战后经济增长减缓因素的影响。的确,7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有倾向新右派的意识形态转变,自由市场的热衷者和自由主义政治学者都把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首位。然而,作为新自由主义高涨的首要理由,它还不够令人信服,因为这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为什么产生了影响。恰恰是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形成一种气候,使国际上包括澳大利亚更加欢迎新自由主义思潮。
推测全球化是工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确的,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中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和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本身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的确,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的负面作用能够损害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早在全球化之前就已承受了同样的压力。就像意识形态因素一样,这个解释不能完全说明惠特拉姆政府为何如此迅速地取消干预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策。
虽然同样有证据显示工党政治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相信,减少干预主义政策在选举上能带来回报,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很难说明1975年工党政策的突然转变。更令人信服的解释要从战后经济繁荣的突然崩溃中去找,因为工党的再分配政策大多建立在经济繁荣这一基础之上。
工党与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
尽管从早先的惠特拉姆政府的政策中可以窥见新自由主义的端倪(如1973年单方面削减25%的关税,以抑制通货膨胀,并为澳大利亚工业注入活力),然而其为了应付经济危机而长期转向经济理性主义的最早的主要标志出现在1975年。其实,早在1974年12月,政策转变的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为应付萧条,政府延期征收了涉及64,000家公司达5亿美元的公司税,并双倍降低了工厂的设备折旧税。1975年1月政府走得更远,它甚至放弃征收资本收益税及对公司汽车征收的新税。政府还成立了公共开支检查委员会,以阻止任何进一步增加公共开支的举动。
虽然上述做法更多的是对经济衰退的一种回应,并不能证明政府已经转向了敌视高税收和公共开支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也预示了政府政策的一种转向。保罗·凯利把这描绘成“经济政策在最短时间内发生的最剧烈的转变”。另一位报纸评论员说:“改良主义的政府变成了一个自由放任的政府”。在斯特兰焦看来,政府正形成一种共识,即“失业率上升是遏制澳大利亚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惟一方法”。
根据奥蒙德的说法,1975年初举行的两年一次的澳大利亚工党会议(工党的最高决策集团),是“工党理念的历史性变化”。惠特拉姆在会上坚持不应抛弃原有方案的同时,也提到“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萧条引起的特殊困难”。在这次会议上,加强公共部门而不是努力使私营部门重新赢利的提议在党内遭遇了致命的失败,这标志着党向新自由主义的明显转变。从许多其他会议决定中也能看到这种政策转变。比如,放弃一部分惠特拉姆的集权主义倾向,更愿向地方政府转移一些权力。但不是新采取的所有政策都刻有新自由主义的印记。总体上讲,这次会议可看作是工党放弃改良主义政策的开始,这就为向市场政策转变扫清了道路。
工党政策转变的更重要的标志是,当时的财务大臣比尔·海顿公开的1975—1976年的财政预算,这份预算结束了工党的“扩张时期”。预算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表现在它极力强调限制公共部门。此预算的双重目的是,既削减消费,又限制通货膨胀。斯特兰焦认为它“预示了澳大利亚迎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府”。早在1976年,就有一名记者用“经济理性主义”来形容支持海顿预算的内阁。海顿在文件中声明:“本预算的主旨是巩固与限制,而不是扩张公共部门;从经济角度看,通货膨胀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不再是在凯恩斯那简化的世界里发展经济,在那个世界里,失业率的降低,是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而如今,通货膨胀越严重,失业率越高。”
惠特拉姆称这一预算“实现了福利与经济责任间的平衡”。他许诺降低“政府开支增长率”,描绘了政府的目标,即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在更广泛意义上,这些言论属于经济理性主义范畴。
工党与繁荣期结束后的政策制定
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对澳大利亚工党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使工党可以摆脱在主流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之间作选择的困境。70年代末80年代初,处于在野党位置的工党加快步伐,主张在政府中实行新自由主义,党内人士广泛赞同凯恩斯主义不能适应“新情况”的看法。惠特拉姆于1976年指出,“旧式治疗方案不能像从前一样起作用了”,“目前的经济问题新奇古怪,难以治愈”。布赖恩明显受到詹姆士·奥康瑙尔著作的影响,把70年代的经济危机归因于“国家的财政危机”,这使政府因过多的财政负担而“不堪重负”。这一评论暗示,政府必须“减负”。另外,如果工党相信政府决策能力减弱,它将转向市场寻求解决方案。
事后想想,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当时的工党可能认为限制公共部门只是暂时的,但70年代和80年代持续不断的低经济增长率,使工党依然继续它在1975年制定的政策徒劳无功。因此,1975年可看作是工党开始逐渐过渡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折点。
在1977年澳大利亚工党全国会议上,惠特拉姆指出,工党改良主义政策必须等到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后才能进行。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发展为工党提供了方法和理由,使其能向选民许诺,通过扩大公共部门来推动社会改良,而七十年代的经济则完全是另一派景象。考虑到经济实际情况和工党的纲领,我们不得不设定稳健的社会目标。
惠特拉姆总结说,今后工党须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制定稳健的目标。他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工党领导层普遍认同。1977年,比尔·海顿继任惠特拉姆的职务担任工党领袖。他在1979年工党全国会议上警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推行早先那些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计划的年代了”。海顿也指明“改良只能要么通过增加税收来实行,要么把它限制在经济增长时期,而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可能性会很小”。
工党减少其改良主义抱负的决定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所受到的束缚。因为主张改良主义政府计划往往耗资巨大,在经济低迷时期,几乎没有条件承担昂贵的新改良,因此工党政府不得不变得更为温和。1978年,比尔·海顿宣布“处理如土著居民、社会福利和艺术等事务,都以经济增长为必要条件”。
理论上,工党可以不顾经济环境的变化而继续推行大型的改良主义计划。但在经济危机时期,要为这些计划纲领筹措资金就需要从经济增长以外的领域寻找收入,比如增加公司税收,削减国防等方面的巨大开支。在比较紧张的商业条件下,这些选择很可能引起公司的反对,也必然会挑战资本主义逻辑。与此相反,历史上执政的工党往往通过缩减其改良主义计划来应付经济危机,更糟糕的时候,甚至实行对其选民不利的政策。
在工党接受新自由主义一事上,完全否认选举因素、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是不对的。但只有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结束,尤其是1974年后经济增长徘徊不前这一因素才能解释执政工党政策的突然转变。如果政府不能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政府“负担过重”,如果对公共部门的约束被认为是解决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的必要手段,那么人们就很容易跨出求助市场的一步。
无法回到战后的经济繁荣状态成为工党一直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当然这种说法颇具争议。近来,工党新领袖马克·莱瑟姆许诺要“限制政府规模,因为支出太大,政府机构臃肿不利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我们只有在澳大利亚和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条件下才能理解他话语的含义。除关于9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大肆宣传外,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未达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基德伦指出,在90年代美国经济的辉煌期(经济既不过热,也不过冷),经济增长率也不过2.2%,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达到3.5%和4.5%。
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环境的变化才能解释当前社会民主党对新自由主义的偏爱。很明显,还有意识形态的转变促使工党偏向于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民主党对政治事件的回应。正如前文所述,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结束和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形成了真空状态,这就分别由货币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填充。随着柏林墙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弗朗西斯·福山关于这些事件预示了“历史的终结”和自由市场的胜利的观点引起了政治精英的共鸣。在应对1991年以来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社会民主党在提出意识形态新选择方面遇到了困难。近来,马克·莱瑟姆评论道,自从柏林墙倒塌,我们社会民主党在重新定位方面遇到了困难。结果,某些政党如工党,曾把市场看作控制和规范的对象,现在也开始接受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名的格言——我们别无选择。
从本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工党抛弃干预主义政策最主要的因素是70年代中期经济环境的显著变化。工党的计划纲领原估计是在高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推行的,现在战后繁荣期的结束动摇了该计划的经济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因素才能解释1975年工党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这反过来也是工党和自由市场全面和解的先兆。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并不是非得放弃改革政策,它可以选择缩减国防等方面的巨大开支,可以增加对富人和公司的征税。但从历史角度看,当工党遇上经济衰退时,往往放弃改良主义计划。这个例子便是如此。
因为个案分析只涉及一个国家,所以结论就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是有证据表明,尽管其他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采取策略的时机和程度不同,但都是基于类似的原因。改良主义政党曾许诺社会变革,但经济危机限制了它们的选择,这不足为怪。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澳大利亚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内长期占据上风,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深植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的危机的结果,这种危机严重侵害6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经济。即使不考虑全球化的限制性因素,除非世界经济增长率重新达到战后繁荣期的水平(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独特性,这种前景极为渺茫),社会民主党要再次推行那个时代的扩张主义政策已不可能。
(朱昔群:中共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