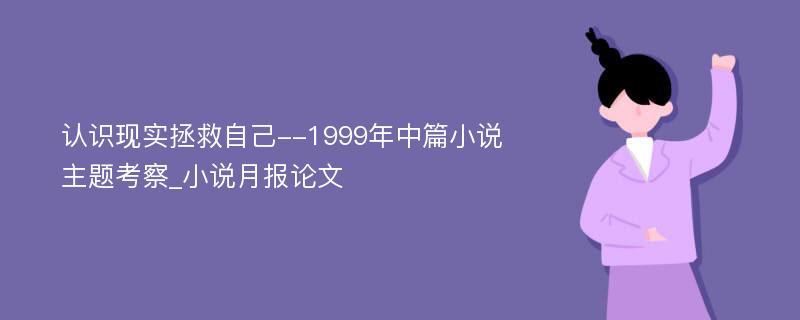
体察现实与拯救自我——1999年中篇小说主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现实论文,自我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末是个喧哗骚动与沉思静想互现的时段。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同样在经历着喧哗之后的沉思。1999年度的中篇小说就呈现出一种在艺术反思中酝酿突破的新迹象。中篇小说作家们一方面以敏锐的艺术触觉完成着对当下现实的迅速体察,另一方面又以凝重的忧思和沉郁的感悟传达着对于人生和艺术的双重探索。总的来说,99年度的中篇小说无疑是色彩绚烂,令人欣喜的。本文试图从纯粹主题学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和梳理,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希望以此构成对99年度中篇小说的某种理解。
一、现实“官场”的审视与表现
关注“当下”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当然责任与使命。然而,要真正有效地完成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的艺术观照,还需要作家们有相应的艺术勇气和艺术能力。99年度中篇小说对当下企业和民众生存困境的大胆揭示以及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细微体察,就让我们真实地体味到了小说强烈的现实品格。99年度中篇小说敢于触发矛盾,有时甚至把笔直接伸向了“官场”——这个容纳政治、文化传统积淀的奇特空间,剔骨疗毒,给人痛快淋漓之感。作家们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真诚态度,不回避现实,更不粉饰现实,客观真实而又大胆地记录了官场内外的是是非非。它们组合起来称得上是一部“新官场现形记”。皮县县委书记李智因上面没有靠山,是个无根县令而难以开展工作。而小辛庄的暴发户贡天华却仗着省里有根,向李智施加压力,迫使其选儿子为乡党委书记,并允诺事成之后帮李智向上提。他们从上到下,组成了一个人情关系的互联网,难怪有人稳坐江山,有人朝不保夕(《无根令》)。潘长水牺牲自己做了回枪得以升为办公室主任,度过“过渡时期”之后,便很老道地开始以权谋私,还搞上了女人,最后因贪污巨款而东窗事发(《腐败分子潘长水》)。昔日的好友如今在为官之道上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缝隙》)。小小一亩二分地的纠纷,乡里领导拖延、推脱,竟以状告省领导而告结束。其中又有几人得道,几人升迁(《一亩二分地》)?陈宗辉为融入官场,钻营着升迁之术,无所不用其极(《陈宗辉的故事》)。而《选举》则更是借一次“民主选举”副县长的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官场上明争暗斗、不择手段的真相,并把“现代政治”、“现代民主”与封建性积淀相杂交后的畸型状态,触目惊心地展示在小说中。
如果说“官场”的黑幕显示的是作家们的艺术勇气的话,那么这些小说意义深刻之处还在于其揭示了这种“官本位”心理的社会普遍性,以及它对普通人生存心理的扭曲。《找人》中尽管儿子的高考分数已上线,但深谙世情的瘸腿老汉仍孤身去省城托毫无关系的关系,结果累病致死。故事读来令人辛酸,但却让人不得不反思“官”、“民”之间的巨大鸿沟对百姓生存心理的戕害。《一亩二分地》中的管细林给未来的儿子起名“大官”。他说:“当大官好嘿,管人,嘴巴皮轻轻动动,下面人狗样听话。”而《金莲,你好》中的“老二”为了“权”,为了做派出所所长,竟然无视“金莲”的纯洁爱情,甚至以爱情为祭奠作为晋升“官场”的手段。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读来更是让人心寒。我们看到,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锐利的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切入这一空间,使小说在干预现实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学和文化学的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说在揭示社会矛盾,正视生存困境的同时,并没有流于抽象的理性化的说教之途,而是力求对生活对人生有立体的、感性的把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小说的艺术纯度。作家们不是以某种社会理性、现代思想来支撑作品,而是力求把感性生活、直接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放在小说的首位,从而有效地赋予了小说原生态的生活汁液和丰满的艺术内涵。在《腐败分子潘长水》中,我们既看到了潘长水现时的腐败生活,同时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动态蜕变过程。老潘转业到单位看管仓库,尽职尽责,他立了功却未被提拔,尽管心中有憋屈,但工作上却更加卖力。在本职工作以外,还主动提水,打扫厕所,忍辱负重。然而在做了主任后,他由不习惯→习惯→心安理得→腐败,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即便在他滑入腐败之渊后,作家也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单面人,而是步入了他心灵的深处,挖掘其更为复杂的人性和心灵的自省与矛盾,这就把一个动态的、立体的、丰富的“人”艺术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二、人生的顿悟与命运的叩问
对人生终极的关怀,对人生意义的追索,历来是文学的重要命题。从屈原的《天问》到鲁迅的《野草》,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式的革命教科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都从不同意义层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启蒙性的发掘。而在99年的中篇小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些久被规避和搁置的形而上主题的回归。但是这些中篇小说已褪去了“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浓厚的哲理思辩色彩,而是把圆熟的笔触落实到了在凡俗尘世里劳碌奔波的芸芸众生的人生情状和生活故事中。作家们借助他们的悲喜遭遇在氤氲的人间烟火中传达出对人生的一点觉悟和感触,对生存方式的一分怀疑或首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表述着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或诉说着她们对生存意义的困惑。何立伟的《光和影子》中,三个年轻人马高、戴进、孟东升在海南空手套白狼发了一笔财后回到了长沙。不久,马高患血癌死去。此事对戴和孟的震动很大。戴把自己交付给了牌九和教堂,孟消沉一段时间后复出生意场,赚赚赔赔后因涉嫌杀人而出逃。戴的妻子苏苏,一个原本天真纯洁的女孩,炒股发了大财后与戴进离异。戴的牌友“我”,是个商业化的剧作者,在得到金钱后又生出茫然与彷徨。这些在追名逐利的人世中沉浮的人们,除了能抓住一点“光和影子”似的虚名浮利外,还能抓住什么别的更为实在的东西吗?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小说发出了疑问,但它并没有提供一条诺亚方舟,而将思考留给了读者。《浮生》则在一个聊斋式的充满佛意禅机的神玄故事中参悟了寻常人生的本质:人生无常,生命苦短,可把握的东西实在太少。天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的实际。《老乔的某年夏天》讲述了一个夏天里市民老乔身边的人事变故:亲友们猝然之间或病或亡,在忧伤悲凉中感叹着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脆弱。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女主人公黄苏子由于男友的报复被迫做了一次“鸡”。出人意料的是,从此她竟然热衷于做“鸡”。她的生活分割为两种姿态:白天是清纯高雅的白领,晚上蜕变为浮浪妓女。她轮流变幻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她就是要测试一下,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活法,把一个人活成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这个现代社会中由于种种的原因,人生活得过累,整个身心处在一种分裂状态,只能以生存方式的改变来得以解脱。储福金的《平常人生》抹去了现代先锋性的笔触,而是把笔投向了市井百姓的生存状态。下乡知青孔圆圆,从结婚生女,招工进城到下岗离异,遭遇了一些坎坷。面对这些变故与不顺,孔圆圆总是能够随遇而安,平静对待,度过难关。这种生活状态与生存心理对应着我们时代的精神氛围和生命态度,其平静淡漠之外,仍透发出某种人生的苍凉之感。
可以看出,在表达对生存主题言说的这些中篇小说中,生活中的具象和抽象,形而上和形而下,此岸与彼岸,是交融统一在一起的。作家们试图在生活具象的描写中传达某种超越的意念,引导人们的目光挣脱现实的迷障,投向高远的精神天空。
三、女性境遇的书写
对女性的关注是99年中篇小说的又一创作热点。一度如火如荼的“身体写作”、“私人写作”曾将对女性的关注推进到无以复加的极致,那么在这块被掘地三尺、几乎开发殆尽的园地里,99年的中篇又能作出什么新动作呢?对这个主题的演绎,今年的中篇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套路。一路沿袭了女权主义的老路,又与先前的女性写作有所不同。先前的女性写作借助对女性的关注这一小说意义载体,营构女性话语,以同男性中心话语相对抗,进而解构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关注是她们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有效武器。这一主题具体化到她们的文本里则是对女性欲望的铺陈和对女性隐私的书写。99年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中篇更多地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呼吁社会生活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位置和权力,没有流露出以往的女权小说那种对男性世界激烈的敌视和拒斥态度。相反,在小说中倒是男性对和他们一样强大的女性加以漠视和贬斥。叶弥《城市的露珠》描写了一群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拥有亿万资财的女性,但经济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她们对社会生活的平等参与,这群先富起来的女性被专为男性服务的俱乐部拒之门外。她们仍然受着社会中既存的性别秩序的规约,难以与男性平等分享世俗的体验。另一路是在爱情婚姻框架中透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经历,这是关注女性的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模式,但依然能常写常新。女性特有的身心结构使得她们常将爱情和婚姻作为情感的最终归宿和生活的牢靠依托。她们不由自主地对这块圣地生发出种种浪漫的幻想和热情的期待,而现实又往往将她们的幻想击得粉粹,使她们含情脉脉的期待落空。北村《周渔的喊叫》里周渔因少年时遭生父强暴,因而在成年后把爱情当作惟一可以给她安全感的港湾,将丈夫陈清视为惟一的依靠,在对陈清的爱情里渗透了非常强烈的占有欲。陈清非常爱周渔,为了适应周渔而处处改变自己,失去了独立的个性而变得越来越象周渔,这使他十分苦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李兰邂逅成了情人。李兰是独身的才女,她给了陈清一份周渔所不能给予的自由生活。陈清触电身亡后,周渔整天神思恍惚,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与缅怀中。李兰最后也为他殉情而触电自杀。周渔、李兰这两个女性的误区在于把爱情看得过重,过分抬高了爱情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结果使得爱情或者成了所爱者的桎梏,或者成了自己的心狱。这是女性生存的误区。《关系》则从两性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上揭示了女性与爱情失之交臂的内在原因:女性需要的是稳定牢靠的婚姻,是一个归宿;男性需要的是能够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事业,爱情则是第二位的东西。性别差异导致的迥异的情感态度取向注定了女性幸福家庭美满婚姻梦想的破灭。在人欲、物欲汹涌如潮的现代商业社会里,女人“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总难觅到一份灵肉交融的爱情,不是落入夫妻间无活可说的庸常婚姻套子,就是沦为优越男性一时的恩宠对象。程先利的《情殇》和赵凝的《符号人》都向我们讲述了女性寻觅情感家园的故事。如果把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也放在这个框架内来解渎,那么它干脆就消解了天长地久的爱情神话,也戳穿了亲情友情的虚伪。
这些关注女性的中篇,捕捉到了女性在世纪末穿行的脚步声,状写了女性作为性别的一极在世俗生活里的生存景况。小说中浮现出来的女性生存图景,是对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某种意义的回顾和总结。
四、理想的寻觅与自我的拯救
99年中篇小说中我们既时时感到现实的沉重,但理想的光芒仍时时在小说的天空闪耀着。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的丰富与满足,然而其负面效应也相伴而生。特别是步入世纪末以来,人们逐渐滋生出精神的茫然感、焦灼感和失落感。生活中没有了理想,人类的精神家园迷失在重重雾霭背后。在新潮小说的诸多文本中,流淌着灾难与死亡的淋漓鲜血,铺张着罪恶与暴力的巨大双手,萦绕着绝望的连绵叹息。然而人类不会自暴自弃,而是渴望着灵魂的救赎。他们或者通过对乌托邦的钟爱与热情,或者通过对精神还乡的歌吟,对神性光辉的直接祈求来实现救赎。然而这些都未免太虚无缥缈。试问救赎以后的心灵又用什么来支撑呢?人最终还是要用一定的理想追求来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里的理想泛指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它们或者是未来的现实,或者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梦想,但只要你曾经朝着它的方向努力过,奋斗过,那么你就再也不会失落心中的家园。在99年中篇小说中这种理想主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永恒信念的理想追求;一类是美好人格、人性的理想追觅。
首先是永恒信念的理想追求。理想在此无所谓高远或卑俗,关键是你是否在用你的生命追逐着。《我的天空》里,我的父亲、徐明为那一片蓝天献出了生命,但他们的生命却在毁灭的那一瞬间充满了激情和诗情。蓝天是他们理想驰骋的疆场。生命逝去,英魂不散。还有许许多多在为蓝天事业奋斗的战士,头上都有一片湛蓝的天空。《朝着东南走》里的父亲不惜抛妻别子执意要往东南走,开始他是为寻求太平快乐,而后那个东南方就失去了具体内涵成为理想的一个象征。东南方在哪里,它永无止境。明知如此,仍然要踏上旅程。人的一生,可以小憩却不可驻足不前,生命也许不辉煌却永远激情搏动,无怨无悔。
另一类是美好人格、人性的理想追觅。永恒信仰是人的外在表现,而人格人性却是人的内在修养。人性之初无论善恶与否,追求独立的美好人格却是人类最大的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宏愿。铁凝《永远有多远》里的白大省从小到大,仁义、善良、热情,她痴心地迷恋她所爱的人,却总是失恋,最初的男友在走投无路时才选择了她;她把新房让给弟弟和弟媳,心中全没有自己。她做出这一切没有权衡,而是天性使然,想到做到。她似乎是二十世纪末现代京城里的一个汲取甘露精华的纯洁赤子,凄美而又孤独,然而正是有了她,“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感更加平安。”许世峰的恋人舍他而去嫁给了城里人,尽管他心中对那人充满恨意,但在危难关头,他拼出生命救出了被洪水围困的夺妻之人。象题目《飞翔的鱼》所标示的那样,他化作一条鱼在水中游动,而高尚的灵魂却在天空飞翔。
其实理想的追逐何止于此呢?它们只不过是人类理想的一个个寓言象征。仅从题目的字面来看,“走”、“天空”、“魂”、“飞翔”、“永远”本身便具有一种永恒、纯洁、辽阔的理想色彩,似乎是一个个跃动的神性光环在熠熠闪烁,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和感觉上的力度。他们不做抽象的思辩,而是取材于日常生活,在感性中孕含理性哲思。特别是《朝着东南走》,它本身的哲理意味非常浓,它可以看作所有理想的一个总体象征:朝着东南走,理想在等候。
世界是多彩的,文学的表现也是多样的,以上对99年中篇小说的梳理不可能把所有主题都面面俱到地囊括进来。但是,通过对主题的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出,99年的中篇小说以写实的姿态深入到现实日常生活,对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又发人深思的现象和事件进行了原生形态的状写和入木三分的开掘,在体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作出了扎实的努力。一切都在发展,中篇创作也在继续,愿中篇小说在二十一世纪初升的朝阳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附 文章所提作品的出处
《无根令》,阿宁,《人民文学》1999年第7期。
《腐败分子潘长水》,李唯,《小说月报》1999年第6期。
《选举》,毕四海,《人民文学》1999年第1期。
《缝隙》,祁智,《小说月报》1999年第2期。
《一亩二分地》,阙迪伟,《小说月报》1999年第4期。
《陈宗辉的故事》,祁智,《收获》1999年第3期。
《找人》,许春樵,《小说月报》1999年第3期。
《扭曲》李肇正,《小说月报》1999年第3期。
《金莲,你好》,阎连科,《钟山》1999年第2期。
《光和影子》,何立伟,《小说月报》1999年第4期。
《浮生》,朱文颖,《收获》1999年第3期。
《老乔的某年夏天》,程青,《十月》1999年第3期。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方方,《小说月报》1999年第7期。
《平常人生》,储福金,《十月》1999年第3期。
《周渔的喊叫》,北村,《小说月报》1999年第5期。
《关系》,潘军,《小说月报》1999年第5期。
《情殇》,程先利,《当代小说》1999年第6期。
《符号人》,赵凝,《山东文学》1999年第3期。
《永远有多远》,铁凝,《小说选刊》1999年第2期。
《我的天空》,姜凡振,《小说月报》1999年第5期。
《飞翔的鱼》,王立纯,《小说月报》1999年第4期。
《朝着东南走》,阎连科,《小说月报》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