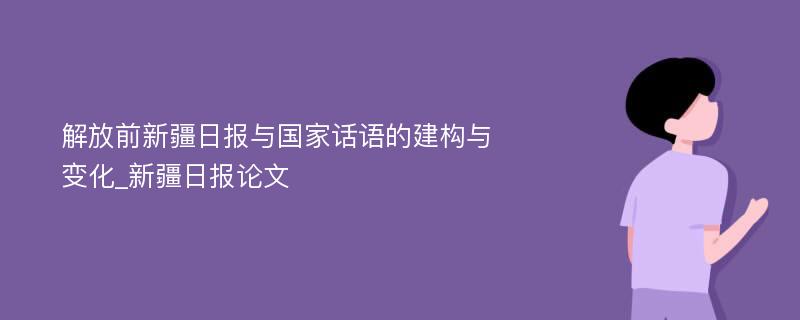
解放前《新疆日报》与国家话语的建构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前论文,新疆论文,话语论文,日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先后发生在北京、昆明、新疆多地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频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新疆问题成为当下中国最为纠结的政治与社会议题之一,也成为威胁社会稳定难以治愈的顽疾。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与社会问题困扰着历代统治者,新疆问题并非是当下社会的产物,而是分裂主义在中国西部边疆持久的积累。新疆问题带有古老的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1]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至和1949年和平解放前,新疆处于一个持续动荡的历史时期,政权的不断更迭,带来的是决策者为维护政权而转变的话语叙述结构,以及如何消解原有具有感染力的叙述结构,而呈现国家话语,大众媒体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其中。 一、研究缘起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省制,“新疆从此由满军的军事自治领变成中国国家的领土”[2],先后派遣刘锦堂、魏光涛、陶模等9人担任新疆巡抚。新疆建省后,为了巩固满人的统治地位,阻止当地少数民族与汉人交流,以免他们被传统的汉文化吸引。这一狭隘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疆原有居民的中国人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提供了话语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它一开始就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同时还有国家建设的一面——主要的反映是国家统一。[3]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垮台,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督办,自此新疆进入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的军阀统治下的半格局状态。决策者们不再利用封建制传统的叙述结构,而是把乡土之情放入了他们的自治理论中,以强化地方来建设国家,将新疆省政府作为主权政府。1912年至1928年,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奉行“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利用新疆各种族之人,以保新疆”[4]。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防止各族人民的联合反抗,杨增新利用民族矛盾与宗教隔阂,相互牵制,“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5]。实行民族的优待政策,“蒙古歌部落沿前清有待条例不纳钱粮,凡一切国家收入均由回缠担负”,加大了民族间的矛盾。“民智已开,人心日险”[6],因惧怕强大的革命力量,杨增新实行“愚民政治”,遏制新思想传入,限制学校教育与报刊书籍,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并未解决新疆长久动荡的局面。金树仁是杨增新政策的忠实追随者,在他主政时期,新疆经历了政治大动荡。由于杨增新时代的牵制与愚民政策,以及金树人吏治腐败、滥发纸币,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引起民族纷争。加之苏联在新疆的特殊优待,英国势力在南疆的渗透,及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受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行民族分裂活动。1931年以哈密小堡事件为导火索,发生了哈密农民暴动,并迅速波及全疆,武装暴动的烈火摧毁了金树仁政府。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正值中国遭受日本大肆侵略的时代,同时新疆也进入了一个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持续的时代。盛世才将新疆民众的省籍身份与国籍身份结合,号召全民“反帝”、“建设新新疆”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塑造符合历史需求的叙述结构,企图转移民众的注意来缓和新疆内部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事与愿违的结果,恰恰是这种以维护“省自治”为目的来建构国家意识的矛盾——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为1944年“三区革命”的爆发留下了话语空间。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盛世才在国共间摇摆不定,最终宣称“新疆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也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始终在以地方主义为主体的叙述结构中寻求新疆的归属,而最终在政治权力的利诱下放弃了。盛世才借助孤悬塞外的封闭地理环境割据称雄,国家政策在新疆的辐射力远不及地方独裁统治,他的这种左右摇摆的国家叙述结构,无疑成为新疆民众理解国家的主要渠道。然而不稳定的国家话语的表述,模糊了新疆民众的国家意识,为外来的民族分裂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提供了空间。最终,权力政治和权威语言的相互作用,中央集权的国民党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7] 1944年10月吴忠信抵达迪化,主持新疆工作,公开表达国家与国家主义的话语。决策者开始致力于建设新疆民众的国家意识,构建“大宗族”的话语体系,以地方主义为核心的省籍文化开始逐渐消解,但伴随而来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持续影响。抛弃省籍身份后的单一国家话语的建构却不得不面临“民族身份认同”与“宗教认同”的阻碍,面临突如其来的文化改造和政治变革,当决策者以具有优越感的现代性文化来塑型新疆时,遭到了少数民族民族的“反教化”抵抗,转而倒向民族与宗教的认同。当然这一倒向并非完全源自于民族自觉,国外势力扶持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此外,国家话语在新疆的形塑与表述还受到了少数民族居民国家意识淡薄与国籍不明的事实阻碍,在新疆常常有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族被国境线分割为两个国家的人民,分居在两个国家,甚至同时拥有两国国籍的民众,对于他们而言,国家的影响力远不及民族与宗教。1945年秋,在苏联的支持下,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以反抗国民党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将新疆的民族问题推向高潮,并形成了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体的三区革命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党直接统治新疆后,新疆被拉入到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新疆的表达也从以地方主义为主体转向民族自治与国家认同的叙述结构,一方面歌颂“大宗族”文化与“三民主义”,一方面宣扬非汉族的少数民族高度自治。这种既重视民族个性又不放弃国家意识的叙述结构,并未给新疆带来永久的稳定,相反在张治中一再退让的民族政策中,新疆的民族矛盾达到了顶峰。面对频发的暴力冲突,政府一方面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凭借对知识生产体系的控制,利用报刊书籍对民众的公民意识施加影响与塑型,企图通过控制民众的话语与思想空间来建设一个稳定的新疆。然而一次次的武装镇压,最多只起到了短暂的震慑作用,而分毫未增加少数民族对国家及新疆政府的忠诚与认同。如何利用书籍报刊及一切意识形态工具,试图改造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与认同,成为决策者们的一道难题。无论是军阀时期的新疆地方政府,还是作为中央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无不根据具体的社会实际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并认可这一政策的可行性,大肆的宣传与赞扬。 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后,三区政府回归中央。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不再赞美大一统的民族传统,认可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8]此种叙述结构强调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的一体。此外,在1990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将“稳定与发展”确定为当前民族工作的两大任务。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成为新疆叙事的主流结构。但是,事实表明,困扰一个多世纪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未解决,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成为少数分裂分子用以颠覆国家认同的替代性叙述结构。 新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加之杨增新实施“愚民政治”,内地的刊物很难输入新疆。《新疆日报》是当时新疆为数不多的被允许公开出版的刊物,成为决策者控制民众话语与思想的理想工具。《新疆日报》自创刊即扮演省政府机关报的角色,横跨杨增新、金树仁与盛世才三届军阀,1944年底国民党直接控制新疆期间,将其作为省政府的重要宣传工具,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宣扬“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帮扶边疆各族的地位”[9],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日报》作为新疆自治区的地方党报,开启新的里程,担负起维护边疆民族团结与稳定的伟大使命,并将这一使命延续至今。本文将以解放前的《新疆日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决策者在传承与断裂之间如何进行国家话语建构与叙述,以期获得对新疆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从而掌握问题根源之线索。 二、从《天山日报》到《新疆日报》:国家话语的建构与变迁 《新疆日报》原名《天山日报》,创刊于1927年[10],1935年12月3日更名为《新疆日报》,并成立新疆日报社。 1912年5月杨增新担任新疆都督,代表着新疆从传统的封建制叙述结构逐渐被现代观念所消灭,然而由于强大的地方主义与军阀观念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淡薄了新疆民众的国家意识。然而杨增新未将早期的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带给新疆民众,相反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他实行愚民政策,限制报刊书籍的传播。“杨增新惟恐民智之渐开也,对于内地或外国入新各种刊物,始终施行封锁政策……本省只有《天山日报》所载消息皆登津沪各报。”[11]至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资产阶级报刊,只准由省府订阅一份,百姓订阅则在禁止之列,对于内地寄至新疆的报刊书籍,检查甚严,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的报刊书籍,都在杨增新的查禁之列。[12]然而正是由于杨增新的严厉限制,增强了民众对于信息与知识的欲望,致使世界各地出版的维文或阿拉伯语系的书刊不断流入新疆,苏联出版的《解放报》、土耳其出版的《新土耳其斯坦》、德国出版的《民族新路》、日本出版的《新日本通讯》,知识分子们奉为至宝,巡回传阅,并诵读给不识字者听。[13]同时新疆本省的革命刊物也开始萌芽,《伊犁白话报》和《新报》向新疆人民输入革命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文明。面对外来异己思想的不断涌入,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杨增新才于1927年创办《天山日报》,以此作为他宣传政府政策与思想的工具,对抗外来异己思想。此时《天山日报》“虽名为日报,其实是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因为销路来源缺乏,只能排剪内地从邮局寄去的报纸,其新闻时间相差一两个月”。[14] (一)作为方法的国家话语 1929年金树仁上台后,接收《天山日报》作为其统治新疆的宣传工具,并“创设报馆以启民智也……纠合同志集资创办《天山日报》社为中国国民党言论机关,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引导民众使同为党治下之信徒,而尤以启迪缠、蒙正确之智能,俾人人有爱国爱党之思想,三民五权之认识为重要之工作,此项日报系用汉缠合璧之文字,庶不识汉字之缠蒙亦得直接读报。”[15]由刘光汉、潘树基、伍尚志等担任主笔,在各大行政区聘有消息员,[16]设有专职记者,报道新疆新闻。作为中国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和金树仁政府的机关报,在报道言论方面,该报突出国民党重要任务的封建军阀的活动,宣传当时的南京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同时进行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国内外对其声讨活动。[17]在报纸的新闻性方面,不仅重视其他各省的新闻报道,除订有全国各大报纸外,还在伊犁区订有俄文报纸,喀什区订有英文报纸作为参考资料。[18]而且它的“消息来源不单靠从内地邮来的报纸了,每天用收音机听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不过一遇到天时有变化,则听不清,便影响报不能照常出版……”[19],“外县有的也有通讯员提供情况,但外县消息见报,大半在半月以后。”[20]1930年起,报纸时事新闻多转载自京沪各报,“九一八”事变后,大量刊登抗日救国文章,[21]展现爱国情怀。但由于新疆当时各方面还比较闭塞,无线设备不健全,加之人为原因,一些新闻事件从发生到被《天山日报》报道出来,新闻往往变成了“旧闻”。[22] “七七事变”后,金树仁迫切地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名”来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尽各种手段,以求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23]不惜在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宣言“三民主义”。将《天山日报》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构,“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引导民众使同为党治下之信徒,而尤以启迪缠、蒙正确之智能,俾人人有爱国爱党之思想……”,输入“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建立新疆人的国家意识。同时刊登系列抗日报道《举国一致共驱倭奴》,副刊发表《仇日歌》与《抗日救国歌》,表达爱国情怀。[24]事实上,1928年7月下旬,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新疆省设党部指挥委员会,就遭到了金树仁的公开抵制。金树仁只不过是试图通过颠覆传统的封建制的叙述结构,拥护国民党“三民主义”,以国家话语为方法,通过建构国家话语示好中央,以此获取中央的正式任命。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这一时期《天山日报》不再过分地主张地方主义,开始构建一种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结构,探索地方与中央间话语空间的平衡,这种观念的转变,至少可以部分的为新疆民众国家意识的树立提供背景与话语空间。 (二)以“地方”为中心叙述国家 1933年,这一略带平衡的地方与国家话语被盛世才的“六大政策”所消解。“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掌控新疆军权,登上统治新疆的宝座后,《天山日报》过渡为盛世才政府的机关报。盛世才在政治与经济上拒绝国民政府的参与,《天山日报》的使命开始向维护地方独裁统治回归。由于实行“亲苏”政策,因此在报纸编辑方面,与苏联方面联系,不但获得排版方面的建议,还常常使用来自苏联方面的国际电讯稿,但根据盛世才的要求,报纸上又不能表现出新疆要实行共产主义的言论。[25]《天山日报》在盛世才的控制下,将话语围绕着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主题展开,把新疆稳定与民族团结与国家的强大与发展密切结合。 1935年12月3日该报正式更名为《新疆日报》,成为盛世才宣扬“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工具。联共党员万献廷接替盛世才的同源老乡郎道衡担任社长,增加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及新疆经济文化建设相关内容报道。为便于控制报纸,同年,盛世才将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与省政府合办并铅印了《新疆维吾尔报》改名为维文版《新疆日报》,[26]此后相继出版了哈萨克文版和俄文版《新疆日报》。同年12月5日报社更名为“新疆日报社”,报社除在迪化设总社外,还在伊犁、塔城、喀什、阿山设立分社。但此时总社与分社并无联系,亦无通讯稿供应和编辑工作指示,分社自成一家。[27]随着盛世才与苏联的密切合作,苏共党员领导报社,苏联思想影响了这一时期报纸实践与社会意识形态。《新疆日报》以“宣传民众,煽动民众,组织民众加强扩大建设新新疆的意识,用我们的报纸统一新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群众,各行、各界、各阶段的共同的情感思想与行动”[28]为目的,不再倡导传统的封建叙述结构,而是将新疆问题放入反帝亲苏的“六大政策”理论之下,将反帝与发展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平等、发展新疆以及祖国领土的完整等概念结合在一起,强化反帝斗争文学。“我们要把反帝的知识充实起来,武装起来,必须要把文化为条件,如果不能把各族固有的文化发展起来,那么反帝的战线一定不会牢固的,新疆将得不到永久和平,也不能保持新疆永远为中国领土。”[29]毫不掩饰的揭示政府发展民族文化的唯一目的是提倡以民族为形式、以反帝国主义打到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为内容,以建设新疆为目的的民族文化。将新疆的反帝口号与新疆的稳定与建设联姻,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新疆民众作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当然,盛世才同时利用反帝建国的口号将新疆民众的眼光引向国家,缓和疆内民族矛盾,达到依靠国家话语的构建来稳定新疆的目的。 1938年,应盛世才之邀,赵实、汪小川、李宗林、萨空了等一批中共党员先后进入报社,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国宣传,《新疆日报》成了统一战线形式的特殊党报,强调“民族意识”与“国家”,强调“我们中国所以遭受惨痛之压迫,多半因为民族意识不正确,因受数千年来之家族制度与私产制度之洗礼,有些人形成了损人利己的典型,只知道自己有家族,不知道有社会、有国家……”。[30]1938年至1942年间《新疆日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话语围绕在抗日救国的主题展开,配合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动员新疆民众献金、募集寒衣以支援抗日前线,并以此建立了一种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叙述结构。 盛世才正如20世纪初的大多数军阀一样,并不主张地方分裂主义,面对自身的权力欲望、内部的民族纠纷以及孱弱的国家,只不过在地方、民族与国家间寻找平衡,既想维护独裁统治与民族团结,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在原本省籍意识不强的新疆,企图通过话语叙述结构的改变,增强新疆民众的省籍意识,以便维护新疆的稳定与团结,同时伴随着联共党员与中共党员的努力,又在以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叙述结构中融入抗日救国的国家话语。然而,尽管决策者想依靠报纸发展出一种新的具有合法性的叙述结构,但是这种努力受到了阻碍,阻力恰恰来自于大多数不具有阅读能力的少数民族民众对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的认同。 (三)超越“地方”的国家话语 军阀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可能是最缺乏思想倾向性的集团,他们在制定整治计划等重大问题上,不是根据个人的思想观点,而是根据力量的对比。[31]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暂时失利,盛世才担心因为战争的原因,苏联不能再大力的援助新疆,于1942年倒向国民党。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7月31日,李啸平领导编辑部编发最后一批稿件,就在当天报纸的大样出来后,多数党员同志先后离开了报社”。[32]在共产党人士退出报社后,盛世才从重庆聘请中央政校新闻系毕业的吕德昌、李恩生、雷渊澄和陈万祥进入报社工作,次年李尚友担任编辑长。[33]1943年初宋念慈出狱担任《新疆日报》社社长,盛世才对报社进行严密监控,嘱咐“接事之后要好好整顿,此后言论非常重要,要注意宣传,不能有所差错”,宋亦唯唯听命。[34]1月16日《新疆日报》刊发《忠实举行三民主义 增强抗建力量》,高举“三民主义”大旗,20日发表社论《新疆民众的新任务》,声称“把伟大的三民主义,作为我们每个人的终身信仰,应该把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作为我们每个人的终身事业。”[35] 1944年,新疆彻底告别了军阀统治时代,蒋介石委派吴忠信担任新疆省主席,国民党政府开始直接控制新疆。如何将新疆的“六大政策”转化为“三民主义”的政治,是迫切而且“实事艰而责巨”的问题。[36]吴忠信委派其亲信张振佩接替金绍先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吕器任总编辑。加强对边疆人民思想的控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宣扬“宗族论”——“中华民族是多宗族融合而成”,[37]汉族与维吾尔族的“祖先都属同一种族,统一血统”,[38]否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新闻内容的选择上,突出国际与国内报道,缩减省内新闻,淡化民众的省籍身份。此外,《新疆日报》还宣扬儒家思想与佛教文化,大篇幅地介绍基督教,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弱化伊斯兰教文化在新疆的主体地位,从而将新疆民族从民族与宗教身份的认同转移到国家认同上。当然,这一带有“挑衅性”的叙述结构并没有赋予足够的意义可以支撑“三民主义”的国家话语,反而引起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怀疑与警惕,转向了更为保守的民族文化与宗教生活。 (四)从民族与宗教的历史中叙述国家 1944年秋在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爆发了以反抗盛世才与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依附于民族身份认同与宗教身份认同的“民族独立”的叙述结构迅速在新疆蔓延,成为构建“三民主义”国家话语的最大威胁。民族与宗教在新疆是更适合目标发展的认同单位,分裂势力以他们为基础,抵抗以“三民主义”与“国家统一”观念的输入。三区革命爆发后,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成立新疆民主联合政府,任命黄震遐和张紫葛接任了汉文版《新疆日报》,贯彻以“维护新疆和平”为中心的宣传方针,维护新疆民主联合政府,不报道内战消息;在国内问题上主张和平谈判,不搞反共宣传;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中苏友好。[39]《新疆日报》在张治中的指示下,一方面回避暴力冲突事件本身,表现出一个稳定团结的新疆,把国民党政府建立为稳定的、负责任的、值得信任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角度介绍“三民主义”,以迎合少数民族喜好的方式来确定“三民主义”在新疆的合法性地位。《新疆日报》刊登包尔汉的《伊斯兰教和三民主义之比较》、《国语与维语同一系》及马次伯撰写的《回教精神与儒家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将“三民主义”与宗教话语交织在一起,“希望各宗族精诚团结,官民密切发展,信任政府,执行法令,和衷共济,协同一致,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新疆”。当然,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包尔汉便不再用“三民主义”话语来为民族国家观辩护,而是转向了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团结于一体的话语。 1946年6月6日,三区政府在“十一项和平条款”上签字,“东土耳其伊斯坦人民共和国”破灭,成立联合政府,“民族独立”的话语丧失了往日的合法性,而被符合现实语境的“民族自治”的叙述结构所替代。在此种状况下,1946年7月维文和哈文版《新疆日报》由“三区”政府管辖。汉文版《新疆日报》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反“三区”活动,打破了以团结和统一为主体的叙述方式,而是把民族建构为历史主体,在历史的叙事中解释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华文明的相关性,改变民众对于过去及现在的民族、新疆与国家的意义和看法。《维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新疆的历史观》、《历史上的三种“口里人”》、《匈奴霸权的崩溃——中国对东方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等文章,在历史语境中揭示新疆境内各少数民族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与统一,企图将新疆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改造为国家认同。最终,新疆和平起义之前,在包尔汉与陶峙岳的主张下,“和平”成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替代性叙述结构。随着新疆和平解放,“和平”的叙述结构即被消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1月7日,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作为军代表宣布接管《新疆日报》,[40]该报开始全面使用新华社电讯稿,为解放军进疆做舆论准备。自此,《新疆日报》作为新疆地方性党报,开启新的里程。 三、现实的新疆问题与孱弱的国家话语 新疆问题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变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延伸,但现代“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新疆当下的延续与新疆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在“两泛”思想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群体与国家主体的话语出现失衡。这种失衡关系与新疆孱弱的国家话语息息相关。1933年新疆经历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伊斯兰圣战理论”推动下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开始呈现以“民族独立”为中心的强化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的叙述结构。1930年代,维吾尔人开始大量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并形成以“东土耳其”为中心的民族划分理论,将维吾尔称为部落,与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兰其、乌兹别克、塔塔尔及塔吉克人组成一个民族——土耳其族。[41]以麦斯武德与默罕默德·伊敏为代表的“大土耳其族”或“大突厥族”的民族划分理论,将其他少数民族划入维吾尔族范围共同反对新疆汉族及以汉族为主体的政府,抵抗国家话语的建构。当然,这一理论引起了部分国内学者的反对,黎东方从历史的叙述结构出发,揭示以上七个民族并非突厥系,而是“夏后氏匈奴之后裔”。[42]盛世才选择了以强化省籍身份的联邦制话语来消解具有分裂性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思潮,将新疆的稳定与民族团结结合在一起。然而,在政治权力频繁交替和民族纠纷纷繁复杂的民国新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如此之大,这种孱弱的国家话语叙述结构受到了怀疑与警惕,为“两泛”思想在新疆的传播提供了话语空间。1944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再次爆发,动员了新疆所有的突厥语系的伊斯兰宗教居民,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的民族冲突在短暂的缓解后,1980年代又逐渐成为威胁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因素,新疆问题成为中国最为纠结的政治与社会议题之一。2009年的“7·5”事件与2014年7月28日发生在新疆莎车县的大规模的暴恐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建立在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上的东突厥斯坦独立意识,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统一。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政治来说,能否消除来自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影响,成为了一块真正衡量成败的试金石。[43]民族与宗教都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形式,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隶属于社会关系,民族、宗教与国家并不具有冲突性。面对利用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的极端思想传播和社会心理,以及在国际国内各种现实因素之下衍生出的恐怖主义,媒体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必须正面地回应并在宽容与理解中强化国家话语,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属性与国家意识有机结合,平衡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宗教与国家意识,而非仅仅依靠简单的情绪性的宣泄与宣传性的总结。 ①维吾尔族。标签:新疆日报论文; 盛世才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 东突厥斯坦论文; 新疆天山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突厥论文; 天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