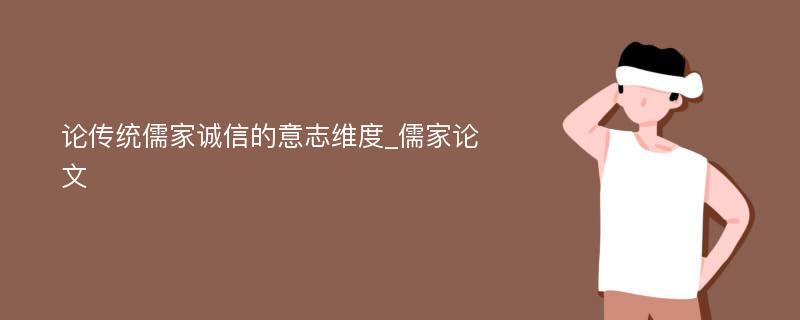
论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意志论文,传统论文,诚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3-0056-06
意志与认识、情感、信念等一起构成道德的内在心理结构,而且意志是道德心理向道德行为、道德品质转化的关键环节和要素。意志是个体德性的基础,个体德性也必然彰显意志的力量。传统儒家诚信蕴含着极其强烈的意志精神,服膺于“天人合一”观念,诚信主体具有鲜明的意志自由;执着于“诚”的价值,诚信主体获得不竭的意志动力;忠诚于“内诚外信”的要求,诚信主体表现出坚毅的意志行为;遵循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路径,诚信主体实现自我的意志修养。从意志维度探讨传统儒家诚信,有利于我们深入解析传统诚信伦理的内在本质和作用方式,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儒家诚信思想的价值性资源。
一、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
诚信从何而来?诚信是他律的社会规范还是自律的德性要求?诚信主体的行为是被决定的还是自由自觉的?对此等问题的解答必然要涉及诚信思想的形而上学问题——意志是否自由。在西方学者看来,意志是钩联道德行为与道德责任的必要纽带,没有意志自由①,人们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无所谓道德之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上,持有宿命论倾向,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控制,忽视个体的感性欲望和意志自愿,个人的意志总体上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认为儒家伦理中没有意志自由。[1](p.91)实际上,这一看法失之偏颇,儒家自孔子以降,在强调知命,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同时,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人具有独立的道德意志,肯定道德意志的积极作用,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
儒家诚信思想中的意志自由观念是以“天人合一”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和逻辑出发点的。儒家认为诚信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天道的自然法则与人道的当然之责的合一。从儒家“诚”之范畴内涵我们大体可以得知。“诚”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具有形上性质,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特别提出“思诚”命题,认为思诚的目的在于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在于取信他人。[2]《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宋儒更是将“诚”之范畴作了极大的发挥,将诚与道、诚与理、诚与性打通,认为诚既是天之道,亦是人之性。宋儒皆言天道本诚,诚是天道的本真状态并成己成物,人道即性,诚是人性之本原。
出于对天道的感应,儒家没有形成西方的“天人相分”与“上帝存在”的逻辑思维和道德理念,而是将诚信的意志自觉和对天道的虔敬统一起来,形成儒家独特的意志自由观念。孔子肯定人有独立的意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每个人都是自我道德上的主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作为“仁”统摄之德目的“信”(诚信),孔子认为亦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孔子指出君子应该“谨而信”,赞许“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比孔子更明确强调意志的自觉能动性,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存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人是愿意而且可能“思诚”以致成贤成圣,把人的道德意志能动性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从而对普通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荀子也充分肯定了个体诚信的意志自由与自觉。他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荀子·解蔽》)荀子讲心对身的主宰作用,主要是意志、情感的主宰作用,这里的神明之主即自主的意志。所谓“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就是讲意志的自由选择。“心容其择也”,也是说意志具有选择的作用。“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中庸》讲“诚者,自诚也”。张载言“诚,善于心之谓信”(《张子正蒙·中正》)。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更是强调良心的自觉自为,诚信就在于良心之“磨镜去垢”之后的澄明。
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高扬了人的道德自觉和担当精神,使得传统诚信具有鲜明的德性伦理的特征。借助于天人合一观念,儒家诚信获得了形上支持而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人们对于诚信的人道规范天然具有一种敬畏感,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历史条件下,通过借助天的权威甚至神秘性,人们的诚信观念确实较为容易确立,亦是不争之实。[3]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理论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看不到诚信产生的社会历史本质,在诚信的来源问题上,由天道直接引出人道,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必然与当然、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混为一体,把“人道”这个人们行为的“当然之则”看作是不可违背的“天命”、“天理”之必然,陷入了道德宿命论,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是极其不可靠和虚幻的。另一方面,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并非没有限度,其限度就在于诚信的指向及局限,“诚”受制于“礼”,“信”受制于“义”,传统“礼”、“义”的时代局限直接影响和决定诚信意志的广度与深度。
二、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动力
儒家诚信除了获得天道的支持,还需要有心灵的自觉,需要有自我心理的认同和意志驱动,而这个心理认同和意志驱动的力量就是心性之真诚。儒家在天道观的关照下,打通了天道的实有到人道的应有的关系,又通过人性论和心性论的解释,使诚信获得了主体的认同与连绵动力。
认识诚信的意志动力,需要做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诚信自我价值何在?二是诚信能否获得主体的认同?
儒家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除了借助天道观的支持,还需要通过对“诚”与“信”的解释,揭示诚信的内在之德性。在儒家思想中,“诚”是兼具道德的“知”、“情”、“意”、“信”等现代内涵的词(在宋明理学那里甚至具有本体论的色彩),尤其具有强烈的意志意蕴。朱子说:“诚者,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诚者乃“开心见性,无所隐伏”,指的是作为人的一种真实的内心状态和品质,表现为个人自身的品行、品德、修养、情操,它是道德的、内在的。而“信”本意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和誓言等,表现为对某种允诺、信念、原则等发自内心的忠诚。儒家认为诚是百善之基,一切真正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真诚,有诚才有德。[4]宋儒周敦颐对“诚”“信”关系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周子通书·诚下》)。“诚”为五常之一的“信”的本原和内在根据。“诚”即内在的精神气度,“信”即外在的行为表现,无诚即无信,无信未必无诚。只有出于真诚,才能形成德性之知、情、意、信和行,形成道德习惯,养成道德品质。诚信的本质力量就在于诚,诚乃是诚信之德形成、增进的内在保证和驱动力,诚也是其他各种德性的基础。正如朱熹所言:“如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方会日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若不实,却自无根了,如何会进?”(《朱子语类》卷六十四)儒家将诚信与“善”紧密相连,注重其诚信的道德实质,而不是仅仅注重于诚信的外在形式要求。儒家诚信就是真诚于心,信于道义,强调对自己真实本性的忠诚,对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高度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这与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基础上的契约诚信、功利诚信与宗教诚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论是否有外在规则他律(如法律)的强制约束,是否有功利性的后果和是否有超越性的上帝存在为基础,而仅仅出于对道义的认同去实施行为,因而具有相对的纯粹性和自律性。
个体心灵如何能认识“诚”并接受它呢?儒家借助心性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心性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和最终落脚点,它强调心统性情。儒家所言的心不仅指人的思维器官,而且具有道德内涵,即指道德意识、道德思维和道德修养之意。儒家不离“心”谈“性”与“诚”。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心是性的根源,而心是思的主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那里,诚虽是天生就落根于心的,但由于人心有利欲之求,诚心能被蒙蔽而放失,故要发挥心的思虑功能,“求其放心”,觉悟到天道之诚而使德性澄明。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他亦认为“心生而有知”,能知社会“义理”,从而规范自我言行,并且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论及“心”与“诚”的关系:“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荀子·不苟》)。宋明理学均认为“诚”存在于“心”中,但心对“诚”的认识因理学各派观点不同而存在分歧。程朱理学认为“心包万理”,“性”即“理”,义理是心的认识对象,但也承认心外有理,故主张“道问学”、“格物致知”,同时亦不反对“尊德性”、“自我体认”。陆王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心即是理,心对理的认识即是心的自我体认,无需外求,从而将“诚”与心、性、理完全等同起来,诚为心之本体,心对诚的认识就是“自家之体认工夫”。张载、王夫之气本派认为“心”与“诚”并非本体的同一关系,而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诚”在他们那里是没有超越性的本体内涵而只有认识论意义,“诚”被视作为一种心理的意识,如情感、意志、信念等的合集。
当存在于心中之“诚”被人“心”所认识,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之后,诚信观念才真正树立,但这种诚信还没有表现出现实性,因为意志还没有对主体的情感、行为发挥作用,还没有呈现诚信的外在载体。[5](p.66)诚信观念的发用还有赖于“心”主宰功能的发挥,一是“心”从积极方面的扬善并“择善而固执之”;二是“心”从消极方面止恶并“见不贤而去之”。“诚”的意志通过诚己、信人、欲人信、使人信等几个环节的交融,从而完成完整的诚信运行过程,至此,个体诚信实现了内城外信的历程而获得圆融。
儒家正是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由于真诚心性的缺失导致社会礼崩乐坏、伪善盛行之流弊,极力倡导真诚无欺,以诚统信,应当说是抓住了诚信道德建设的根本和关键,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6](p.197)但我们应认识到儒家把诚信视为一种自我的德性,其重心在“己”而不在人,重主体之“诚”轻他人之“信”,强调自律却忽视了他律,过于依赖人的内心信念,缺少必要的外在利益制约力量,缺乏坚强有力的诚信制度的保障。
三、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行为
在儒家看来,个体诚信的意志品格既是内在的意志自觉与良善,亦是外在行为的自律和持久。“内诚于己,外信于人”,“诚”的内在的意志精神气度,必然体现为外在的“信”的意志行为。
学者陈劲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人诚信心理结构及其特征》中将儒家诚信心理结构划分为正性取向和负性取向,其中正性取向有5个维度,即义、敬、真、仁、勇;负性取向有4个维度,即虚滑、欺诈、轻妄、奸狡。对应“义”之意志行为有“坚贞、强毅、披肝沥胆、守信、执着、刚直、有始有终、舍生取义、高义薄云”等,对应“敬”之意志行为有“稳重、踏实、本分、敦厚、认真、恳切、温良、从善如流、开诚布公”等,对应“真”之意志行为有“正直、诚实、光明磊落、坦荡、耿直”等,对应“仁”之意志行为有“内恕、豪爽、慷慨、心心相印”,对应“勇”之意志行为有“面折廷谏、铁面无私、理直气壮、直言无讳、敢作敢为、勇、不卑不亢、乃心王室”等;负性取向的虚滑、欺诈、轻妄、奸狡即是道德意志的无力或意志取向的偏离正道所致,每个取向都有相应的行为表现。[7](p.6)这种划分让我们对儒家诚信的意志内涵与表现有了整体的了解。
从儒家的理论和其生活世界中,我们可以得出儒家诚信行为在意志维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内在“诚”德的引领和内外一致。王夫之说:“有不诚,则乍勇于为而必息矣。”(《诚明篇》,《张子正蒙注》卷三)缺乏“诚”的勇敢,行为最终难免要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如前所述,诚德是“义”、“真”、“虔”、“仁”、“勇”等众德之门,“舍生取义”是因为有道义的根基,“本分敦厚”是因为有虔敬的心理,“光明磊落”是因为有“真诚”的底蕴,“豪爽慷慨”是因为有“仁爱”的关照,“直言无讳”是因为有“勇气”的支撑;诚信需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做到内在与外在的协同。对此,《吕氏春秋》中有经典的解释:“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吕氏春秋·淫辞》)二是行为“恒久”的努力。诚信即“至诚无息”,具有坚持性的品格。唐孔颖达说:“以行之一长久,能成就于物,此谓至诚之德也。”(《十三经注疏·中庸》)可见,诚的德性就在于它的连绵不断,如果不能做到持之以恒,就谈不上具有诚的德性。[8]大凡虚滑、欺诈、轻妄、奸狡的行为,有可能蒙蔽众人一时的眼目,亦有可能蒙蔽一人永久的耳目,但不可能蒙蔽所有人永久的耳目。三是行为勇于应对困难、恶逆的环境和条件。意志因困难恶逆而生,亦因困难恶逆而显。儒家诚信的意志品格因其勇于面对艰难困苦、逆境危险的环境或条件而彰显其魅力。在困顿环境中始终诚信如一,如“蔡勉旅坚还亡友财”、“阮湘圃耻得不义财”;在守信与利益冲突面前重信守诺,如“杨继宗要廉不要钱”、“曾子舆杀猪教子”、“辞曹操关羽千里奔刘备”;在遭受挫折和逆境中守信如初,如“杖汉节苏武牧羊”、“宋弘富不易糟糠”;在危险的境况中勇守诚信的道义,如“晋董狐书法不隐”、“高攀龙视死如归”、“陈小官不附和王申”、“铁面无私包文正”。[9]正是诚信的行为成就了古圣先贤的德性和境界。
我们在看到儒家诚信行为内蕴和外显的意志力量时,不得不慨叹其德性伦理的崇高和伟岸,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认识到其标之过高的诚信伦理要求对普通民众的悬隔,认识到其单向的诚信义务而无平等互通的角色定位,认识到其纯粹的诚信义务而无权利的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要剔除其时代的糟粕而创新发展其合理的价值内涵。
四、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修养
儒家诚信修养方法极具特色,重视意志方面的心性纯化和实践磨砺。儒家个体诚信的心性修养,即从个体修身的源头“正心”、“诚意”阶段就着手,纯粹、凝练、强化诚信良善的意志动机,夯实诚信的内在根基。
《大学》是儒家典籍中较早系统论述诚信修养思想的作品,提出了许多包括诚信的修养方法,如“正心”、“诚意”、“慎独”等。“正心”是儒家进行道德修养的起始阶段,“所谓修其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忮,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礼记·大学》)在儒家看来,“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动机,就是增强、扩充自己善的欲望和感情而减弱或摒弃自己的恶的欲望和感情。而心之正,即是诚,即是信。如何做到正心,儒家提出了各种方法。孔子强调要“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这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正心,又提出“克己”、“修己”、“正身”去克服那些不正当的道德动机,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去正心。孟子提出要志在仁义、志在圣贤,要“不动心”,要养“大男”,树立坚定而正确的道德信念,不要因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动摇自己的信念。朱熹提出了“省身克己”的诚信意志锻炼说,他主张关起门来,按曾参“吾日三省吾心”的方法,“专用心于内”。
“诚意”即包括诚信道德意志的修养和集中,就是自觉地把意志集中到高尚的诚信目标上来,使自己的意志诚实而无欺,不虚伪,不受恶、邪所染。也就是使诚信意志按其本然的状态得以发生、发展,这样就能到达诚信的意志纯一之境。《大学》解释“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熹在解释《大学》时指出“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诚其意”。朱子解释说:“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这是对“意”和“诚意”的一个经典性的解释,后来的儒家包括王阳明,都同意并接受了这一解释。如何做到“诚意”?周敦颐强调“主静”、“无欲”,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剥落”物欲,张载提出“尽性以至于穷理”(自诚明)、“穷理以至于尽性”(自明诚),程颐重视“敬义夹持”、“格物致知”,朱熹突出“居敬穷理”,王阳明高扬“致良知”、“尊德性”。
儒家“诚意”还开出了别开生面的“慎独”工夫。“慎独”的要义在于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制,不以外在因素作为自己践履道德的根据,它是在“不睹”、“不闻”、“莫见”、“莫显”的独处情境下,在“隐”和“微”上下功夫。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就能做到“表里内外、精粗隐微”、人前人后、明处暗中始终如一。如何做到慎独呢?《礼记·大学》云:“所谓诫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拼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之,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谈到要修身养性,提高自己道德水平,就不应自欺,而应尽力让自己如同讨厌恶臭一样,从内心讨厌恶,如同喜欢美色那样追求善。应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应只是做给外人看。可以说,“慎独”充分体现了诚信道德意志的自制性特征,是具有诚信之人自觉的道德实践,它不仅是通过极其严格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增强道德意志、升华道德信念的一种方法,又是一个人在社会现实中将自我需要同社会要求统一起来,凭借道德意志的力量来践行道德信念,养成一以贯之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
把诚信意志修养寓于丰富的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要求凝练成坚定的道德认知和意志自觉,是儒家诚信思想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躬行践履是传统儒家极为重视的诚信修养方法。“躬行”即身体力行,亲历亲为。中国的传统伦理学家无不强调“躬行践履”,以“躬行践履”作为诚信修养的最重要途径。儒家从孔子肇始就很重视个人的笃行,他教导人们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认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同上)他看不起“巧言令色”之人,认为他们“鲜矣仁”。孟子在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理性运作的同时,又提出“存心养性事天”的实践功夫,并且最终落在“存心养性事天”的道德实践上。荀子也是重行主义者,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这是对于行的重要性的最明确的说明。《中庸》之“诚”重笃行,宋明理学更是强调在实践中培养诚信道德,在实践中磨砺诚信意志品格。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虽然在“尊德性”与“道问学”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但是在对“由实践而形成德性”的认识方面却有相同的看法。朱熹重视道德、道德意志修养的“道问学”,但并不忽视“尊德性”,始终坚持认为“论轻重,则行为重”,“《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语类》卷十三)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明确地把实践提到第一位,并作出了理论性的总结。“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传习录》上)王夫之在诚信修养的路径方面作出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回答,他说“心志专一,意气就随之而动,而后可德成。故学、问、思、辨、行五者的关系,以“笃行”为“第一不容缓”、“必以践履为主”(《读四书大全说》卷六)。[10](p.58)
儒家诚信的意志修养方法对传统社会个体诚信德性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仍极具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