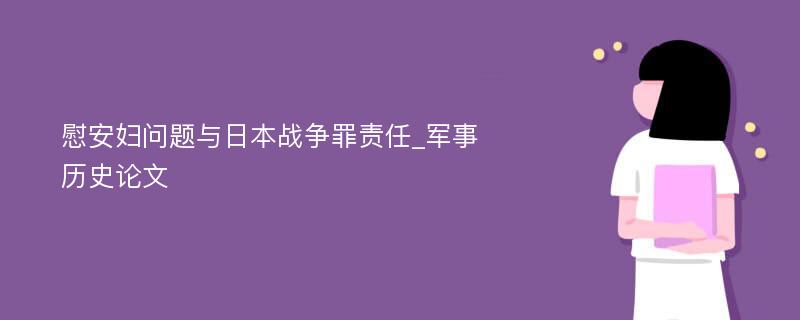
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战争罪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责论文,日本论文,慰安妇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近些年来,在抗战史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热点问题,在民间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由于相关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难以搜索、当年受害妇女随着年岁的增高而相继辞世,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慰安妇问题研究的进展却很缓慢,与世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对比。
在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学者和内阁阁员,为了推卸日本侵华罪责,也不时站出来,发表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蒙蔽日本国内视听,伤害中国人民感情。1998年8月,以小渊惠三为首的日本新内阁在组阁当夜, 其农林水产相中川昭一即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发表了“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注:参见《参考消息》1998年8月15日,第2版。)起而与之唱和者是号称日本第一大报的《读卖新闻》。8月11日, 《读卖新闻》发表了题为《损害联合国权威的“慰安妇报告”(注:此报告当是指1998年8 月发表的由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人麦克杜格尔草拟的《战时有组织的强暴的性奴役》。)的社论,声称:“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谓慰安妇的亚洲妇女被迫当军妓”,“不应只单独指责日本,尤其不应在还未证实战时日本政府曾强迫慰安妇提供性服务前便作此定断。”(注:参见《参考消息》1998年8月15日第2版《日本政治上的“没落”令人震惊》一文。)
发表上述言论的日本人,在“慰安妇”问题上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二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当年的受害妇女能活到现在的已不多见,能见到者也许会由于各种个人的或社会的原因不会开口说话,即便说出话来又可以对之加以歪曲或否认;而中国国内学术界由于档案资料缺乏等原因而导致的对此问题研究的相对薄弱,和日本现政府当局乃至一般民众对上述类型言论有意无意的纵容,更使得这些人在歪曲历史时肆无忌惮。于是,他们置历史的真实和亿万亚洲人民刻骨铭心的记忆于不顾,大肆宣扬“慰安妇问题”是“没有证据”和“未被证实”的说法,对日本人民进行反历史的教育,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予以极大伤害。
那么,真的就如中川昭一或《读卖新闻》社论等所说的那样,当年日军随军慰安妇并不具有强制性吗?真的就如目前日本国内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没有证据来证实日军当年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罪恶事实吗?回答是否定的。下面,我就这些年来所搜集到的资料及最近发现的10件档案资料,谈一谈侵华日军当年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暴行事实以及日本国家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
一 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是在当年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直接策划指使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罪行
二战期间,日军曾大规模地征集中国妇女充当其随军慰安妇,这已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八年时间里,在天津、山西、河南、安徽、南京、海南,在日军的铁蹄所到的每一个中国地方,都有无数的中国妇女受到耻辱的蹂躏和残酷的摧残。这一事实,同样也已为无数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和当事人的回忆所证实。
至于实际上有多少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人们的估计相互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战后协助美国处理军需情报的一位日本人曾经说过:“中国慰安妇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妇女当随军妓女的67.8%。”(注:引自江浩著《昭示:中国慰安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也就是说, 在当时日军所设的慰安所里, 每100名慰安妇中,就有被强征的中国妇女同胞近68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管宁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估计认为:“当时日本军队中慰安妇的总人数,最高限应为30万人,最低限应为20万人……在这些日军慰安妇中,数量最多的不是朝鲜人,而是中国人。”(注:管宁:《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国际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9期, 第36页。)而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先生在其《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一文中,则进而估计认为:日本军队中的慰安妇总数“不少于36万—41万……按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朝鲜慰安妇的人数在16万左右,日本慰安妇人数为2—3万人,台湾、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慰安妇各有数千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而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注: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 年第4期,第103页。 )这些估计数字与慰安妇实际人数之间或许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日军在侵华期间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同胞残酷蹂躏,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年日军如此大规模地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出于某些日本士兵的违犯军纪和个别部队长官对这种违纪行为的纵容,还是出于日本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划和安排?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判定日军强征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暴行的总体性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通过我们这些年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和资料的搜集分析,我们有理由认定,当年日军强迫广大中国妇女同胞充当其慰安妇,绝非是哪一个违纪士兵和部队长官的个人犯罪,而是出于日本侵华最高当局和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蓄谋和安排,是日本军方和日本国家有组织、有意识的犯罪行为。
据《远东审判案》备有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所载,当时日本情报部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地征用中国女人作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侵华期间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8日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曾就记者所提出的日本是否有秘密强制日军占领区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一事的问题,毫无掩饰地回答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此种事情,就像你不能否认美国士兵能请假去驻军当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注:转引自江浩著《昭示:中国慰安妇》,第62—63页。)这就是当时日本国家首相和日本军部对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看法和主张。把女人当作一种“战略物资”,是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最高当局和日本军部在观念上忠实信奉和在实践上切实执行的信条。不仅仅是中国妇女、朝鲜妇女,即便是日本本国妇女,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都只能是“战略物资”;不仅仅是在侵华日军部队中,而且在侵略亚洲各国的日军部队中,也都广泛地设置了慰安所。这更能证明慰安所的设立及日军对他国妇女的强迫征集,是当时军国主义的日本针对其所侵略国家的一种基本政策,具有十分明显的普遍性,而不是零星的、偶然的个别性犯罪。所以,正是当年的日本最高当局和日本军部,有意识地策划了这一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严重亵渎人类尊严的犯罪。
《近代史资料》总94号上刊出的《侵华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更为我们的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一组档案共10件,其中4件形成于1944年6至10月,分别为日军强迫当时伪天津当局强征中国妇女前往河南和唐山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其余6件形成于1945年5至7月, 主要是日军强迫天津当局强征中国妇女在天津和前往山东莒县充当慰安妇的资料。这10件档案,都是根据当时日本军方——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注: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是日军在天津的最高军事机构,由1938年11月从武汉前线撤退下来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组成,该师团前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任最高司令官。)——向天津伪政府所下达的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命令或“通知”而形成的,其中在《来仲威为选送妓女去山东慰劳日军给警察局长的报告》中,还附有一件《军方等遇说明》,是当时驻山东莒县日军第一四三七部队为赴鲁慰安妇所提供的军方待遇的说明,更是直接出自日本军方之手。所以,从这10件档案产生经过本身,即可看出,当年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在日本军方一手操纵策划下的产物。
其次,在10件档案中,有好几件行文中都记载了当时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为强征慰安妇事下达给天津政府和天津警察局的命令或通知。如:
在1944年6月8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劝遣妓女赴河南慰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记录了当年5月30 日“天津防卫司令部”给伪天津警察局的通知:“本市妓女应赴河南一百五十名慰劳军士,一月为期,凡有押账暨有领家者均即取消,皆为自由身,从速办理,三二日即当起行。”
在1944年10月7 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就办理选送妓女赴唐山市慰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之呈文》中,也记载了日本宪兵队的通知:“选送美貌妓女十五名,限一星期内送往唐山市,担任慰劳工作。”
在1945年5月3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关于选派妓女劳军给市政府的呈文》中,则载有1945年4月11 日天津防卫司令部给伪警察局的通知:“本市应选派妓女一百名,交由军医验选二十名,集合第二区槐阴里一号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劳工作。”
1945年7月17 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办理慰军妓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载有天津防卫司令的通知:“自七月一日起,前设之防卫司令部慰安所办事处取销,所有慰军事务交由各乐户分会轮流负责办理。”
1945年8月7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办理选送妓女赴山东慰军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准关系方面通知,选送妓女二十五名,赴山东莒县慰军”,并发《军方待遇说明》一纸。同月30日上午11时,天津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召集局保安科股长来仲威和乐户总分会长刘仲和训话称:“此次选送妓女赴鲁慰军,系为协力东亚全面圣战成功,不能拘于某一地区,希望速办。”(注:以上所引资料,皆见于,《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近代史资料》总9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等等。这些保留在档案行文中的“通知”,为我们证实当时日军在天津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在日本军方——天津防卫司令部——的直接策划指挥下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提供了至为确凿的证据。
第三,根据这10件档案资料的记载,每一批被强征的慰安妇都由日本军方直接派出军医进行检验,并由天津防卫司令部派人押送或由所赴慰军地点的日本军方派人前往天津接收。在慰劳所或慰军地点,受到日军的全封闭的管理,毫无人身自由,成为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如:
1944年6月被强征赴河南慰军的慰安妇, 即是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所派出的军医官出崎从290名中国妇女中检验选出86人, 并由防卫司令部派遣中井进曹长率日兵10名,于当月4日下午5时,由东站登车转北京赴河南的。
同样,1944年10月所强征前往唐山的17名慰安妇,则是由唐山日本宪兵队长及诹访部少尉检验,以确认为“合格”。
1945年4月所强征集的在天津“日本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军的20 名慰安妇,则是从100名中国妇女中,于4月25日先后经过日本军部儿玉大尉、出崎军医官等依次检验,选出34名。复于4月28日下午3时,又由天津防卫司令部德本文官派车押送至第十一分局界内秋山街同仁会妇人医院进行第三次检验,选取“合格”者20人,并于当日下午7 时由德本文官亲自送往“军人俱乐部”,交由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
1945年8月所征集的赴山东莒县慰军的25名中国妇女, 是由天津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出面与天津警察局会同强征,于8月1日由同仁会妇人医院院长荒木一郎检验,并于2日11时19 分由莒县“来津之军方责任者佐藤中尉等三人”率领,押送莒县。(注:以上所引资料,皆见于《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近代史资料》总第94号。)
所有这些,都可使我们看出,这10件原始档案所反映出的当时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从征集命令的下达,妇女的征集,妇女身体的检验,押送和当地军方的接收,全部是在天津防卫司令部和“慰军”地点日本军方机构一手操纵强制下的罪恶行为。所谓“一叶而知秋”,一时如此,一地如此,那么我们同样敢于认定,当年日军在中国各地强迫我妇女同胞充当其慰安妇的暴行,都是出于日本最高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更是在侵华日军当局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已为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加以证明,也必将为将来陆续发现的资料更进一步地证明。
二 日军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及其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关于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是否具有“强制性”,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却偏偏喜欢在这上面发表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似乎只要他们坚持住“从军慰安妇并不具有强制性”这一主张,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强征他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犯罪性质,进而减轻甚至推卸日本国家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但历史的事实却恰恰又是,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尤其是在中国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都是以其强大的军事武装为后盾,用各种极其野蛮的手段进行的;在慰安所中,日军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和肆意虐杀,更是令人发指,无法言喻的。
近些年,中国学者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日军在中国所设慰安所的类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方法等等方面,都已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日军在华所设慰安所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由日军自己设立管理的慰安所,其二是日侨娼业主随军所设的慰安所,随着日军部队的移动而移动,其中多为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它所存在的目的,是商人谋利,而且在整个日军慰安妇中所占比例不可能太大。我们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其三是日军强迫汉奸组织或伪政府出面设立的慰安所。
日军自己设立管理的慰安所,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的有计划地设立的,以日本和朝鲜慰安妇为主;另一种是日军前线部队根据日本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的策划和授意而有意设置的,以中国慰安妇为主。(注:参见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94页。)很显然, 在这后一种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大部分是日军沿途掳掠拐骗到的中国青年妇女或女战俘,被强迫充当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它所具有的强迫性是无法遮掩的。
我们这些年的资料搜集和调查,为证实日军以各种残酷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城镇中,日军大规模地掳掠青年妇女在当地或劫往别处,充当日军慰安妇,这是日军强征慰安妇之犯罪中一种较为典型的手段。日军攻陷南京时,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同时对中国妇女同胞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奸淫。在日军进城之初的几个星期内,强奸案多达数万起,而且,其中许多妇女在经过日军的疯狂蹂躏后又被残酷地杀害。不仅如此,日军还从南京掳掠走大批中国青年妇女到各地充当日军慰安妇。其中有320人被秘密运往东北充当了慰安妇。 这些被日军强行掳掠至异地他乡的妇女,或为日军践踏至残,或为日军残酷杀害,其遭遇惨绝人寰。当年受害人中的一位幸存者,向调查者控诉了自己遭到日军奸污和随同众多姐妹被劫往东北的亲身经历。(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523页。)这岂不正是慰安妇之具有强迫性的有力的证明!
在《拉贝日记》(注:《拉贝日记》中文版于1997年8 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本根据拉贝生前编辑整理的原稿本复印件完整译出,忠实于原文。目前日本国内也有一个日文版的拉贝日记,书名为《南京的真实》,是据德人维克多的编纂本翻译。译者是平野卿子, 1997 年10月讲谈社第一次印刷,同年11月第三次印刷。日文本的拉贝日记被删节了很多,许多记载有日军当时在南京的严重暴行的附件和拉贝等国际安全区负责人给日本军方的交涉文书或抗议书尽被删除。但这似乎又不是译者出于体例上的考虑。比如1938年2月13日《拉贝日记》附件中, 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同年1月30 日《字林西报》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出面“辟谣”并表示怀疑,声称:“无论您到哪里去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日文版中就将这一段被拉贝题作是《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的附件译出。然而对于紧随这一附件后面的拉贝本人的评论:“从《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全世界这时已获悉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残酷暴行。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日文版却又避而没有译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文本的《南京的真实》及其译者,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拉贝日记》的原貌进行了否曲,意图使谬种流传,借以掩盖日军当年在南京的暴行。这也正是某些日本人常用的伎俩。不过,这种做法确实过于拙劣了。)中,同样也有日军攻占南京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记载。在1937年12月25日条下,拉贝这样写道:“日本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20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去作苦力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注:〔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中文版)第2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此条记载也见于日文本的《南京的真实》,第144页,1997年11月讲谈社第3次印刷。)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拉贝写道:“现在日本人想到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注:〔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中文版,第285页; 日文本第147页。)
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南京城破兵溃之时,无数难民皆成日军的砧上之肉,在日本最高当局授意和纵容下的日本军方,手握着滴血的战刀,从难民群中挑选青年妇女,劫往其慰安所,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哪里又有反抗的力量和机会呢?如果硬要说当年日军在对南京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后,再从难民中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不具有强迫性,又岂不是一些人有意在对历史进行歪曲吗?
成立专门的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诱骗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日军征集中国慰安妇的另一重要手段。据日本东京《时报》1998年8月18 日报道:原侵华日军特务永富博道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承认,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至少有20名中国人被他活活杀死,大批的中国妇女被押送到由他一手筹建的6个慰安所内, 强迫她们充当日军慰安妇。他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亲自负责设置了6个慰安所。在沿途, 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注:参见《参考消息》1998年8月19日第8版。)这是一个日军当事人的回忆,他的回忆应该更具有说服力。在他的话语中,诱拐与掳掠是同一含义,其所具有的强迫性同样是无法掩盖的。
同样,1942年日本以香港“合记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广州等地诱拐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也是日军这一手段的典型案例。这一年,日军以招收女工为名,先后拐骗300多名青年妇女, 押至海南石碌,强迫她们进入了慰安所充当慰安妇。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石碌慰安所地处今天石碌河南派出所和县供销贸易公司所在地,建筑面积约300 多米,房屋两面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这些小房间本世纪80年代才被拆除。当时四周设有铁丝网,日军日夜巡逻,逃跑者捉回后,或活活打死,或剥光衣服吊起毒打及施以各种酷刑。慰安妇每人每天只给米饭三两或几块蕃薯,每天却要接待日本官兵至少8次,休息日则多达24 人次。至抗战胜利时,300多名妇女,被日军折磨致死达200多人。(注:《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第748—750页,转引自《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495页。)很明显,所谓的“合记公司”,是日军所设立的拐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专门机构。在这里,中国受难妇女不仅被强迫做了日军的慰安妇,更为悲惨的是她们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摧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尊严,生活生命也绝无丝毫保障,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仅此一例中,300多人被日军迫害至死者多达200多人,这本身已足以说明日军对中国慰安妇的野蛮而无人性的摧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战场上不幸被俘的中国女军人,同样遭到日军官兵无情蹂躏,成为日军慰安妇的重要来源。在徐州会战中,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旅第三旅团第六联队长小男一雄,将被俘的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带往树林深处(据现在的调查,即今江苏省丰县和沛县之间的昭阳湖),“秘密成立随军妓院,供士兵与军官淫乱”。此事前后因果,有1938年6月7日《日本军方的调查报告》为佐证。(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第507页。)根据相关国际法之规定, 对战俘应有适当安置。那么日军把被其俘获的中国女军人强行当做供其官兵发泄兽欲的工具,不仅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同时也更是日军在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有力证明。
在其占领区的乡村,日军更是随时随地随意地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其随军慰安妇,这却又恰是日军征集中国慰安妇最为普遍的方式和手段。1940年4月10日, 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第二十三中队袭击河南新乡王各庄,屠杀乡民487人,拘留213人,烧毁民房106户,掳掠当地妇女82 人充当随军慰安妇。其中有9人不堪其辱,愤而自杀,另有9人在三天之内即被日军蹂躏致死。其余64人皆被押往山西大同慰安营,直到抗战胜利才得幸免(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第523—529页。);在海南乐东县黄流机场,日军也设立了慰安所,名曰“军中乐园”,有房两间,其一专供空军军官玩乐,内有慰安妇5人;另一供日军士兵玩乐, 内有慰安妇16人。至日本投降时,这21名慰安妇,幸存者仅有4人。 其中有一名叫吴惠蓉,她控诉说:自己16岁时被抓来, 同时被抓的有100人左右,到黄流仅余40多人,其中一部分留在黄流据点,她与其他一些姐妹则被挑选到黄流机场“军官乐园”中充当日军慰安妇。(注:《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第508页。 )日军在海南乌牙峒(今陵水祖关镇)砧板营油棕坡建立兵营时,勒令各村选送20多名黎族妇女去日本军营,充当不固定的慰安妇,这些黎族妇女白天在军营中替日军挑水煮饭,夜间则成为日军官兵奸淫泄欲的性奴隶。据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陈金妹老人控诉,她还记得起部分受害姐妹的名字:卓亚扁、陈亚妹、陈进女、卓理女、陈亚曾、卓亚天、陈毛姩、卓石理、卓毛夫、胡有英、卓亚广、陈亚合、卓毛定等。(注:《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第509—510页。)
此上所列举的,仅是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各种手段和暴行事实的极少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无耻手段和罪恶事实,无不充满着日军血腥的暴行和中国受难妇女悲惨至极的苦难,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迫和摧残,又岂是短短一文所能诉说净尽!又岂是只言片语即能否认得了的!
至于由日军命令汉奸组织或强迫沦陷区当局组织设立的慰安所,其中的慰安妇也都是被强征的中国妇女。即便是这一种由汉奸政府出面组织和征集的慰安所,日本军方也不可逃脱其罪责,而其本身所具的强迫性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很简单:在沦陷区的伪政权和大大小小的汉奸组织,皆为日军的爪牙而已,他们的一切所为,皆为仰承日军意旨,听命于侵华日军当局。而侵华日军当局却又正是直接受日本政府的派遣而侵略中国的,侵华日军是日本国家的军队,其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一切战争罪行,其责任最终只能由日本国家来承担。因此,侵华日军当局及其之所受命的日本政府当局和天皇本人,才是一切日军在华暴行的最终的罪魁祸首,永世都不可能逃脱其对中国人民所犯暴行的战争罪责。
在慰安妇的征集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暴行和压榨,则更是不一而足。由此所引发起的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连带性迫害,其程度和数量更是无法估计的。例:
1945年7月3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特务科关于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征中国妇女充作军妓之社会情报》中所载:“查王士海领导下之别动队(即天津防卫司令部慰安所),迩来办理征集妓女献纳于盟邦驻津部队。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为期。于征集之际,流弊百出,凡被征者,能出以相当代价者,亦可收回;而近更变本加厉,在南市一带有良家妇女被强迫征发者之情事,致社会舆论哗然,一般良民惴惴不安。”(注:《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近代史资料》总94号。)
而被征集的中国妇女从慰安所的伺机逃亡,更是慰安妇之具有强迫性的最有力的证明。据我们前文所提到的10件档案所载,1944年6月8日,天津防卫司令中命令天津市警察局强征86名中国妇女,由防卫司令部派遣中井进曹长押送河南郾城。但在短短的二十天内, 除了生病遣返8名外,郾城仅余36人,其余42人据称全部逃亡(注:《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近代史资料》总94号。)——当然,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42名“逃亡”的中国妇女,并非是“逃亡”而是“失踪”,其大部分被当地日军蹂躏致死了——逃亡是以强制性为其存在前提的,如果慰安妇不具有强制性,可以来去自由,则所谓的“逃亡”也即无从谈起。
从日军征集中国慰安妇的各种手段,日军对中国慰安妇的残酷迫害和肆意屠戮,以至中国慰安妇的伺机逃亡,清楚地说明,在慰安妇的征集和从军过程中,充满着日军血腥的暴力,具有着十分明显的强制性。这种事实,不是由任何狡辩所能掩盖得了的。
三 战争罪没有法定时效限制,日本国家无从推卸其战争罪责
在前文,我们已经通过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和各种旁证资料,认定侵华期间日军在华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其随军慰安妇的行为,是在当时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的蓄意策划和安排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在侵华日本军方的直接插手操纵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犯罪和军方犯罪,是日本国家对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国际性的犯罪。在其犯罪过程中,作为犯罪者的日军对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慰安妇所采取的诱骗、劫掳、抓捕、强征、残杀等等手段,也都证明其具有无可否认的强制性。
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残酷罪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手段和借口,搪塞推卸,淡化否认,表现出了极不诚恳的、无视历史事实的态度。对于慰安妇问题,也正如同劳工、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一样,日本政府一直坚持“不能承认国家赔偿”的主张。换言之,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所犯的残酷暴行,日本政府不承认日本国家所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进而并以时效、国际法主体等种种借口,拒不履行日本国家随其战争罪责而连带产生的对受害国的受害人民的战争损害赔偿义务。
然而,是罪恶终究逃脱不了审判。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也永远铭刻于中国人民的记忆中。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抗战胜利后,中国广大的受害人民,未能及时向日本侵略者清算其战争罪责,行使受害索赔权力。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时,中国政府出于宽宏博大的心怀和建立中日永久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中国作为受害国向日本进行战争索赔的权力。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日本国家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同时也无碍于至今尚幸存人间的当年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向日本国家行使索赔的权利;同样,这也绝不是日本国家推卸战争罪责的借口。
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作为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它伴随着日本国家对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严重的战争罪的同时而发生,对其总体性质的认定, 在国际法学界也有一致的看法。 1996年,受联合国委托进行“慰安妇”问题调查的法学家拉迪克·克马拉斯瓦密指出:根据国际法,慰安妇是日本在战争时期犯下的有组织强奸及奴隶制的罪行(注:转引自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89页。); 据日本《读卖新闻》1998年8月8日报道,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人麦克杜格尔于此前不久草拟了一项题为《战时有组织的强暴的性奴役》的报告书,认为二战期间日军设置随军慰安妇是一项反人类的罪行,建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和日本政府确立对造成这一事态的责任人和有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并要求日本政府设置行政基金,以便对受害人及其遗属提供赔偿。接着,《读卖新闻》也评论说:该报告书的内容与日本政府的“不能承认国家赔偿”的主张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对于日本政府一再坚持的日本国家不承担战争赔偿责任的主张,拒绝承担日本侵华战争罪责,拒绝承担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在1998年8月24 日于北京举行的以“战争损害民间索赔问题”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日法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法学界代表严正指出:日本政府援引1941年2月2日日本大审院的判例,认为日本军人即使从事了犯罪行为,受害者也不能向日本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这个判例是不正确的,因为日本军人从事了犯罪行为,即使受害者是日本公民,他也有权向日本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因为军队是日本国家的军队,这是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同时,由于国家的国际法责任高于国内司法判例所确定的责任。因此,这个判例根本不能适用于日本国家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它根本不适用于被侵略国家的战争受害者要求日本国家进行赔偿的情况。同时,二战以后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也表明,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要承担其战争罪责——政治上的被占领、被管制和对战争受害国家和人民的赔偿责任;战争罪犯个人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当年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和日本国首要战争罪犯的判决,不能免除德国和日本国家被管制和被占领的政治责任以及赔偿损害的责任。这种国际法理论也反映在1998年7 月17 日联合国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之中, 该规约之第25条第4款规定:本规约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应负的责任。(注:参见《中日第三届法学国际研讨会——战争损害民间索赔问题·会议纪要》(未刊稿)。)
因此,当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战后其首要战争罪犯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制裁,只是作为战犯的个人承担了他本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这丝毫不能减轻或开脱日本国家所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战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国家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这正是以日本国家存在着战争罪责和战争赔偿责任为其前提的。否则,也就谈不到中国对日本国家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了。这一点,也可反证出日本国家无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另一个经常为日本政府引以为据而推脱战争罪责的借口是责任时效问题。日本政府根据《日本民法》第724 条规定:“因不法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从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在知晓损害以及加害人的情况之时起,经过三年期间之后,其时效将丧失;从不法行为发生之时起经过二十年之后,其时效亦同。”认为中国平民在日军侵华期间因被强征为慰安妇、劳工、细菌实验对象、屠杀对象等所构成的损害,向日本法院提出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已经丧失时效,因而日本国家不再有履行赔偿的义务,力图藉此逃遁其所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人民所具备的对日本国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由于日本国家对中国所犯下的战争罪以及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和日军所犯的反人类罪而产生的,并非由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因而不能适用于民法上的时效规定。对此,国际法上有着明确的规定:鉴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上最严重的罪行,它给受害国和受害国的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所以,联合国大会1968年11月26日通过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危机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论何时所犯,均不适用于法定时效限制。1970年联合国大会第25届会议又通过决议,要求非缔约国不得进行任何与此公约的主要目的相违背的行动。1998年7月17 日联合国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9条也明确规定,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不适用任何时效。(注:参见林欣:《中日之间战争损害民间索赔的几个法律问题》,及《第三届中日法学国际研讨会——战争损害民间索赔问题·会议纪要》。谨按:笔者以前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国际法问题关注得较少,同时由于没有能够查阅足够的国际法资料,因而不能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林欣研究员的《中日之间战争损害民间索赔的几个法律问题》一文及《第三届中日法学国际研讨会——战争损害民间索赔问题·会议纪要》,对日本国家在侵华期间所犯的战争罪责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借以希望引起学术界对相关理论和国际法原则的关注和运用,以推动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进展。同时在此对林欣先生个人及第三届中日法学国际研讨会表示感谢。)
也就是说,不论何时,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铁的事实永载于人类历史,作为罪恶则永远不可抹煞;日本国家不论是否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危机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缔约国,都应该履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遵守该公约的规定;日本国家和日本政府,无论何时都得承担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一切搪塞都是无力的,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世界舆论更激烈的谴责。同样,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作为日本国家当年犯下战争罪的同时所犯下的一项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也无任何时效可言,无论何时,日本国家都要对此承担其无可推卸的战争罪责。日本政府代表其国家,认真地正视历史、反省历史,严肃地向当年受其侵略的国家及其国民尤其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道歉认罪,并对向其提出战争损害索赔要求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履行赔偿的责任,是其基于国际法原则所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
我们希望,国内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和海内外的一切有识之士、正直之士,对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对资料进行深入的发掘,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那些别有用心者所制造的谎言进行有力的驳斥,对日本当年对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所犯暴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半个世纪前我受难同胞的沉冤得以昭示天下。
1997年,在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之际,本人应国内一家刊物之约,曾经写了一篇《世纪暴行——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我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当年南京城内那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惨象,是否已经随着今天一个新南京的崛起而变得苍白?当年侵略者用手中的屠刀给我们留下的那刻骨铭心的创痛,在经过60年时光的冲刷后,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是否已经变得淡漠?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问:我们是否真的忘记了这段血腥的历史,当年日军用侵略战争,用大屠杀,用七三一活体实验,用毒气战,用细菌战,用蹂躏我们的同胞姐妹等等残酷至极的手段,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空前屈辱,真的就如现在日本国内那些否认历史的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人民的心灵里被淡化,在我们民族有记忆里被遗忘吗?同样,日本在其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而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能否真诚地正视历史,反省其过去对亚洲包括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我们就有愧于做为一名炎黄的子孙;不能使这段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使我们受难同胞的冤屈伸张于今日,我们就愧对于3500万死难的英灵。作为日本,不能对亚洲人民表现出诚恳的反省历史、正视历史的态度和决心,那么,它将永远无法建立起与亚洲各国间真正友好的关系,同样也将永远无法获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