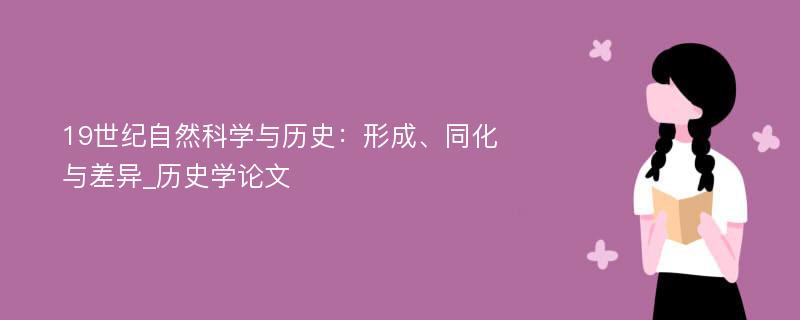
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自然科学论文,化与论文,区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2-0005-07
历史学作为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性质如何界定?长期以来,特别是历史研究职业化以来,就一直是个纷纭难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是想把历史文学化,就是想把历史哲学化,抑或想把历史艺术化;其中流行最广、影响至今的做法,是力图把历史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因此,澄清“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关系,就成为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一把钥匙。本文将集中讨论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同化作用、二者研究对象及方法的差异,以展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基本面相。
一、19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同化
“近代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她的长姊,即自然科学方法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1](P319)这一现象不仅揭示出历史学与科学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更点明了近代的历史学就是由自然科学直接塑造的这一事实。近代的自然科学、特别是19世纪的自然科学,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了历史学:
1.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必须是严格实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确立事实。“中世纪哲学和神学一直认为思想是可信的权威。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18世纪大批大批的科学家胜利地认定可信的权威是‘事实’,而不是意见。历史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重要性。党派偏见、政治或宗教成见、英雄崇拜、野心、民族情绪、种族或民族自傲诱使历史家歪曲或隐藏他们手边的实况。他们并不像科学家那样尊重事实。当真实情况对他不利时,有些历史家甚至于低下到想象出他们的‘事实’。他们不这样犯罪时,就用别的方式犯罪:他们往往醉心于推理式的猜测,或略去重要的证据,因为这种证据会打翻他原来的先入之见。这是……18世纪史学思想的一个污点。”[2](P605-606)在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开始将“事实”置于首要地位。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作了这样的描述:“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在19世纪30年代,当朗克很正当地抗议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的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些有魔力的词句的:‘如实地说明历史’。”[3](P3)力主把历史当作科学,因而“崇拜事实”,进而遵守“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之中得出结论”[3](P3)的工作程序,是19世纪历史学的基本特征。
2.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必须在“确定事实”之后,“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以发现规律。这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1](P89)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实证主义可定义为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哲学”。而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就是在实证主义影响之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这一历史学“服从着实证主义精神”。“根据实证主义的精神,确定事实仅仅是全过程的第一阶段,它的第二阶段便是发现规律。[1](P190)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当年就认定,应该“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比比皆是的法则的科学理论照原样引进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中,“这样做就有可能发现制约人类社会的‘定而不移的法则’”。孔德及其门徒们“相信对社会‘法则’的了解会使国家不但掌握历史方向,并能预知历史进程”。总之,“实证主义者的目的,是想发现一套解释历史的有效的假说或法则,就像牛顿和其他一些人为自然科学发现的那样”。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历史的最后解释是什么,或者更朴实一点说,决定社会事件的那些力量是什么,这些事件是按什么法则活动的?”[2](P609-610)生活在19世纪“唯科学主义”高潮中的恩格斯声称发现了这些所谓“定而不移的法则”:“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所谓的“剩余价值学说”。[4](P574)而且,不仅马克思、孔德在这样做,“19世纪自然科学获得空前伟大的成功,这就使得许多历史理论像要在历史学中追求一种像是在物理学中那样的因果律的努力,一时蔚成风气”。由于这些发现,人们认为,社会历史研究从此步入了科学化阶段。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的欧洲,历史编纂学只接受了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即收集一切所能到手的事实,而排斥了第二部分,即把寻求法则的主张悄悄抛到一边,认为发现和陈述事实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够了。[1](P194)这就是前边说的,19世纪仅是个“尊重事实”和“崇拜事实”的“伟大时代”。而“尊重事实”本身在许多人看来就已经很科学了。
3.19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使历史家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事物根源的重要性”。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科学的主要胜利是通过追查事物的根源取得的”。例如,“在物理结构方面,追查到分子和原子;在动物生命方面,追查到神经细胞、原形质或任何最简单最原始的东西”。影响所及,史学家“在近代史方面,也作出完全相同的努力。和18世纪比较肤浅的历史学派比较起来,最明显的努力莫过于作出决定追查各种制度的起点与原意。对原先被传说和神话占领的那些古老岁月都进行了耐心的研究”。[2](P607-608)这种对社会制度“起源”的追溯,当然主要应归功于“进化论”的促进。“自从达尔文以来,任何历史家都不能忽视历史发展上的进化因素。……这种概念使历史学者对各种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认识到现在的一切都深深植根于过去,而使他们尊重传统。”[2](P624)而且,“进化论”还导致了整个19世纪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而更深刻地塑造了这一世纪的历史观念。“所有近代思想和科学用的都是历史方法……博物学一直都是对现存物种的分类,现在人们以同样的力量研究物种的起源了。地质学已不仅仅研究地壳,而是要考察地壳如何形成的问题了。……运用历史方法,是我们的近代思想和过去所有时代的思想区别开来的主要特点;这种方法和进化这个概念联系密切,进化……指的是一个过程,不只是事物现在的情况,还有它们是怎样形成这个样子的。”[2](P629-630)
4.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方法,真理就会从中产生,而且准确无误”。因此,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也是“可以向完全正确的知识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简直和一门自然科学同样明确”,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也能做到“就像人们观察昆虫蜕变那样”。[2](P623,613)导致历史学家产生上述自信的“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由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别是兰克发明的“语言学考据方法”。这一方法有以下特征:历史可被切割为无数细微的事实,每件事实都要单独予以考虑;[1](P194)目击者的叙述和原始的文献材料最为权威,“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5](P179,193)“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被当作一个证人,除非他的诚实能得到验证,否则是不能信任的”;[6](P354)等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兰克提出的“不偏不倚的教诫”了。[6](P355)
“不偏不倚的教诫”主要源于下面这一实证主义观念:每件事实不仅要被思考为“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像是它们被人称为的)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1](P194)譬如,兰克为了写出“无色彩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和“不加臧否”、不作“判断”的历史,“决心有效地压抑自己身上的诗人、爱国者、宗教和政治党徒”的气质和倾向,“不支持任何事业,并使自己从书本中完全摆脱出来,且决不写作会满足自己感情或宣示个人信念的任何东西”。因为在兰克心目中,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事业”、“神圣的事业,因为它带来真理和荣誉”,“不偏不倚就是力量的源泉”。[6](P357,356)“历史学以最高限度的缄默,以大量的自我克制,以及时的和审慎的超然态度,以对生杀问题的保密而可以超越于争议之上,并造就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法庭,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6](P355-356)而且,“当他控制自己不下判断时,那对他来说乃是一场道德上的胜利,这时他表明(他描述的)双方都可以畅所欲言,而其余一切则留待给天意”。[6](P358)据说,兰克还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愿望:“为了使自己成为事物的纯粹镜子,以便观看事件实际发生的本来面目,他愿意使自己的自我泯没。[7](P237)兰克就这样确立了一种“以旁观者不偏不倚的态度编写历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最高境界是:“他从不让我们知道他对任何事情的看法,而只让我们知道他面前的事情”;“使历史学从历史学家那里独立出来”。[6](P349,344)达致这一境界,历史学就成为“客观的”历史学,也就是成为一门“和数学一样纯的科学”了。[2](P624)
总之,“客观主义”的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历史学,看来是以下面三点基本认识为基础的:(1)历史是在历史学家头脑之外存在的一个或一系列的事件;(2)历史学家可以知道这些事实,并一如其实际发生的那样客观地描述它们;(3)历史学家可以排除任何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等等利害的考虑。[8](P683-684)一句话,历史学家可以像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那样面对和处理它的研究对象。再进一步地说,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即使有差异,也微不足道。其实,它们之间的距离很大,非常值得分析。
二、史学对象和事实与科学对象和事实之间的差别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形式。这种不同当然有许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比较主要,一是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二是由此差异所导致的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
1.自然科学可以直接面对和研究确定的、能感知到的事实,而历史研究无法面对“过去”本身。这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
科学的对象可以直接观察。史学的对象则没有可能和条件现场感受。无论是可以直观的花鸟虫鱼,还是在实验室里虚拟的自然现象,人类都可以借助所谓的“哈勃望远镜”、显微镜等技术手段和中介工具,予以直接观察。但是,凡是成为或可称作“历史”的东西,均是在事实上已经发生过且已经消失了东西。这样,“历史”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昭示的是个悖论:“历史”在本质上意味着“真相”和“事实”,但这个作为“真相”和“事实”的东西又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历史事实的独特性在于它与当下事实是不同的,当下事实具有历史事实所不具备的某种在场的性质,而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是当下缺席的。”[9](P43)这种“不在场”的“当下缺席”的“历史”,只有借助于自然科学那样的所谓的“观察报告”才能察知,只有借助于通常所说的“文献”,后人才能感知过去的“社会”、“事件”和“人物”。前边说过,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能做到就像昆虫专家“观察昆虫蜕变那样”。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实际上是幻觉。不在场的历史怎能像昆虫一样供你拿着放大镜反复观察?花鸟虫鱼可以采集作为“标本”,但以往的哪一页可以原样保存作为“标本”?癌症可以切片观察,而历史事件、革命、危机却无法照此来切片观察。
兰克的理想是书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即“如实直书”,但如上所说,作为“历史”的“实在”已经“缺席”,而永远“缺席”。“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又如何能写得出来呢?当兰克说“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的时候,在他心目中大概有一个明确的预设:历史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始终在那里存在着、矗立着,时刻等待着人们去复查、去核实、去实验,不然的话,如何去“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呢?事实上,“实在”或者说作为历史研究真正对象的“历史”,早已灰飞烟灭,遗留下来的仅仅是些“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保存在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之中。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轰轰烈烈的“秦”王朝,这没有一点问题,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虚无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但另一个事实也是确凿的:这个一度存在过的“秦”王朝,无法像“秦时明月”一样仍在那里“实在”着。“秦”王朝现在只存在于《史记》和《汉书》等典籍之中,它在当下的存在也已不可能离开《史记》和《汉书》。17世纪的牛顿曾经对宇宙天体运行秩序作出过自己的描述,即使是四百年过去了,当年的天体仍然照旧运行着,四千年后仍会如此。这就是说,“秦”不可能像处于同一秩序中的天体可以离开牛顿的描述而存在。既然“实在”不在了,怎样“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呢?又有谁能充当这种历史真假的参照与见证呢?仅仅在近几十年间,学术界不知道出版过多少部“秦始皇传”、“刘邦传”、“唐太宗传”、“明太祖传”,同一个传主在不同的传记作者笔下形象差别很大,哪一部传记更像传主、更符合传主的本来面目呢?老实说,我们缺少最终的“参照”与“见证”。而自然科学几乎与此完全不同。一句话,“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确实只是一种“高贵的梦”。但我们当然又绝不能放弃这个“梦想”
2.科学的对象仅仅是“现象”,而且永远是“现象”,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却并不仅仅是“现象”,何况这一领域的现象本身也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东西。
自然界仅有外表,人类社会则在外表之下,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一位哲人所说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由此造成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根本不同,即“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划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0](P243-244)另外,人们参与历史创造的“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10](P244)总之,“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10](P245)这一点对理解科学的对象与史学的对象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的确,“自然现象”背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追查,而“历史现象”背后却有挖掘不尽的思想、动机、考虑、构思、阴谋、算计等等。一场地震可以使几十万人丧生,但你无话可说,亦无可分析;一场战争、一次战役也可以死几十万人,但这就有大量的文章可做了,如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部书,就是这种专门研究一场战争和一次战役的述作。1976年7月的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市,死亡28万人,有什么可供推敲的?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的被毁,却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而且可能会成为永远的研究对象。一个人被天上掉下来的一块殒石砸死,医生仅仅根据外部现象即可判断致死的原因,但凯撒被布鲁图斯刺死,史家却不能仅仅断言布鲁图斯是刺客就完事,他必须追究这一事件背后的一系列阴谋和这一事件的后果。因此,柯林武德告诉我们: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可以由发现一个事件的外部开始,但决不能在那里结束,他必须经常牢记事件就是行动”、行动由思想支配这一事实。“就自然界来说,一个事件并不发生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因为“自然界的事件都是单纯的事件”,“但历史事件却决不是单纯的现象,决不是单纯被观赏的景观,而是这样的事物: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他举例说,当一个科学家问道:“为什么那张石蕊试纸变成了粉红色?”他的意思是指“石蕊试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了粉红色?”当一位历史学家问道:“为什么布鲁图斯刺死了凯撒?”他的意思是指“布鲁图斯在想着什么,使得他决心去刺死凯撒?”这个事件的原因,在历史学家看来,“指的是其行动产生了这一事件的那个人的心灵中的思想;而这并不是这一事件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是事件本身的内部”。[1](P301-302)
因此,柯林武德告诉他的读者:一个自然过程仅仅是各种事件的过程,而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1](P302-303)仅是根据历史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的过程这一事实即断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自然稍嫌武断,但他由此指出的历史事实与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知识形式都基于事实,但作为两者对象的事实的性质却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心灵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11](P10)历史事实当然是心灵事实。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由于它们所依据的“事实”的性质的差异而拉开了距离。而且,这种距离还决定了两者基本研究方式方法的不同。
三、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异同
爱因斯坦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意见: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的或者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是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使用直觉是危险的,但在所有各种历史工作中却都是必需的。[12](P622)把同一个历史事件剖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两种,而且把两者对立起来,当然有问题。但我们能否尝试着把两者统一起来即能否写出以“有文献证明”为基础的“内部的或者直觉的历史”呢?应该说,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如此的。既然历史的对象与科学的对象,历史的事实与科学的事实之间有如此大差异,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研究它们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如同上文所说,历史是人们自己在自觉或有意识状态下的活动。但历史的创造者又早已消逝。后代的研究者如何把握这种“自觉”状态或“有意识”状态?看来,唯有设身处地的“体验”和“理解”,才可能是通向历史“内部”的管道。
1.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历史学接近和进入历史本体的基本方法基本途径应该是“体验”和“理解”。
无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多么复杂,它们均外在于研究主体,这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可以外在于研究主体,那就意味着主体可以仅以观察者或旁观者的身份来对待它的研究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宇宙天体还是花鸟虫鱼,对人来说,它们均属外部自然现象。何况,这种外部自然现象不仅可以“观察”,还可以在人为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通常所谓的“观察”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感受外部的各种刺激,形成对周围事物的印象”,而“实验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利用科学仪器、设备,人为控制或模拟自然现象,使自然过程或生产过程以纯粹的典型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便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一种方法”。[13](P37-39)“观察挑选自然提供的东西,而实验则从自然那里把握它想把握的东西。”[14](P115)作为科学方法的“观察”和“实验”看来均具有下列特点:第一,它们都可以直接面对或作用于对象本身;第二,对象就是对象、就是“实验”材料,与研究主体不发生任何情感上或精神上的联系,科学家完全可以做到“价值中立”、“客观公正”。历史研究的方法则与此不同。
这种不同,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历史所研究的是历史学家也置身其中的人类自己的活动。历史认识的实质是人类自我认识与反思的形式之一。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把自己对象化在时间隧道另一端的自我,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来认识历史,史学的对象永远也不可能外在于自己。所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在这里不适用。其次,“认识你自己”,是历史认识由以进行的前提。尽管时间与空间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类的活动造成很大影响,但“自有史时代(historic time)以来,人的变化极为有限,人性的共通性,大致为中外学者所承认。史学家能够隐约窥见历史真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15](P206)对这一点,王夫之看得特别清楚:“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16](卷二十)今人之所以能认识和理解古人,端在于古今人性是相通的,全部历史研究的基础实际上都奠立在这个隐含的假定之上。其三,正因为古今人性是相通的,所以今人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古人,进入古人心灵之中,乃至“重演他们的思想”。这就是钱锺书说的“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17](P166)也是古人所谓“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16](卷二十)“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18](“史论”篇)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更重要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生命与生命之间,只有通过“体验”和“理解”才能对流。历史研究的深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家对人性体验的深度。“自然需要给予解释说明,对人则必须去理解”。[19](P103)“理解”,是通向他人、也是通向古人的桥梁。“历史作为过去,与我们的时代之间横着一个时空上的距离,征服这个距离……沟通建立起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在心理、思想、价值等方面的联系”,[19](P110)这个任务,看来只有由“理解”来完成。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心理学家所能做到的一样。”[20](P534)而且,这种理解也可以是直接的。如:教授理解听他课的学生的举止;主人可以理解来赴宴的某些客人的拘谨;家长可以一下子就能理解初恋中的孩子的某些异常表现;后人也可以理解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面对彭德怀指名道姓批评时的感受与反应;等等。总之,“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社会行为具有一种可以理解的结构”,“行为和目的、一个人的行为与另一人的行为之间的某些可理解的关系常常可以立刻被感知”。[20](P533)人们的行为之间的这种共通性质给历史理解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但人类行为的这种可理解性丝毫也不意味着历史举家仅凭直觉就能理解这些行为,“理解丝毫不是一种神秘的才能,一种理智以外的或高于理智、高于自然科学方法的能力。”[20](P534)恰恰相反,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各种书籍文件才能逐渐把这些行为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立即对他人的行为和著作作出解释,但不经研究不取得证据,我们无法断定哪些理解与解释才是正确与准确的。“拿证据来”,历史理解必须被置于证据的限制之下。
2.自然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概括出某种普遍的而且是确定不移的自然规律,所以,它的又一个基本方法是逻辑推理和本质抽象,最后则归纳为用数字和公式来把握自然。历史研究的终极梦想是依据有限的材料“还原”或“再现”早已消失了的特定人群、事件、故事……所以,它的又一个基本方法是想象推理,理想的境界则是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化了的往事。
“历史学家必须运用他的想象,这是常识。”[1](P336)为什么?因为“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21](P431)所以,“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22]资料告诉后人:有一天凯撒在罗马,又有一天在高卢,而关于他从这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却没有资料说明。“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白,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于是我们不得不想象凯撒曾经从罗马旅行到高卢。这就如同我们眺望大海,看见有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已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它从前一个地方到五分钟后的这个地方,其间所经历的各个中间位置,只能靠想象来确定。历史思维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不“构造历史的系统”便罢,一“构造历史的系统”,就不得不借助历史的想象。前人的陈述总是残缺不全,我们所欲构成的历史系统又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贯性,其间待填补之处当然就是历史想象的空间。
“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成叙述既生动又感人。”[23](P260)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这句话说出了多数人对“想象”功用的认定:想象能使历史叙述生动感人。柯林武德则认为,这种认定“低估了历史想象力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历史想象力严格说来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1](P273)使历史叙述生动感人只是“装饰性”的、技术性的,而所谓“结构性”的,则是指“历史的系统”的“构造”本身即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关于他的对象的画面,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用想象构造的网。[1](P275)在用想象来构造这种“网”时,柯氏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都把构造出一幅图画当作是自己的事业”。“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小说家只有单纯的一项任务: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而且,“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也就是指它能诉之于证据来加以证明”。[1](P279)进一步的说,就是它必须受到证据的限制。而所谓证据,不过是“靠批判的思想来获得的”某些“固定点”,历史学家用想象构造的网就在这些“固定点”之间展开,如果这些“点”出现得足够频繁,那就意味着可靠的证据就越多,由历史学家所构造的画面受到的约束就越多,那它也就越真实。对于“证据”与“想象”之间的复杂或互动关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一书,可能提供了最好的诠释。
《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充满了考证,而且不少考证“发三百年来未发之覆”。但陈寅恪研究专家余英时认为,这部大书的主要贡献和作者的基本意向却不在这些细节上。在余氏看来,整体地说,《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据虽精,但这些考据的结果只不过建立了许多不易撼动的定点。由于点与点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又由点形成许多线,再进一步则因线的交叉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网络。考据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换一个比喻,我们不妨说考据足以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更重要的,楼宇中人一个个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而活动。陈寅恪之能重建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在余英时看来,则不是依靠考据的功夫。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余氏说: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力并不是始于或仅见于《别传》。事实上他在中世纪史研究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由于想象力的运用。但也许因为受了“乾嘉考据之旧规”的拘束,他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像在《别传》那样驰骋奔放过。通过丰富的想象,他使明清的“兴亡遗事”复活了,其中每一个重要的主角都好像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以至虚荣、妒忌、轻薄、负心等等心理状态,我们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到。余英时说:“陈寅恪运用历史想象力重建明情兴亡的故事在《别传》中到处可见,而且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他所着力叙述的若干个历史故事,“都写得很生动,但最关键的地方都不是考证所能为力的,而是依靠想象力的飞跃”。[24](P370-373)想象”之于历史研究,其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历史叙述中,“想象”的功能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基础性的、本体性的。不少西方杰出历史学家在谈论自己的治学甘苦和经验时,也都曾根据亲身感受道及此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布克哈特在一封信中说:“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7](P25)《罗马史》一书的作者是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蒙森同时也是《拉丁铭文集成》和《货币史》两书的作者,而后两部枯燥的书根本就不是一位艺术家工作的结果。“但是当蒙森应邀就职柏林大学校长并作他的就职演讲时,他却说历史学家或许更多的是艺术家而不是学者,并以此来说明他关于历史方法的理想。”[7](P258)人们承认:“在探索真理方面,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受制于同样严格的规划。他必须利用一切经验调查的方法,必须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并且比较和批判他的一切原始资料。他不能遗忘或忽视任何重要的事实。然而,最终的决定性的步骤总是一种创造性想象力的活动”,是“对实在的真相的想象力”。“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7](P259)
收稿日期:2003-12-21
标签:历史学论文; 科学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历史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