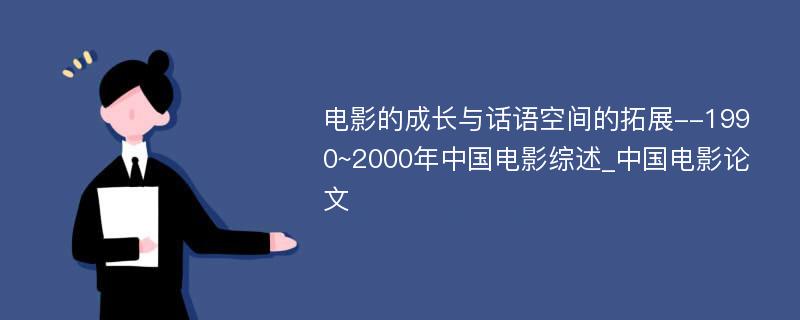
电影的成长与话语空间的拓示——1990—2000年中国电影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话语论文,国电论文,电影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2000年的中国电影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在整个社会生活迅猛变化的语境中,努力培养以至置换、位移主体,不断拓展话语空间来显示活力。
时间川流中的电影:解构与建构
文革结束,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幕布。伴随着焦虑、沉思与展望,已获新生的电影家们不断求索,努力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确立主体位置,实现和释放个性创造力,逐渐形成了多元竞赛而又相对整一化、具有清晰的时间印迹的历史发展格局。
80年代电影作为文革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产物,其发展里程都和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紧密关联。在这一发展阶段,沈浮、吴永刚、汤晓丹、桑弧、水华、成荫、王炎、谢晋、谢铁骊、白沉、于彦夫、李俊等老一辈从禁锢状态走出来的电影家们,调整并突破了单一的政治价值取向,恢复了面向人生的现实主义,个性创作力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与此同时,黄健中、杨延晋、吴天明、张暖忻、谢飞、滕文骥、韩小磊、黄蜀芹、胡炳榴、郑洞天、吴贻弓、丁荫楠、王好为、赵焕章、颜学恕、陆小雅等第四代电影导演开始了他们的创新与探索之旅。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每年都有他们色彩斑斓、富有一定独创性的电影作品涌现,形成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新气象。在电影观念更新、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呼声中,第四代导演摒弃单一的宣教模式,追求艺术表现上的纪实美学样式与风格,成绩可喜。
自1984年开始至1989年的事件止,可视为80年代电影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个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正逐步形成,政治、文化、道德、美学的反思运动丰富复杂而又迅猛异常,经济体制实现转轨,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较为宽阔的历史/文化的选择视界。从一定意义上说,80、9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程,正是电影家们主体选择精神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一发展阶段,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的喧哗和骚动,使电影家及其作品的选择精神和文化意识均呈明显上升趋势,第三、四代电影家们不断超越自己,进入多元求索阶段。像颜学恕的《野山》、黄蜀芹的《人鬼情》、丁荫楠的《孙中山》、谢晋的《芙蓉镇》、吴天明的《老井》等,都曾在中国影坛形成冲击波。一些青年影人则带着颇为明显的艺术探求、历史文化反思和主体选择的精神,进入了新时期电影创作的行列。第五代电影的崛起为80年代电影打开了全新的一页。这批才华横溢、思想活跃且更具创新意识的青年艺术家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黄建新、张泽鸣、何平、何群、孙周、周晓文等,宣告了一个新的电影运动的开始。他们的电影作品除反叛与批判思想明显,富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识与追求外,在艺术表现上,着意将电影造型语言提到中心地位,作品大都引起轰动效应,使中国当代电影为世界影坛所瞩目。
无疑地,第五代电影家及其探索创新的作品,占据了80年代电影发展旅程中颇为重要的地位,但就在其竭力发起一场美学革命,共同选择反思的基调,不断地争取个性创造力解放和实现的同时,恰逢社会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对电影业投资政策开始转变,同时由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发行渠道的一时不畅,使电影市场持续滑坡。影片制作活动,很自然地便要受制于这一时期整个经济/文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电影业被迅速推向市场,电影家们则需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语境中重建话语空间,找寻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日渐影响、渗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市场经济规律制约和左右下,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开始越过创新探索的求变起步阶段,进入世纪转折期的多元并存的阶段。
近10年或者说90年代的电影,不是“无主题变奏”,但其统一性很明显地不再是存在于其自身之内。在20世纪这最后10年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国家经济体制和立法等方面的改革步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加快,甚至较之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文化、艺术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电影与市场、社会和国家的交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日益复杂,电影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以及电影活动所蕴含的政治/经济/艺术诸元素之间的界限日益难以厘定,新都市、新民俗、新纪实、新体验、新主流等样式影片,以及历史文献故事片、革命人物传记片和重要现实题材影片等,交织在一起,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和第六代以至近年出现的所谓新生代电影导演,还有难以归代的一些电影人,从不同角度切入电影美学本体的发掘(有时也因功利束缚或适应市场化,使其精英性探索受到明显抑制),感受电影,继续其创新与求索的步履。
其中的第五代导演,90年代以来仍然不失活跃,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海外资金为来源拍片,《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荆轲刺秦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在国内外继续产生着影响。而拍有《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巫山云雨》《谈情说爱》《冬日爱情》《长大成人》等非常规影片的胡雪杨、管虎、章明、娄烨、李欣、王小帅、阿年、路学长等所谓第六代的出现,则成为一种颇有意味的事件,个人化的电影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与之相近而又显不同的更年轻(大都不到30岁)的导演,尽管还缺乏足够的艺术成熟和思想深度,但其存在引人注目,这些新一代青年电影创作者拍摄的影片,如《美丽新世界》《网络时代的爱情》《爱情麻辣烫》《洗澡》等,注重新的生命体验,关注现实,主流化与商业化在新的人生视角与新的社会、文化视点统一中显示出丰富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带有青年朝气的创作活动,标志着一场沉默的心灵革命的开始。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有着繁盛与丰富景观的90年代电影发展的基本格局及其历史趋势。
作为一个整体的新时期电影,可以被称作电影家们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不同的群体与话语的出场与在场使电影伸向无限性;电影的解构与建构,使其超过传统的疆界与局限,转换成了新的形式。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可以预期,中国电影经过这20年尤其是近10年的发展,铺平了通向新世纪的道路。
90年代电影审美风尚与消费社会:分离与融合
在一个转型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历史语境里,人们的价值理想、思想观念、审美追求纳新吐故,发生急遽变化,是很自然的。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的发展,作为“代”的电影群体产生,及其更替演示发展,之所以不断形成整体的新的眼光、新的追求、新的价值趋赴,其实端赖于时代的赐予。新的一代出现,往往会形成新的不同以往的目光,并构成对前辈一代的整体超越。前代的电影家们在受到影响、激励与冲击,内心保有一种可喜的胸怀的同时,也不免会有一种苦涩。第四代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承上启下,开始他们的探索的旅程,但充满矛盾的这一代人,其探索似未见透底。这为年轻的一代留下了淋漓发挥的空白。在第五代那里,影片情节表意淡化,影像表意增强,强调用电影造型语言来表现编导者的创作主体意识与历史文化蕴涵,个性化追求及其成就颇为超卓突出。其所获国内外大奖甚多,一些代表人物甚至有影坛“常青树”或获奖专业户”之称,张艺谋于1999年9 月在威尼斯的《一个都不能少》获得金狮奖,2000年2月又以新片《我的父亲母亲》从柏林电影节捧回“银熊”,更成为明证。第五代成了真正划时代意义的一代。但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当第五代以其作品突破旧形式并作进一步开创而使人振聋发聩的时候,它很明显地受到了政治一体化要求与市场经济活跃消费主义成为迷人旗帜的双重制约和影响。这引起包括第五代电影在内的整个90年代电影发生显著的根本性变化与历史性变革。第五代和仍然有力量为影坛贡献作品的电影家们,在逐渐形成并得以重行确立的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和娱乐片三足鼎立的格局中,被不断要求作自己更新的抉择。
影响90年代中国电影态势与状况构成的主流影片、娱乐片与艺术片的格局之得以形成与发展,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大众化转型和社会政治变化有关。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一个从艺术趣味、美学追求到具体运作、生产、发行体制全面探索与变革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探索与变革过程中,无数有实力的分属老中青各代的电影家仍然活跃于影坛,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一些更年轻的大多在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80年代与90年代经过正规影视教育的电影新生代——第六代与后第六代,开始踏上艰难成长之途。无论如何,这些电影人的成功努力或失败教训,他们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方语境中所做的分离与融合,他们不断自省与突围的姿势,所表现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是值得人们珍视的。
诚然,90年代电影汇入主流艺术的进程,是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创作即受到普遍重视。1990年由于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和意识形态氛围格外浓厚而凸显,90年代电影表现出的大众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特征,已露端倪。一些比较适应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的一些主流影片制作者,在这个电影的“小年”或调整期里,仍然拍出了《焦裕禄》《龙年警官》《中国霸王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特区打工妹》《你好!太平洋》《大城市1990年》等影响较大的影片。其中的《焦裕禄》一片,以其主人公在为实际事务奋斗中所显示的一种境界,以及它所达到的政治与伦理、社会意识形态与人生本源结合的文化政治策略,而受到来自中央领导、电影专家和广大观众的普遍盛赞与好评。
1991年,在纪念建党70周年之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格外集中,以至有人称该年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年”。这些影片气势恢宏,丰富多姿,反映创作者对重要革命历史文献资料和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物的理解与阐释的深度。它们所写题材都很重大,人物则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创作者们在记事、写人的语言、风格、样式等方面,努力突破低水平的重复,实现某些新的开拓与掘进。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中国战争片的叙述语言方式上,运用客观的全知性视角和多重交叉组合的结构,将一般的革命战争表现,发展为全方位地整体性地反映那些关系到党、国家或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或重要的战略战役,努力在历史与文献中做更丰富的开掘与发现;二是着力在战争或重要事件中写人,写人的性格和个性,写人性和人的感情,像《周恩来》等可入“伟人传”的传记故事片,在以这些领袖作为主角叙述故事,展示他们的伟大人品和人格力量的同时,格外注意贯穿着一种价值伦理的感情的力度与厚度;而战争的或记事的故事影片,除着重展示革命领袖和我军将士的银幕形象外,还注意到了其他人物的立体刻画。如《开天辟地》表现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革命的抒情时代,着意刻画陈独秀的形象,《大决战》描写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注意表现林彪、杜聿明等人物形象,《大进军》中对宋希濂、胡宗南等人的刻画等,都取得较大的成功,尽管缺乏诗性的沉重的反思,但并没有人物表现太过拘束或平面化的倾向。
当然,在当代中国情境中,人们很显然在这样一点上已经形成共识,即主旋律影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无论就其表现题材、方式方法,还是它的终极的艺术追求,都应该有更丰富与宽广的理解。比较形成共识的是,不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举凡表现人间真善美,弘扬主旋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体现一种正义感、社会良知和道德勇气,丰盈饱满地发掘时代之于人的精神或文化沉积的深厚内涵,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上激发人们开拓进取的,不论历史题材抑或现实题材的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其内。各以其敏感的艺术触角、深切的伦理情感与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感应着主流文化与时代前进的脉动,显现了创作者们对90年代以来“主旋律”策略有深切体会,有较全面的思考,有满腔激情,其中所渗透着的共同共通的社会共识与对历史、对时代、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责任感,是很显然的。《蒋筑英》表现主人公为人忠厚,对技术工作竭尽心智,最后长逝于出差途中,《凤凰琴》结束时教师和学生沉浸在国歌声中观看升旗,《孔繁森》展示的无私奉献的集体本位思想和鞠躬尽瘁的“清官”的魅力,《鸦片战争》所贯穿的那种与主流思想的内在契合及其所体现的不断的反思精神,《国歌》把国家的命运作为结构的主角……这些凝聚共识而又充满活的生成力的基本价值思想呈现,不同于简单的政治说教,其中也并不都有大场景或大制作支撑,所蕴示、展演的往往却不是小境界,而是有引动人心的大气象、大沟壑在。至于主旋律影片的泛化或大众化倾向,在《离开雷锋的日子》《红色恋人》《非常爱情》以至近年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等影片中,在政治、历史与审美风尚转型之间均提供了操作性与想象性的启示。
90年代电影审美风尚建立,与作为拥抱大众文化的市场化形态的娱乐片在80年代末开始成为影坛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有着重要的关联。在十年来的电影创作活动中,娱乐片的拍摄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潮,相关理论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在80年代下半期《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刊组织的对话与研讨以后,人们对娱乐片主体地位的确定有了基本的共识,意识到娱乐电影作为电影文化的主流,它在最大程度上给最广泛的观众提供了感性娱乐,认为“任何对娱乐电影的轻视,实际上也就是对电影自身的轻视”(注:饶朔光:《走向多元分化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回顾》,《当代电影》,1995年第2期。)。电影理论界根据90年代电影发展走势,深入思考如何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娱乐片的出路。如有论者认为:“寻求主流政治与大众娱乐的统一,是当前中国娱乐性电影发展的基本前程,而从中国大众文化传统中去寻求叙事原型和建立叙事模式,则是一条现实出路。”(注:尹鸿、陈航:《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电影》,《当代电影》,1993年第1期。 )另有论者则指出:“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电影的商业目的和艺术目的之间的关系。有的可以一致;有的,也不一定要求一致,这就在于你在创作时所给予作品的定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当然不能仅仅为了商业目的而忘记它的艺术品性和文化内涵;更不能忘记它的意识形态性。然而,电影毕竟是以经济物质载体而存在、以市场运作而生存的。人们可以赋予电影以种种功用,比如教育的、宣传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可以拍种种类别的影片;艺术家也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大众娱乐品特点却是它的最根本特点。”(注:李少白:《位置·策略·前景——对中国电影跨世纪发展的一点感想》,《电影艺术》,1998年第2期。)这些意见, 体现了对电影本体的新认识和对电影创作全局的新把握,反映了90年代电影批评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部分。主流政治与艺术性和娱乐性的分离与融合及其寓示的广阔的电影话语空间,对于9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与批评者说来,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现实的选择、一条民族电影的自我认证和自我发现的必由之路。
电影业界在娱乐片的道路上摩肩接踵,开始有生气的迅跑,终于获得了显著的成果。多为类型化电影或消费性的娱乐电影,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尝试走出一条从容发展的路数。这之中,注意效率,懂得竞争,甚至适当摹仿,都可以理解,但拍娱乐片,走相同的路线,如何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使之更个性化,走出好莱坞范式,突破喜剧或闹剧电影模式,富于电影创造的智慧与职责感,则是一个值得深切省思的重要问题。强化导演个性与观众市场的衔接,娱乐片创作在这样的层面深入地进行下去,自然就不会流于一般,而可能获得成功。其实,优秀的影片,不拘是主旋律影片、艺术片,还是娱乐片,都应能最大限度地折射创作者的个性,反映创作者对人生、生命与世界的独特体验,也就是,对表现内容或对象题材能作真生命的投入、看取与开掘。对有追求有作为的创作者说来,创作个性和观众与市场这一决定因素做怎样的有机融合,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方面,张建亚的探索富有特色,值得重视。他的《三毛从军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和《绝境逢生》,虽采用娱乐片的形式,但又可谓相当个人化的电影,导演通过包括解构性策略在内的电影手段,将一向视为矛盾的电影的个人化与电影特征中的某些商业性元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赢得了观众和市场,在引起人们“愉快的震惊”的同时,拓展了银幕创造的话语空间。《三毛从军记》在抗战的背景下,漫画化地演绎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这是张乐平的三毛,更是张建亚的三毛。创作者运用了假漫画、仿卓别林影片、新闻片与仿新闻片、30年代报纸与仿30年代报纸、真纪录片与卡通片的拼接以及黑白影片与彩色影片交叉融合的手法,包括插入《沙家浜》“十八棵青松”的样板戏造型,增强了影片戏谑荒诞的效果。稍后的《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巧妙利用了有关《红高梁》《菊豆》《战舰波将金号》《蝴蝶夫人》《红灯记》等的调侃、反讽与解构;《绝境逢生》则以各类体育项目造型,别开生面地用于正面人物和鬼子的游戏抗争与搏杀之中,诸如此类,均可谓异想天开,而一些绕口令式的语言,在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很显然,其中融有严肃的思考,而人们是否都能以民主的心情去接受,则也是难说的。张建亚的这几部影片,和漫画存在重要关联。从素材到创作,不啻是电影漫画,而显然,漫画虽颇通俗,意义却不俗。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将电影本文简化为一种带有明显世俗化的大众消费趣味的游戏文本,别开生面,在保持一定艺术追求的同时,使观众在观赏中释放自己被抑制的潜意识,受到观众欢迎。他的努力也喻示着90年代中国艺术影片创作既在艺术上做各种各样的追求又充分占据电影市场的价值趋赴。
张艺谋是第五代导演中较早注意到市场要求的。除了1988年他导的《代号美洲豹》属于明显的娱乐片样式以外,他的其他艺术性影片,也是努力争取“把电影往好里拍”,尽量争取最大多数观众的。在他看来,好电影第一要好看,这种好看包括满足不同层次人的不同需要,让想看热闹的又觉得好看,想看“想法”的人也觉得还不错。第二就是言之有物(注:李尔葳:《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铺路——张艺谋访谈录》,《张艺谋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他艺术上继续求新求变,不拘一格,90年代先后拍摄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丰富了电影叙事的大众情感模式,将前卫艺术和通俗性大众化的表达方式结合,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陈凯歌在这一时期的影片,包括《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等,也是在作个人化的电影探索的同时,又比较注意商业运作,将个人化的电影与电影的商业性及观众观赏性因素结合了起来。张艺谋、陈凯歌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除具有各自独特而明确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艺术创作风格外,较多利用海外和民间资金拍片,且因投资方式改变所带来的一种“他者”的声音,以及影片在国内尤其是国外获得声誉,频获大奖,努力打入世界电影市场,这些基本策略,也几乎成了他们影片最重要的特点。
选择和定位的焦虑:怎样感受、拓展电影的中国性
近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处在转型时期,一切还在方生方成之中。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以平民化的视角,表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恰也构成1990—2000年影片创作的重要策略与景观之一。为观众所瞩目的张艺谋、陈凯歌的绝大多数影片,便是重要例示,其他例如谢飞的《香魂女》《黑骏马》,胡炳榴的《安居》,夏刚的《遭遇激情》《我心依旧》《大撒把》《无人喝彩》《与往事干杯》《伴你到黎明》《生命如歌》,黄建新的《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周晓文的《青春无悔》《青春冲动》《二嫫》,宁瀛的《找乐》《民警故事》,李少红的《四十不惑》,刘苗苗的《杂嘴子》,孙周的《心香》《漂亮妈妈》,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以及《离开雷锋的日子》《没事儿偷着乐》《男妇女主任》《好汉三条半》,等等,这些影片,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反映人生百态和普通中国人的基本生命存在与生活状态,通过常人故事及其富有个性的构思,写当下状态,使其所写所述成为别一样平实的现实之一部,构成常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观众因此给予它们更多的亲切感与信赖感。
霍建起于1998年导演完成的《那山·那人·那狗》,写大山里的邮差,给予观众无法释说的感动,让人不能不感叹电影的无限魅力。影片以舒缓而深沉的节奏和平静的常规叙述方法,讲述了发生在一对父与子之间的平凡故事。影片传达温馨与美好的民间传统与情感,在融入主流的同时,呈现出探索与思想的复杂态势,从而导致电影文化解释与实践体系的多元性,这使近年电影创作表现在探索与创新的融合趋向展示得很明晰。
在近10年以来的电影创作中,第五代之后的年轻的新生代电影,开始是以其所具有的较强的探索性和实验性,以及其所蕴含的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的。他们在影片主题与叙事方式上,有意规避和消解第五代电影的话语模式与叙事态度,但他们从一个侧面恰巧又喻示并证明了第五代电影的内在生成力。他们“先锋也保守,边缘又主流,因此很复杂”,他们的影片特点鲜明,富于前卫意义,但他们的探求与追索,还要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旅程。新生代导演的影片大都尚不够十分成熟,也缺乏相对统一而明确的美学风格,但其以自命不凡的前卫性姿势和比较客观的视点,描写置身“边缘”的一群边缘人的边缘生活,往往拍得比较精致而流畅,镜语充满才气,色彩鲜明,叙述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结构散文化,有时还采用了纪录片或MTV手法,显示与众不同的视听风格, 呈现出了较强烈的探索性趋向。章明说到他以三个段落结构拍摄的影片《巫山云雨》时,说:“我这个电影不是为主流拍的,是为边缘的观众拍的。”“吴刚作为一个警察并不重要,麦强作为一个航道工也不重要,陈青作为一个旅馆服务员也不重要,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这种生命的状态,这唯一是我们强调的。这个身份代表很多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光有这样一个题材一个想法还是很浅的东西。关键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电影很多年一直在变的就是一种表达方式。”(注:程青松、徐伟:《此情可待——章明访谈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显而易见,以怎样一种表达方式或镜语形式,表现有关生命、生存、人性的纯粹事实,感受中国性与复杂性,是他们所关注的。但是,作品技巧智慧太多,而灵魂血肉有所欠缺,有些影片显得太过自恋或主观化,一味表达自我,影响观众面的拓示,是第六代的不足与缺失。拍了《头发乱了》再拍《浪漫街头》的管虎自省:“刚毕业那几年,觉得好东西是阳春白雪、少数人喜欢的东西,比较个性化的。现在全变了,应该是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才称得上是好东西。”(注:黄地:《管虎撞墙有心得》,《北京青年报》,1997年2月21日。 )张元在开拍影片《过年回家》之前也开始意识到,这部影片,“它将面对整个中国的观众”。(注:黄燎原:《张元:渴望中国观众》,《南方周末》,1998年7月24日。 )张元以往拍的五部电影除《妈妈》发行过四个拷贝外,其他四部均未能与国内观众见面。纪实风格的《过年回家》可以视作张元改变“地下导演”的身份成为主流导演的标志。但从2000年2月陆续在北京、 上海、广州上映《过年回家》以来,观众反应一般,票房不好(北京地区影片票房不到6万元),使“渴望中国观众”的张元感到了沉重压力。
这些9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活跃的年轻影人,在努力拍出一部部与众不同的影片时,不得不开始去考虑他们的话语困境,考虑影片有没有卖点受不受欢迎,怎样拓展电影的中国性为本土中国观众接受与欣赏诸问题,也就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努力寻求新的适应方式,选择既竭力保持个人化艺术倾向,又努力向商业化、主流化靠拢的策略,重新确认拍片的前提,恢复电影艺术的活力,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他们前辈人物身上的那种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在80年代部分影片中弥漫的那种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一些活跃的青年导演对电影批判性及电影知识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觉,在90年代末的年轻影人创作中都已经不再一见,而与资本和市场关系变得日益密切的普遍事实和日益严峻的创作空间,不仅深刻改变了他们的电影范式,而且90年代电影自身的同一性也不复存在。
这些成长于80年代,在学校期间便大量接受海外文化,特别是前卫的实验性的文化的青年影人,对传统的反叛性很强。出于中戏的年轻群体,像张杨、施润玖、金琛等,都是影坛上活跃的“先锋”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张杨,在毕业后处于一种自由流浪状态,拍MTV、 电视专题片,排话剧,写剧本,各种各样的事都干。这使他比较了解生活(都市生活),了解新的大众与新的流行文化。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爱情麻辣烫》,采用一种流行的分段型的小品化样式,表现年轻人的爱情。徐静蕾的戏不多,从头到尾没一句话,但观众很认可这一新形象。她的自然状态,非常符合新新人类所要求的偶像标准。他的第二部电影《洗澡》,比较第一部影片,题材似乎比较老旧一些,但其细腻发挥的,并非老旧主题,影片中,把角色所感受到的丰富情感化解为戏剧性的姿态,从一点一滴的小细节中挖掘人性,为市井生活提供了一幅独特的画面。特定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使高度艺术性形象和创作者质诘思辨的努力为广大观众所理解。两部影片,通过写人的情感,展示并把握人的生存之间的状态,虽然题材、人物、感觉有反差,是一种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原生态;影片不艰涩,不缺乏观赏性,没有某种市场“力比多”,却都赚了钱,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性。
靠电影本身的情感触动观众,让观众感到亲切便是好电影,好电影就有商业性,张杨等人仿佛很轻松地就让当代中国观众对他们的影片产生新的感觉,感到兴趣。也许这一代年轻的电影人的作品尚缺少强烈的冲击力,但他们还是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是富有启示意义的。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近两三年以来,资本和市场全球化与网络化步伐加快,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土电影介入国内以至国际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界呈现出普遍的选择的困惑、焦虑与苦涩。当其太看重电影商业化,太青睐市场,仿佛就远离艺术的真谛,一味去做个电影的商人了,而为艺术做电影,一有艺术追求,就自绝于市场,走向一种绝境,和市场说“拜拜”了。这种思维模式,在其二元论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道德姿态。诚然,商人需要赚钱,但是电影家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电影家不是商人,电影也不是工业,不是全都好莱坞,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但是超越市场/艺术二分法的思想方式,回到电影自身,用心和电影对话,和观众对话,和自己对话,相互歧异而相互关联的电影实践都以寻求体验、感受并确立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为基本的要务。这应该视为世纪之交中国电影的趋势。
在这一基本理解的前提下,种种已经成功或尚未成功但连绵不绝的电影话语活动,像一阵阵躁动的风,不断向我们吹来。无疑地,中国电影在21世纪将进一步成为世界性电影艺术,但在现实性和民族化的道路上将继续进行长期的形式和内容的探索与变革。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中国电影将出现新的分化。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不会也不应该走向凝固,它应是丰富、复杂、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它形形色色,面目各异,真实表现普通中国人的状态和心情,寻求传统的价值,或者自觉呼唤社会使命感,或者孜孜不倦地去探索个人化的生活,努力使电影语汇实现民族化,追求并汲取在“新世界网络”中的变革动力。在不久的将来,全球五大洲的民族电影艺术会伴随互联网技术与高速光纤、电缆和无线系统的完美融合,真正汇入世界电影之流,不仅中国电影在其中将扮演一个重要而显耀的角色,而且,任何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毫不费力地利用语音、数据和视频点播中国电影,就世界电影说来,中国电影将亲密无间地与外部的世界接轨,真正成为全球性艺术,成为世界电影艺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虽然会面对着新的多重困难,但21世纪的中国电影充满挑战性与建设性的探索势必延伸、拓示出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并且散发着新时代的真诚与激情。这是可以预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