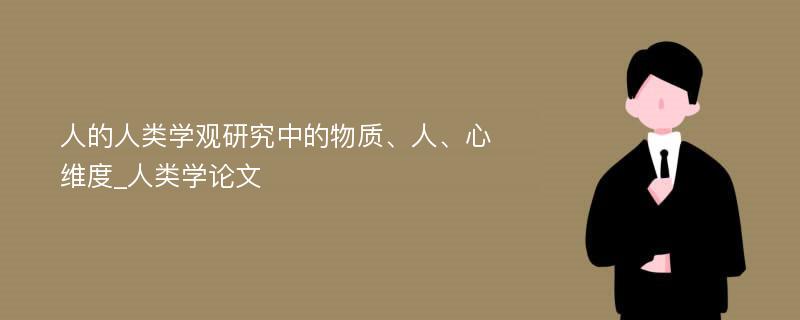
论人类学人观研究的物、人、心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人观,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出生于其中的任何一位历史个体所持有的生命价值观念。对应于物、人、心三元,人观可以划分为自然观、社会观和自我观,而自我观中的“我”又可划分为物质我、社会我和精神我。物、人、心三元与学科分类相对应:对第一元进行描述的学科为物的自然科学系列;对第二元进行描述的学科为人的社会科学系列;对第三元进行描述的学科为心的人文学科系列。在人类学人观研究的物、人、心三元宏观描述系统里,对人—物关系的描述可称为第一维关系的描述,对人—我关系的描述可称为第二维关系的描述,对人—心关系的描述可称为第三维关系的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对每一维关系的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对两个元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描述,不涉及构成某一维关系的二元中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元不等于第一性,第二元不等于第二性: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宏观描述系统并无实体主义和本质主义于本体论方面的承诺。本文对人类学人观研究描述本身的描述,有时候在一元之内或一维之内进行,有时候在一元以上或一维以上进行。①物、人、心三元之间呈现出多种可能的二元对立的互动过程,其三元互动所形成的态势导致了人类学人观研究不同的理论取向。
物、人、心三元的差异连续性
“物”(工具)作为进步的标志一向为承认普遍规律的进化论者所偏爱。进化论者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注重生产和技术工具的唯物史观;同样地,新进化论者怀特借用物理学和热力学中有关能量的定律来解释进化的规律,也选择了物的一元。进化论者所使用的残存物分析法归根结底来源于自然科学。考古学家通过地质层被发现的遗留物即人类创造物再现物质文化,而生物学家把身体的非功能性器官看成是远古人类器官的遗留物,甚至连非功能性的习俗与信仰也被看成远古人类的遗留物。马林诺夫斯基受当时尊崇实证知识的影响,对“库拉圈”习俗中项圈和臂镯之类的宝物作了准确的描述。他认为制度与风俗、语言与行为是文化整体的有用的事项,而不是进化阶段的残存物。这位为人类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的人类学家以科学方法描写了蛮族制度与风俗并分析其功能,按照严格的学科要求认真研究通过长期参与性观察所得到的人类学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的位置、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与周围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把人界定为一个留恋着过去和希望着将来的怪物。注意到“流连着过去”与“希望着未来”的心态就说明功能论者在关心有用的生物需求的同时,也关心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②莫斯思考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说明这位法国社会学领袖人物眼中之物并非纯粹的物理之物,几乎所有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礼物交换行为都是为了建立某种社会关系。③物的象征意义显然不是来自它的物理属性,而是来自人我之间交换过程中被赋予的特征。人类存在和认同的物质客体包括人体、衣着、家具等拥有之物,特别是通过使用工具或交换所获之物,因其物性与人性相连而进入了人类学家的视野。利奇用物质文化的眼光从物的一元看到了许多克钦人生活中从火枪到铜锣的许多家庭器具,看到了纺织、冶铁和种植稻米的技术和工具,还看到了工艺有着强烈的印度尼西亚风味;用社会文化的眼光从人的一元看到了强调自然属性的亲属关系的结构特征;用观念文化的眼光从心的一元看到了某个特定的社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里持有的态度和观念。④离开了物、人、心三元,人类学家什么也看不见,物、人、心三元构成了对田野文本实践者的人类学知识进行共时性和构成性分析的切入点,而选择三元中的哪一维度会直接影响到人类学人观研究所建构的客体、理论及其表述风格究竟是什么样子。
着眼于人的一元的人—我关系维度指向了社会,由个体组成又超越个体的社会不是简单的个人相加的总和。原始部落时代,社会化程度很低,人—我关系基本上是亲属关系的总和。只有到了大工业社会,人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特征才得以充分体现。布朗提出的“社会结构”概念为许多人类学家所接受,其指的是人—我关系组合的各种群体及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其内容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其形式就是制度。他认为社会呈现给人类学家的问题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图腾崇拜动物的选择是根据人类社会关系相似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的。⑤如果说布朗强调的是社会和谐论,那么,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冲突论。布朗主张用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归纳方法来研究社会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用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用的是抽象力。通过抽象力,马克思看到了“看不见的手”在调配着物的流动,还看到了受制于物的人—我关系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对立的二元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通过抽象力,物化在商品中凝结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被抽象为本质论范围内理解的人的社会属性——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应于人的二重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同时也对应于物(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⑥
对纯粹的自然之物的一元的描述容易做到价值中立,可以较少或没有“自我”的特性,而人自己对人的一元以及社会作为人际间互动之结果的研究则不可避免地带有自我认识的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物已经包含了人所赋予的意义,还包含了意识形态,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又往往接受了理论建构应该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或辩护的逻辑。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社会层次只能是一种近似的、简化的处理,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任务主要由人文学科来完成。⑦人类学人观研究在理解和解释意义时还用了将心比心的“软科学”的方法:虽然把调查点当做实验室,但了解当地人的观点又不用心理学的试验程序;虽然注重参与性观察又不借助社会学的问卷和抽样调查。所以田野工作者自己的人观、主观选择等等因素的介入使得人类学人观研究作为科学的客观性只能限定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范围内。有持进化论观点的人类学家如泰勒坚持人类本质一致性的观点,相信社会的运行如同分子或有机体的运动一样受整个世界自然法则的制约。但他只看到了人作为纯粹的自然之物一元的同质性、可实证性和规律的普遍性,却忽略了从人的一元到心的一元逐渐增强的异质性、不可实证性和文化的相对性。一位人类学家如果囿于见物不见人或有物无心的思维惯习,即使有揭示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勃勃雄心,揭示出来的规律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总是个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们当然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大体的趋势,但没有谁能写出可以准确预测变化规律的社会发展方程式。
“物”可以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但“心”却不能。例如蒸汽机就可以作为由工业革命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我们可以断言由工业革命导致的资本主义之前绝对没有蒸汽机之物,但没人敢断言前资本主义社会绝对没有博爱之心。远古时期,物、人、心的观念世界浑然一体,而人类一旦跨入文明的门槛,开始是物和人,稍后是心,三种观念次第生成。赖尔将身心二元论比喻为“机器中的幽灵理论”,将心界定为通过具体的行为可以外显的倾向或意向。⑧格尔茨承袭了赖尔的这一思想,并以此作为解释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就这样,研究对象及报道人生活在其中的观念世界成为了理解和解释的对象,人类学人观研究的重心由体现人—我关系一维的社会结构观转向了体现人—心关系一维的文化现象观。与此相适应,人类学人观研究的文化表达由科学转向了诗学,而描述对象备受关注的行为也由生物行为、社会行为转向了符号行为。
据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描述对象的物、人、心三元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三元之间又是一个连续体。对存在于物、人、心三元之间的差异连续性,人类思维由于能力有限或为了表述的方便,只能将其划分为非连续的认知对象,而人类所具有的分类能力也有助于认识到心就是物的对立面。从物的一元到人的一元再到心的一元,同质性、可实证性和规律的普遍性依次递减,而异质性、不可实证性和文化的相对性依次递增。在自然和社会领域,若以经验事实寻求和证实普遍规律,则选择物的一元完全行得通,选择人的一元部分行得通,选择心的一元就完全行不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于心的领域探究自我、超我和本我之类的人格基本心理结构,或于心的领域探究潜意识的深层结构即使被人誉为极富社会学的想象力,但终因无法实证而导致了科学性的解释力的弱化。
探究隐藏于文化多样性后面的心智的一致性和内在于人的大脑神经系统这个物质实体中的二元心智结构,一种简化的办法就是有意识地将时间从有意识的符号行为创造的文化领域移走。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经验事实是心智或心灵活动处于时间的绵延之中,所以若想确定人物情感、人观包括其中的自我观的空间位置,那一定是很荒谬的事情。好在人物是身心二元论的存在物,虽然情感、人观包括其中的自我观是时间性的,但只要把它们归属到相应的个人身上,也就具有了空间性的载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着眼于心的一元的人类学人观研究远离通则的追求而倾向于个案的深描就可以寄希望于内心深处的观念可能体现于言辞、形象和行为等,也有理由相信通过报道人的言谈举止从外显的可观察记录的人的行为(包括身体行为和言语行为)入手,即使无法认识到人本身的本质属性,也可以领会到通过对人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包括自观和他观。格尔茨赞同韦伯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意义的方法,用“意义的编织之网”之隐喻表述人观。他区分了“传统的”和“理性化的”两种极端类型的宗教,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人观的精妙而深刻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对特定文化的人观加以描述作为了解文化多样性和相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实际上承认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对应于物、人、心三元之间的差异连续性,转向人心一维的人类学人观研究很讲策略地脱离了寻求普遍规律的实验性科学的影响,与观念形态打交道的旨趣就在于寻求各种可能性的意义解释,而呈现文化多样性和相对性、提供一种象征符号行为自我表达的语言正好是民族志的理论作用之所在。
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平衡
透过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将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类学人观研究对人观的陈述当做统一的、进行共时性和构成性分析的陈述对象,可以看出:民族志文本实践如果偏向物的一元,就会倾向于使用科学实证或抽象力的方法以发现普遍规律;如果偏向心的一元,就会倾向于使用文化解释的方法以寻找象征体系的意义。150年来,以“物”为中心的物本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论或以“心”为中心的心本论理论取向此起彼伏,处于三元互动动态平衡过程中的二元对立有时候“东风压倒西风”,有时候“西风压倒东风”。但耐人寻味的是,任何一元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销声匿迹。当其中一元快走向极端或已经走向极端的时候,同一时期或一段时期内,与之相对立的另一元就会以“反对派”的面貌和力量出现。例如,着眼于物的一元的科学实证方法对于心的领域力不从心时,着眼于心的一元的文化解释方法就应运而生。就理论范式而言,当进化论范式的弊端暴露无遗时,功能论范式和历史特殊论范式就成为了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历史特殊论的极端形式出现以后,新进化论、文化生态论、文化唯物主义探讨“物”(经济生活)与“心”(象征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用力方向又指向了物的一元。物、人、心三元就这样循环往复,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又往回摆动。人类学人观研究中这一“风水轮流转”的转向就类似于利奇的钟摆理论所描述的动态平衡。与钟摆不同的是,物、人、心三元互动的周期不规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条起决定作用的能够准确预测其摆动轨迹的人类学人观研究普遍原理。
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宏观描述系统只是提供了人类学人观研究和再研究的观察视角和理论陈述的维度,不涉及本质和本源问题,也没有作出任何本体论方面的承诺。韦伯注重人—心维度,反对马克思过分地关注经济因素,认为作为精神要素的人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有很大影响,这一解释路径针对当时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马克思注重人—物关系和人—我关系维度,用前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西欧封建生产模式之内在矛盾运动态势及其结果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所隐含的人观,认为对人的看法或价值观念是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萨林斯却认为,人们对生活的看法这种“观念的东西”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以及交换与消费的方式。萨林斯提出经济制度发展的序列,说明他把社会进化的动力建立在经济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后来他反对以经济基础或能量角度来研究文化,这说明他看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人的科学”之“非科学性”,目光也由此转向一套复杂的象征意义体系。人类学人观研究中,作为研究策略,技术—生态原则主张优先研究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明显地带有技术工具决定论的思想,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生态决定论等思想。历史特殊论者猛烈抨击了进化论中包含的物质决定论和种族人类学中包含的生物进化论,但有时又持有一种文化决定人格论的决定论。决定论者很自信地作出以物为中心的物本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论或以心为中心的心本论于本体论方面的承诺。其实,在人类学人观研究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的宏观描述系统里,决定论观点的形成只不过是田野工作者研究路径主观选择等因素介入的结果。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惊喜地发现各执一端的决定论与选择论在这里出现了两极相通的场景: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田野工作者选择了对应于物、人、心三元中的某一个维度并走向了极端的人造物。例如,如果将人界定为符号化的寻求意义的动物,再把生活意义的根据设定在心的领域,只要沿着人—心—维的路子走下去,不断地扩大象征符号的范围,就会找到许多看上去显得很片面又很深刻的理由来论证人们就生活在象征符号的世界里,体现人—我关系维度的社会本质属性就是符号的象征表达的统一体;再走下去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论证:人的本质就是符号化的寻求意义的动物。
注重物的一元着眼于人—物关系维度设想出来的由共同人性而不是由某种文化提出来的人类共同目标,坚持了普遍的规律,但忽略了文化多样性和相对性;远离物的一元着眼于人—心关系维度的意义解释强调了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却放弃了对可公度性目标的追求,还放弃了根据实践理由提出来通过分享事实判断本身而形成的共同的希望和信任。人类学人观研究的观察视角由第一维的人—物关系转向第二维的人—我关系再转向到第三维的人—心关系领域,只能说明有更多的人观研究者特别看重其中的一元(维),而不能说明其中的一元(维)可以决定另一元(维),更不能说明从一元(维)到另一元(维)的转向就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时过境迁,冷静地反观自身的人观研究维度,研究者自己以往特别看重的物、人、心三元互动中的任何一元走向极端都会暴露其局限性。
偏重物的一元的文化科学于实证主义的难题就在于任何一位民族志撰写者对于构成任何一个社会或历史事件的任何一部分——无论他对于这一部分的田野材料收集和整理得如何完备——都不可能做穷尽描述,因为构成这一部分的成分是无法穷尽的。实证主义的教条就在于渴望将一切不可观察的事物还原为可观察的事物,以规避任何相信一种非实在物的危险,但终极绝对价值的信仰只存在于心,谁也无法还原为可观察的存在物。格尔茨的文化解释人观研究最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但“深描”的认识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认识了一种文化的种种外显行为并不意味着就认识了该文化的“心”,理解了自己的心不一定就理解了能理解真理的方法。
任何一种人类学人观研究都要涉及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的描述,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存在方式也都要涉及物、人、心三元的动态平衡。民族志撰写者心里很明白人—物、人—我和人—心三个维度都同样重要,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但到了具体的研究场景,用力方向实际上还是指向了其中的某一元(维)。一旦“无知之幕”后面的其他许多研究者由于社会心理等因素的介入,结果用力方向都指向了同样的一元(维),于是就形成了某个维度“一边倒”的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理论话语权力格局,也就是说,物、人、心三元之间出于了失衡状态。遇上这种情况,一个稳妥又能取得表面效果的补救措施就是提出设限概念。例如,从事科学研究最直接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规律并作出事实判断。但科学与意义无关,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答案。所以一旦科学理性泛滥超过了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我们就提出“有限科学”这一概念。同样只要假定人类学人观研究中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的宏观描述系统里任何一个维度的理论陈述都有其贡献和局限性,提出“有限功能”、“有限结构”、“有限实证”、“有限进化”和“有限传播”等概念就都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牢靠的逻辑基础。其目的就在于使人类学人观研究中物、人、心三元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一种可靠的现实追求,并促进理论范式转换时对话双方或多方从容商讨过程的形成。
注释:
①赵仲牧:《赵仲牧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第428页。
②[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岛上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③[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3~125页。
④[英]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4页、第246页、第270页。
⑤[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第11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第188页、第189页。
⑦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⑧[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