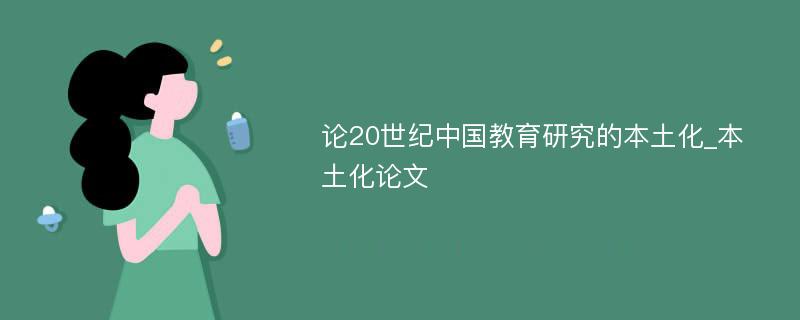
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中国教育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中国教育研究的百年历史,对其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总结,不仅能使21世纪的中国教育研究从中吸取教益,获至启迪,更重要地,并将由此而催生出新世纪的繁荣。
一
关于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分期,学术界颇多争议,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1901~1929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引进欧美及苏俄教育理论、研究方法等。从引进的形式上看,结构和内容在初始阶段相当简要,至后期才渐趋繁复。这一阶段重在翻译域外教育理论著作,接待国外学者讲学。总的来说,还处在“本土化”的初级阶段。但这一阶段无疑为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1929~1958年。这一阶段是直接从欧美和苏俄大规模引进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尝试形成本土化教育研究特色的时期。从形式上看,初步形成了欧美实用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两大教育研究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本土化。
3.1958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量引进域外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吸纳机制。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大陆、台湾、港澳教育研究的发展并不同步,但总的来说,在教育研究方面形成了分途发展,多元互补的特色。
上述历史分期与业已存在的种种分期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此,笔者觉得有必要阐述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早在19世纪下半叶即已开始,在清末教育思想及教育改革中已初露端倪,但是,由于本文是论述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因此,将时间上限定在1901年较为合适(但这并不否定1901年以前有识之士为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所作的努力)。
第二,有学者将第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定在1915年或1919年,这并不准确。因为中国大规模引进国外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从1915年前后开始的,但引进工作并未就此停止,而是一直延续到1929年左右。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有学者开始致力于欧美和苏俄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应该说,这一年为引进洞开了方便之门,其影响波及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并形成了引进的一个小高潮。正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合力,至20年代初期,引进工作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20年代初期西方不少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并多有教育理论译著(文)出版,即是明证。这一引进工作持续至1929年,随着杨贤江《教育史ABC》一书的出版而宣告结束。正是这本书,标志着真正意义上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开始。1927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处于“春秋战国”时期,1927年以后,随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形式上的统一,政治上的“春秋战国”便结束了,教育形式渐趋定型,政治方面和教育实践都不允许中国教育研究仅停留在引进层面,转而提出了本土化的要求。《教育史ABC》的出版正是适应了这种要求。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1949年是教育史上的重要分野。但由于教育研究超前于教育实践,并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因此,用它来标志教育研究的分野并不十分合适。实际上,从1929年后,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本土化,如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主张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教育实际加以改造,“翻了半个跟头”,既同杜威的教育思想有着渊源关系,又严格区分于杜威的教育主张,自成一说,并由此产生了重大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着这一工作,只不过将引进和改造的重点放在了苏联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方法上。因此,1949年~1958年这段时期内的教育研究的学术性质与1929年—1949年这段时期的并无二致。这一阶段延续到了1958年。
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重引进而不重消化。
教育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但是,“通过研究(Research)来取得有关教育的确证了的知识,作出教育对策,对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件陌生的事件”。[1]教育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行为,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并在西方社会得以迅速发展。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和西方文明的东移,许多有影响的教育理论及研究方法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所袭用。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大批有识青年留学日本欧美和苏俄,回国后常常通过各种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将原留学所在国的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一方面,这对中国人开阔眼界,理清思路大有裨益,为教育研究的本土化作了最初的物质和心理准备,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大面积的引进必定会良莠不分,将中国变成了别国教育研究的“试验田”。特别是,不加批判地加以引进,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
第二,重教育理论的引进,不重研究方法的引进。
教育理论与研究方法联系紧密,教育理论源于实践,但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教育理论,必定要借助教育研究这一中间桥梁。研究方法的运用,直接关系到教育理论的水平,从这一角度讲,研究方法对教育理论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了先进思想的启蒙作用。因此,整个社会学科都十分注重理论的引进与介绍。教育科学亦如此。确实,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思想对20世纪的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毫不夸张地讲,没有这些先进教育理论的引进,也就没有中国的新式教育。
但是,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使得不少学者只注重教育理论的引进而忽视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引进。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研究绵延达100年之久,介绍这一学术派别思想的评著不下百余本。遗憾的是,我们只注重了对其理论与思想的介绍,相对忽视了其研究方法的引进。本来,赫尔巴特在其研究历程中,十分注重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作用,但20世纪中国的教育研究,并未得此“真传”,不仅哲学的功用没有得以发挥或者功能被世俗化、庸俗化,就连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的影响也被视而不见。今天,当我们宣称中国的教育学实际上仍处在“赫尔巴特时代”时,我们能说我们学到了赫尔巴研究的“精髓”吗?同样,对于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我们又能真正懂得了多少呢?
第三,重科学方法的引进,不重人文方法的引进。
在19世纪最后不到25年的时间内,经验主义教育研究诞生,并且开始探讨至今仍困挠西方教育的一些普遍问题,这决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这主要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哲学思考,并由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涌起所激发。世界教育研究的历史表明,现代教育研究的直接起源是自然科学,而不是当时尚在酝酿中的社会科学。正是这个原因,加上20世纪初期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的教育研究者们十分注重引进国外教育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相反,20世纪以前一向厚实的人文传统在中国教育研究中被严重削弱了。这种削弱不仅表现在对原有人文传统的批判上,更表现在对国外人文研究方法的遗弃上。人们常常不可理解: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在西方学术研究上可谓并驾齐驱,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却一反传统,厚彼薄此呢?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教育研究者们的自卑心态、急躁心态和急功追利心态。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教育研究一直落后于世界,国门洞开后,强烈的对比严重刺激着中国教育研究者,特别是西方因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产生了大批理论成果,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惯用的人文研究法,不由得自卑起来。自卑的过程中又不甘落后。企望奋起直追,在短期内赶上甚至超过人家,因此,在引进时,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循环直接效果的、在短期内能够见效的、效果显著的东西。自卑心态导致了急躁心态,急躁心态直接导致了急功追利心态,急功追利心态反过来又促成了人们自卑心态的形成,这样无休止地循环下去,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
今天,当我们为数理统计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大量被运用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是否该为调查法等方法的冷落而悲哀呢?
二
从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总体呈现出如下规律:
(1)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的发展与同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实践活动等息息相关。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实质上是一部斗争史。由于战争时间持续较长,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还是无产阶级学者,都无法真正从容地引进和消化国外教育理论和方法。这是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看,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教育进步,教育研究就健康发展;反之,则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
但是,应该认识到,教育研究与政治、经济因素并不必然地呈正相关,有时是呈负相关的,这一点已被中国教育研究的历史所证明。譬如,1919年前后,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内乱不止,然而,此时教育理论的引进却掀起了一个高潮。再譬如,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透顶,经济亦处于崩溃边缘,但陶行知、陈鹤琴等一大批学者却能引进和有意识地消化国外的一些教育理论,并在中国加以试验和推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其一,经济、政治等因素并不直接作用于教育研究,而是通过教育实践活动间接地对它产生影响;其二,由于引进的对象主要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理论本质上对当权政治没有多大影响,有些甚至对其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尚能被当权政治接纳;其三,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氏政权,均没有完全关闭国门,断绝与世界的对话。这一点至关重要。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必须是中国与域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缺少了交流与对话,引进和消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2)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是循着“引进→消化→自我体系的建立”这一轨迹演进的。
没有中外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碰撞,也就没有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这种碰撞,首要的是将国外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翻译、引进。前文所述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然而,“本土化”并不能与“不加批判地吸收”划等号。国外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移植过来后,还得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谓消化,一是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一是指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当然,称植、引进和消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教育研究的发展,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发展,为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从本世纪初期起,要求中国教育充分发挥主体性的要求不绝于耳,这种努力也始终未曾停歇。时至今日,我们只能说,这种努力取得了初步结果,但离本土化的要求与目标还相差甚远。一个显著的例证是,作为教育研究重要方面的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一直未能脱离赫尔巴特、凯洛夫等人创建的体系。建国以来出版的100多部教育学著作,大都是凯洛夫(也是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翻版。由此看来,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还得循着这条轨迹艰难跋涉下去。
(3)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虽因国土的分裂,大陆与港台地区分途发展,但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学术渊源等因素的作用,三地教育研究又各存特色,各有优势,并且能优势互补,从而达到殊途同归。
20世纪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理论主要有三种,即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大致说来,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引进中国时的时间差不多,杜威的教育理论的引进则稍迟一些。这三大学派的理论对中国教育分别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开始传播,并且始终指导着苏区、解放区的教育实践活动,而赫尔巴特和杜威的教育理论主要影响着“国统区”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前者成为大陆教育活动的主要依据,而后者则在港澳台发挥影响。但是,由于两岸三地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因此,撇开意识形态争论后的教育理论特别是教育研究方法能相互交融,并有进一步融合之势。
中国教育研究如何遵循上述规律,真正实现“本土化”?
笔者认为,要使教育研究本土化,着重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教育研究要做到“古为今用”。
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2]教育研究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当以我们中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在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同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只能是一具外壳,没有生命活力。近几年来,人们对我国教育学教材研究的批判不绝于耳,认为我国现行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教育教材缺乏我们民族的特色,脱离我国教育实际,脱离我们民族的教育历史,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那些优良的、科学的、合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成就。[3]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古为今用”重视不够。
当然“古为今用”并不等于向传统回归,到教育历史文献中去寻找教育研究的全部材料,甚或沿用中国原来使用的传统术语和名词,而是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对古代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原则等进行审慎的分析与批判,总结其历史的经验教训,找出中国古代教育内在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扬弃性的改造。
第二,教育研究要做到“洋为中用”。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虽然都是发生、成长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之内,但生长到一定程度,文明必然要突破固有的躯壳向外传播。从总体上看,这种传播是双向的。教育如此,教育研究亦如此。文化交流的历史告诉我们,外来文化被接受、消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这从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
不过,在中国教育研究本土化的过程中,“洋为中用”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
其一,怎样突破凯洛夫的教育研究模式?这是长期困扰我国教育理论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影响了中国教育研究40多年,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其研究方式,也一直被教育理论界所甚用。正因为如此,教育理论界才反思不断。凯洛夫教育研究模式的缺点是明显的,许多人对此作过痛心疾首的批判,但偏激地将它“一棍子打死”,就没有道理。至少,他的研究方式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比如他十分注重教育学的心理学基础,比如他对教学论的系统研究等等。全盘否定凯洛夫,是一种荒谬的态度。对凯洛夫研究方式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恰恰说明我们不能辩证地分析问题。
其二,怎样对待当代国外的教育理论问题?这也是教育理论界的一个敏感而又热门的话题。别的国家不讲,只谈日本的。近10几年来,日本教育研究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大河内一男等著的《教育学的理论问题》等已在我国翻译出版。因内部分教育工作者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认为教育研究应该是“问题研究”,教育理论应改称为“教育问题的理论”等等。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一定十分正确。因为教育中的任何问题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表现为问题,质言之,现象与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教育研究如果只关注“问题”,则会忽视“现象”,甚至对教育领域某些明显的“现象”缺乏敏感性。这样,教育研究很难透过现象探讨教育活动的本质。
其三,“洋为中用”的内容是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国外当今优秀教育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吸收与运用上?应该说,不是的,其内容应扩大到国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凡是对我们进行教育研究有用的,我们就要大胆地借鉴、吸收,特别对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更应如此。近年来,系统科学、自然科学在教育研究中被广泛加以运用,但真正领会其实质,并与教育研究很好结合的,还较少见,社会科学中诸如社会学的调查分析法在教育研究中也并未得到较好运用。“洋为中用”的目的,是要扩大眼界。借鉴内容人为地过于狭窄化,是不利于我们进行创造性转化的。
第三,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要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出发。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无论科技、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中,这是当今世界发掘发展的共同趋势。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对此,教育研究不应熟视无睹。
社会变革的诸层面中,对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观念的变革。在我国,教育的重要性已日渐被人们所认识,教育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有识志士的广泛关注,迫切需要通过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由于教育工作者工作性质不同,有些人是从事宏观决策的,有些人是从事具体教学工作的,再加上这些人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有的文化程度较高,有的较低;有些是教育问题的专家,有些则不太懂教育的有关知识,这就给教育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要么满足前者,研究重思辩性;要么照顾到后者,研究重经验性。要想在研究中做到二者兼顾,确实是很困难的。目前国内有些学者提出的“普及”与“提高”并重,笔者认为在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难以实现,不过,从教育研究的总体上去要求还是可行的。教育研究应该呈现多种格局,体现出层次性的特点,有的重思辩性,有的重经验性,有的重“提高”,有的重“普及”让研究者自己依据实际情况抉择。从而在教育研究的总体格局上体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来。
教育变革是社会变革的一根敏感的神经。教育研究要把握住我国社会变革的国家脉搏,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问题。随着社会的变革,有些问题的探讨可能越来越深入,教育研究要适应这种变革的需要。
注释:
[1]张胜勇:《建构与反思——20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54页。
[3]郭齐家、毕成:《教育面向现代化与儒学教育》,《中国教育学会通讯》198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