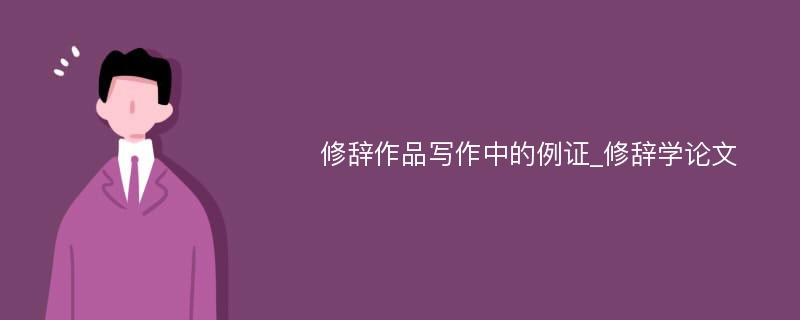
修辞学论著写作中的例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论著论文,例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例子在修辞学论著中,特别重要。
台湾修辞学家董季棠在他的《修辞析论》的自序中说:
“其次是辞例的搜寻。以前所记诵的名文佳句,用来讲课有余,取作著书不足;而有些记得的文句,却忘了出处;更有些只剩浮光掠影,不省全文。为解决这个问题,书桌上排满了书真像獭祭鱼;爬罗剔抉,又如沙里淘金。再其次是有了辞例,怎样去分析它。多数辞例,固然意义明确,容易了解作者的用意;但少数辞例,意义隐晦,很难猜透作者匠心,而精微要妙之作却正在这些辞例中。为了加上适当的分析,夜半不寐,蹀躞寻思,也是常有的事。又其次是,别人认为平凡的辞例,笔者认为不错;别人认为有名辞例,笔者却认为不好。评优论劣,下笔实难。排比研判,斟酌推敲,常有旬日踌躇的情形。这样念兹在兹,除教课外,所有时间精力,灌注在此,经两年而完稿。再经修饰琢磨,成为本书。”(台湾益智书店1988)
这是叫人不得不佩服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修辞学家都像董季棠教授如此地重视例子的。不同的研究者对例子的态度也不一样。台湾修辞学家在例子方面是非常重视。运用大量第一手的精当的例子来说道理,是他们的论著的一个特色。大陆修辞学家中,也有对例子非常重视的。但是比较而言,忽视例子的现象还是存在着的,有些偏好理论创新和建立理论体系的论著,常常随手从他人处借用(抄袭?)例子,甚至通篇都没有自己寻找来的例子。
对例子的不同的作风,反应了研究者、写作者对例子在修辞学论著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不同的认识。
例子在修辞学论著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修辞学论著中如何运用例子?如何评价修辞学论著中的例子?目前修辞学论著中的例子有哪些偏差?
这些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似乎是多余的,不值得一谈的。但是,我长期起来,就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不简单,也并非可有可无,其实是很值得谈论的,而且还不容易说清楚。
这里提出些问题来,目的是希望大家关心,共同解决。
二
对修辞现象,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即使是不自觉的看,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对修辞现象有这样那样看法的人当中,具有有系统的固定的看法的人,就是不少的。这其中有一些人的系统的固定的看法,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他只是为自己的,并不对他人说,更不为他人写作,那他就不是一个修辞学家,因为他的修辞学思想不能为他人所把握。没有修辞学论著的人是很难算是修辞学家的。
修辞学论著,是修辞学家之所以是修辞学家的资本与标志。它是写给他人阅读的。所以修辞论著的语言表达形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修辞学论著的理论体系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修辞学论著与语法学、语音学和语义学论著有所不同。对于语法学。语音学和语义学论著,读者与学术界,不大注意它的语言表达形式,重视的只是它的内容——学术命题与理论体系。即使注意到了,也绝对是放置在第二位的。然而,对于修辞学论著,人们往往很是重视它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果说一部语法学、语音学和语义学论著的表达形式不怎么的好,人们总是原谅的,那么,要是一部修辞学论著的表达形式不好,人们就常常要加以指责,不大肯原谅。这是可以理解的,身教与言教要统一——如果拟定学说是正确的有效的,那你自己的语言表达为什么如此差劲儿呢?你的修辞学理论是否科学,读者有权首先用你自己的修辞实践来检验!
读者对修辞学论著的语言表达有较高的要求,这是对的,不应当反对的。
但是,细细一想,这也并不完全统一。二者之间有差异有距离,本是正常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在科学的各个部门里,都是同样存在着的。因此,我们认为,应当把修辞学论著的理论体系与它的表达形式区别开来,在评价一部修辞学论著的时候,它的学术价值只能是根据它的理论体系来评定,其学术水平并不取决于它的语言表达水平。虽然学术高语言表达也好的修辞学论著是存在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也一定存在着学术水平高而语言表达差劲的修辞学论著和学术水平低下但其语言表达水平极高的修辞学论著。这时候,从修辞学的学术观念上看,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学术水平高而语言表达差劲的修辞学论著,而不能够给学术水平低下但其语言表达水平极高的修辞学论著以较高的学术评价。因为在给一部修辞学论著作学术鉴定、评论的时候,其主要的根本的标准只能是它的修辞学体系,而不是它的表达形式,语言表达水平的好坏是第二位的,并不很重要的。
如果把修辞学家论著区分两种类型,一是以推动修辞学学科的进步为重要目标的,二是以普及修辞学知识为任务。那么我们前面的话就有些偏激了。只是对前一类修辞学论著,才能够如此要求,而对于后一种修辞学论著,在对它的评论中,其语言表达水平似乎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前一类修辞论著,我们不必,不应当过多地从语言表达方面来苛求它。但是,对于后一类,读者与学术界是完全可以同时从语言表达方面来要求与评论的。
三
修辞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例子也没有的修辞学论著好象是没有的。与语法学和词汇学相比,例子在修辞学论著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例子几乎是修辞学论著的生命,是修辞学论著的评价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就出了“修辞学论著的理论体系与所选择的例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语法学与修辞学都非常重视例子。但是,重视的角度有所不同。在语法学中,例子的合格性规范性是最重要的。而在修辞学中,例子的好、美、艺术性、权威性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修辞学比语法学更加重视例子的出处,要求是名作名篇名言。不管同意不同意修辞学是为美之学,但是修辞学家们几乎都承认修辞学是与美相联系的,所以对美的例子的追求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修辞学家的习惯了。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习惯,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语法学研讨会上,学者会对观点以及观点与例子的统一争论不休,但是不会为一个例子的好坏美丑而费口舌。在修辞学研讨会上,学者们会对某一论文的例子评头品足,指责他抄袭、陈旧,赞美他提供了第一手的全新的例子。在评论修辞学论著的时候,它例子多而美,总是大受赞扬的。
在修辞学研究中,对于例子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轻视、忽视例子,一味地强调理论体系的构建。
有些修辞学家把自己的全部力气花在理论的构建上,把自己的精力用在移植外国的理论学说活自己的思辩上,而以为例子只是事后用来证明他的创新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外来的后加的手法而已。忘记了理论是从事实概括抽象而来的,没有足够的语言事实,就不可能有修辞学理论。巴甫洛夫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翅膀。修辞事实是修辞学理论大厦的基础,任何修辞学理论都是从一定的修辞事实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其中也有人甚至先创造出一个理论体系来,然后随便地到他人的修辞学论著中去选择、抄袭一些例子来。其实,不是从修辞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纯洁思辩的、或者移植来的理论体系,好象只是一种空中楼阁、沙漠上的大厦。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大科学家巴甫洛夫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翅膀。“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总是主张,人类知识的最高任务就是给我们以事实而且只是事实而已。理论如果不以事实为基础就会是空中楼阁。”(卡西尔《人论》74页)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是,的确是不能否定的。
如果忽视例子的作法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倾向,那可能是很不利于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的。中国修辞学的真正的科学现代化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英国学者卡尔·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第一章第七节“科学的无知”中批评了“体系贩子”:“急躁或沉湎构造体系都是无用的。谨慎而辛勤地分类事实比当前在时机成熟之前就下结论,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进展。”(21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恐怕这也是中国修辞学现在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二种,高度重视例子。这里又有两类。
第一类,可以称之为“为例子而例子”,不想探索和创造修辞学理论体系,只是把例子当做证明已有的修辞规律规则的手段,有时也是在显示、炫耀自己发现选择例子的才能。这一类论著对修辞学的普及是有大功劳的,作者的劳动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不指出,对修辞学的科学发展繁荣的益处并不大。
卡西尔是不同意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他接着说:“但是,这并不是对可靠的科学方法这个问题的回答,相反,它本身就是问题。因为,所谓的‘科学的事实’是什么意思呢?显而易见,这样的事实并不是偶然的观察或仅仅在感性材料的收集下所给予的。科学的事实总是包含一个理论的成分,亦即一个符号的成分。那些曾经改变了科学史整个进程的科学事实,如果不是绝大多数,至少也是很大数量,都是在它们成文可观察的事实以前就已经假设的事实了。”(《人论》74页)所以他告诫人们:“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人论》30页)这话是很值得中国某些修辞学家深思的,因为他们常常为自己找到了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例子而沾沾自喜,甚至把这些例子当做个人的财富。
第二类,对于例子的高度重视,是因为:修辞事实是他的理论的来源和依据,任何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他所观察到的修辞事实的一种分析和感悟与描写和解释。修辞学论著选用例子的目的是要证明和阐述其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理论更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可接受性。但是,例子只是例子,例子决不是理论和例子体系,例子的丰富并不能保证生成出一个比较科学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来。这正如卡西尔所说:“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人论》30页)在修辞学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修辞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修辞思想或修辞理论的财富。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复杂的修辞现象迷宫的理论上的指路明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修辞现象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
四
例子在修辞学论著中的功能是什么?
直到目前为止,修辞学界对于例子往往比较注意与重视美的要求。而从科学体系方面来考查和评价例子的相对要少一些。
台湾学者王熙元在评价黄庆萱的《修辞学》的时候说:
“‘选例要选最好的作家’,黄氏做到了;‘选例要选最好的例子’,这一部分尚待充实。以余光中为例,他有许多‘名句’没有选入,已选入的句子中又有些相当平凡的。这些地方修改很容易。”(黄庆萱《修辞学》602页)
这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意见。这一要求有其合理的地方,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修辞学的看法——把修辞学当做是一种鉴赏指南了,修辞学成了唯美之学了。其实,在修辞学论著中,本身平凡的例子,是不可缺少的。一来,既然例子的功用是说明阐释理论的,那么只要能够证明理论观点,成为体系的基石,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使这例子本身是平凡的;二来,例子平凡可以缩小修辞学理论与学习者之间的距离,给他们亲切感,增加他们的信心。
如果修辞学不是生花妙语的鉴赏之学,而是一门科学,那么,在修辞学中,也如同在语法学中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例子只是理论的来源和证明理论的论据。修辞学论著一味地重视例子的美,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修辞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能够最恰当地证明这一理论的例子就是好的例子,并不在于这个例子本身是最好最美的。重要的是理论本身是否符合事实的,是否有说服力的,而并不在于所选用的例子的美丑。重要的是理论原则本身的价值,而不在于所来证明这一理论的例子的美或丑。过分重视例子本身的美,一来必将削弱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的注意力,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二来也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八十年代,一个考研者说:因为参考的修辞学著作的语言表达太美了反而忽视了对内容的把握,结果才没有考取。这话多少还是值得注意。当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修辞学论著不需要。也不能够运用美的例子来作为自身的表达形式。
真正的修辞学家决不能是整天寻找美的例子的人。如果修辞学家只是寻找与收集美的好的例子,那修辞学论著当做是美的好的例子的汇集、汇编,那么对作为一门科学的修辞的发展和繁荣来说,则是没有多少益处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就读者而言,他阅读修辞学论著的目的不在于重复论著中美的例子——这是不可重复,重复了也毫无价值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握理论体系。例子平常而简单,他会感觉到亲切,就像老朋友。他就会有去实践的欲望,他就相信他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一理论。例子太美,他会觉得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就像是面对一个时装模特儿!太美的例子牵涉的东西太多,一时难以把握,也很难实践,于是,他就只能欣赏与赞叹而已。甚至会产生自卑感。
我的想法是,修辞学论著应当重视例子,但是例子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修辞学家不应当忘记自己的目的。而且他重视的应当是最恰当的例子,最恰当的例子不一定是最美的例子。修辞学家应当更多地关心理论体系,而不应当把自己的有限的精力过多地花在对最美的例子的求索方面。
认为寻找与收集最美的修辞例子,就是修辞学研究,这可能是一种误解。这对修辞学的科学化是无大好处的。
五
修辞学论著中运用例子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应当是论点与例子的统一。但是,做到这一点也颇不易。唐松波、黄建霖主编的《修辞格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
〔反对〕上下两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对。
或作报告,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反对的定义中说的是“上下两句的意思”的意思,并不是其中的个别词语的意思!那么,“无实事求是之意”与“有哗众取宠之心”的意思是相反的么?不是。事实上,“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中取宠之心”!“实事求是之意”与“哗众取宠之心”是相反的,但是加上了“有”与“无”,整个句子的意思就相同或相近的了。所以这不是反对,而是正对。编者对正对下的定义是:“上下两句的意思相同或相近或相补相对。”“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是完全符合这一定义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本身是一个好对联,但是在这部辞典中作为反对的例子就不是一个好例子。
要做到例子与观点的统一,就要求定义明确经当,不模糊。
经典的修辞论著中,也常常会偏差。例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对“飞白”下的定义是:“明知其错故意仿效, 名叫飞白。 ”(16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他的这一定义, 许多修辞学论著中都坚持着这一定义。陈望道所引用的例子是鲁迅《鸭的喜剧》:
在旁的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希珂”,当然是错了。但是,这孩子并不是“明知其错故意仿效”,他还以为这是正确的说法呢!这里的例子,几乎都是如此,《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与李贵,都不少“明知其错故意仿效”的。
真正符合陈望道的定义的例子,是他所举的《聊斋志异·嘉平公子》中的那首讽刺诗
一日,公子有谕仆贴,中多错谬。“椒”讹“菽”,“姜”讹“江”,“可恨”讹“可浪”。女见之,书其后云:
“何事可‘浪’?花‘椒’生‘浪’。
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那公子,并非“明知其错故意仿效”,所以不是飞白。作者只是如实写来,也算不得是飞白。他不这样写,你叫他如何来写?只有这首讽刺诗才是“明知其错故意仿效”,是飞白也。
符合陈望道的定义所要求的例子,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谈话:
请不要再吹毛求“屁”啦!
你怎么总是心不在“马”呀!
哇,好一个风度“piapia”的绅士!
“piapia”,快钻进来吧!
但是,你不可以简单地否定陈望道,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说的写作者的鲁迅与曹雪芹的“明知其错故意仿效”。
其实,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表达者——说话与写文章的人,小孩子、史湘云、李贵等;第二是复述与记录者,鲁迅与曹雪芹等。由于陈望道下定义的时候,没有明确区别这两种情况,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混而为一了,于是所举出的例子也就是不同性质的,不纯一。那么读者对这一个修辞学格的把握也就是模糊的。
再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李贵无知,胡说八道,把《诗经》说错了,效果是好的,但是如果把它当做成功的修辞的一个例子。那就不妥当了。因为修辞是主体的一种积极的活动,李贵既然并不是自觉地主动地运用错误来提高自己话语的表达效果,那显然就不是修辞活动。然而,这个例子常常被当做成功的修辞,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还不够严密,对例子的运用的重视也还不够。这是应当加以改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