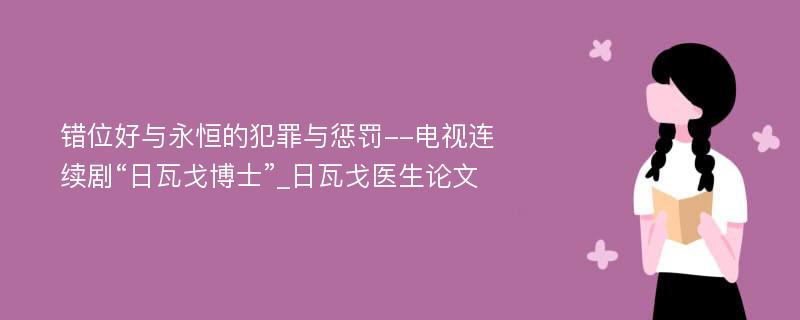
错位的善与恶 永恒的罪与罚——评电视剧《日瓦戈医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视剧论文,医生论文,罪与罚论文,日瓦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日瓦戈医生》凝聚了帕斯捷尔纳克毕生的心血,为他带来巨大的荣誉和灾难。在读者心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继1965年和2002年美国好莱坞、英国相继拍摄了同名电影及电视剧后,2006年这部作品终于在俄罗斯被搬上了荧幕,改编成了十一集的同名电视连续剧。2006年5月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大影视论坛里,网友们各抒己见,评论家们也纷纷撰文品评。在2006年度俄罗斯电视“金鹰奖”评选中,该剧荣获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最佳美术四大奖项。
该剧导演亚·普罗什金在俄罗斯国内享有盛誉,执导过《53年寒冷的夏天》、《俄罗斯暴乱》等广受欢迎的影视作品。编剧尤里·阿拉鲍夫(Юрий Арабов)是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奖的获得者。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日瓦戈医生由奥·缅什科夫扮演。这位2000年曾因在《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中的精彩表演荣获国家文艺奖的俄罗斯人民演员,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除了外形与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主人公神似:“长得不帅,翘鼻子”,更是把主人公20多年沧桑岁月的变迁演绎得淋漓尽致。经验丰富的老演员奥·扬科夫斯基为头号反角科马罗夫斯基增色不少。而秋·哈马托娃扮演的拉拉从外形到内在,独具特色,也深得好评。
对于熟悉原著的观众而言,这部电视剧犹如一棵被砍去了繁茂枝叶的大树,只剩下了主干,未免感觉单薄,意犹未尽。名著的改编本来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编剧阿拉鲍夫采取了“形异神同”的改编方式:“基本素材取自原作,但对原作的诸多方面作了较大的调整、整合。而这种调整和整合是原作不具备的,是改编者的一种艺术创造。”[1](112)除了把小说语言转化为戏剧语言外,阿拉鲍夫对原著做了大刀阔斧的删改。略去了大量的背景交代,减少了很多人物,对人物的命运也作了改编。与另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大师和玛格丽特》相比,大师还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但日瓦戈已是阿拉鲍夫的日瓦戈了。难怪在片头字幕上,没有打上:“根据帕斯捷尔纳克作品改编”,而代之以“根据帕斯捷尔纳克创意改编”。巧妙的一词之差,给了改编者很大的空间。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对电视剧的改编颇为不满:“谈论这种改编毫无意义。人物情节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是那些漫画般可笑的人物,和荒诞的情节。”[2]
与之相反的是,该剧的主创人员和大多数观众却认同了这种符合当今社会观点的改编。距离小说《日瓦戈医生》问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日瓦戈及其所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牵动了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心。每个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日瓦戈、拉拉、科马罗夫斯基。好莱坞的改编尽管获得了奥斯卡奖,却并未得到俄罗斯人的认可。他们认为,电影中表现的并不是俄罗斯。英、美、德合作耗巨资拍成的《日瓦戈医生》同样让俄罗斯人感觉,画面虽华美壮观,但只求得了形似而非神似。导演普罗什金认为,“虽然这两种版本在西方人当中引起了轰动,让西方人认识了帕斯捷尔纳克。可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真正让电影成为一座丰碑,让人们记住这位历经磨难的作家。”[3]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上个世纪的作品,编导首先考虑的是本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因此需要对原著进行一番时代性的选择。俄国版的《日瓦戈医生》已经不是对历史的重现,而是21世纪的俄罗斯人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对当今社会的剖析。它不再拘泥于再现近百年前这个国家的人民遭受的灾难,而是通过重新塑造人物形象,告诉人们在时代变革中的处世之道。
俄罗斯知识分子到底是怎样一种人?数百年来,探讨者众多。《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吉舍夫被别尔嘉耶夫称为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他曾说:“我的心被人类的痛苦充盈。”[4](17)这句话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沉重的,落寞的,淡泊的,或者说不得志的。帕斯捷尔纳克塑造的日瓦戈正是体现了这种宿命。在革命的洪流中,他既没能拯救国家,也没能保护自己的小家,甚至无力捍卫自己的爱情。落魄一生,最后黯然离世。在俄罗斯的传统中,英雄不是叱咤戎马,挥刀冲杀的人,而正是这种历经磨难却一事无成的人。像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良心,可是这也无法让他摆脱罪孽的困扰,只能用痛苦荡涤心灵。屏幕上,当格罗梅科教授勾搭上了家里的女仆,终日沉溺于杯中物;当医院的学术权威更关心的是何处才能买到更好用的炉子,当日瓦戈医生为了面包不得不与妻子沿街叫卖,每个人都会问,这究竟是谁之过?电视剧比小说更直接地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个人的眼前。小说中,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总是能以一种近乎神秘的力量在关键时刻帮助他,可电视剧里,编导残酷地删掉了这个救星,让日瓦戈独自一人在清苦的岁月中飘摇,在有轨电车上静静地死去。当他人生的列车缓缓驶向终点,红色的大门在他身后紧紧关闭。
在剧中改变最大的是拉拉的形象。她成了一条贯穿全剧的线索。片中,日瓦戈因受伤在野战医院重逢拉拉。他们谈到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时,后者的一句话:“世界上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那就是罪孽,负罪感。”成为了全剧的主题。拉拉周旋于三个男人当中,至少造成了其中两个人的悲剧。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场赎罪之旅。其他人也何尝不是如此。罪与赎罪成为剧中每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主题,她就像一朵美丽的恶之花。有放荡桀骜的一面,也有正直率真的一面。她给了日瓦戈梦寐以求的激情,但也为后者酿成了妻离子散的苦果。她一面忠于自己的丈夫,可同时又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剧中,拉拉与安季波夫相识于街头游行的混乱中。从一开始,她便成为了绝对的主宰,让安季波夫目睹了自己与科马罗夫斯基的调情,对安季波夫忽冷忽热之后却突然向之求婚,新婚之夜,曾半推半就委身于科马罗夫斯基的她却难于向丈夫献出自己的身体。影片中专门设计了一个小说中没有的场景:婚礼上,牧师刚拿出结婚戒指准备让新人进行下一步仪式,安季波夫激动地一把抓过去套在了自己手上,然后却无论如何也取不下来了。后来,当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在妻子心中的位置,在参军奔赴前线的列车上,戒指被轻而易举地取了下来,并被他抛出了车外。这一戴一取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安季波夫对拉拉的态度:他曾如此热切地梦想着这个上天送给他的尤物,没曾想到的是,这却是铸成他一生悲剧的开端。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抛弃家庭,抛弃一切人世的凡俗,包括父子感情,做一个纯粹的职业革命者。戒指在这里有了明确的象征意义:这个婚姻的证物却成了人世悲欢的转折。从大喜到大悲,也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小说中对他们的婚礼完全是另一种描写,场面热闹、温馨。亲友祝福,“一对年轻人含羞带笑地接吻”,“为了帕沙的幸福,拉拉宁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于是她尽量把蜡烛举得很低。不过还是没有用,因为不管她怎么想办法,她的蜡烛总是比帕沙的高。”[5](94)而电视剧里,肃穆的教堂里,在幽幽烛光的映照下,写在一对新人脸上的全是紧张、不安,甚至惊恐。错戴的戒指更让这桩婚姻平添了些许滑稽色彩。
影片的开头是老日瓦戈和科马罗夫斯基分别在火车上结识了戈尔东父子和拉拉姐弟。随着老日瓦戈跳下铁轨,火车急刹,在餐桌上交谈正欢的科马罗夫斯基和拉拉姐弟面前血红的葡萄酒轰然倒下,染红了桌布。一大片红色弥漫开来,充满了整个屏幕,颇具视觉冲击力。这红色,既宣布了革命的开始,又预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当一个男人在三个女人中选择的时候,“每次都出现在女人中作出自由选择的情况。而且这种选择必定落在死亡上。没有人愿意这样选择,可命运偏偏让人成了死亡的捕获物。”[6](63)日瓦戈不幸又落入了这样的宿命:在他的三个女人中,他最爱的拉拉却是他的死神。拉拉的一生充满了罪孽:对自己的母亲(勾搭母亲的情人),对丈夫(无爱的婚姻),对日瓦戈(破坏别人的家庭)。这注定她的一生必定饱经磨难,洗涤罪恶,获得重生。原著中,帕斯捷尔纳克让她在送走自己心爱的人后,不知所终,或许进了集中营。这恰是她洗涤心灵的最好归宿,如同《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的流放之旅。而影片中编导或许出于对女主人公的同情,给她安排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流放地:日瓦戈从收到的妻子的唯一一封信中得知,冬尼娅在巴黎看见了带着两个女儿的拉拉。她同样在流放中完成自己的赎罪之旅。
拉拉这个角色的塑造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尽管她已经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形象,但她具备了今天现代女性的元素:泼辣干练、敢爱敢恨、独立自主、心地善良、收放自如。难怪有人把她称为近八年来荧幕上最成功的女性形象。[7]
另一个改变很大的形象是科马罗夫斯基。同美国版《日瓦戈医生》相比,科马罗夫斯基不是个大腹便便其貌不扬的市侩,而是一个风度翩翩,还不时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形象。由老演员扬科夫斯基扮演的这个角色十分出彩,也最具现实意义。毫无疑问,科马罗夫斯基是片中最大的反角。他圆滑世故,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占尽风头。但他究竟错在哪里?他刚好是日瓦戈的投影——一切正好相反。他合理地利用了日瓦戈所唾弃的一切,却得到了后者所得不到的东西,甚至成为后者某种意义上的救星。日瓦戈的善良、真诚与爱情都无法拯救拉拉母女,而科马罗夫斯基的罪恶与谎言却让她们逃离了窘境。科氏是每个时代的胜利者,日瓦戈却总是被时代抛弃。善导致痛苦,恶却能拯救。这是命运的嘲弄吗?日瓦戈的时代过去近百年后,科马罗夫斯基类型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日瓦戈与科氏的对话已不再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对话,而是现代人对生存之道的思索。1999年俄罗斯《文学报》主编尤·波利亚科夫的小说《无望的逃离》也正是一部四十年之后的《日瓦戈医生》。其中同样描写了在苏联解体前后两类知识分子的对话。一类坚守信念却始终不得志,处处碰壁。另一类却抓住每一次转折的机会,步步高升。人应该如何适应社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命题。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几经周折的国家,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有得势者与失势者,都会造就新贵,也会让另一些人失去利益。人们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回头审视,对科马罗夫斯基的形象会有更深的理解。当俄罗斯人已很少谈及“良心”,而代之以更模棱两可的“精神”,社会的道德观也开始悄然改变。
导演普罗什金承认,虽然他也认为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反面形象,但他对之深怀同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熟悉原著的观众感觉,这个科马罗夫斯基不但不够坏,甚至让人觉得可怜。拉拉以报复的心态接近科氏,多少有些投怀送抱的成分。目的达到了,可以将后者一脚踢开;弟弟需要钱的时候,又用自己的身体诱惑科氏。她完全成为了主宰,倒是后者为她时常受到情欲的折磨。日瓦戈一天夜里救了被抢劫受伤的科氏后,在他家里提及拉拉,科氏表现出明显的关切。包括后来对拉拉母女的拯救,科氏的形象变得更人性化。从中可以玩味出当代人对这类人物态度的微妙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附在小说最后大量的诗歌,在剧中出现不多。但最震人心魄的出现在影片的结尾。日瓦戈去世半年后,戈尔东来到日瓦戈过去的家,现在仆人马克尔已经成了这里的主人。戈尔东用钱买下了日瓦戈的遗物,包括他的诗集。影片开头,老日瓦戈送给戈尔东的一枚奖章从他指间滑落,画外音响起,日瓦戈亲自朗诵了《相逢》:“你我何处来,/有谁能说个明白?/尽管留有闲言碎语,/那时我们已不存在。”[5](520)镜头一一掠过发黄的诗篇,年轻时代日瓦戈的照片,以及他生命中重要的人。这恰似一首安魂曲,让医生动荡的一生终获平静。编剧把戈尔东塑造成了一个电影人,又特意让这个电影人来送日瓦戈最后一程。让他的诗在电影中升华,这也许正是编导的匠心所在吧。
导演普罗什金说:“成功描写我国20世纪历史的有三部作品:《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和《日瓦戈医生》。这三部作品能获得诺贝尔奖,绝非偶然。我早就梦想着把《日瓦戈医生》拍成电影,尝试着去了解、阐释我深爱的祖国,这个美丽、忧郁、折磨人、不可理喻又独一无二的国度和具备这些特质的人们。”[8]有评论称电视剧《日瓦戈医生》是“20年来最好的历史剧,也是20世纪以来最严肃,最有深度的电视剧。”[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