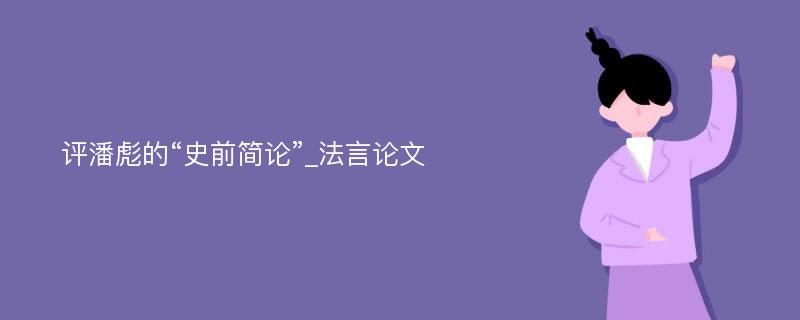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评班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4—0021—06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史学史论文,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值得注意。
一、这是篇史学史论文
班彪(公元3—54)是公元1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幼从学,长入仕,因“性沈重好古”①,“所如不合”,② 对做官兴趣不大,而“好述作”,“遂专心于史籍之间”③。在史学方面,他著有《史记后传》,写有《前史略论》。《后传》早已散佚,少数篇章或文字为其子班固《汉书》所汲取④。这里从略。《略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⑤,尤其是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才能,这是一篇简要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为了便于分析,避免断章取义之失,又因其文不长,乃全录于下: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皇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⑥
这不足700字的论文,内容丰富,试做分析。
班彪专就以前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发表评论,有据有论,言简意赅,可谓是一篇中国史学简史名作。专标史学,独树一帜,使得史学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单独成为一个学派。这是继司马迁“欲成一家之言”后的创举。故自《史记》以后,史学专门,单线发展,以至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学蔚为学术大国,成为世界文化史上耀眼的明星。
指出《史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意谓《史记》写当代史(汉史)厥功尤著。这十分中肯而重要。司马迁于《史记》写古今三千年史,略古而详今。其写秦汉百余年间的历史,约占百分之七十的篇章,写汉代史则占全书半数以上的文字。⑦ 班彪指出迁书写汉史功著的特点,又指明其书“下讫获麟”、“至武以绝”,也是为自己继《史记》而作《后传》张目,说明本人著作之必要与价值。中国史学有写当代或近代史的优良传统。整个“二十四史”都有这个传统的特点或影响。治史若不注重近世,意义不会很大。
指出《史记》是颇有价值的“可法”之书。说它与《左氏》、《国语》等等史籍都使“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故值得效法。但以为“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即写项羽列入“本纪”,写陈涉列入“世家”,而写当代淮南、衡山等王侯只列于“列传”,有“条例不经”之嫌。故其《后传》“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对《史记》体例作了一定的修正。这一点被其子班固写《汉书》所采用,不立世家,只是纪、传。自此以后的纪传体正史也大多是以纪、传为重点或只是纪、传而已。传统史学是以纪传为主体,是以人明史的。
二、着重点在史学思想
班彪评论《史记》着重点在史学思想。他论《史记》,略谈其取材、起讫、体例之后,便着重谈《史记》思想性问题,批评司马迁“议论浅而不笃”,抓住三点。这是需要推敲的。
先谈“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问题。所谓“术学”,这里是指先秦以来的儒学与诸子之学。所谓“崇”、“后”是言第一、第二或主次问题。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全录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具有明显的崇黄老而轻俗儒的思想。而对《五经》并不轻薄,是推崇的。他写《史记》,声明“继《春秋》而作”,推崇孔子,列《孔子世家》,并有“高山仰止”的赞语。书中还多有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观念。此中似有或崇黄老或尊《五经》的矛盾现象。我的看法是,司马迁将《要旨》列入《自序》,显然是接受了其父谈思想的哺育,而直接继承之。《要旨》所言的六家,既不是先秦以来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全面的思想或其主要思想,而是经过作者主观选择,根据汉初学术形势与趋向,有所取舍的六家在“治”道方面的精神,故他批评儒家的重点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点是汉世儒林的特点;而他所阐述的道家要旨,是吸收了黄老又取各家之长熔铸成的司马谈黄老思想。《要旨》大约产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大兴功利之元朔、元狩之际,以其与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国策大事针锋相对。当时,汉武帝信用阿顺苟合的儒者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大动干戈,大刮民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使得民众思想波动,生产下降,甚至社会不宁。司马迁于《史记》写《平津侯(公孙弘)列传》、《酷史(张汤等)列传》、《平准书》等篇,据事直书,并尖锐地针刺,而《汲黯列传》所写“学黄老之言”的汲黯,“无为”而治,对武帝及公孙弘、张汤等人当面指责。司马迁曾指出汉世儒、道两家是互相贬“绌”的。⑧ 在汉兴百年由“无为”向“有为”政治转化形势下,面对汲黯与公孙弘的政治思想交锋,司马氏父子鲜明地表示了思想观点,他俩是站在汲黯一边而讽刺公孙弘的。《史记》肯定汲黯为人正直,“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立浮说”⑨;讽刺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⑩,阿顺君主兴功兴利,“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11)。将《史记》与《要旨》两相比照,可见司马父子在刺儒崇道方面,灵犀相通,跃然纸上。班彪所评“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用词有点欠当,反映出论者思想倾向于汉儒,但其抓思想问题还是很准的。
再谈“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问题。司马迁于《史记》写了一篇《货殖列传》,大讲社会经济生活同历史发展、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经济生活之所需,社会发展之必然,秦汉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的封闭性的经济模式里去。司马迁以为人人都有“欲”,都求利,而且竞争,在求利竞争中产生了货殖人物,这些是优异人才,故特为其立传。此传写了古今几十个各种货殖人物,并指出有些富有者往往可与封君侯者相比,可称“素封”。还认为,人类求利,民众富有,是好事。民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国富则强盛,家富则明礼,人人才能尽为人之道。故言“无财作力,稍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以为求利竞争是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撰写了货殖人物之后,司马迁以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口气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守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意思是,所写这些富者,值得肯定的货殖人物,都不是靠特权特殊待遇及弄法犯奸而富,不是以特权谋私利而富,而是用力斗智,既营工商又务农业,从容治生,以致富有,所以值得称道。他鲜明地反对奸利,反对官与民争利,指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意思是推崇经营农林畜牧的“本富”为上等,肯定从事工商的“末富”次之,指责抢劫掠夺、盗窃、弄法犯奸等不正当行为而暴富的“奸富”最为下流,基于此,他对当时的经济政策还发表了异议,当时皇朝强调“崇本抑末”,即以农为本,抑制工商。官府轻视工商业者,政治上加以压制,经济上予以打击,官营盐铁以专利。司马迁则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提到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因之”、“利道”,即因势利导,让老百姓自主谋生,求利致富。中策是“教诲”、“整齐”,要求从事工商业者知礼义守法度,不能违法乱纪,否则要加以处治。下策是“与之争”,以为官府垄断经济剥夺民众之利是不可取的。在他看来,若有国家的因势利导政策,社会的安定环境,人们的勤劳致富,是大有可为而较为理想的,货殖人物是有作为而获得成功的。正因于此,司马迁才说:“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12) 意思是,人应该有所作为,可以求利致富,应尽为人之道,而以贫贱为光荣,好语仁义的漂亮词,是羞耻的。班彪不细审《货殖列传》的思想内容,仅抓住一点,片面地理解,而责难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显然偏而失当,知表而不知里。
再谈“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问题。司马迁于《史记》写了一篇《游侠列传》,热情地歌颂游侠仗义助人行为。他在《太史公自序》表述作游侠传之旨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此传表彰游侠为守信义之士,尤其是写郭解扶危济困而被官府迫害致死,极尽描绘之能事,并深情地发论:“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虽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这话语多么亲切,对郭解多么热情,对其死又是多么怜惜。此传的开篇说:“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故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韩非以为,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都予以针刺。而在司马迁看来,侠与儒不一样,儒之俗儒与处士也不同。儒士多称于世,在社会上吃得开,尤其是少数人以儒术取得公卿地位,围绕君主意旨转,更是名噪一时。这实际上是暗刺俗儒如丞相公孙弘之流,像季次、原宪等下层儒士,身居陋室,粗衣淡饭,自甘清贫,实在可怜。而游侠,其行虽不合于法度,然守信仗义,救困扶危,忘己助人,精神实在可嘉。下文又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矣。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入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意思是,今拘学孤陋之儒士,孤立于世,还不如面对现实,做有益于世之事。布衣之侠,能舍己为人,难能可贵。孤陋的儒士是不如布衣之侠的。这是勉励下层懦士弃孤陋之见,学游侠之长,做有益于世的豪杰。班彪认为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失之片面。“拘学”孤陋者并不能等同“守节”,学是要致用的;善意规劝也不是“贱”之,而是同情;而贵有益于世之“功”,有何不可!看来对儒与侠有不同的思想观点。
由此可见,班彪所谓“大敝伤道”乃俗儒之见,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尺度来衡量司马迁的论术学、序货殖、道游侠的。所谓“论议浅而不笃”,是指责司马迁不笃于儒家之论而自成一家之言。班彪着重抓史学思想,尽管其思想倾向与司马迁大不相同,但问题抓得很准,是很重要的。
三、注意叙事行文之才
班彪肯定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这是称赞司马迁善于叙事行文而为“良史之才”。这是很高也是很确切的评价。
所谓“善述序事理”,就是善于把史事原原本本、原委曲折、个中情理叙述出来。司马迁详写秦汉史,所写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化等等,都能纲举目张,条理分明,揭示出内情缘由。试以《平准书》所写汉代经济问题为例。其写楚汉之际的经济,“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同时有“不轨逐利之民”,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这就把战时经济特点勾画了出来。接着写战后汉初几十年间经济,官府重农轻商,“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于是社会经济复苏,个别私人已富了起来,国家的边防有所加强,官府的宫观舆马也开始增修。
再就着重写武帝时期的经济情况:“至今上(武帝)即位,汉兴七十馀年之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馀货财。”因汉初七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又无大的自然灾害,经济大有增长,百姓和官府都很富足,官库的钱粮很多,百姓穿衣吃饭不成问题,人们的行为也颇文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但此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豪强兼并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贵族高官“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司马迁感叹:“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到各色人等的思想与行为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善于叙事而点明的事理。
不尽如此,司马迁还写武帝因国有积蓄,民裕国富,欲有作为,便“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加之奢侈享用,使得经济捉襟见肘,“财赂衰耗而不赡”,“府库益虚”,“大农陈藏钱经耗”,“县官大空”。于是兴利,武帝以桑弘羊为干将,以张汤为助手,大事搜刮民财,残民以逞;不断地铸钱,卖官卖爵,定赎罪令,官营盐铁,算缗令、告缗令、均输法、平准法等等,花样百出。搞得政治腐败,官员失职,民心波动,生产下降,社会不宁,风气日坏。而由于搜刮到很多钱财,又大事兴作,继续征伐,铺张更甚,耗费惊人。于是民怨沸腾,张汤死“而民不思”,甚至天旱而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言。(13) 这样,《平准书》全篇就将楚汉之际因战乱而经济萧条,汉初几十年间经济逐渐复苏,有所好转,至于武帝即位之初已民裕国富,于是大事兴作,开支浩大,不久国库空虚,不得不用奸商酷吏搜刮民财,由是社会不宁,经济滑坡,民怨不已。在叙述经济问题时,把“事理”交代得一清二楚。
所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就是叙事行文真实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鄙,是说写实生动。写史实与人物,必须真实,不能虚假,不能粗劣,也不在于字句花哨,而要传真,传情,生动传神。有人说:“古人称史才,才者裁也。序事有裁制之为难,其要唯在辨轻重而已……传一人必择其人尤异之事而叙之,使曲折并列,上下四旁毕奏。”他举出《史记》写项羽巨鹿之战、垓下之战等,说是“摹写逼真,须毫欲动。”(14) 此论有点道理。《史记》许多传文都是如此。《项羽本纪》也不仅写巨鹿之战、垓下之战颇为逼真,就是写鸿门宴也很精彩。《鸿门宴》的文字历来脍炙人口,这里稍摘其中一些文字于次:“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范增也。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扑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以卮酒。’则与斗卮酒。”这段三百余字的文字,写情事、环境、场面、各色人物,以及人物的动作、言语、阴谋、神色等等,据实写真,无不绘声绘色。项羽之粗豪自大,范增之阴谋策划,张良之筹划应对,项庄舞剑之意,樊哙勇敢之为,无不曲尽其妙,生动传神。
所谓“文质相称”,就是行文与史实之吻合、恰当,即一致性、准确性。有人说:司马迁作《史记》传人写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洸洋、倜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轥、执辔蹑珠之状。余不瑕枚举,然若此者何战?盖各因其人之行而添颊上三毫也。”(14) 意思是说,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因其人其事其情加以描写,好像化工用模子铸物一样,做到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里试举司马迁写韩安国与狱吏矛盾一事为例:“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梁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15) 溺,音niào,同“尿”,即小便。韩安国言死灰复燃,田甲则说尿之;安国做大官后,田甲来请罪,安国笑曰可以尿了。此写韩安国与狱吏的对话,很符合身份、处境以及人物语言的特点,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并了解到韩安国仕途起落及长者风度,田甲为小吏的势利作风。可谓“文质相称”。
班彪根据司马迁善于述序事理,叙事行文准确、生动,而称其“良史之才”。这个称号,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也为学术界评断史家之良莠立了个标准。
四、在史学史上的意义
《前史略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班彪与扬雄曾有过接触。《汉书.叙传》提到班彪时说:“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对年长的大学者扬雄定会聆听教言,读过其书,受其影响。在《略论》中显然有《法言》的思想烙印。《法言》曾评及司马迁“《五经》不如《老子》之约”,“或问货殖,曰蚊”,“或问游侠,曰窃国灵”,以及“子长多爱,爱奇也”,“(或问)太史迁,曰:实录”,(16) 等等,这些观点,多为《略论》兼收并蓄,而以己意发挥之。而《略论》又直接影响其子班固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请看班固之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 这些评语,几乎是《略论》的翻版,还有可能是班彪的手笔,无论如何,班氏父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此思想,影响中国传统史学极其深远。
从班彪的《前史略论》可以得到几点可贵的启示:
首先,评论前史,或谓治史学史,要抓住史官、史家、史书、史学,要略古详今,要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作重点分析研究。
其次,应当认真剖析史家与史书的史学思想、撰史才能。关键是注意其史学思想倾向。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再次,在分析史家撰史才能时,要把握其是否述序事理,叙事行文是否准确、生动;如果是肯定的,则可称“良史之才”。这个桂冠的含金量很高,不可弄虚作假,也不可随意封赠。
还有一点,评论任何史家与史书,都需要一分为二,论司马迁与《史记》是如此,评今人今书也当如此。
[收稿日期]2006—05—20
注释:
①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
② 《汉书》卷100上,《叙传》。
③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
④ 见于《汉书》之《元帝纪》、《成帝纪》等篇及《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语等。
⑤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
⑥ 《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上。
⑦ 参考拙文《司马迁写当代史》,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⑧ 《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
⑨ 《史记》卷120,《汲黯传》。
⑩ 《史记》卷112,《平津侯列传》。
(11) 《史记》卷30,《平准书》。
(12)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3)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30,《平准书》。
(14) (清)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15) (清)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2,《释言》。
(16) 《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
(17) 参见《法言》之《重黎》、《渊骞》、《君子》诸篇。
(18) 《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
标签:法言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迁论文; 五经论文; 国语论文; 汉书论文; 史记论文; 平准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西汉论文; 东汉论文; 离骚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史论文; 后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