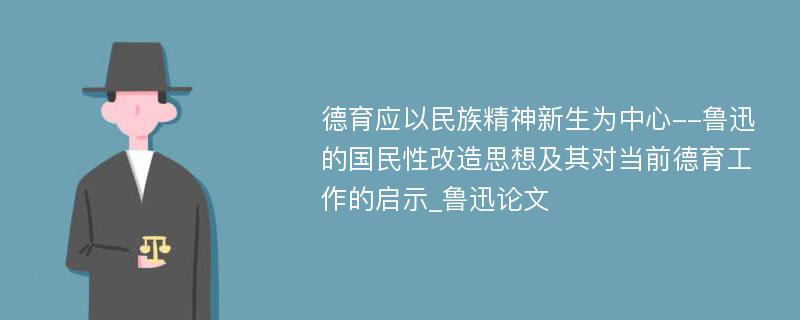
德育,应以国民精神的新生为着眼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及对当前德育工作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眼点论文,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启迪论文,德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1881-1936)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泽东语),也是卓越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中,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形成了意深义远、博大深邃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这是他留给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进入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深入学习和研究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当前的德育工作,培养“四有”新人,仍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价值。
一、改变国民的精神当为“第一要著”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国势日衰,救国成为当时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挫败,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先进的志士仁人愈来愈意识到,国民落后的精神状态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如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弱民无强国”的观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了“欲新国,必新民”的主张,邹容在《革命军》中发出了“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呐喊;鲁迅,则是这一思想探索的集大成者。自弃医从文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集中研究了国民的劣根性问题。他所提出的改变国民的精神当为“第一要著”的主张,是其国民性批判的起点和归宿。
较之前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刻,因为他不是空泛议论,而是切中时弊地深入解剖国民性。在日本仙台留学期间的一幕,深深刺伤了鲁迅的爱国之心:“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呐喊〉自序》)鲁迅由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改变国民的精神,是鲁迅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鲁迅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等,无不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一篇篇杂文更对国民的劣根性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特别在小说《阿Q正传》中,通过阿Q这个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把国民的劣根性集中概括为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具体讲,一即驯服与奴性。1934年,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描述了一个中国孩子两次照相脸部神情的变化:“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孩子了。”鲁迅进而指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奴性心态。犹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奴才一样,不是以抗争来改变自己的不幸,而是心甘情愿地做奴隶,“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我谈“堕民”》)这种奴性正是鲁迅感到最可悲哀的事。再即麻木和卑怯。鲁迅曾在《一思而行》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假如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的确是国民麻木心理的绝妙刻画。“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灯下漫笔》)鲁迅这话真是透彻极了!麻木是卑怯的反映:阿Q在赵太爷、假洋鬼子面前逆来顺受,在小D、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面前却显得很“英雄”。这就是卑怯者,决无抗争的勇气和本领,惟有遇到比自己更卑怯的同胞,才显出一点可怜的勇气。第三即圆滑与欺瞒。《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就代表着国人的圆滑,看似无所不知,却仅长于逢场作戏,止于“今天天气……哈哈”而已。“‘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当然,“聪明人”也有自己的本领,那就是瞒和骗。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第四即迷信与惰性。国人的迷信病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愚昧至极。1932年日本人占领上海不久,有一天上海的市民大放鞭炮,搞得日本兵很紧张。“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会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今春的两种感想》)原来,那天逢月食。迷信者不会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此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惰性。鲁迅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驯服、奴性、麻木、卑怯、圆滑、欺瞒、迷信、惰性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当然还有贪婪、不认真、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等。而奴性则是其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高兴。”(《灯下漫笔》)这是“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的通病。改变国民的精神,就是要改变他们愚昧、昏聩、低靡的精神状态,使之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性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讲,这要比政治、经济的变革更加重要。
鲁迅把改变国民的精神作为改造国民的“第一要著”,直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价值。就德育而言,更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德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所在;德育工作必须追求深层次的东西,而不可简单化。只有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新生,立足于国民性的改变,才是彻底的、真正的德育。换言之,德育要追求的是持久的、稳定的、本质的目标,而不是一时的、不确定的、形式的目标。建国以来,我国对德育不可谓不重视,这集中体现在“德育为首”的口号上。然而,德育的效果却始终难以令人满意,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并非妄言;相当长时期以来,德育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即是明证。我们认为,导致德育效果较差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放弃了对深层次东西的追求,没有把改造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作为德育坚定不移的目标,而是满足于一时,满足于肤浅。最严重的偏颇,就是用政治的目标取代德育的目标。政治与德育的确无法截然分开,但二者毕竟有本质性区别。政治以现实的问题为着眼点,德育则以国民精神的新生为着眼点;政治重在一时,德育则追求持久;政治处于多变中,德育则更趋稳定;政治注重形式,德育则更强调本质。因此,必须把德育目标与政治区分开来,真正把国民精神的新生作为德育一以贯之的目标。这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的最重要启迪。
二、改造国民性是个历史的过程
在鲁迅的研究视野里,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及文化条件制约下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的体现。劣根性是人性丧失和残缺的表现。改变国民的精神,就是驱除劣根性,改造国民性,促进国民精神的新生。
鲁迅认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历史上讲,长期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主要原因。“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这段骇俗之语,极其深刻地写出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虐杀和摧残。《故乡》中的闰土,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到“像一个木偶人”的变化,正是封建宗法制度吞噬人性的鲜明写照: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像毒蛇一样,已经紧紧地缠住了他的全身心,精神也变得格外呆滞麻木了。封建宗法制度完全扭曲了国人的灵魂,使之畸形、变态、麻木不仁,因为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取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灯下漫笔》)这是国民劣根性形成的内在历史根源。外来侵略则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外在原因,这包括历史上元、清两代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更主要的则是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从历史的考察中不难看出,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民的劣根性是历史的积淀。因此,改造国民性也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鲁迅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随感录三十八》)“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两地书》)鲁迅曾说过一句与其文学伟人身份极不相符的话:文学文学,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其实,这正是他对改造国民性之艰难的愤激之辞。这对当前的德育工作应当具有多方面的启迪。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应当认识到改造国民性依然是德育的基本任务。建国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明确地把改造国民性作为德育的一项任务,这是一种失误。国民性是历史的积淀,往往不会因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发生聚变。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经济变革相比,国民性的变化要迟缓得多。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已经沐浴在21世纪的阳光下,但恐怕我们还不能由此就说,鲁迅在近一个世纪前所痛陈的国民的一些劣根性就已经绝迹,至少那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及“谣言世家的子弟”,我们仍不感陌生;“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上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等现象,我们还经常耳闻目睹;至于“十景病”、“要面子”、“揩油”、“官魂与匪魂”、“党同伐异”、“奴才式的破坏”、“不为最先”、“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窃书不能算偷”等心态更司空见惯。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与国民的劣根性也并非毫无关系。那些腐败分子的思想境界,比起土谷祠里阿Q的“革命理想”,也实在高不了多少,许许多多的阿Q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二是应当认识到德育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过分强调所谓的“实效性”。我们不反对提高德育实效性的提法,但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若过分强调所谓的“实效性”,强调形式、“活动”、报告等这些有形的实效,则往往适得其反。正如前面所言,真正的德育应立足于国民精神的新生,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客观性。过分强调所谓的“实效性”,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以主观性代替客观性,以短期性代替长期性,以时效性代替实效性的弊端,说到底就是以形式掩盖本质,这正是德育工作中形式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每年的3月5日,大中小学校、党团工会都要大张旗鼓地组织各种学雷锋活动(须知,雷锋当年做好事是不留名的),形式上轰轰烈烈,但社会上却在流传着“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民谣,这就是我们的德育工作的效果!事实上,我们的德育历来都是轰轰烈烈,从现象上看效果也是不错的,正因为如此,才难以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中,更不能促进国民精神的新生。德育是塑造灵魂的工作,必须循序渐进,不能靠突击,更不能靠运动。只有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人们思想道德的进步和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德育才会有效果,这理应是德育追求的最大实效。德育的真正效果(也就是实效)往往不是指向当前的有形的效果,而是指向未来的无形的效果,这是德育工作的本质与规律的体现。
三、“致人性以全”
改造国民性为的是“立国”,而“立国”必以“立人”为首,“人立而后凡事举”,概言之,就是“致人性以全”,使国家成为“人国”。“致人性以全”,就是要真正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明白人生的要义,这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
“致人性以全”,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与国民的劣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题,它的核心是“立人”,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不是奴隶,不是“聪明人”,不是示众的材料,更不是看客。他们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鲁迅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随感录六十六》)他们正是开辟新路的先锋,是“中国的脊梁”。因此,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首要的是去奴性。奴性不仅存在于阿Q、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闰土这些不幸者的灵魂里,像咸亨酒店的掌柜、康大叔、赵太爷这些“上层”人的灵魂更浸泡在奴性之中。奴性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是人性的最大扭曲。怎样才能去奴性而“致人性以全”呢?鲁迅的主张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多次感叹中国向来只有“合群的自大”,而缺乏“个人的自大”。中国少有“个人的自大”,是因为中国庸众容不得“个人的自大”,这是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西洋人的民族性格是:“人+兽性=西洋人”,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则是:“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即现代中国的“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其区别就在于有“兽性”的人,具有不屈服于任何强暴,敢于反抗,敢于决一死战,争强好胜,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而失去了“兽性”的家畜,则“渐渐成了驯顺”,逆来顺受,柔弱卑下,充满奴性。鲁迅曾经主张人“不如带些兽性”,实质上正是对个性的期盼,对一种民族精神的期盼。“致人性以全”,“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鲁迅为改造国民性开出的药方。民族精神不是庸众的累加,而是无数个性鲜明的国民精神的凝聚。20世纪的中华民族正是由于造就出了以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众多个性鲜明的优秀国民,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毫无疑问,鲁迅关于“致人性以全”、“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对于当前的德育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完全应当成为德育工作的核心。德育只有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才能培养出能够承载民族精神、创造民族精神的一大批优秀国民。相反,如果漠视个性的存在与发展,只是按照某种固定的、刻板的模子,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就范,那就不是立人,而只能是对人性的扭曲,这是在制造“机器”,制造奴隶,是有悖德育之本义的。忽视个性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教育的传统弊端,在德育工作中尤为突出,至今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片面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片面强调社会的规范而忽视个体的自主发展,把德育简单化地理解为管学生,对学生管得太多,管得太细,惟恐有管不到的地方,就是无视个性的存在和发展。试问,这样的德育除了养成奴性,还能养成什么呢?这样的德育,实质上就是鲁迅最反对的“兔子式”的教育,只许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不许独立思考反对抗争。在《论“赴难”与“逃难”》的文章中,鲁迅这样说:“施以虎狮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前几年,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报道,曾引起举国关注。前事不忘,我们的德育工作的确该反思了。德育所追求的目的永远不该是整齐划一,千人一面,而是为了立人,为了成人。个性是立人、成人的核心。一个人只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个性,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也惟有这样的人,才会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德育就是为了造就这种具有完全意义的人,而不能是片面发展的、病态的、畸形的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德育工作必须“致人性以全”,“尊个性而张精神”。
四、解放儿童
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中,儿童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领挈其全部作品基本主题意向之总纲的《狂人日记》,最后的呐喊就是“救救孩子……”鲁迅认为,疗救“不长进民族”的根本方法,就是“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随感录四十》)。儿童是民族最根本的希望所在。“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改造国民性最后的落脚点就在儿童身上。只有彻底地解放儿童,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国民性的改造,这是鲁迅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正是由此出发,鲁迅对儿童教育寄予了特别的希望。
什么是解放儿童呢?就是使之获得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是要“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具体讲,解放儿童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把儿童从“静”的教育中解放出来,驱除奴性。鲁迅反对中国传统的对儿童的“静”的教育,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束缚成“低眉顺眼”、“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弯腰曲背”、“畏葸退缩”、“少年老成”的小老头,“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没落、灭亡。与“为儿孙做牛马”相比,这种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做牛马”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儿童应该健康、强壮、活泼、挺胸仰面,甚至顽皮,这才是鲁迅的主张。其二是指把儿童从“为所欲为”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克服任性。不能“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因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儿童,“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上海的儿童》)当然,鲁迅更清醒地意识到,解放儿童,培养后代健康地成长,“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在中国尤不易做”。解放儿童是一个“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的过程,需要“先从觉醒的人开手”,“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20世纪初,鲁迅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放儿童,这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儿童教育领域的一场革命。在鲁迅的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鲁迅看来,那种“百草园式的”生活才是儿童应当拥有的生活,而“三味书屋式的”生活则完全远离了童趣,是儿童发展的桎梏。那么,今天的儿童是否完全地从这种桎梏中解放出来了呢?恐怕我们还不能下此断言。今天的儿童以独生子女为主,在他们的教育问题上,家庭、社会、学校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这种教育却是重智轻德的、偏颇的教育。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用心良苦地让他们学唐诗,学识字,学算术,学绘画,学英语,学钢琴,学计算机等,几乎每天都要有学不完的东西,但惟独忽视了他们思想品德的发展。这种偏颇教育的代价就是,孩子们在变得越来越聪明的同时,任性、自私、懒惰、怯懦、贪图享受的心理也在令人担忧地日益膨胀,有的甚至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去年,发生在浙江金华的学生弑母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是重智轻德,缺乏必要的德育熏陶导致的必然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他们就会成为新一代病态的国民,那么我们的国民精神又将面临一次大倒退,这是不堪设想的。这种既“杀了现在又杀了将来”的教育是毫无前途的。鲁迅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仍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启迪,我们实在不该忘却。
诚如冯雪峰的精到评述:“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鲁迅的文学道路》)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鲁迅作为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给予了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最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鲁迅的这种影响在21世纪将会延续下去,仍然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21世纪的人们应当听到鲁迅的声音,21世纪的教育也应当继续从这位民族伟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启迪。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学论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灯下漫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