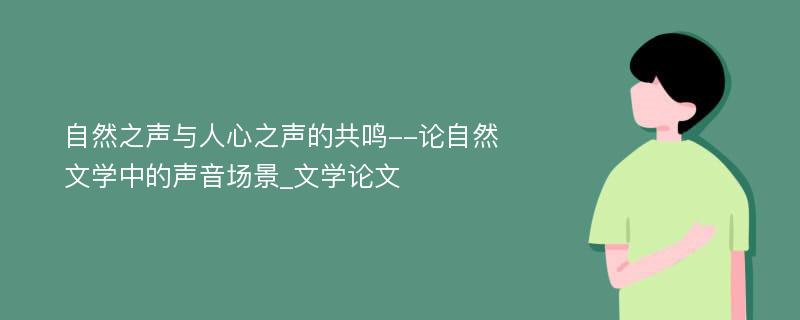
自然之声与人类心声的共鸣——论自然文学中的声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之声论文,共鸣论文,心声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3)04-0030-06
我们所熟悉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大都有一种对声音的偏爱。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专有一章写“声”,在抱怨了火车的汽笛声之后,他笔锋一转,将家乡康科德小镇的钟声、风声、牛叫、犬吠和鸟鸣写入自然的风景之中。贝斯顿(Henry Beston)在其代表作《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中,描述了在他那个被称作“水手舱”的临海小屋中倾听海浪的惬意。奥尔森(Sigurd F.Olson,1899-1982)索性将自己书写美国北部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的处女作以《低吟的荒野》(The Singing Wilderness)为题,生动地唤起了人们对原野的视觉和声音的感受。威廉斯(Terry T.Williams)则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或许现在如同以往一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聆听。如果我们真正地去聆听,大地就会告诉我们它的意愿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相应适度地生活。”(Jensen:315)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自然文学作家在写风景(landscape)的同时也在写声景(soundscape)。有评论家称之为“共鸣的写作方式”(the echo system of writing),即试图使文学中的声景与自然界的声景产生共鸣。(Chandler and Goldthwaite:84)
“声景”一词最初用于音乐领域,亦译为“音景”,后来它的使用范围扩展到环境保护、建筑设计等领域。近来,声景也被用于自然文学之中,即人们从声景的角度来欣赏评述自然文学作品。在充满噪音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听觉日益迟钝,诚如意大利哲学家菲乌马拉(Gemma Corradi Fiumara)所述,“现代语言已经失去了其‘生态合理性’的尺度。”她继而解释道,现代人不再能够听到大地及山河湖海的声音,不再能够听到诸如风声、树声、虫鸣、虎啸这些自然之声。(Chandler and Goldthwaite:91)自然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对“声景”的描述,旨在唤起那些我们曾经熟悉、但却渐渐离我们而去的自然之声的记忆,让我们去捕捉并欣赏自然之声带给我们的那些简朴的愉悦,从而尝试着去过一种留住自然之声、与大地的脉搏相呼应的生活。恰如特丽·威廉斯在其文集《无言的渴望:原野的故事》(An Unspoken Hunger:Stories from the Field)中说的那样:“回音是真实的,并非想象。我们呼唤,大地回应。那就是我们与生态系统的共鸣……”(1995:80)
当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对声音的重视,源于他们对远古的揣测。贝斯顿在其另一部作品《芳草与大地》(Herbs and the Earth)的开篇就写道:
古人有一种奇妙的幻想,即上苍之光,太阳和月亮,移动的行星,井然有序的恒星,当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和谐地运行时,都吟唱着自己的歌,因此使得宇宙空间充满了高贵的音乐。倘若人类的耳朵准备好了来享用这种悦耳的曲调,古人认为,那么,他或许就会在一个无云的正午,在一片宁静的高地上听到太阳高声呼唤的声音,在夜晚听到月亮的声音,那是另一种不是来自地球但却掠过大地及其家族的乐曲。
此时,贝斯顿转而问道:“在这和谐的天国之音中,大地又唱着怎样的歌曲?”他继而将自己的想象力注入笔端:地球在运转时迸发出的那种庄严的乐曲,大地上江海奔流、溪水潺潺的响声,树叶的抖动与雨声交织在一起的美妙,犁在农田中耕作时翻土的声音,甚至女人在梦中心满意足的吟唱。(2002:3-4)贝斯顿对古人那种对自然之声、天国之声充满敬仰的描述,体现出他对自然世界中声音的偏爱与重视,这与他另一本书的主旨不谋而合。
2003年出版的《早期美洲的声音》(How Early America Sounded)旨在表明,17至18世纪的美洲,人们是怎样用耳朵来倾听他们的世界的。或者说,美洲印第安人比我们现代人能够更多地利用耳朵这个感官,通过自然之声来感受和了解世界。他们那时听到的声音是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的“自然的”声音,是诸如雷雨声、瀑布声、风声等自然的声景(the natural soundscapes),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声音。由于当时生活在以听力为主的口述文化(ear-based oral culture)背景中,美洲印第安人经常将声音视为个性行为的象征。比如,他们将自己的歌声和话语视为如同雷声及风中树叶的响声一样的声音,是张扬个性的行为。(Rath:x;2;9;174)然而,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类早期某些对于求生至关重要的灵敏感官却因为不常应用而渐渐退化。当代美国作家约翰·海(John Hay)在题为《聆听》(“Listening”)的散文中就提到,现代社会中各种机器的轰鸣声已经压住了其他诸如鸟鸣与兽叫的自然之声。他写道: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成为视觉的生物(creatures of sight),即当我们走过一片风景时,并非充分使用天生的感官来解读它,因此看到的只是一片低落的、变了样的风景。大地以其多变生动的语言向我们述说,而我们却失去了捕捉那种语言的本能。(1984:142)
在《早期美洲的声音》一书中,也有与海相似的观点,但更为形象,即现代社会中,人类已经“以眼代耳”(an eye for an ear)了。(Rath:2)美国文化历史学家、作家贝里(Thomas Berry)曾说过:“宇宙成员的组成是用来相互交流的,而不是被利用的对象。万物都有其独特的声音。可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却变得自我封闭。我们听不见那些声音。”他在以《聆听大地》(Listening to the Land:Conversations about Nature,Culture,and Eros)为题的访谈中以印第安文化为例,提到了聆听自然之声的重要性:“我在这里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山河及星辰怎么说。”他解释说上述自然之物正当有力地说出了人类所需要的真实性,它们告诉我们关于生存的硬道理,那些诸如四季更替、生死及复苏的自然之奥秘。他还举例说明风是怎样传递它的神秘之声的:“风有其神秘之声;人看不见风,但风有声,风穿过树林,风传授着花粉。鸟在风中高高地飞翔。风唤醒了我们内心对精神的感觉,因为风承载着一个隐约世界的神秘感。”(Jensen:2;40)其实,贝里及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然之声的重要性,并非是要现代人走回远古或原始,而是想在这个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中,让人们从亘古以来就从容不迫地进行着四季轮回的古朴而又可靠的自然之物中找到人生的定力,听到自然的呼唤,体验到对自然世界的归属感。诚如奥尔森在《低吟的荒野》的序中所述:
漫长的原始社会已经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烙印。社会文明并没有改变人类历史开始之前我们那些情感的需求。那就是我们渴望倾听、不懈求索的原因。假若我们真能捕捉到远古的辉煌,听到荒野的吟唱,那么嘈杂的城市就会成为宁静的处所,忙乱的进展就会缓缓与四季的节奏接轨,紧张就会由平静来取代。(3)
在美国自然文学作品中,自然之声寓意非凡。约翰·海在散文《听那风声》(“Listening to the Wind”)中,为风声赋予了深远的含义:“听听风声,加入秋叶在风中的舞蹈,堪称与宇宙和谐共存。”(1995:45)这不由地使我联想到中国宋代名园沧浪亭石柱上镌刻的那副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至少东西方文化在一个层面上是相通的,那就是以文学的形式、词语的力量来描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品中对声景的描述,从动感及整体的美感方面体现出这种文学的潜移默化的词语之魔力。
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堪称史诗般的作品,写出了海浪的动感、悲壮及诗意:“秋天,响彻于沙丘中的海涛声无休无止。这也是反复无穷的充满与聚集、成就与破灭、再生与死亡的声音。”随后,我们跟随作者一次次地观看着海浪一个接一个地从大西洋的外海扑打过来。它们越过层层阻碍,经过破碎和重组,一波接一波地构成巨浪,以其最后的精力及美丽映出蓝天,再将自己粉碎于孤寂无人的海滩。贝斯顿还精辟地归纳了大自然中三种最基本的声音:雨声、原始森林中的风声及海滩上的涛声,他认为涛声最为美妙多变,令人敬畏。他劝导我们:“听听那海浪,倾心地去听,你便会听到千奇百怪的声音:低沉的轰鸣,深沉的咆哮,汹涌澎湃之声,沸腾洋溢之声,哗哗的响声,低低的沉吟……”浪涛声在他听来是不停地改变着节奏、音调、重音及韵律的音乐,时而猛若急雨,时而轻若私语,时而狂怒,时而沉重,时而是庄严的慢板,时而是简单的小调,时而是带有强大意志及目标的主旋律。难怪作者感叹道:“对于这种洪亮的宇宙之声,我百听不厌。”(33;32;35)从贝斯顿的描述中我们感到,是声景给了自然文学以活力、动感及诗意。如果没有声景,自然文学就会缺少立体感,甚至显得单调和苍白。
自然文学中的声景不仅仅是河与海的声音,它与风景结合有着整体的美感。比如,巴勒斯(John Burroughs)的代表作《醒来的森林》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林地全景。他写初春的林地:“蒲公英告诉我何时去寻找燕子,紫罗兰告诉我何时去等待棕林鸫,当我发现延龄草开花时,便知道春天已经开始了。”因为,延龄草标志着众鸟归来,暗示着醒来的森林。(5)试想一下,倘若没有鸟鸣、风声、水声及雨声,我们怎样能领略《醒来的森林》中的整体美?又怎能感受到寒冬已过、大地回春、万物苏醒的动感?贝斯顿在其另一部自然文学作品《北方农场》(Northern Farm)中没有描述汹涌澎湃的海浪,而是在一个寒冬的夜色中,静观一个封冻的池塘,倾听“冰的低吟”。一轮冷月照着孤寂的池塘,风扫光了池面的残雪,周边的田野树木在宁静的月光下都处于静止的状态。然而此时,作者从封冻的池塘中听到了一种颤动的、神秘的声音——那是一种当流动着的强劲力量受限制、被压抑时的号叫。他写道:
当我顿足聆听池下冰的声音时,意识到实际上我是在听整个池塘。举目向北,江河、海湾及河畔形成了一片冰川,而所有的冰都在月光下发出了滔滔不绝的声响。这声音时而来自东边,时而来自西边,时而来自某个远方的海口,时而来自隐藏在松树林下的小水湾。那池塘以其独特深沉的嗓音在呼喊。(Beston,1970:73-74)
寥寥数语,贝斯顿勾勒出了一幅北方寒冬的多维全景,他对冰声的描述则给这原本宁静的景色增添了冷艳流动的美感。
自然文学中的声景实际上是将自然之声与人类心灵进行沟通。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人类心灵的感应,自然之声难以成为“声景”。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论自然》中称“眼睛是最好的艺术家”。(877)由此,我们不妨可以说,倾听自然之耳是人类最美的乐师。自然文学中的声景,将充满动感的自然及心灵的风景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兹温格(Ann Zwinger,1925-)与友人一起泛舟,沿着美国西部最大的一条河绿河(Green River)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峡谷,横跨怀俄明、科罗拉多及犹他三个州,随后将亲身经历写就了一本书《奔腾的河流》(Run,River,Run:A Naturalist's Journey Down One of the Great Rivers of the American West,1975)。在此书的序言中,作者寥寥数语就把人们带入声情并茂的意境之中:“我生长于河畔。那是条不太大的河,就在路的对面……夏天,当树不摇、蝉不唱时,隔窗便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尽管水声不大,但却总是在那里。”作者动情地写道:“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继而,作者笔锋一转,向我们展示出另一条河流:“这本书是关于另一条河,一条大得多的河——绿河……在许多河段依然处于狂野荒凉的情况下,它是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对我而言,它是这世上最美丽的河流。”她是带着儿时就养成的那种强烈的河流感(sense of riverness)上路的:她从河水拍打在岩石和树木上的声音,从浪花打在手上的感觉,从河水散发出的多种气味中,感受到了它的表达方式。她甚至得出结论:一旦有了这种河的感觉,河就无所不在。一旦记住了河的气味,即便是在看不见河的风景中也能感到它的存在。《奔腾的河流》开篇的第一句是:“在狂风中我听到了那条河的源头。”而当作者的绿河漂流即将结束、她的书也开始向读者告别时,她感叹道:“我不想听这条河的尾声。”由此,我们看到声景从始至终都在《奔腾的河流》中闪现,这的确是一种出手不凡的写作方式。(程虹:48—53)
自然文学作家视荒野为一种情感,他们对荒野之声的描述中自然也充满了深情。比如,奥尔森在向读者介绍《低吟的荒野》的写作背景时,回忆起年仅七岁的他在伸向密歇根湖的一个险峻半岛上初次听到的湖中如泣如诉的雾号,那是一种心灵的反响,是一种对荒野之声的渴望,以至于他总是夜不成眠,听着远方茫茫暗夜中的那些低吟,思索着将会吞没它们的漫漫长夜的神奇奥秘。寻求荒野的吟唱成为他童年的梦想、一生的追求,而奥尔森的代表作《低吟的荒野》确然实现了他的梦想及追求。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于声景的描述,使得自然之声与人在荒野中的心声交汇。书中作家的感官发挥到了极致:在众鸟南飞、夜色朦胧的晚上,他听到了这种吟唱;在薄雾渐消的黎明、繁星低垂的寒夜,他捕捉到了这种吟唱。这种悦耳之声,甚至也可以在缓缓燃烧的火苗中、打在帐篷上的雨滴中听到。他深感这种荒野的吟唱,就像从悠久岁月中传来的回音,仿佛是往昔当我们与江河湖泊、高山、草原及森林心心相印时众心所向的某种内心的渴望,而现在却渐渐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内心才存有一种不安、一种对现实的急躁,于是聆听荒野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必需。(6)
当谈及渐渐离我们而去的荒野时,特丽·威廉斯说过:“如果你像爱一个人那样去爱荒野,那么,你就不会让它离去。”(2002:76)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荒野之声甚至比宗教更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因而弥足珍贵。在她的自传型作品《心灵的慰藉》中,威廉斯通过与大地的亲密接触,展示了自然界的声景,重拾现代人失去的听觉。在母亲去世后,她开车去大盐湖,路过摩门教会堂时,她听到了唱诗班的歌声,因为整个广场都在广播唱诗班的歌。然而,这些宗教之声并不能给她以慰藉,荒野之声却能够:“一到了湖边,我便如鱼得水。这才是属于我的土地。风在吹,浪在打,自然的节拍如同非洲的鼓点令人心动。……我甩开了长发,风吹着卷发,如同翻滚在水上的白浪花打在我的脸和眼上。风和浪。风和浪。”(240)重复的“风和浪”,以声景的形式增添了湖畔的动感,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波动。风景与心景在此巧妙地相遇了。①自然文学作家对于声景的描述旨在通过耳朵这个感官,让我们去捕捉、欣赏并爱惜荒野之声,从而体验人与自然界那种密不可分、血脉相连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仅是一种生活的必需,而且是情感及精神的渴望与需求。
由此可见,在自然文学作品之中,作者不仅在用笔书写自然,而且也是在用耳聆听自然,用心体验自然。因此,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含有风景、声景及心景(soulscape)②的多维画面。有学者认为,诸如威廉斯等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使用了诗意的呼吸法(the use of poetic breath),此法源于美国诗人及作家斯奈德(Gary Snyder)。(Chandler and Goldthwaite:100)斯奈德声称:“诗歌是声音之奥秘的载体。”他继而解释道:
吸气是外部世界进入人体,随着与呼吸同步的脉搏形成人体内部的节奏感。吸气是精神,是灵感。带着声音的呼气发出的是联结宇宙万物的符号。某些情感及心境会令你鬼使神差,于是,你便成了一个充满气流的管道——皆是声音。(53;57)
或许,正是由于熟谙这种诗意的呼吸法,某些自然文学作家才能与大地共鸣,自如地挥洒心中的诗意。威廉斯在其文集《红色:沙漠中的激情及耐心》(Red:Passion and Patience in the Desert,2001)中写道:
我想用青草的语言来述说,在风暴来临之前,小草轻柔地随风飘舞,但却又根植于大地。我想用南飞大雁的形体来写作,那雁群呈V字形飞向安全的南方。我想永保文字中的野性,这样,即使大地及我们所心爱的物体被目光短浅的贪婪行为所毁坏,依然会留下些许鸿爪雪泥,展示大地之美及有幸亲身体验之人的激情。(2002:19)
威廉斯生动地记录了她在一条溪流中漂游时所产生的这种激情:“水。水的音乐。黑色的音符,白色的音符,如同爵士乐,我的身体与水的载体相融合,水流如同爵士乐。我也自由自在地与水同歌。”(2002:202)与大地同呼吸,与自然中的万物同歌。人类的语言与大地的语言产生共鸣。自然文学作品中的声景给文坛注入了流动的活力。
①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撰写专文评述威廉斯作品中的“声景”,详见:Masami Raker Yuki,"Sound Ground to Stand On:Soundscapes in Williams's Work",in Surveying the Literary Landscapes of Terry Tempest Williams(U of Utah P,2003).
②心景(soulscape)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简言之,它是自然在人的内心所产生的共鸣,是一种人们看到特定自然景物时心灵的感受。在文学作品中,从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就开始赋予自然以精神的色彩,关注特定景物中精神的重要性,这种传统一直持续至今。比如,19世纪英国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就模仿“风景”(landscape)一词,首创了“内景”(inscape)的概念。2009年出版的《海景与心景》(Seascape Soulscape),是已故美国达拉斯大学英语教授柯蒂斯杰(E.C.Curtsinger)评述梅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的专著。在此书中,作者将梅尔维尔笔下史诗般的海上冒险视为“内在及外在的旅行”(inward and outward journey),声称“大海及心灵的神秘可以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