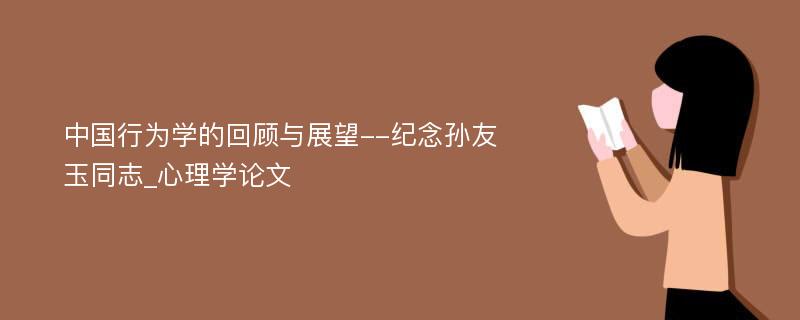
行为科学在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为悼念孙友余同志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而作论文,同志论文,科学论文,孙友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浙江大学的成立,原杭州大学的心理学系,因缘时会,拟扩展成为心理与行为科学学院。对行为科学,饮水思源,便不得不思念中国行为科学学会的倡导人,孙友余同志。他是安徽省寿县人,1934年至1937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7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他就投奔延安,第二年即1938年就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后从事于工业的领导工作。“1978年在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率先从日本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在所属企业试点后,召开全国机械工业电话会议,在全行业推广,使机械行业成为我国最早推广这一先进的管理方法的行业。1980年,他著文提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科学’,认为‘它的发展,可以借鉴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一机部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筹建并于198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他被选为会长。十多年来,行为科学的研究和普及迅速发展,召开过六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近千篇论文,出版了上百本教材、专著,全国已有百余所高校和干部学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为培养造就国家急需的管理人才作出了贡献”。(注:引自孙友余同志逝世后,由国家经委给他出的《孙友余同志生平》一文的3—4页。)在上面的引文中,曾纪录了在他生前一段时间里行为科学发展的盛况,我自承无力对此提出具体材料供人参考,因此我不得不提出,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昶,大连理工大学的余凯成,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钱冰鸿,和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的卢盛忠合编的《组织行为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作为佐证。这四位同志的专业不相同,但都是行为科学学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四人在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在杭州集体讨论,分章撰写,然后由卢盛忠教授主编出版。我认为这本书代表了当时国内外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致总结,我曾誉之为“为行为科学正名,为组织管理开路”的大著。我最近又翻阅了一遍,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当时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际,所以对当时的许多论著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我现在不得不提提我和孙友余同志的一些关系。有些话自己说了不作算,我只好引用张洁女士的大作《沉重的翅膀》分上下篇发表在一九八一的文艺刊物《十月》第四、五期上。张洁对孙友余同志相知甚深,当孙友余同志在1983年因心脏病要动手术,从机械工业部退了下来以后,曾和张洁女士结婚,《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事实上就是孙友余同志。这篇作品曾获巴金文学的金奖,许多事实,也都有实在根据的。我知道孙友余同志曾向教育部写过一封信,他复印给我,可惜我现在已找不到了。但张洁同志曾把它写在她的大作《十月》一九八一年的第四期第105页上,我照抄如下:“行为科学的介绍正在开始, 各地都很活跃。大学和科学部门起了很大作用,同工业部门的结合正在开始。我知道,H大学的陈校长,是中国工业心理学专家。 这个学校明年要开工业心理学专业。这位校长七十多岁了,亲自出马,带着教师和研究生,到工厂做调查研究。工业心理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前些年,心理学被打倒了,现在逐步恢复。师范大学是搞教育心理学的,只有H 大学是真正搞工业心理学的,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条根。陈校长是英国留学学工业心理学的,他现在有个困难,因为H大学是属于地方管的, 心理学的毕业生一个省要不了那么多,我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因为中国就这么一条根,能否在这位老专家健在时,把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基础打好,教育部能不能特别支持一下,把它做为一个重点专业,由中央管起来,给他一点钱,培养学生,全国分配”。我对他过誉之词,愧不敢当,但他对高等学校要与经济建设服务,和对工业心理学教育的重视,我是始终感激的。他对行为科学的发展,说“从长远来看还要有个牵头的单位,是否由企业管理协会牵头组织,下面搞个行为科学学会,各地设分会……”。当时实际上是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牵头成立一个行为科学学会。但现在再要由任何部委来管是不可能的,所以向前看,行为科学全国学会的恢复是势在必行的了。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孙友余同志这个先见,我是衷心佩服的。我在现已成为历史的暴乱时间,曾多次下乡,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参加“改造”劳动。每天上午听到村里的哨子声音,便随队荷锄上工。到了工地,先跟着念语录,然后听取队长布置任务。这大概花上半个小时。劳动了一个把多钟头时间,哨子又响了,休息喝茶。快到十二点,大家又即整队回家。在这种军队似的纪律下,就是看到禾苗快干死了,也没人敢下田挖泥放水,其它象这类不费工的农活,见到也不敢动。这样形式的劳动,其效率之低,不想也就知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头是分田到户,情况就大不相同,到后来联产承包,就更不用说了。这当然是农民分到了田,他们的自主积极性提高的缘故。我就想到如果工人有些这样的自主权,是不是劳动效率也会很快就可以提高?我就想到在德国看到的弹性工作时制度,它本来是一个城市市长提出来解决早上八点上班车子拥挤而想出来的办法。我想利用工人在完成一日任务之后,就可随便下班,或继续劳动得到加班的报酬,对工作时间有些自主权能否和农民分田到户一样,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就是我当时对弹性工作时制实验的设想。
当然,要实验就要有实验的场地,我不相信实验室的实验可以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这里,是孙友余领导的行为科学学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在行为科学学会的组织下,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曾举办过几期企业领导和工厂厂长的短期培训班,在某一届培训班的毕业会后,我和一个既是厂长又是书记的同志提出我想在他的工厂中做一个弹性工作时间的实验。我认为弹性工作时可能提高工人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他毅然接受我的建议,并保证让我能完全按计划实行。我当过浙江省科普协会主席,知道得到这样的保证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实验的风险谁也不敢承担。类似这样的实验,如果没有象行为科学全国学会的招牌,是无法实现的。
实验是在北京一个钢锉厂由我当时的助手郑全全同志做的。实验结果也只在10年后才在《心理科学》上发表。我这里只把结果,粗枝大叶地讲讲。实验分两组,一组是实验组,进行弹性工作时的制度,即上午八点钟上班,完成工作一日的全额时即可自主离开或是继续工作,得到超额的工资。而对照组则仍按通常的八小时工作制。因为这是实验,两种工作制度的比较。我们不得不先了解这两组工人的工作,然后才好比较这两种制度的优劣。所以头一个月,就先比较这两组的工作能力,结果是控制组的月成绩还略高于实验组,当然不甚显著。在实验条件下,一个月(实际劳动24天)完成354486件(月计划两组都是216500),控制组则只完成231389件,因为实验组平均每日工作时只6.3小时, 控制组仍为8小时,所以实际效率,实验组比控制组提高2.1倍。可惜的是为计算方便,实验阶段采用了计件付酬制,这样一来,控制组的产量也就有大增加,因为效率受到付酬制度的影响,月产量也增加了30.0%,实验组增加了32.5%,从统计看,两组受计件付酬的影响有些差异。我认为这是实验设计的失策,因为这两个因素的交互关系,混在一起,现在只能从实验组笼统地减少30.0%(即控制组增加的效率),这样实验组的净增值就要从2.1—0.3,即等于1.8倍了。 这个实验报告就只好如此纠正,弹性工作时的效率就不得不打折扣了。(注:因为实验组因实行弹性时的干劲已有很大提高,即再加一个积极条件,力量也就有限了。正如一个百米差1/10 秒的人要夺冠就比另一个跑千米只差十秒的人夺冠要难得多了情况相似。)
总而言之,这个实验证明对工作时的这一点点自主权,对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有显著效果的,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制度因而无法实施。这时材料与销售都由计划规定,效率提高成倍,材料与市场出路都无法承受。我重视这个实验结果,因为这个实验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是贯彻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初期转折点一个成果,既表示劳动效率可以提高,宏观计划经济也有改革为市场经济的必要,所以明眼人可以一看就知道这是学习邓小平政治理论的一个在科学实验的小试结果。
对这个实验结果的估计,尚有许多好处可以提。从经济一点说起,据该厂反映,实行弹性工作时,在加工过程中可省电11%,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节省费用在管理费(overhead expenses)。 这包括管理人员的全部工资、房产租金、机器设备的折旧、以及资本的利息等等,这些无形利益,一般比例很大,不能轻视。
孙友余同志给我的私信中,还提出“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情况的变化,行为科学要研究种种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能把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看作一成不变的。”这是他对行为科学研究的希望。现在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时代的转轨,知识经济社会的新趋势,行为科学也就当然要适应形势加强改革,新时代的特征是知识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信息流通就不能闭关自守;着重开放加强信息交流。这对组织改革就提出更重要的要求,孙友余同志的逝世,行为科学学会的解纽,是个重要问题,一定要马上解决,现在已无法由某个部委领衔组织全国学会,是否可以由现仍存的几个分会联名发起,在北京或上海等中心城市恢复总会,值得大家考虑。
行为科学的中心课题,随时代的要求也要重点转移,由过去的效率改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为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但马克思曾进一步提出,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例如水本可满足渴的要求,但现在喝水已经不够了,要喝茶、喝咖啡、喝各种饮料、还要喝各种各样的酒,光是满足喝的要求,就有数不清的饮料需求,食更如此,即居室服装,文艺音乐,我可以说,人生一切,无不如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就更加如此。经济目的改变,经济管理也应随之改变,所以信息时代的管理就不可“萧规曹随”了。由硬性管理变成柔性管理,亦即松弛管理(slack management),这一改变就比X到Y理论的飞跃还要大多了。在信息时代,不仅不要上班,作息的计划可以自己安排,领导与下属就变成共济的关系,领导的工作也只是协调,大家都处于同一平等的直线上。管理的层次变到很扁平,官僚主义也就当然少了。有这样的松散的组织形式,创新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在知识经济的范畴下,信息交流就变成一大支柱。过去的许多大会小会,以后就都上网进行,甚至不用出门,也可以参加国际会议,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当然,面对面的交流仍是不可少的,吴季松在他的权威著作《知识经济》中,就曾指出过,“一个好教师胜过1000台电化教育设备。”当然,即是在国内,有些会议也还是要的,不能专靠电话会议。这就又牵涉到组织问题,企业和其它组织一样,不是靠一个网络或者一部主机就可以完成的。正如勒温在敏感训练班(sensitivity training)的举例,情绪逻辑是很重要的。感情对元认知有很重要的作用。感情有些象化学的触媒,从化学性质讲,触媒好象对合成物没有关系,但作用之大竞成为成功的关键,类似一个小小的火花把炸药和氧引燃而爆炸一样。佛家讲因缘,因是必然,缘是偶然,辩证统一乃为成功之母。如果不讲这点,就可以不靠人,心理学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自然界的一切关系,原来就有它们的预定的因果锁链。我在上面举例以火花引炸火药,但人人知道枪弹就只靠一击,也就引炸,把子弹发射出去了。
将来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模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猜想,但我敢大胆地说,知识经济既以知识为本,将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无墙的大学。我这样讲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没有不提议终身教育的。或者说“活到老,学到老”的各种名称的教育,这就不用我提了。我是指一般的组织如工厂,本身就应该成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学校功能的组织,劳力劳心界限要彻底消除,教育要成为终生的教育。劳动也要成为全人的劳动,当然,在廿一世纪的新时代,一些机械性质的工作全部都自动化了,创新的劳动当然是知识领域的,也就是劳心的。如何在劳心的工作中,发挥积极的革新要求,在劳动中学习就成为必要的条件。我在上面曾提及吴季松提出过:“一个好的教师胜过1000台电化教育设备”,所以我在上面谈到信息交流时就曾提过面对面的会议仍不可少,我经常引用孔老夫子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文中的三不一定指1、2、3的三,三人从众。所以“三”是指多人,或会议。 一个人独坐冥思,常常被当时的心向(set)或定向(determining)所限制,不会改变思路,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集体作用是不可少的。这也是我所以重视组织的作用。
我们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话,真理来于实践,所以我重视劳动中的感性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直觉可以触动灵感是创新的一个来源。但我更重视决策的多源性策略,所以我又重视咨询作用。工业心理学家,以其广博的背景知识,以及其在咨询中的广泛接触,常常对见怪不怪的情况能有所帮助。行为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会起很重要的作用,也就等于学校中的教师作用。要工厂成为革新作为的组织,就要既有案可查教师的指导,又要有类似讨论课(seminar)的功能, 这正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所以有人把将来的企业看成是继续教育的最好形式。自然,这种组织到底不同于正规的学校的按时上课、按时下课,而是一种无固定形式而具有学校教育的功能的组织,正如家庭有取代学前教育的作用。要使下一世纪的企业保证创新的作业,我认为这一建议可以提供大家考虑。
从上面的继续教育,使我触发另一奇想。最近因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我有机会参加过许多社团的联欢会,看到许多老年大学组织的文娱活动,使我非常羡慕。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载歌载舞,好象年轻人一样,一方面我想到这些活动对身心健康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这里也许是更有关系和更对创新有益的另一方面。大脑两半球是有分工的,靠胼胝体把它们联系起来,左半球的功能是理智思维中心,右半球是艺术想象中心。一般的技巧运动和想象力的中心就在右半球。所以这方面占优势是创新活动的神经基础,在工作之余,这方面的活动,在作为工厂的学校是容易组织的。蔡元培当日提倡美术教育作为正规学校课程支柱之一,这也是继续教育一大优点,对以创新为特点的劳动学校就更加重要了。
所以行为科学在过去十多年固然对产业的改革起过重要作用,只因孙友余同志的逝世,行为科学在全国缺乏领头组织,事业因无人过问而淡漠下去,这对全国经济因缺乏管理人才而不振很有关系,有心人应该积极行动,为行为科学学会的恢复,为继昔日的辉煌而努力。
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访问俄罗斯的回国途中,曾在新西伯利亚发表重要的讲话(登载在1998年11月25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明确指出“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进展,为科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这是党和国家对行为科学的高度关注。为此我们应该以此作为复兴行为科学最有力的推动力量。全国行为科学工作者,应振奋精神,团结起来,群策群力,恢复全国行为科学学会,努力创新,为廿一新世纪的知识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引自孙友余同志逝世后,由国家经委给他出的《孙友余同志生平》一文的3—4页。
跋:孙友余同志于1998年逝世。因为他“生前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遗体送别仪式,不留骨灰,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我直到1999年三月才收到国家经委邮寄来的正规印刷的《孙友余同志生平》一文,因为没设治丧委员会,所以也不知是哪个单位印发的。我念故人对行为科学的重视感激不已。因写短文纪念。如能得到响应,恢复全国行为科学学会,继续发扬这门社会学与心理学密切的联系,我想这也是对孙友余同志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