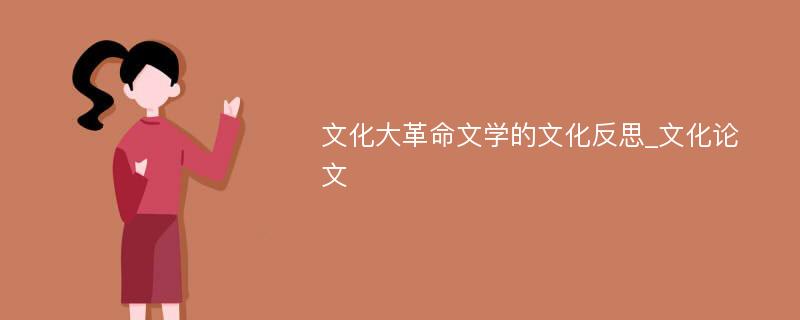
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下简称“文革”文学)的研究文章开始多起来。这是因为,要想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把握,还是史的线索的清理,绕开十年“文革”显然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在这些研究文章出现之前,对“文革”的不同认识已经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选择。新时期伊始,对“文革”的研究主要还是一种情感上的控诉,认为“文革”是“封建主义”在当代的复辟。“封建主义”一般认为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这就是将“文革”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这种认识推动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鼓励着人们从封闭走向开放,积极吸取西方的文化与文学成果。然而,海外的新儒家对这个问题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文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大破坏,而其渊源,则是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这种观点鼓舞了中国当代的发扬国粹的学者,在文学创作中则有“寻根派”作家出现。陈忠实的《白鹿原》与阿城等人的作品,就分别弘扬了儒学的道德价值与道家的审美趣味,这在1917-1949年的新文学中是较为罕见的。
既然对“文革”的不同认识制约着后“文革”的文学与文化选择,而清理20世纪的文学发展脉络与文化沿革,又绕不开“文革”文学;那么,对“文革”及其文学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研究:“文革”文学的研究方法
当前,文化学研究(Culture Study)正席卷世界学坛。西方批评界对大众传媒与通俗文学的文化研究,后殖民批评中的文化研究趋向,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向,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浪。而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热,比西方来得更早。在80年代的中国学坛,一股“文化热”的暗流就在涌动着。如果说西方的文化研究热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亨廷顿(S·Huntington)的文明、宗教、种族的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冷战之说,就颇能说明西方文化研究兴起的后冷战背景;那么,中国的文化研究热则是在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涌入中国而产生的。不过,这二者都不能构成“文革”文学的研究方法应为文化研究的理由。
以文化研究观照“文革”文学,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对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或审美批评,需要文本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具有复杂的内涵,从而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然而,“文革”文学本身就是对这种审美文本的颠覆,它以文本的简单、直露,消解了多重阐释。从一般的美学原则来看,文学虽然应该具有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关怀,但是作为审美现象,终归是要导向感性生命的个人的。同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不同于雪莱;同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也不同于杜甫。然而,“文革”文学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性的,它是以消解个人性、特殊性、偶然性,推崇共性、普遍性、必然性为特征的。许多“文革”时期的诗文,根本就不标明撰写人,一般只署上一个群体单位的名称,以显示其群体共性与普遍必然性。因此,“文革”文学有破除作家与非作家、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界限的趋向。在“文革”中,几乎所有专业性的作家都遭到排斥,报刊上的诗文多为非专业的“工农兵”所作。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知识很少的“工农兵”就受重视了。于是,在知名的作家无一不受到批判的同时,工厂与乡间的赛诗会等群众性文艺活动倒是兴起来了。当诗意的流露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时,标语口号式的文本就大为流行。《毛主席语录》多为理论形态的命题,却被谱成曲到处演唱,形成风行一时的“语录歌”。这就将文学文本与政治文本、文化文本完全等同起来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文革”文学的研究方法应为文化研究。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是对文化的一场大破坏,留下的仅仅是文化沙漠。就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文化”概念而言,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文革”是有其价值标准与伦理尺度的,它追求的目标也不仅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文革”时期既有数不胜数的“颂诗”,又有反复演唱的“样板戏”,还有《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一类的小说,怎么能说“文革”没有特有的文化?你可以从艺术上、审美趣味上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仍然是可以分析研究的。即使从避免类似的“大革命”角度,对这个运动进行文化的反省与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正如列宁所说,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在中国向着现代化大踏步前进的21世纪,对20世纪走过的弯路进行文化反思,不是很有必要吗?
当然,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因为“文革”不是一个常态的文化运动,而是一个非常态、反常态的文化运动。“文革”的发动者就以为这种文化躁动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看法至今也仍然难以被驳倒。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主动发动群众颠覆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而赢得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群众的疯狂崇拜,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识性的文化分析法也不适于分析“文革”及其文学。我们将在下文中,从清理对“文革”的传统看法入手,对“文革”以及“文革”文学进行全面的文化反思。
二、五四与“文革”:迥然相异的文化革命
十年“文革”结束后,海外学者对这场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方向是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的。香港、台湾以及美籍华人学者,其中多为新儒家及其外围学者,几乎都认为“文革”的“文化浩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结果。甚至并非新儒家的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也认为“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并未丧失力量,所以他坚持进行文化革命和全盘否定过去的思想。”(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253-25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香港的《法言》作为新儒家唐君毅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发表了不少将“文革”与五四直接挂钩的文章,如二卷三期的《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一文,就认为“文革”是五四的继续,是对五四的发扬光大。
林毓生还追根溯源,认为五四与“文革”的思想方式都没有逃出儒家“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然而,这却使林毓生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按照他的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论,五四与“文革”不正是对儒家“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种创造性转换吗?笔者早就对林毓生的观点进行过质疑,认为“过分夸大孔子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就无法解释孔子对功能、实用的置重”,另一方面,耶稣的思想倒可以说是视“内心的思想远比外在的行为更为重要”。(注:高旭东、吴忠民等《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第25-2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至于新儒家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对五四与“文革”的抨击,虽然能够自圆其说,然而,不加分析地将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强调其同而不顾及二者的巨大差异,就犯了抹煞基本的文化事实的错误。在笔者看来,五四与“文革”是两个尖锐对立的文化运动。
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核心层面,而五四与“文革”在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上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上,五四张扬个人,推崇自我,提倡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反对社会群体对个人的束缚和压制。陈独秀认为,“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因此,“欲转善因,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卷4号。)胡适在《寄陈独秀》论文学中强调“语语须有个我在”,在《易卜生主义》中推崇易卜生“刚愎主己的个性主义”,在新诗《老鸦》中以群众不喜欢的老鸦自比。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将“人道主义”也作了“个人主义”的解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鲁迅将《文化偏至论》中的“任个人而排众数”,变成了《热风·三十八》中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这也成了五四时期鲁迅小说的全部主题:以“狂人”或自由的个人反对阿Q式合群的“众数”。与此相反,“文革”正是以“合群的自大”来反对“个人的自大”,以社会群体来压制个人的自由,以阶级的共性来抹煞人的个性。在这方面,“文革”比中国传统文化更为极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个人,虽然按鲁迅的说法是“非帮忙即帮闲”,但文人还是表现了对帮忙的个人看法,或者“不得帮忙的不平”。即使在文字狱横行的清代,文人的诗词也抒发了个人的情怀,《红楼梦》也以肯定性的笔调描写了富有个性精神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然而在“文革”文学中,任何表现个人情感、个人兴趣与个人爱好的文字全被禁止了。讲感情只能讲“阶级感情”,这种感情是在消灭了个人的“私心杂念”之后出现的一种被纯化了的普遍感情。正如《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谊重,依我看,阶级的情谊重如泰山。”重骨肉之情而有血缘根基、家族伦理,是中国古代文学所要抒发的情怀;重阶级之情而借歌颂党、领袖等等表现出来,才是“文革”文学的特征。因此,在“文革”的诗坛与剧坛上,可以说是颂声一片。个人与“私”字总是相联,“文革”就是要“狠批‘私’字一闪念”。个人与作品署名也有联系,所以许多“文革”文学要么就不题撰人,要么就署上一个“集体创作”。八个“样板戏”没有一部是个人创作,诗歌《理想之歌》也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甚至连一些短诗,也署上一个“集体创作”。给人一种一哄而上、人数众多的感觉。在“文革”文学的语言中,“我”基本上消失了,或者作为批判、检讨时才用,到处充斥着的,是“我们”二字。
五四对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倡导,是与反对禁欲主义和风化主义密切相联的。当时汪静之的爱情诗与郁达夫的性暴露遭人非议,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就纷纷出来为之解围。与此相反,“文革”对人的自由与个性的抹煞,导致了严重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那种以无“性”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找不到。《诗经》既是中国最早的诗集,也是儒家的经典,其中歌咏爱情的诗歌有很多。即使是在理学产生的宋代,柳永、秦观的爱情词,李清照的思妇词,都写得情深意长。而在“文革”文学中,“儿女私情”已被“阶级感情”所取代。任何描写儿女私情的书,几乎都被视为“毒书”,都具有腐化革命人民的功能而受到无一例外的批判。甚至在衣着上,男女两性也是一律化,不要显示性别特征,否则就可能被斥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种无性的文化导向,在“样板戏”中表现得很典型。《智取威虎山》是根据《林海雪原》中的故事改编的。《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女卫生员白茹本来是有点罗曼蒂克的,然而到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就纯化成革命同志的关系。李勇奇是有媳妇的,然而一出场就遭到了不幸,只剩下他与母亲。这种安排与猎户老常只剩下父女俩可以前后对应。总而言之,不能在戏台上出现夫妇或恋人关系的男女,而且连思念异性的念头也不能有。猎户老常的女儿小常宝在向杨子荣控诉土匪时唱道:“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在没有阶级觉悟的正面的群众中,思念父母的伦理情感是可以有的,就是不能有思念异性的念头。所以,《沙家浜》中的沙奶奶与四龙,正如李母与李勇奇。阿庆嫂是有丈夫的,然而阿庆早就跑单帮去了。《海港》、《龙江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独身,《杜鹃山》中的柯湘是与丈夫一道来寻找雷刚的,但一出场,丈夫就牺牲了。最典型的是《红灯记》,祖孙三代全是光棍。从这个意义上讲,《沙家浜》中的郭建光率领新四军在胡司令结婚的那天去“擒贼擒王”,显然有禁欲主义的象征意味。
五四对个性精神的推崇表现在文学中,就是社团蜂起,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即使是同一个社团的作家,也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文学研究会中的冰心与庐隐、许地山与叶绍钧各有自己的创作风格。郁达夫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然而在“文革”文学中,丰富多彩被划一整齐取代了。除了一些带有民歌色调的歌曲外,语录歌、革命歌与豪气冲天的革命呐喊汇成了一律化的红海洋。这也正是“文革”的发动者“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结果。在五四的叙事文学中,肯定性的人物如狂人、于质夫等,都是个性化的人物;类型化的人物如阿Q等,总是受到否定性的艺术处理。然而在“文革”文学中,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几乎都成了类型化的标本。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江水英、柯湘等人是一类,《龙江颂》中的大队长、《杜鹃山》中的雷刚等又是一类,胡司令、鸠山、座山雕则是坏人的一类。第一类人物也就是浩然《金光大道》中的主人公高大泉——高大全。而且叙事的情节也是类型化的,全剧必以雷刚式的人物的提高觉悟并以座山雕式人物的灭亡而告终。这种人物与情节的类型化,必然导致作品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五四时期,鲁迅要求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认为“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要求作家对现实社会与自我人生都有一种批判性。他与胡适一起倡导悲剧,反对“大团圆”。与此相反,“文革”则让人们安于现状——中国已成世界革命的中心,还有什么不满足!不满仅仅是对过去而言,或者是“一小撮走资派”的捣乱。对于前者,“文革”时期最为普及的艺术活动就是“忆苦思甜”;对于后者,这一小撮在情节的发展中就会被打倒,绝对不会影响结局。“文革”中的所有作品都要乐观主义的,要歌颂光明,在抒情作品中是颂声大作,在叙事作品中几乎没有一部不是以“大团圆”结尾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觉者”的姿态出现的,要向广大群众进行“启蒙”,使群众的思想由传统形态转化成现代形态。所以鲁迅对于群众,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文革”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的拿文化领域开刀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要向广大群众“低头认罪”,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也就是让工人、农民向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因此,“文革”将五四的启蒙主体与对象完全颠倒了。五四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反省,在激烈地反叛韩愈之后的古文传统的时候,又对在市民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白话小说大加赞赏,尤其是《红楼梦》与《儒林外史》,对五四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在“破四归”的“反封建”的旗帜下,却又继承了历代农民造反的“造反精神”、“破坏精神”、“平均意识”与“大同理想”,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所以“文革”中编的“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农民起义史”。这与五四至为不同,五四并不以为农民造反有什么新的文化因素,所以鲁迅骂黄巢、骂张献忠、骂朱元璋……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五四是为了中国观念形态上的现代化,张开胸怀大力吸取。而“文革”却在“反帝反修”的旗帜下,又关上了国门。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际歌》,“文革”对于西方文化教育一概加以排斥。这就是所谓的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国是一个空白。因此,奇怪的倒不在于五四与“文革”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在于为了一种理论目的而故意抹煞这种差异。
三、“文革”与中国传统文化
将“文革”说成是“封建主义”的复活,是国内较为流行的看法。“文革”与五四的巨大文化差异,说明“文革”已将五四新文化的遗产扔掉,在一些人看来,“文革”承传的只能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一般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然而“文革”却大批“孔老二”。道家文化作为儒家的补充与退路,更得不到“文革”的认同,因为“文革”是反对消极逃世而主张积极战斗的。法家与秦始皇等在“文革”后期曾备受推崇,然而“文革”是以砸烂“公、检、法”起家的,人民群众自觉的“革命精神”是不受法制约束的,而秦始皇也不会发动群众批斗他治下的官僚,从而“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在将“文革”与五四比较的时候,确实发现“文革”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更近,“文革”文学在审美形态上更接近古典美,然而我们也同时指出,“文革”比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走得更极端,甚至超出了其容许的范围。“文革”文学的常用词的确是从中国古代的诗文中借用的,如“万寿无疆”出源于《诗经》,“万岁”是古代臣民对皇上的尊称,等等,然而,“文革”又的确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和”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和而不同”就是在万事万物中分出差别来,然后使之和合。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又以为“礼之用,和为贵”。而伦理之和又基于情与理的中和:“发于情,止乎礼义”。情感本身也要中和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于是,天地和,才会有万物;男女和,才会有父子;父子和、君臣和,社会有机体才会正常运转。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如果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那么,和合就是天地之大德、人伦之大德,也就是“仁”。(注: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第十二章《中和与分化》。)所以《中庸》将“中和”提高到参天地赞化育的高度来认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于是,个人的心平气和与国家的和谐稳定,就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追求。然而,“文革”崇尚“斗”而反对“和”。在“文革”文学的词汇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斗争”、“打倒”、“批判”等。孔子为了伦理的和谐,宁肯不要是非而倡导父子相隐;“文革”时一个家庭发生分裂——夫与妇分成两派斗、子与父分成两派斗的现象却并不少见。当时到处张贴着倡导“斗争”的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文革”时的抒情诗歌无不表现了敢于斗争的昂扬斗志,所谓“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样板戏”中也斗劲十足:“斗倒地主把身翻”,“看那边练兵场杀声响亮”(《智取威虎山》),“斗地战天志气昂”(《龙江颂》)。而且在“样板戏”及稍后的小说中,总是出现“阶级敌人”,以便于展开斗争。《海港》中的韩小强稍稍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就受到了方海珍、马洪亮的严厉批评。如果说推崇和谐、“温柔敦厚”的中国古代诗文富有阴柔气息的话,那么,“文革”文学以对“斗”的推崇,一扫阴柔之音,而代之以铿镪有力的阳刚之声。“文革”时的许多歌曲是以战歌、进行曲的面目问世的,连女子也变成了高唱“战天斗地”的“铁姑娘”。
中国传统文学虽然不少颂声,然而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有感则发、不平则鸣的作品也一直在发展着。《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虽然有颂声,然而怨刺上政、发抒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诗篇也很多。但在“文革”文学中,除了“斗”音,便是颂声。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朝能够让其治下的文人与百姓不厌其烦地歌颂、歌颂、再歌颂,然而“文革”做到了这一点。在一首歌曲中,居然连呼近十个“万岁”,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咳,万岁、万岁毛主席。”然而,人类表达赞颂、感恩之情的词汇,毕竟是有限的,致使“文革”文学中许多赞颂最高领袖的歌曲,稍稍改动几个词,就会变成男女之间的情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向着您跳动,千万张笑脸向着红太阳……”又如在读了毛主席的书后唱道:“好像那旱天下了一场及时雨,小苗挂满了绿水珠……”旱天雨露,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男女和合的一个隐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将“文革”完全归为“封建主义”,并由此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对“文革”又一种误读。也许正是这种误读,刺激了海外的新儒家及其外国学者,从而对“文革”进行了更严重的误读。笔者认为,这两种误读都不利于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尽管国内的这种误读曾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对外来文化的吸取,然而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可能不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海外新儒家倒是特别推崇这一资源,然而他们在否定“文革”的时候,连“新文化”也一并否定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一些文化课题,在20世纪的中国并没有获得解决。
四、“文革”文学的文化渊源
对于“文革”的中国文化渊源,笔者曾在前文分析过,下面笔者将反思“文革”文学的西方文化渊源。自严复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译介到中国,“斗”的世界观就开始取代“和”的世界观,这也伴随着对争天抗俗的文化性格的推崇。不过,这都是浅层的显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在西方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西方文化的现代杰作。将马克思主义无意识地、不自觉地中世纪化、基督教化,是西方文化对“文革”的深层影响,也是“文革”文学的重要特征。
“文革”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早请示”与“晚汇报”的对于“救星”的忠心不二,饭前会前上课前对于“救星”的祈祷式祝福等,都是“文革”的宗教仪式。基督教基于人的“原罪”,就不断地让人忏悔;“文革”虽不信“原罪”之说,但不断地让人“斗私批修”,洗脑子,挖根子,狠批“私”字一闪念,就有类似的宗教色彩。基督教分出神与魔,并且也将人进行了神与魔的二分,让人去除魔鬼而信神、颂神。这种二分法在“文革”中是很普遍的:人的“公心”是神,“私心”是魔;“救星”是神,地、富、反、坏、右等是“牛鬼蛇神”,是恶魔。“文革”文学对于前者是一片颂祝之声,对于后者则是“狠斗猛批”、“杀声响亮”。因此,“文革”文学不是斗便是颂的总格调,正是基于对人的神与魔的二分。在基督教中,耶稣为了让人专心不二地信神,不惜疏离人伦感情与亲子关系:“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6节。)这种人伦感情的疏离乃至父子反目、夫妇分离,在“文革”中的一些家庭中的确又试演了一遍,因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作为“救世主”是神,而“文革”文学中的“救星”却是现世中的人。尽管如此,“文革”文学中的颂声大作与基督教颂神的宗教歌曲是非常相似的,“文革”文学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也可以到基督教中去寻找。当然,不是20世纪的基督教,而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基督教。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以儒道为代表的正宗的精英文化传统,继承并弘扬了从五斗米道、太平道到太平天国的民间文化。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置重,转而向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认同,无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文化影响。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文化劫难,那么,对这场劫难的文化反思是远远不够的。中外学者对“文革”极大的误读,便是最好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