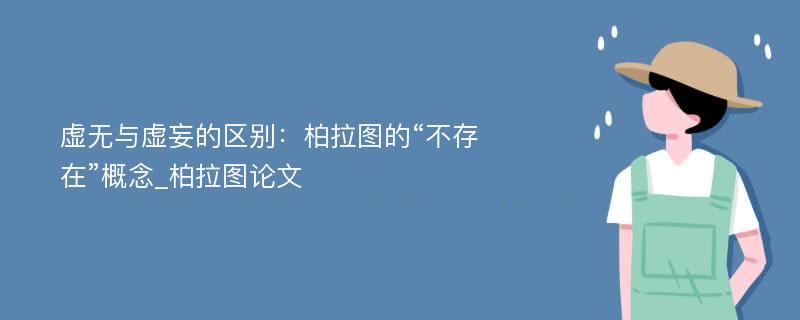
虚无与虚假之辨:柏拉图的Not-being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虚无论文,虚假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文献标识码:A
我们分别用英文Being和Not-being来表示希腊文的to on和to mē on。Being曾广泛地被翻译为“有”或“存在”,而Not-being则被翻译为“虚无”或“非存在”,其实这些都是不准确的。因为Being不仅表示“存在”或“在场性”,而且还表示“真实”,同样,Not- being不仅表示“虚无”或“绝对非在场性”,而且还表示“虚假”。一些人主张把Being和 Not-being分别改译为“是者”和“不是者”,这似乎可以用来表达“真实”和“虚假”的意思,但却又掩盖了它们各自表示“存在”和“虚无”的意思。我们毋宁说,Being兼有“在者”和“是者”(真实)两方面的意谓,而Not-being则兼有“不在者”(虚无)和“不是者”(虚假)两方面的意谓。我们试图通过分析柏拉图关于Not-being的讨论来澄清这点。
一、为什么Not-being与Being成为柏拉图的论题?
为什么Not-being和Being成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这个问题需要回溯到哲学的本质。“哲学”在希腊语中是“爱智慧”的意思;而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智慧(sophia)不同于实践智慧(phronēsis),它并不突出关注生存论层面上的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区分,反之,它首先关注形上学层面上的真与假、知识与意见之间的区分。“爱智慧”首先意味着“求真”,亦即真与假的划分。恰好,古希腊语动词einai(to be)直接被用于表示“真”,并且mē einai(not to be)被用来表示“假”,于是,它们的动名词形式to on和to mē on就分别被用于表示“真的东西”和“不真的东西”。这样,求“真”就等同于领会to on,同时拒斥to mē on。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西方哲学中,Being和Not-being的问题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真”和“假”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与古典汉语思想中关于“有”和“无”的思辨根本不同。
既然古希腊语动词einai(是/存在)从本性上就与“真”相关联,那么,利用einai及其衍生词,如分词性名词to on(是者)、抽象名词ousia(所是)以及副词ontōs(真正地)等等来思考“真”的问题对于希腊人而言就是非常自然的。在希腊语中,ontōs几乎与alethōs(真实地)同义;to on(实在,是的东西)与alētheia(真实)在许多场合可以理解为同义,换言之,对希腊人而言Being与Truth直接相关联。由此我们已经隐约可见:希腊哲学通过将to on形成为主题从而走向了“求真”的道路,并且这道路注定通向所谓 onto-logy。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道路。亚里士多德把第一哲学表述为研究to on hei on的学问,并通过einai这个词构造了不少新的表达式来澄明他的形上学,这些都运行在希腊语言的可能性范围内。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形上学的基本论题也是探讨智慧的本性,划分真与假,区别知识与意见,澄清Being和Not-being的意义。然而,就在柏拉图利用Not-being来思考“假”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独特的困难,其潜在原因是Not-being的多重含义(至少是两重),亦即,它不仅表示“不是者”或“虚假”,而且也表示“不在者”或“虚无”。我们可以分别用“相对Not-being”和“绝对Not-being”来标记它们。这种多重含义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是明确的,但对于柏拉图而言并不如此,它导致柏拉图多次陷入思想困境之中。下面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柏拉图在《国家》、 《泰阿泰德》和《智者》中关于 Not-being的探讨。
二、《国家》(第五卷):作为“虚无”的Not-being
《国家》第五卷475e中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智者?“苏格拉底”对此的回答是:爱智者乃是“热爱观察真的人”(475e)。那么,什么是“真”?这个问题引向了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当“知识”被了解为“灵魂”对“真”的“持有”(hexis),那么,知识与智慧在本性上就是一回事。于是,哲学的任务就是求“知”。但是,这个“知识”首先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各种感觉和经验,而是“知识本身”。换言之,爱智慧的首要任务是将“知识”从与知识有别的东西中划分出来。
“什么是知识本身”这个问题导致了对Being和Not-being的考察,因为Being被了解为知识的对象,而Not-being与“无知”(agnoia)相对应。柏拉图说,“知识从本性上就关涉于Being,亦即认识Being如何is”(477b)。在知识与Being的对应关系上,柏拉图的论证一帆风顺。但是,他随即遇到一个困难:知识的对立面不仅仅是无知,而尚且还有介于知识和无知之间的“意见”(doxa),它的对象是什么?
如果Being是绝对可知者,它就不可能是意见的对象,因为可意想者与可认知者是不同的。那么,意见的对象是Not-being吗?也不是。因为Not-being不是任何东西,“它最正确应被称为‘虚无’(mēden)”(478b12-c1)。“虚无”不可能成为意见的对象。在希腊语中,“意想虚无”(doxazein mēden)与“不意想”(oude doxazein)是一回事。这样, Being和Not-being均不是意见的对象。因此,结论只能是:要么,根本没有“意见”这回事,要么,在Being与Not-being两者之外有一个领域可以充当意见的对象。
如果根本没有“意见”,那么就不可能有虚假的思想,换言之,人们要么完全无知,要么就有真知。这是柏拉图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断定有虚假的思想,它既不同于知识,又不是完全的无知。那么,在Being与Not-being之间找到一个领域作为意见的对象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这个居间者是什么呢?柏拉图说它是“分有两者的东西”(to am photeron metechon),这也就是既分有to be,又分有not to be的东西。实际上,柏拉图将这样的东西解释为与“理念”或“型相”(idea)不同的具体的可变事物。这样,“知识”关涉于“理念”本身,它是“纯粹的Being”(to heihkrinos on)或“永恒自身同一者”;“无知”关涉于绝对的Not-being,或“无”所关涉;“意见”则关涉于杂多而流变的事物。我们看到,柏拉图在这里将存在论(ontology)建基于知识论之上,亦即,Being的意义乃是从绝对可知性的角度来理解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在《国家》第五卷中,柏拉图表示爱智者是求真的人,求真也就是达到知识,知识的对象是Being,纯粹的Being是“理念”。既然“纯粹的Being”被认为是“理念”,那么,与“理念”不同的个别和流变的事物很可能已经被当作某种Not-being了,——尽管Not-being被解释为绝对的“虚无”。第二,在《国家》第五卷中,柏拉图并不把Not-being了解为“虚假者”,而把Not-being了解为绝对的“虚无”,因此,他断定意见的对象不可能是Not-being。但是,我们在后面将看到,在《泰阿泰德》中,柏拉图将“意见”本身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而虚假意见之对象恰恰被认为是Not-being。这样,Not-being在“虚无”和“虚假”这两个意义上就发生混淆。
三、《泰阿泰德》:Not-being的双重含义之混淆
《泰阿泰德》属于柏拉图的中后期作品,它的主题很明显,亦即讨论“什么是知识”。对“知识”的探讨自然涉及到“真实”和“虚假”的问题。就在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谈论到“虚假”之本性的时候,问题又被引向了einai(是/存在)和me einai(不是/不存在),从而引向了Being(是者/在者)和Not-being(不是者/不在者)。①在其中,柏拉图陷入了一种语义混淆之中,这也即“是”与“在”的混淆。
要澄清这个混淆,我们必须跳出希腊语的框框,因为它正是由希腊语的独特性所引起的。这种独特性也就是动词einai“至少”兼有现代汉语中的“是”和“在”这两层含义。当动词einai表示“是”的时候,它所隐含的意思是“是真的”(to be real,to be true),“是如此这般”(to be the case);当它表示“在”的时候,它所隐含的意思是“存有”或“实在”(to exist)。这两层意思在同一个希腊语动词einai中出现,这是不容否认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另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这么揣测:在自然语言中,当某人说“这个东西是如此这般”的时候,他同时暗示了“这个东西”的“存在”(existence);换言之,如果说“这个东西存在”,它也暗示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假如“它”不是真的,“它”就根本只是幻象,不“实在”。在这里, “真”与“实”相互隐含,被当作同一回事。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希腊语中的alētheia这个词既可以表示“真”或“真实性”,也可以表示“真实的东西”或“实在”。同样道理,to on既可以表示“在的东西”或“在场者”,也可以表示“是者”或“真实者”。我们将它们分别称为Being的“表实含义”和“表真含义”。
通过以上这个说明,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柏拉图将“虚假”的问题引向Not-being这个概念。这是因为,既然Being含有“真实者”(是者)的意思,由此推出,它的否定形式Not-being自然含有“不真实者”(不是者)的意思。这样,通过说明Not-being来说明“虚假”也应当是合法的。《泰阿泰德》中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么做的,他说道:“我们很容易断定:意想任何Not-beings的人不会不意想‘虚假’,虽然他的思想可能还持有其他状态。”②接着,他又把Not-being解释为“不真实者”(mē alēthē)③。到此为止,苏格拉底在“表真含义”上使用Being。但是,接下来苏格拉底话锋一转,突然从“表实含义”上来解释Being,从而把Not-being解释为“虚无”(mēden)。④这样,一方面,“虚假”被认作为Not-being;另一方面,Not-being又被等同于“虚无”。泰阿泰德没有能够洞察到这里的混淆,就连苏格拉底(柏拉图)也似乎被蒙蔽过去了。
然而,只要我们仔细检查苏格拉底的推理过程,就可以发现问题出在Not-being和Being之双重含义的混淆上:当Not-being被解释为“不真实者”或“虚假者”的时候,Being就充当了“真实者”(是者)的含义;当Not-being被解释为“虚无”或“不在者”的时候,Being就充当了“在者”或“存有”的含义。下面让我们引用柏拉图的原文,以更好地说明Not-being被解释为“虚无”的推理过程。
苏:那么,这个情况在另外的场合也是可能的吗?
泰:哪一个?
苏:某人看见了“某个东西”(ti),他又看见了“无”(ouden)。
泰:怎么会呢?
苏:不然,如若他的确看见“某一个”(hen ti),那么他也就看见了“某个在者” (tōn ontōn ti)。抑或,你认为“一”(to hen)乃是在“非在者”(mē onta)之中?
泰:我的确不。
苏:那么,如果他看见“某一个”,他就看到了“某个在者”(on ti)。
泰:显然如此。
……
苏:如果他进行意想,那么他岂不在意想“某一个”?
泰:必然。
苏:意想“某一个”岂不是意想“某个在者”?
泰:我同意。
苏:当他意想“非在者”(mē on)的时候,他在意想“无”(ouden)?
泰:显然。
苏:意想“无”(mēden)亦即全然“不意想”(oude doxazei)。
泰:这似乎很清楚。
苏:因而,无论这个“非在者”(to mē on)对于“在者”(ta onta)而言还是就自身而言,意想它是不可能的?
泰:显然如此。
苏:那么,意想“虚假者”(to pseude)有别于意想“非在者”(ta mē onta)。
泰:似乎如此。(188e-189b)
在所引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先行地把to on翻译为“在者”,把to mē on翻译为“不在者”,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可理解的,——假如把它们换成“是者”和“不是者”,这段话就不可理解,因为to on这里明显是“表实”,而不是“表真”。苏格拉底首先把ti(某个东西)等同于to on(在者),亦即任何某个东西都是ta onta(诸在者)之一。这样,to mē on(非在者)作为对to on(在者)的否定也就是对任何某个(ti)的否定。对任何某个东西的否定也就是全然的“虚无”(mēden)。让我们用一些式子来表示:
前提:1.to mē on是to on的否定,2.mēden是ti的否定
当:to on=ti
可以推出:to mē on=mēden
假如to mē on(Not-being)的这两层含义(不是者/不在者)没有得到澄清,那么就会出现把“虚假者”等同于“虚无”的结论。我们看到,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没有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只是点到为止,但是在后续对话录《智者》中,他花了大量篇幅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下面就让我们对《智者》中关于Not-being和Being的讨论进行阐释。
四、《智者》:Not-being的真正含义和“虚假”之可能性
《泰阿泰德》中关于“虚假”与Not-being的讨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隐含着把“虚假”等同于“虚无”的可能性。这样就会推出:凡存在者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不真实者。这里的意思很显然:“虚假”无论如何不可能“存在”。但是,在《智者》中,取代苏格拉底而占据对话主角的“访客”(Xenos)却把“智者”指认为“制作虚假的人”。现在,假如“虚假”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对智者的这个指认就是无效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智者》从236e到264b的整个讨论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一)Not-being的双重含义
访客(柏拉图)对“虚假不存在”这个难题的解决依然是从分析Not-being和Being这对概念出发。他将这个难题的根本难点归结为巴门尼德的箴言,亦即:“决不能受这个所强迫:Not-being is;反之你在探究中要让思想避免这条道路”⑤。很明显,巴门尼德这句话所针对的是Not-being。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Not-being可能有两重含义:“不在者/虚无”以及“不是者/虚假”,那么,巴门尼德所主张的“Not-being is not”(to mē on mē einai)这个命题(以下称为P)可能有以下四种解释:
A:“不在者不在”;它相当于“虚无不存在”。
B:“不在者不是”;它可解释为“虚无不是真的”。
C:“不是者不在”;它相当于“虚假者不存在”。
D:“不是者不是”;它可解释为“虚假者不是真的”。
从中文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四个命题的差异,但是,在古希腊语中却只有这么一句。我们不能非常肯定巴门尼德究竟在哪一个意义上使用einai和mē einai。如果他将它用作单义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所批评的那样,那么,P要么表示A,要么表示D。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einai是多义的,那么,P还可能被解释为B或C。B和C正是《智者》中柏拉图遇到的真正困难。他要突破巴门尼德的命题P,一方面必须保留A和D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克服B和C所引起的问题。这样,区分Not-being的不同含义成为首要任务。
柏拉图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首先,他引入一个新的表达式:to mēdamōs on(Absolute Not-being)。这个表达式是to mē on的强化形式,它用来表达绝对意义上的“不在者”,亦即“虚无”。接着,他开始论证这个to mēdamōs on是不可思考和不可表达的。不能说to mēdamōs on“是”什么,它什么也不“是”,从而根本上不能说。任何对它的言说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因为言说总是把所言说者当作一种to on。柏拉图到此为止澄清了命题P在A和B的意义上该做如何理解。
但是,柏拉图认为必须告别这种绝对意义上的Not-being,因为在这里只有“虚无”和“在者”的区分,找不到“虚假”和“真实”的区分。作为“虚假”的Not-being必须从另一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他再次引入一个表达式:to ouk ontōs on(Not-really-be ing)⑥,它是to ontōs on(Really-being)的否定形式。To ontōs on用来表达“严格意义上的Being”或“真实的Being”,所以,to ouk ontōs on表示“非真实的Being”。这样,通过改进to on与to mē on的二元区分,我们得到了新的三重区分:to mēdamōs on(绝对非在者),to ouk ontos on(非真正的在者)和to ontōs on(真正的在者)。通过这个新的划分,柏拉图成功地给“虚假”找到了一个容身的位置,亦即to ouk ontōs on。它使得to mē on与to on在某个意义上“结合”起来了。⑦
然而,在希腊语中说to mē on einai毕竟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用柏拉图的话说,这意味着“Not-being与Being可能已经缠绕成了某种结合物”(240c)。于是,接下来的任务是:1.解释这种“缠绕”(plechein)或“结合”(koinōnein)是怎么回事;2.说明这种“结合物”(samplokē)是什么。
(二)“结合”(koinōnein)如何可能?
在柏拉图看来,首先需要阐释的是Not-being和Being怎么可能相结合,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铺垫。他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巴门尼德,因为后者主张“一切是一”,从而把 Being等同于“一”(hen)和“全”(holon),这使得任何“结合”都根本无法出现。“访客”的推论可以简单总结如下:首先,假定Being是“一”,那么“Being”与“一”至少是“两”个“名”;此外,“名”(onoma)与“实事”(pragma)也不能是“同一个”;然后,假定Being是“全”,那么“全”总隐含着“部分”,因而“一切”(panta)多于“一”。总之,Being与“一”和“全”的各自具有自己的“本性”(physis)。从巴门尼德作为“一”和“全”的pan(单数的“一切”)过渡为panta(复数的“一切”),这就给某种“结合”开辟了可能性。
接着,“访客”进一步批评了两种关于Being的观点:其一是唯物论者,他们只承认“物体”(sōma)或“感觉对象”是真正的Being;另一是理念论者(可能含早期柏拉图自己),他们只承认“理念”或“型相”,亦即“理知对象”才是真正的Being,而“感觉对象”是变易的东西,不能算作Being。针对前者,“访客”迫使他们承认“实有” (einai)某些不可感觉的东西,如“灵魂”、“智慧”和“美德”,同时,检验Being的标准并不是它能否“被感觉到”,而是它是否有“能力”(dynamis)起作用或被作用;针对后者,“访客”的评论是变易和运动的东西也应当被看作真正的Being,亦即,Being既包括“静止者”,也包括“运动者”。这两方面的批评都围绕一个中心,亦即Being有“能力”进行相互作用,亦即进行“结合”。
通过这个铺垫,“访客”开始具体说明“结合”(koinonei)问题。他提出三个可能性:第一,无任何东西具有任何能力以任何方式与任何东西相结合;第二,一切都有能力相互结合;第三,有些东西能够相互结合,有些不能相互结合。前两个可能性最终被排除,而第三个则被接受。正如字母的结合需要一种相应的技艺(technē),亦即“语法”一样,“种类”和“理念”之间如何结合也需要一种特殊的“技艺”或“知识”来处理,这就是辩证法(dialektikē)。辩证法被认为是哲学家特有的技艺。不管柏拉图在其它对话中如何描述或界定“辩证法”,它在《智者》中被界定为“按照种类进行划分” (to kata gēnē diaireisthai)的知识。柏拉图关于“辩证法”的这个说明曾被命名为“通种论”而为人所知,但这个“通种论”的产生缘由及其具体含义仍然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重要论题。
现在,凭借这个所谓辩证法,“访客”重新回到关于Being和Not-being的讨论之中。他将Being和Not-being考虑为两个“种类”(genos)。假如这两个“种类”根本不能结合,那么我们既不能说Not-being is,也不能说Being is not;但是,假如它们能相互结合,则可以这么说。“访客”并没有直接解释Being与Not-being的结合问题,而是首先讨论了 Being、静止、运动、同一和它者这五个所谓“最大的种类”之间的结合和分离。这个讨论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被谈论的Not-being的真正含义是Being的“它者”(heteron)而不是“相反者”(enantion)。Being的“相反者”是绝对的,亦即to mēdamōs on(虚无);但Being的“它者”则是相对的,它不是“虚无”,而只是不同于特定being的be ing。例如,假如“美”作为某种being,“不美”并不表示“虚无”,而只表示“美”的“它者”,它仍然是某种being,但对于“美者”而言,它是not-being。至此,柏拉图终于完成了关于Not-being与Being之结合问题的漫长论证,其最终目标是拯救被巴门尼德所拒斥于可研究道路之外的Not-being概念,从而为“虚假”的可能性奠定了逻辑上的基础。综上,柏拉图在《智者》中对Not-being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越了《国家》和《泰阿泰德》中的认识;他在Being的“相反者”和“它者”之间做出区分,几乎辨明了我们所说的Not-being的两重含义:“虚无”和“虚假”。
(三)作为虚假之载体的“结合物”
既然Being与Not-being之“结合”问题已经得到说明,最后的任务自然是澄清这种“结合物”的本性。这些“结合物”也就是“虚假”的“容身之处”。亚里士多德后来把真与假的问题归结为结合和不结合的问题,其思想起源就是柏拉图这里的“结合理论”。“访客”提出了三种“结合物”,它们分别是:logos(陈述)、doxa(意见或意想)和phantasia (表象);其中,“陈述”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探讨,而后两者被认为是“陈述”的“同类”,只有些许的解释。论证这样展开:首先,“陈述”被认为是Being的一个种类;然后,“陈述”与Not-being相结合;最后,假陈述实际上存在,——因而也可能有智者的“欺骗技艺”。这样,“虚假”最终被证明为一种作为Not-being的Being,它存在于陈述、意见和表象之中,——把智者界定为“制作虚假的人”也就有了一个形上学的基础。
五、余论:Being和Not-being的多义性及其中文翻译
在希腊哲学,至少在柏拉图哲学文本中,Being“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表真”和“表实”。以前人们一直强调Being的“表实”含义,因而主要将它翻译为“存在”或“有”;即使陈康以及后来一些学者(如王太庆)主张用“是者”来翻译Being,也仍然没有摆脱只从“表实含义”上看待Being,亦即把它看作“外延最广大的概念”。实际上,Being之所以无法用“存在”或“有”来翻译,乃是因为它不仅有“表实含义”,而且有“表真含义”。按同样的道理,Not-being不能简单地翻译为“非存在”或“虚无”,因为它还可以表达“虚假者”。“虚假者”和“虚无”当然不是一回事,“真实者”与“有”也不是一回事;但是,希腊语的Not-being和Being却有这两方面的混淆(或“混同”),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注意的。除了基本的“表真含义”和“表实含义”,Being可能还蕴含别的含义,例如“活动者”或“生命”。在“表活动”这个维度里,Being和Not-being的对应关系衍生为“现实”(energeia)与“潜在”(dynamis,或译“潜能”)的对应关系,这一点由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所强调。因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主题,暂不讨论。
后人对Being和Not-being的含义感到困惑丝毫不用奇怪,因为它们的混杂含义早已让希腊人自己感到十分困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向我们表明,他遭遇到这个困惑并尝试解决它。他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详细分析《形而上学》的文本。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是清楚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决不是要坚持Be ing只有一种意义,并提出一种关于Being的统一理论,相反,他的任务是澄清Being的多种含义之间的混淆,分别从不同角度对Being做出多样的解释。亚里士多德时常说:“Being有多种意谓”(to on legetai pollachōs);并且,他还说:“Being和Not-being的意谓或者依据诸范畴的样式而言,或者依据诸范畴的潜在和实现及其相反者,然而最关键的是真或假” (《形而上学》1051a34-b2)。既然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并强调einai和to on(Being)的“多义性”,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作“单义的”,并且强行用单一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呢?我们经常看不懂某些西方哲学的中文译本,这是一个关键原因。
注释:
①参见《泰阿泰德》188d以下。
②《泰阿泰德》188d。
③《泰阿泰德》188e。
④参看《泰阿泰德》188e3以下。
⑤《智者》237a。
⑥《智者》240b。
⑦《智者》241d6-241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