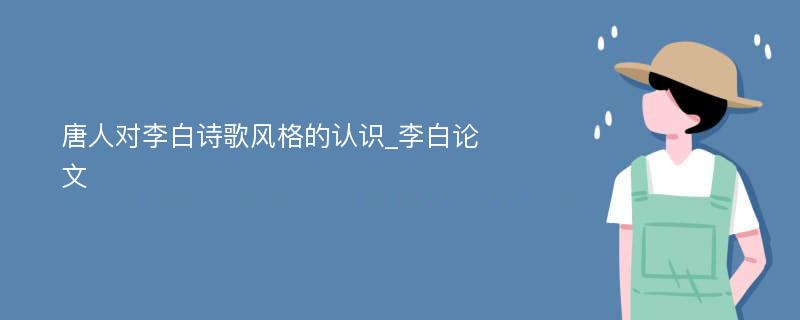
唐人对李白诗歌风格的体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认论文,唐人论文,李白论文,诗歌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 (2000)01—0020—06
对李白诗歌风格的体认,唐人似较我们更多一些直觉上的优越性。从总体上看,唐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文化环境和诗歌艺术氛围中,其心灵感受、艺术趣味以及表现方式很容易沟通,对同时代诗人诗风的体会把握也十分贴切准确;从诗歌评赏角度看,唐人所使用的术语虽有含糊和界定不明等特点,所采用的话语方式也有重描述轻分析等区别于现代学术惯例的地方,如殷璠评盛唐诗:“兴象风骨始备”;杜甫评李白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张碧比较李贺、李白诗:“(李贺诗)春拆红翠,辟开蛰户,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览李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鹍触巨海,澜涛怒翻。”[1 ]但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却是相对清晰而易于理解的。只要经过认真清理,其内涵仍是可以从现代学术意义上加以说明的。
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分析比之对其他唐人诗风的分析要更困难一些,这首先是因为李白的诗歌不依常理,不守常规,率性而作,“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2]。 这就使得时人和后人对其诗歌产生了许多误解甚至偏颇,即使是一些包含真知灼见的评论,也往往穿上了一件玄妙莫测的外衣。严羽在仔细研究过李白诗集后发出感叹:“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3]就是意识到正确认识李诗风格, 确实存在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其次,自贺知章目李白为“谪仙人”之后,便隐约有一种将李白其人其诗神秘化的倾向。《文献通考》引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徐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这种神秘化的倾向必然导致对李诗风格的现实基础的忽视,陷于不可知论的泥潭。对此,严羽曾加以辨析:“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3 ]意在破除神秘化的倾向,还李白诗歌以可知论的现实基础。
唐人对李白诗歌风格的体认,可以讨论的材料并不很多,但涉及的问题却很重要,如李诗风格的类型及其内涵,“天仙之辞”及李诗意象的构成和呈现,李诗风格的成因与评价等等,这些问题至今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而且,就对上述问题的具体结论而言,唐人的许多认识并未被今天的研究者充分理解和运用,这就使得全面认真地清理有关材料变得更为必要了。
一、“清新”与“俊逸”(“纵逸”、“奔逸”)
在李白同时代的诗人中,杜甫言及李白者最多,凡十数首。其中《春日忆李白》论李诗风格最为明朗,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清新”、“俊逸”言李诗风格之有二端,又以“飘然思不群”一语总领,“飘然”而趋向庾信一端者为“清新”,“飘然”而趋向鲍照一端者为“俊逸”。杜甫此诗实开李诗风格类型研究之河。前人对诗歌风格的体认,或概括,或描述形容,概括者多用形容词短语以揭示其特点,描述形容多用情景展现以说明其意境的感性效果。“渭北春天树”,就清新而言;“江东日暮云”,就俊逸而言,为李诗两种风貌特征的具体描述。有言“渭北”、“江东”乃指李、杜二人所处之地,“春天树”、“日暮云”隐喻相思,[4]可备一说, 然须考杜甫作此诗之时间及当时二人之行止。
杜甫以庾、鲍两家诗比李白诗歌的两种风格类型,大体上说是不错的。取李白诗句以证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即意在清新;“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即意在俊逸。就李白个人的取向而言,其清新一格,取谢朓者多,于庾信少有所取,故杜言“清新庾开府”有小误。至于李白学鲍照,前人论之已详,此处仅举李、杜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关于鲍照诗风的评论,以证明李白与鲍照诗风的相似。王云:“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相继,成败兼行。 ”[5]说明鲍照、谢灵运的诗风都有纵逸的特点,只是有成功有失败,成就有所差别。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讨论了八种文章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褥,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不及“清新”、“俊逸”二格。其论“新奇”:“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与“清新”风格殊不类。评阮籍诗云:“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与俊逸有相似之处,但按其八体归类,似属远奥一格。评贾谊云:“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又似属“精约”一类。刘勰有“风清骨俊”之说,《风骨》篇云:“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与论贾谊语合观,似可拈出清俊一格,清就语言省净而言,俊就意气爽朗而言。然而李白诗风的根本特征又非清俊一格所能揭示,一是李诗清而见新,在语言的纯净自然中体现出一股新鲜活力,正如“渭北春天树”描述的情景和感觉一样;二是李诗俊中含逸,即在意气的爽朗迅捷中包蕴超迈的气度,正如“江东日暮云”的变化飘忽。如果说语言的纯净自然是一种外在形式特征,那么新鲜活力即是其内在魅力;如果说意气的爽朗迅捷是一种审美表现形态,那么气度的超迈不群就是其精神本质。
杜甫在诗中对李白的精神气度和思维形式有过多方面的描述,如“飘然思不群”、“剧谈怜野逸”(《寄十二白二十韵》)、“天子呼来不上船”(《饮中八仙歌》),意在说明李白超然不群的人格气度,自由潇散的精神意趣和傲视群物的性格特征;又如“敏捷诗千首”(《不见》)、“两公壮藻思”(《遣怀》),则揭示了李白思维性情既迅捷爽朗又壮阔豪迈的特点,这些描述可以从多方面深入地了解李诗“俊逸”风格的内涵。皎然在《诗式》中曾对“逸”格有过界定:“逸,体格闲放曰逸。”这一理论说明显然偏重于静态的闲逸,与杜甫所揭示的李诗“俊逸”风格的内涵不符。杜甫虽未直接指出李诗风格中动态的一面,但敏捷、壮等词语中所包含的内容显然趋于壮美一路,与皎然概括的趋于秀美的闲逸风格是不一样的。由此可以看出,逸有两格:一种是近似隐士的超然,如王、孟山水田园诗,多写静态的小景象,以韵味幽远取胜;一种是类于壮士的豪迈、洒脱,如李白许多诗歌的风格,多写动态的大景象,以气势超越见长。
与李、杜同时代的诗歌选评大家殷璠正是用纵逸这一体现动感的词语来概括李白诗歌风格的。其《河岳英灵集》评李诗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纵逸与俊逸稍有差异,俊逸一语未能充分揭示诗思变动转换的一面,纵逸则弥补了这一不足。王昌龄论诗思饱肚狭腹云:“诗有饱肚狭腹,语急言生,至极言终始,未一向耳。若谢康乐语,饱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纵横。鲍照言语逼迫,无有纵逸,故名狭腹之语。”[5 ]可见纵逸的风格有“饱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纵横”的特点,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诗思任意纵横的动态变化。李诗风格的这一特点是杜甫俊逸一语所未能揭示的。杜甫注意到李诗思维迅捷、壮阔的一面,但未注意到其飞动的一面,“飘然思不群”主要从人格气度着眼,而不是从思维形态着眼。李白诗云:“俱怀逸兴壮思飞。”逸而含壮,壮而能飞,流转飞动,开阖纵横,正是李白自负得意处。殷璠对李诗风格研究的贡献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指出了纵逸是李诗的主体风格(“率皆纵逸”),二是指出李白诗歌还有奇之又奇这种极富独创性的风格。后一点下节将详加讨论。
同是李白朋友的另一位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对李诗的风格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描述,诗云:“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一作“波动巨鳌没”),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刬见孤峰出。”任华以“奔逸”和“既俊且逸”来概括李白诗歌的风格,并对体现奔逸风格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奔逸与俊逸、纵逸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只是强调的侧面稍有不同。俊逸强调迅快爽朗,纵逸强调的是纵横飞动,奔逸则强调奔腾而又力猛。俊逸之俊侧重语言的多一些,纵逸之纵侧重结构的多一些,奔逸之奔则侧重全篇的气势多一些。奔腾力猛而又归于气势,这就避免了筋骨毕露。这是对李诗风格很精确的把握。在强调李白诗歌有“奔逸气”的同时,任华进一步补充说明李诗有体格高朗的风格特征。高与逸意义有相通之处,孟启《本事诗》即以高逸名篇,并说李白诗“才逸气高”。不过,高与逸还是有所区别。皎然《诗式》云:“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司空图《诗品》分列“高古”、“飘逸”二格。严羽《沧浪诗话》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也将高与飘逸分成二格。大致而言,高与卑相对,有高出群伦,超越世俗的意义,逸在精神意味上具有高的这层意义,但在形态表现上却体现为舒卷自由的体貌特征。“振摆超腾”而归于气势,舒卷自如而至于高格,以至获得“清人心神,惊人魂魄”的诗意效果,这正是李白远远超过被魏文视为“有逸气”的刘桢,被刘勰视为“响逸而调远”的阮籍,甚至被杜甫认为“俊逸”的鲍照的独特之处。
在同一诗中,任华对李诗风格中逸的精神内涵作了较为全面的揭示。任华是从人格与风格的紧密联系来加以说明的,如“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主要说明李白在社会活动领域内傲岸不群,独立不迁的人格特征,这比杜甫以飘然来形容李白的精神气度要具体深刻;又如“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主要说明李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中与自然相知相亲的特殊关系;又如“养高兼养闲,可望不可攀,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则侧重说明李白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傲岸不群主要是对世俗的超越,与自然相知相亲主要是对社会的超越,而超然物外则是对生命的超越。[6 ]三个方面很有层次,也相互联系,而其核心就是逸。
唐人对李诗俊逸(纵逸、奔逸)的风格探讨比较多,对清新风格探讨比较少,这也客观地说明前者为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晚唐皮日休在一首诗中对李诗清新风格有过描述,“澄彻万寻碧”,(注: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九:“庄周变胡蝶,胡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可与此相互佐证.)似在清新一格中体会到壮的成分, 不过总的说来比较含糊。
二、“奇之又奇”与“瑰奇宏廓”
殷璠是以“奇”推许李白诗风的第一人。在肯定李诗“率皆纵逸”的风格之后,他又接着指出:“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细按文意,殷氏似谓“奇之又奇”为纵逸一格的极至或变体。刘勰论新奇一格云:“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论典雅一格云:“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并认为“雅与奇反”(参见《文心雕龙·体性》)。显然,奇有破除常规,师心独造,以新异动人的意思。殷璠、任华在论及李诗纵逸时,曾言李白“志不拘检”、“多不拘常律”。可见在破除常规、摆脱羁绊这一点上,奇、逸是相通的,不过,逸的超越常律是为了求得自由挥洒,奇的破除陈规则是为了求得新警动人,着眼点有所不同。纵逸不一定就能至奇警,而真正的奇警则必须以纵逸为基础,否则奇警只是皮相,终不免小家子气。赵翼《瓯北诗话》有一段论奇警的话,可与此相发明:“诗家好作奇句警语,必千锤百炼而后成。如李长吉……虽险而无意义,只觉无理取闹。至少陵……昌黎……实足惊心动魄,然全力搏兔之状,人皆见之。青莲则不然……奇警极矣,而以挥洒出之,全不见其锤炼之迹。”
在殷璠之前,贺知章、杜甫就对李白新奇风格的诗意效果作过形象描述。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本事诗·高逸》也记载此事,说贺知章读《蜀道难》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又对《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诗而至于“惊风雨”、“泣鬼神”,可以说已经达到新警动人的极至,若不是“奇之又奇”,是不能获得如此效果的。今见《河岳英灵集》选李诗十三首,《蜀道难》、《乌栖曲》俱在其中,不知殷璠选评李诗是否受到贺知章激赏的启发。在殷氏所选诗目中,《远别离》、《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将进酒》诸篇均纵逸而至奇警,可称“奇之又奇”。可见“《蜀道难》等篇”谅非虚语,而这类风格最充分地体现了李白的独创性。
中唐之时,人们对李白诗歌奇的风貌似乎有了更多的认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元稹在为杜甫作的墓志铭中也说:“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但元、白的认识尚局限在“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等艺术表现领域,对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意味认识不足。元和十二年,范传正为李白新墓作碑铭,对李白的性情抱负、人格气度以及诗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分析,将李诗风格的阐释建立在分析诗人性情抱负和人格气度的基础上,从而揭示了李诗“瑰奇宏廓”风格的精神内涵。范《碑》云:“(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接着在叙述李白生平的过程中,对诗人的性情抱负、人格气度作了概括评论。一次是叙及李白入京前,“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一次是叙及赐金还山之后,“(白)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并将作诗视作诗人性情抱负自适的表现。
在范《碑》之前,李华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中就曾感叹,“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侔于天”,并指出李白之志就在于“济难”、“安物”,其根本仍源于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然而李白之“奇于人”的地方并不全在于济难、安物的思想构成本身。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济难、安物的思想,但杜甫的这种思想表现执着甚至迂阔(“老大意转拙”)。李白则不然,他的这种思想更多地是以一种自负、狂放甚至超然的形态来表现的。李白奇于人的地方,一方面在于其济世思想极其弘大,有力度而异乎常人(“众人见予恒殊调,闻予大言皆冷笑”),体现了极强的主体人格精神和个性色彩(“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另一方面在于其济世思想的执着常表现为其反面:狂放、超然(“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这两个方面又因为李白真于性情而表现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灿烂瑰丽。韩愈说李白“烂熳长醉多文辞”(《感春》)恐指此而言。范《碑》以瑰奇论李诗,可能也是注意到这一特点。以超然写执着,因灿烂见天真,这正是李诗瑰奇的内在魅力。如果说超然趋于轻、淡,执着趋于重、浓,灿烂趋于多彩,天真趋于纯净,那么李诗的瑰奇就是在浓淡轻重之间,多彩与纯净之间体现了最好的结合。后人常用“语奇”、“句奇”、“韵奇”论李诗,其实都是枝叶,至于“强弩之末,杂以长语,英雄欺人”的评论,则更是未及李诗的藩篱。
关于李诗宏廓的境界,范《碑》也有具体描述,一曰“万象奔走乎笔端”,一曰“吟风咏月,席地幕天”。前者主要说明各种意象在诗中快速转换的情景,后者主要说明李诗以天地为境界的阔大特征,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元、白在论及李杜异同时,曾对李白、杜甫诗歌境界的优劣作过比较:白居易认为杜诗“贯穿古今”、“过于李”;元稹认为在“铺陈终始”、“词气豪迈”这一点上,李不及杜之藩篱。其实,李、杜诗都有境界宏廓的特点,如韩愈诗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荐士》)。只是杜甫以历史时空为境界,故“贯穿古今”过于李,而李白以自然时空(宇宙)为境界,历史时空穿插其间时多作虚化处理,故“席地幕天”是其特色。若以时空的恢弘廓大而论,李白是胜过杜甫的[8]。其次,李白尚虚重气,杜甫尚实重意, 尚实则时时有铺陈,重意则转换有交待,故“铺陈终始”确为杜诗所长。然而尚实重意,铺陈终始必然影响词气的飞扬,而用意曲折、转换费力则必然限制风调的清远。杜诗之长并不在于“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杜诗虽豪但用迈字不得,虽深但用清字不得,杜诗的长处在于“词气雄浑而风调沉深”。相反,“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则像是李诗所长。同样是诗中体现了“万类困凌暴”的宏廓境界,李、杜是有所不同的。元、白站在写实的立场上,当然是不会发现李诗宏廓境界的独特魅力和永恒价值的。
三、“天仙之辞”与“搜括造化”、“力敌造化”
李白飘然不群的诗歌有着难以言说的惊人魅力,人们或以逸视之,或以奇视之,或者竟以仙视之。始初人们以仙视之,仅仅是一种比喻,意在摆脱难以言说的语言困境,对于李诗风格的现实性尚有一种清醒的意识。这一点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最具代表性:“(白)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焉。……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李《序》很有分寸地指出“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可谓力敌造化”。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的意见也很值得注意:“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聚,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对于李诗风格的现实性及其表现形态,二人的把握是很准确的。
事实上,仙与逸在精神内涵上和表现形态上是一致的,“言多讽兴”、“格高旨远”是其现实基础,“力敌造化”、“天上物外”是其表现形态。司空图在描述飘逸风格时借助于神仙之境:“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惠中,令色絪缊。御风蓬叶,泛彼无垠。”也证明仙是逸的变相说法,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差异,问题是天仙之喻有可能将不可言说变成不可知论,进而对李白其人其诗神秘化,或者导致对李诗的误读,认为李诗言神仙,“飘然有超世之心”[9]。 前者主要源于对李白其人的误解,后者主要源于对李诗其境的误解。
李白生前,对他的气度才华的神秘化就有了萌芽。据李白自叙,在他出蜀至江陵时,司马承祯就认为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后至长安,贺知章在读过李白的诗作后,对他才华推崇备至,呼之为“谪仙人”,“列朝赋谪仙歌凡数百首”。后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对李白的傲岸气度和敏捷诗才进行描述。不过总的来说,李白的人间气息很重,“谪仙”之说主要还是一种比喻。元和年间,范传正为李白新墓作碑铭时,认识开始有了矛盾,一方面认为“(李白)好神仙非慕其轻举”,一方面又说“嵩岳降神,是生辅臣。蓬莱谴真,斯为逸人。晋有七贤,唐称八仙。应彼星象,唯公一人。”对于李诗中的游仙题材和神仙境界,范氏的评价是准确的,但对于李白才华的成因,范说就有了不可知论之嫌。不过终唐之世,谪仙、天仙之说尚限于对李白才华的形容和诗境的描述,并未涉及李白的思想和其诗的主旨,基本上还属于风格论的范围,虽有神秘化的嫌疑,但在具体说明时,多从意象和境界立论。
李白谪仙般的才华,天仙般的文辞,主要体现在“搜括造化”和“力敌造化”两个方面。造化云云,本指天地自然,既可指天地自然之象,也可指天地自然之道。“搜括造化”,就自然之象而言,“力敌造化”就自然之道而言。李白在模写物象方面曾得到元稹的高度评价,认为可以和杜甫相比。韩愈也认为李杜诗歌使“万类困凌暴”(《荐士》),充分肯定了李杜诗歌描写物象的广泛性以及在运用意象时所体现出的主体力量。不过就搜取物象的范围看,李白似乎要更广泛一些,主体力量更强大一些。齐己《读李白集》诗云:“竭云涛,刳巨鳌,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骊龙不敢为珠主。人间物象不供取,饱饮神游向玄圃。”贯休《古意》诗云:“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皮日休《刘枣强碑》云:“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唐人普遍意识到李白诗中出现了大量的非现实的神话仙界意象,并认为这是诗人感到“人间物象不供取”,亦即现实意象的客观有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同时又意味着诗人主体精神的极度张扬,“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皮日休)。胸襟的阔大和气势的宏放使得李诗必然超越人间日常意象,转向非现实的虚幻意象,使“搜括造化”、“笔驱造化”达到极至。这是人们认为李诗“多似天仙之辞”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后人误以为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的一个主要证据。
李诗“多似天仙之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艺术表现上“力敌造化”——取法造化之机,体现自然之道,让艺术表现形式自身就能充分体现生命的勃勃生机。唐人对李诗这一特点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诗中意象形态和意境呈现方面,也体现在语意句法多取散句,少用以句这一点上。任华云:“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刬见孤峰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云:“万象奔走乎笔端。”均注意到李诗的意象、意境呈现多取自然飞动之态,以意象、意境的流走飞动来体现自然生命的节律。具体到句法上则是李白喜用流水句式以写景抒情,如写黄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写明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都用流水句式写景,以突出其气势和生机。前人评“黄河”句云:“有如生龙活虎,非世人所可驾驭。天实授之,岂人力哉?”(《唐宋诗醇》)评“明月”句云:“飘然欲仙。”(《唐诗笺》)便是证明。另外,在意象的模写上,李诗往往是略其形色而取其神气,疏于体貌而真于性情,这一特点就是唐人普遍注意到的清。前言清就语言省净而言,其实清也指意象疏略形色。中唐诗人张碧说李诗“青且无际”,皮日休说李诗“澄彻万寻碧”,就是针对意象的特色说的。任华在选择自己最喜爱的李诗佳句时,选择了“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而没有选择“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因为前者更为脱略形色,更为清空。脱略形色则更近于本真,飞动流走则更富于生机,李诗“力敌造化”的关键可能即在此处,而李白“垂衣贵清真”、“天然去雕饰”艺术理想的真谛亦在此处。在传统诗画艺术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已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如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力敌造化”,使一切艺术表现手段逼近本真,复归于自然,真正做到一喷即是而又出神入化、气足神完,则又上升到艺术境界的极至。李白的很多诗篇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李白的天仙之喻实亦由此而来。
收稿日期:1999-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