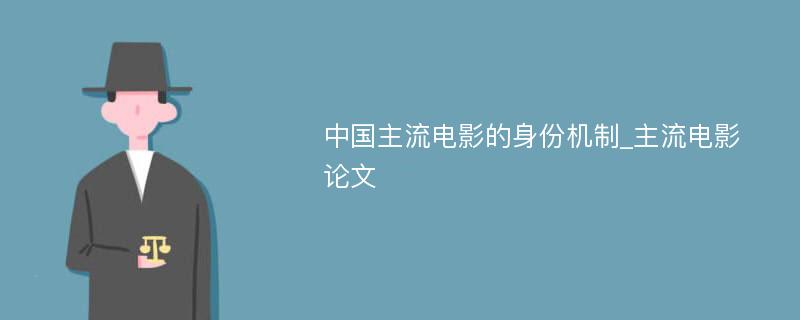
中国主流电影的认同机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制论文,主流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电影界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讨论电影情节剧问题。其间谈到关于中国电影在文学剧作上如何摆脱单一的写作模式,触及到电影与观众在社会心理方面的相互交流问题;到80年代后期逐步确认电影艺术的娱乐功能,在电影界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娱乐片”的讨论,许多学者借助于西方电影理论的方法展开了对电影观众心理的研究,把传统的电影艺术研究引入到电影心理学领域;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电影尝试建立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人们在电影的观念上开始正视电影的商品属性,并且把对电影娱乐功能的认知提高到电影制作体制的层面上,进而改变了中国电影传统的运作方式,拉开了电影体制改革的大幕;到新世纪中国电影开创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制片、发行、放映三大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彻底摒弃了旧式的电影思维方式,把电影观众的认识纳入到整个产业结构之中。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电影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其间,主流电影的心理认同问题,一直是制约我们本土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特别是这样一个涉及到电影创作与观众心理的复杂问题过去被简单地归之于所谓影片的观赏性问题——无形中把制约本土电影市场的核心问题变成了一个电影艺术表现技巧的枝节问题。
中国电影长期以来被区分为“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地下电影”几种不同形态,并且相应地总结出几种不同的叙事风格和市场策略。目前,这种截然对立化分方式不仅很难正确地描述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创作实际,而且这种分法,并不能引导中国电影在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所需要的类型化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应当确认的是:除了那种没有进入电影院线发行放映的所谓独立电影和实验电影之外,我们可以把所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根据相应档期进入电影院正常放映的影片,都统称为“主流电影”。它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柱。目前,就中国本土电影的创作状况而言,提高“主流电影”的专业化制作品质,增强其对电影观众心理的调控能力,进而建构中国主流电影的认同机制,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电影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无论我们把电影看作是大众消闲生活的娱乐形式、还是作为国家盛典的集体仪式,怎样建构主流电影的认同机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认同”是当代电影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论是哪一部电影,整体影片的制造及观影条件已经先替观众指定了某种“观看的位置”,这个位置则透过观众对电影的先验性的心理支配,决定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观众对“摄影机的认同”(“第一认同”)即“观众对自我视线的认同”。同时,电影又必须倚靠每一位观众个人与虚构情境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认同对象。也就是说,电影会挑起观众对片中人物产生各式各样的好恶情感,使观众必定认同片中某个角色——基本上认同“好人”,而“坏蛋”则引起观众的憎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认同”①,这也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其实,电影的认同机制是一个以社会的主流文化为取向、以传统的民族精神为依据、以电影的叙事形态为核心的电影心理问题。在当代电影理论的范畴内,认同涉及到电影摄影机的视点与观众视线的重合,电影中的故事角色与观众想象自我的同一,电影的叙事主题与社会主题的缝合等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电影通过对观众心理的有效控制,能够把外在于银幕的观众,转化为内在于影片的、与主人公“同形同体”的主体。观众通过影像语言所表现的叙述方式,对影片所表现的文化和社会秩序欣然首肯。观众对电影的认同过程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自居性的心理过程。“这里的自居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个通过他物进行对比或反比形成或重新形成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一个认识到自己同影片中某个角色或情境有共同之处的过程”。② 准确地说应当是:观众在对影片的阅读过程中自居于主要角色所处的各种境遇之中。就内心感受而言,自居涉及到一系列观众的自我反应,它包括“移情”、“卷入”、“同化”、“忘我”……总之它意味着叙事本文对观众控制与观众自我意识的转化。所以罗兰·巴特说:“同化不是心理问题,它是一个纯结构式的程序:我是那个人,他占有着与我相同的位置”。这便是观众向电影认同的有效途径。
一、类型化策略是建构心理认同的有效路径
观众普遍的认同趋向源于类型影片的历史观赏经验中。中国电影界过去对类型电影存在着诸多的误识。认为类型影片就是胡编乱造,就是性爱和暴力,就是低级趣味!其实,比起那些具有自传体性质的先锋电影而言,一部真正赢得观众喜爱的类型影片才是最难拍的。在我们的创作理念中经常把类型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对立起来,把类型影片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旋律电影之外的“另类”来看待。其实,归根到底,类型影片的深度模式无一例外都是“主旋律型”的。有许多类型影片之所以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观众市场,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偏离了“主旋律”的心理轨迹;破坏了中国观众长久以来所积淀的对传统文化精神和电影经典样式的认同。事实表明:中国电影在表层形态上的类型化与在深度心理的“主旋律建构”其实是赢得市场的一种有效途径;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策略是其占领电影市场的可靠方式。
如今,主流电影要赢得观众的心理认同,首先应当引入类型化叙事策略,即把革命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一种类型化的电影语言模式上,并且逐渐形成一种经典化的电影样式。《我的母亲赵一曼》的前半部分,描写赵一曼在城市进行对敌斗争的时候,基本上采用的是惊险电影的情节样式。表现了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赵一曼深入虎穴,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英勇斗争。后来她亲眼目睹了与自己刚刚接头的同志被敌人逮捕,自己领导的罢工工人被日寇血腥屠杀!这样的叙事策略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增强影片的戏剧性效果,而是为了在惊险、甚至恐怖的叙事语境里建构观众对赵一曼的心理认同。最近,采用类型电影叙事模式的还有重新制作的动画片《小兵张嘎》(2005)。尽管影片来自于同名故事片《小兵张嘎》(1963),但是整部影片的叙述方式,已经与传统的“小嘎子”的故事有所不同。在这部历时多年精心制作的动画片的结尾,作者采用平行蒙太奇(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叙事结构,设计了小嘎子在军火列车上救出游击队员、炸毁日寇列车的核心情节,用类型电影的经典语法重新书写了小嘎子的英雄性格。
观众对电影的认同并不是单纯地反映在影片的被表述(故事情节)层面上,而且还反映在影片的表述(影像语言)层面上。导演韦廉在《太行山上》将战争与动作两种类型影片进行有机“嫁接”,既还原了现代战争激烈、残酷、变化多端的场面,又展现了敌我双方生死交锋的逼真战斗情景。《太行山上》全片110多分钟,1655个镜头,平均4.2秒一个镜头。这种叙事节奏比胡金铨的武侠经典《侠女》(1975)在处理侠女与官兵在芦苇丛中打斗的段落(1分55秒21帧,22个镜头,接近5秒一个镜头)还快1秒;比当年李小龙创作的《猛龙过江》(1973)在结尾古罗马斗技场上展开的“双雄对决”的动作高潮段落(5分45秒,11个回合,86个镜头,平均4秒钟一个镜头)的每个镜头仅慢0.2秒。显然,当今的电影创作者不仅是把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题材来对待,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类型化的电影形态进行运作。包括启用港、台电影明星出演我抗日军官,都是在这种总体策略的安排下予以实施的。曾在武侠电影《英雄本色》中出演武松的梁家辉,他扮演的独臂团长挥舞大刀血战沙场的场面,显示了中华儿女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观众对梁家辉过去形象的认同,自然会“平移”到他扮演的主人公身上。由台湾著名演员,有琼瑶系列作品的当家小生之称的刘德凯扮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梦龄,也通过他的一系列流行文化作品与观众建立的心理认同关系,演绎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悲壮情怀和身先士卒的壮举,强化了观众对抗战英雄形象的认可。《太行山上》还专门聘请了动作指导负责影片战争部分敌我双方搏斗场面。导演以快速的剪辑节奏和大量的移动摄影,从视觉感受上强化了观众对影片的形式认同,进而为观众向电影的主题认同提供了特定基础。
我们从总体上确认电影是一种影像商品、一种文化产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能够在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按照市场化的规律来进行电影的创作。其实,不论是探讨两代人的感情隔膜,还是在表现同代人情感裂变,主流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都应当是一种能够让观众认同的形象。出演这些角色的演员虽然不能说都是具有市场感召力的一线明星,但是他们所具备的个性风格总应当与当下的文化时尚相同步,应当与观众的审美取向相一致。现在的有些电影在对演员的选择方面依然延续是按照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适应性、而不是按照演员与观众的适应性来确定。这就是说,一位很出色的演员和他所扮演的角色尽管非常合适,但由于这位演员本人已经成为一种“旧时的风采”,成为一种“过景的文化符号”时,他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在艺术上不能说不成功,但是在心理市场上远不如那种一线明星更具有票房号召力。这就是说,演员的选择不仅要适应角色,更要“适应”观众的心理取向。这样才能够保证一部电影能够赢利观众认可、进而赢得电影市场。
在近几年的电影创作中,我们的影片在迈向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着意于对观众心理认同机制的建构,注重引导观众向影片中的主人公的认同。现在中国的主流电影在叙述形态上与过去最为不同的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旋律电影中,叙事语态普遍具有一种“内在”于电影剧情的特点:电影的叙事者不再是一个外在于故事内容的客观叙述人,而是一种内在于影片叙事体系之内的角色。这种叙述者身份的转变,使观众易于“跟随”叙述者进入电影的叙事体系,把外在于电影的观众转变为一个内在于电影中的角色。影片《我的母亲赵一曼》(2005)与影片《赵一曼》(1950),同样是一个以真实的历史英雄为原型,相隔半个世纪,电影呈现的叙事方式与建构心理认同机制已经截然不同。1950年出品的《赵一曼》,基本上采取的是客观化的叙述流程。而《我的母亲赵一曼》开宗明义着意建构的是“一个属于儿子的母亲的心灵的历史”。赵一曼生前留下的一张照片和一封遗书,恰恰为这种叙事视点“内置”提供了历史的合理依据。影片通过儿子的主观叙述告诉观众的除了赵一曼的革命经历,还有她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者身份的变化,首先使赵一曼的形象高度地母性化,为她向观众讲述自己的骨肉亲情提供了叙事的合理性,向观众打开了认知其内心感性世界的通道。
其实,不同的电影,通常采用的是不同的叙事策略。对于现代电影、先锋电影、作者电影这些非主流电影而言,他们并不是要与观众建立传统意义上的认同关系——他们有时甚至是在颠覆这种关系。就像阿仑·罗勃-格里叶的影片,被称为是一种“特有的匿名报导语态或隐身证人的叙事风格……‘摄影机——眼睛’叙事,这种风格把叙事者的作用减至最低程度:人物、背影和暗含的参照世界似乎在直接传播,而叙事者则被降至一种被动地进行观赏或记录的地位。此类叙事者被完全剥夺了所具备的个性和人格的特点。”③ 它“标志着一种零度的个人化”,“它”似乎不代表任何主体个人的叙事风格,而只提供一个观看电影情境的外界视点,就像在影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一样,导演阿仑·雷乃常常不是“合理”地使用摄影视点,观众经常是从一个假想的高位视点俯视“剧”中的情境,这种“零度视点”的运用打破传统电影中的以常规视点、人物视点为轴心的影像体系。从而改变了电影与观众之间原有的同一关系。由于主流电影的创作理念是以大众的观赏心理为基准的,以常规的电影语言形态为构架,所以,在主流电影的创作范畴内,并不适合于过多地采用现代电影那种“零度个人化”的叙事策略。我们中国的许多电影的导演,直到影片在市场面临绝境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不应当用拍摄艺术电影的方法来拍“主流电影”。
二、集体想象与自我欲望相互“缝合”
不论是立足于电影的商业利益,还是立足于电影的思想导向,电影叙事的基本动机都是诱使他们产生观影的欲望,进而诱使观众向影像世界认同。从电影的幻觉化的语言机制和梦幻化的观看语境来看,这种“欲望的达成”通常不仅是建立在观影者意识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建立在其潜意识的层面上。通常看来观众走进电影院不是为了受教育,受洗礼;而是为了追求心理快感,追求感性的愉悦;但是这种心理快感在现实的层面上是很难真正实现的。比如说性的幻想、愤懑的宣泄、爱情的渴望……观众这种观赏心理,实际上必须通过电影叙事规则的“包装”与“校正”才能够被观众所接受。也就是说,它必须建构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的根基之上。有些影片尽管在表面的影像系统上并没有什么暴露的镜头,但是在叙事系统中对古代娼妓制度的表现,使影片的价值体系明显发生了倾斜;还有某些表现当代生活的香港影片,以色情杂志的市场营销为题材,通过色情杂志记者的视线把观众带到娱乐色情场所,把卑劣龌龊的内容直接呈现在银幕上,满足部分观众不健康的心理欲望;有些惊悚探案电影把人蛇互变作为叙事的焦点,玩味丑陋扭曲的生理奇观。这些影片的商业策略明显表现对观众某种潜意识心理的切入,但是由于这种悖逆普遍价值尺度的创作,不仅在没有实行分级制的电影市场上容易误导观众,而且即便就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电影放映体制中,由于其缺少电影叙事程序的精巧“包装”与合理“校正”也不可能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同,即不可能赢得电影市场。
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它所涉及的精神层面不仅仅包括人的社会理性、家庭伦理、文化道德这些领域,电影梦幻化的观赏情景与语言机制,使其必然进入到观众潜意识领域。尤其是在电影观众的心理认同机制中,潜意识的内容往往占据着非常重要的部分——意识有时仅仅是冰山浮出海平面的一角,而潜意识则是深藏于冰山之下的巨大根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电影通过叙事主要注入的是正面的、政策的、道德的、政治的,总之是偏重于社会理性的内容,同时对于那些潜意识的、本能的、人性的内容尽量予以删除。电影的这种理性形态并不是作者个人的主观因素所致,而是中国电影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位置所造成的。在中国电影恢复了其娱乐的与商业的职能之后,特别是在中国电影步入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近年来我们的电影开始注重对观众潜意识的控制,开始凸现人物的自我精神世界,开始建立电影与观众的心理认同路径。这也表现出中国电影现在与过去不尽一致的时代症候。影片《跆拳道》(2003)主要表现的是主人公争夺跆拳道世界冠军的故事。影片弘扬的是为国争光的爱国主题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主题,有意义的是作者呈现这些主题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再现主人公如何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而是在人物的成长过程中设计了她与男教练之间始终尚未言明的情爱关系。这种叙事策略的心理效果是:主人公逐渐登临冠军奖台的过程,同时被演化成两个人在情感上不断爱慕、直至相互倾心的情感过程。影片通过一系列的叙事情节(其中包括个别裸体镜头)诱导观众向女主人公认同:使她在观众的视线中不仅是一位意志坚强、体魄健康、技艺出众的体育健将,更为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位体态迷人、情感丰富的现代女性。影片《惊心动魄》(2004)是一部以抗击SARS为题材的主旋律作品。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将女主人公军医扬萍与其前男友呼吸科专家梁文勇的感情关系作为与抗击SARS始终平行的心理线索。女军医扬萍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她恪尽职守,舍生忘死,同时,作为一种“需要男人”的女性角色,被“书写”成为一位具有女性柔情的银幕形象。观众通过呼吸科专家梁文勇的视线,不断接近她的内心世界。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两人终于“鸳梦重温”,影片结尾两人双双站在救护车上,携手并肩面对未来的生活,是这部影片动人一幕。影片中的另一位女主角是列车上抗击SARS的总指挥,就她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应当说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同时,作为一位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她之所以选择1120次列车,是因为她要把“对逝去人的回忆作为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尽管她面对乘警时时送来的“秋波”也始终保持的某种克制态度,但是这种叙事策略的效果是:这个人物既具备一种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对失去的丈夫的“忠贞”,同时又显示出她依然具有女性对男性的魅力。影片的情感主题与社会主题为此得到重合。虽然这些形象都不是好莱坞电影中那种被完全“时尚化”与“性感化”的女性角色,但是她们的凸现,弥合了中国主流电影曾经“空出”来的心理空间——在这个被潜意识所充溢的空间里,体现出了一种人物心理结构与性格的完整性,使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体验,从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集体想象和一种个人的自我欲望相互“缝合”在同一个电影的叙事本文中。《惊心动魄》为此真正成为一部表现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在飞驰的列车上——人性、正义、爱情、都在危难中复苏、升华”的主流影片。
三、平民化的叙述视点与人格化的精神塑像
对于中国主流电影而言,主旋律影片无疑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强调主旋律电影的所谓“政治属性”和“国家意志”。其实,在电影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境遇中,在电影大众文化、娱乐化的文化氛围中,电影很难具有脱离了商业属性的“政治属性”和背离了大众意志的“国家意志”。现在,主旋律电影也在不断调整策略以求得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相互统一。这种诉求不仅仅体现在影片的表现内容和美学风格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电影的叙述方式之中: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在叙事语态上,越来越多地使用平民化的叙事视点。故事片《我的法兰西岁月》(2004)、纪录片《小平您好》(2004)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邓小平形象。虽然影片表现的历史背景不一样,作品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采取了一种平民化的叙事语态,都是从普通人的视点来“看”邓小平的生活。不论是表现他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艰苦经历,还是表现他在“十年动乱”中的种种磨难,镜头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即便就是讲述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建树,也不只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论述他的前瞻性,而且还从邓小平个人的性格角度来论述他提出这种治国方略的必然性。通过平民化的叙事视点,观众看到的是一位照顾家庭、关爱孩子、和蔼慈祥的父亲;看到的是一位能够戒烟、戒酒,喜欢而且能够坚持运动的老人;看到的是一位时常惦记着普通工作人员冷暖的“老爷子”;与这种表述内容相“缝合”的是以大量的平行视点拍摄的人物采访,以现实的自然背景所构成的影像空间,以真实、生动的历史画面所构成的叙事风格,通过这一系列现代人讲述的“历史故事”,邓小平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为此,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的今天,我们在电影和电视中所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未曾在媒体上完全“接触”到的邓小平,一个被真实的影像语言重新展现的历史人物。为此,我们看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在传播理念上的一种明显变化,这就是作品的叙述内容上越来越贴近普通大众的一般心理,在表现形式上越来越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进而使观众从情感上认同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邓小平形象。
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的认同机制所建构的心理基础通常不在一个领域内。西方的类型电影通常是通过叙事情节把诸种现实问题演化成某种个人情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观众心理的认同模式。不论是对两代人感情的弥合,还是对夫妻间情感的重构,建立的都是一种以个人情感为基础的心理认同模式。尽管我们可以从好莱坞影片的叙事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寻找到它们的“同构性”,但是对社会主题的阐释通常不是这类影片的第一主题。中国的主流电影,在叙事的方式上更加注重的是对于人的社会情感的描写,我们的电影当中通常会把某种社会问题纳入到影片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且把社会化的主题“镶嵌”到影片的叙事过程中。所以,人的普遍情感通常是服从于这个人物社会情感的展现。影片诉诸于观众的并不是那种个人的、隐晦的、潜意识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心理内容。这种叙事的方式,应当说更加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电影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成为一种供人消遣娱乐的商品。在相当的意义上,它还承载的对大众的教化以及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所以,与那种建立在普遍的人性状态下的认同模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电影的心理认同模式和本土化的市场策略,更多的是立足在社会心理之上。
大众传媒通常关注的是领导阶层中的两种人:一种是像成克杰、胡长青、慕隋新这样的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他们是民族的败类,是社会的蠹虫。媒体关注他们是为了将其罪恶昭告社会,同时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另一种是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这样的人。他们是世人的楷模,是民族的英魂。媒介关注他们是为了垂范天下,铭记他们的崇高精神。中国的主流电影在注重对人物社会性格塑造的同时,开始塑造他们人格化的精神雕像。其实,不论是县委书记(焦裕禄)、地委书记(孔繁森)、还是省委书记(郑培民),人们之所以敬佩他们,爱戴他们,追忆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领导地位和拥有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所特有的一种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集中体现在他们为人民做好事,为国家谋利益的时候,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在乎自己的荣辱。这种一心为民的精神,使他们能够默守无数的平凡瞬间,去做那些一般人不想做、不愿做的事。他们并没有留下什么惊世骇俗的格言,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对普通百姓做的每一件事,就像郑培民去倾心照料一个无人照料的囚犯的女儿;他们的力量还来自于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去兑现对社会所承诺的每一句话,就像焦裕禄立志要根治兰考县的盐碱地,就像孔繁森要帮助藏族同胞致富脱贫,就像郑培民要帮助最贫困的火龙坪村修建一条通往山外世界的公路……他们的人格精神是构筑他们英雄形象的基石,他们兑现的诺言是他们赢得观众认同的文化根源。
世界经典类型电影中,英雄的胜利时常意味着以个人为中心的种种幸福的实现:受尽磨难的主人公总会获得甜美的爱情、脱离险境的家人得以团聚,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开始重新建立,总之是一切灾难都将随着一场胜利而告结束。固然我们并不是把每一部主流影视作品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可是一般主流电影的制作规范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方法,也并不足取。如果一种电影的叙事策略是以影片最终失去观众的认同为代价、进而以失去电影市场为前提的话,那么,这种策略就必须要改弦更张。包括有些融古装武侠的人物谱系与现代动作枪战叙事元素的电视剧,在描写英雄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时,不仅自己最后不幸牺牲,而且与他为伍的人个个命丧黄泉。在一部商业性极强的主流影视作品中,给观众的直观印象好像是: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法外逍遥。应当说,对于那些普通的观众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更乐于接受的是一种具有传统伦理力量的感情故事,并且从中得到想象的快感。当电影中某些内容与他们的期待相对立的时候,电影观众就可能会产生某种逆反,以至于使这种影片失去那些期望在电影中得到想象满足的观众,进而在某种意义上自我限制了电影的市场空间。
在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中,亲情伦理历来应当是缝合影片与观众心理的一种叙事因素,而不是一种间离因素。特别是通过家庭的叙事视点,往往能够从一个人的深度心理展现其精神世界,从人的本性上赢得观众的认同。影片《那山 那人 那狗》借助一个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把人的生命之旅与现实的生活之旅进行同步剪辑,父子两人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携手并肩的邮递之路,实际上是父子俩人生之路的一次重演和再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父子俩的情感从隔膜、对立逐渐走向理解、亲密。影片中自然的美景与人伦的亲情相互交织,在一个看似平淡的故事升华出一种人性的光艳。我们诸多的主旋律电影往往把是非、善恶的界线置放在家庭内部,用一种家庭内部二元对立的剧作结构来区分叙事体中的人物关系。这种划界的结果是:要么在家庭里做一个好父亲,要么在单位做一个好干部。两者不可兼得。好干部的代价是不能在家里做好父亲、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女;而要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女的前提就是要与自己的家人划清界限。这样就把人的亲情伦理与社会责任在实质上完全对立起来。像《红色恋人》这样的影片设定了一种要么背叛革命拯救女儿、要么杀死女儿献身革命的两难选择。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叛变是人性的选择,那么,革命就是他的反面。这种完全把个人、家庭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的幸福对立起来的叙事模式,在深度模式上不利于观众对影片革命主题的认同。况且,中国的电影观众是否真正会认同一个《红色恋人》那样病态的、歇斯底里的革命者(无论扮演这个角色的人是谁)?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疑问。
影像传媒在历史上历来就承担着双重职能:“一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一是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心”。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都毫不掩饰电影的这种文化职能。如今,电影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已经“不再从政治的角度去对待观众,即不把他们当作国家社会群体的公民,而是把他们当作经济实体,当作消费市场的组成部分”④ 来对待。让他们在分享电影带给他们的快乐的同时从中得到精神的陶冶与道德的升华——最终,让他们喜欢看自己的电影。中国电影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从行业垄断的封闭型环境到开放竞争的国际化境遇的转变,从单一的影片盈利模式到多元化的市场空间的拓展。中国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好莱坞电影不可一世的市场神话不断破灭!中国电影已经连续三年夺得内地电影市场的单部影片票房冠军(2002年《英雄》一举拿下2亿6千万的票房业绩;2003年,《手机》以5600万票房夺取单片冠军;2004年《十面埋伏》以1.53亿赢得了年度单片最高票房的桂冠,超过当年上映的美国大片的票房成绩)。好莱坞进口分账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屡屡失利证明:中国电影是否吸引观众,其关键因素并不仅仅在于电影的视听效果和用巨额资金搭建的影像奇观,而在于电影所讲述的具体的故事内容是否能够打动人心,在于电影的核心人物与叙事主题是否能够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同。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文化江山”与“媒介领土”需要倾心建设的年代,中国电影要想在世界电影的总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形成一种能够与世界电影界相互对话、交流的主流电影体系,我们不能把整个本土电影的市场征战寄托在有限的几个人物和单一的创作领域内,必须使我们的主流电影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为此,才能完成中国电影发达中兴的历史大业。
注释:
①[法]Jacques Aumont & Michel Marie著,吴佩慈译,《当代电影分析方法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1997年4月1日初版,251—260页。
②贾磊磊著,《电影语言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114页。
③[美]罗·伯戈因,《电影的叙事者:非人称叙事逻辑学和语用学》,载《世界电影》1991年第三期。
④[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4页。
标签:主流电影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电影类型论文; 情感模式论文; 我的母亲赵一曼论文; 太行山上论文; 剧情片论文; 战争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传记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