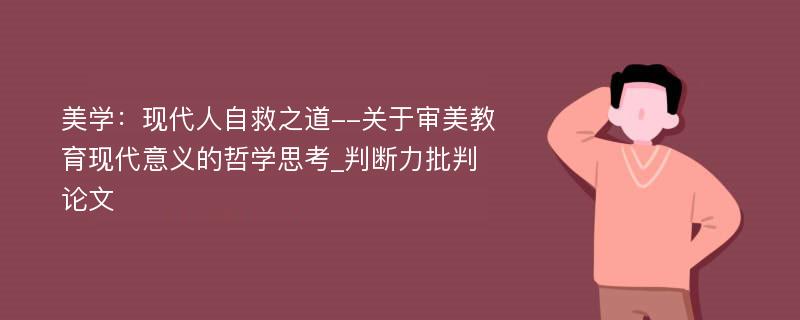
审美:现代人的自我拯救之道——对于美育现代意义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之道论文,现代人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的发现和认识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把审美看作是建设“正义”国家,培养“正义”个人的重要途径。但在以往,人们较多看到柏拉图对艺术否定和排斥的一面(其实,他所反对的只不过是亵渎神灵、挑动情欲的那一部分作品),而没有注意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对于美的艺术在教育青少年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予以如此热切的关注和重视。就在《理想国》中,他提出了要寻找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像住在风和日丽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这样,通过美的熏陶,就可以使青年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他的“性格变成高尚优美”(注:柏拉图:《理想国》,《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4页。)。这就是对美在陶冶人的情操方面的作用所作的一段绝好的描述。
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美在塑造人的美好心灵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比较起来,却从没有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突显出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那种独特而为其他事物所不能取代的重大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比较歧义的概念,一般说来是指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使得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而精密,生产的活动也越来越机械化、标准化、划一化。这种生产分工尽管大大地促使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丰富,但它的负面效应也随着它的发展而日益得以暴露,这就是它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异化”现象,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马克思就曾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即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反过来成为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力量),行为的异化(劳动不是使人感到幸福,而是不幸,不是工人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发展,而是对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类本质的异化(是劳动仅仅成为个人维生的手段而意识不到自己类的存在)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由于意识不到自己类的存在,从而使得私欲支配着人的享受和需要,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敌对)。而在这四种“异化”现象中,产品“异化”又是一切“异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几种形式的“异化”都是由物对人的支配和奴役所派生的。而这种物对人的支配和奴役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人丧失了对自己工作本身的兴趣而把物当作唯一的追逐对象,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为一种纯粹利欲的关系,并完全为利欲所束缚。这样,工人在劳动中就丧失了他的自主性,使劳动变为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4、51、51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9页。)。与之同时,作为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同样被自己的活动工具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从而使得“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成了)人的自我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成为一种仅仅被利欲所支配的工具,人也就完全被分裂了、物化了,也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的异化还是仅仅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那么,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这种被物所支配、奴役而失去自身自由的状况不仅没有因社会的发展而获得丝毫的改变,而且还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增长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剧。按照西方有些学者的看法,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既是一个信息社会,又是一个消费社会。所谓信息社会,就是信息被视为社会生产的重要资源,信息的加工、处理、传递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关键。这样,就造成了社会劳动力的结构的重大变化,以致科学家、信息处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成为劳动者中的主要成员,从而使得知识也随之成了商品。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突出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人们的学习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充实、完善和提高自身的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挣钱的工具,就像弗洛姆所说的,“他的目的是在人才市场上怎样使自己卖个好价钱”。只要能获取高额报酬,就自愿接受支配,按照别人的意愿行事。这样,知识作为一种物质交换的形式、一种物的异在,反过来也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己力量。后工业社会又是一个消费社会,因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高速发展是通过消费来推进和维持的。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以各种手段无限制地刺激人的物质欲望,试图通过高消费来推动生产的高速增长。这样一来,人又进一步被塑造成了一种物的奴隶,以致把自己生存的目的全部寄托在只是为了获得当下的、即时的、物质的享受上,而不再有高尚的、精神上的追求。对此,弗洛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使人本身越来越形成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地人却成了物的奴役”,成了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需要,而是被广告所操纵的、为消费而消费的“强迫的”、“虚伪的”、“炫耀性的”消费者,“尽管他吃得好,娱乐得好,然而他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和情感的”(注:弗洛姆:《生命之爱》,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所以马尔库塞把消费主义看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进行奴役、控制、剥夺人的生存自由的一种新的形式和手段。
这都说明,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人的境况在表面上虽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这些社会都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使人成为物的奴隶,把人与世界本来所具有的丰富的关系都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功利的关系和欲望的关系。以致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注: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这种利欲关系的危害就在于它把人引向只关心一己的利害而丧失了人类普遍的情怀,只热衷于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不再有对自己生存的终极眷念,只为了求得当下的物质享受而忘却了人生根本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也就不会再有超越于经验之上的追求和梦想,他的生存也就失去了精神的根基和依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他即使生活富有、活得开心,但是在物质的面前他已经出卖了自身而成为物的奴隶,时时、处处都在被物欲驱使去从事自己的活动,就像陶渊明所说的“以心为形(所)役”,苏东坡所说的“此身已非吾有”,他自身已经失落,他的自主性、自由性已经消失,他已经不属于他自己的了。这实际上是人生的最大的悲哀和不幸,对于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境况,马尔库塞曾以“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去加以概括。现代人的痛苦即由此而来,现代社会的病态也由此而来。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要摆脱痛苦,获得拯救,从生存论意义上而言,最根本的一点,就得要使自己从物的奴役中摆脱出来而重新夺回自由。
二
“自由”就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使自己回到为自己作主的地位。卢梭说:“仅有欲望驱使是奴隶状态,唯有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所以它也就是不为欲望驱使而自己做主、即自律的意思。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活动的根本特征,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罪恶就在于它使工人的活动变为“不是他自主的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的,因而这种活动也就成了“他自身的丧失”(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4、51、51页。),成了对他的一种奴役。这样,他的活动也就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么,怎样才能使人在活动中摆脱强制和奴役而获得自由呢?最主要的就是在活动中把自己置身于主动的、自己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地位,感到他是为了自己并出于自身的意愿、兴趣和爱好而去从事这种活动的。这样,活动就不再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成为目的;不再是一种苦役,同时也是一种享受了。
而意愿、兴趣和爱好在构成人的活动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情感指向,是不直接为利益所支配而纯粹出自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在人的活动方面,任何领域都可能会有强制、束缚和奴役,唯独在意愿、兴趣和爱好领域,他完全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己决定自己的,他绝不会出于功利目的按照外在的、别人的意志与他自己的活动对象建立情感,产生兴趣和爱好。这就决定了只有意愿、兴趣和爱好,才是人的活动的积极性、持久性、创造性的、真正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源泉,并使得人的活动超越了动物的那种被动的、仅仅在求生的需要支配下的、本能的活动,而成为人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生存方式。
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自身的丧失的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它使人在自己的活动中丧失了自主的、“主人翁”的地位和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和爱好,变成了仅仅为了生存活命的“打工者”(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高收入的管理人员与低收入的普通工人并没有什么差别,尽管他们生存、活动的方式不同)。虽然他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知),熟练的操作技巧(意),但是当他发现他的工作是雇佣的、强制的,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为自己工作而是为别人在工作,而且自己只不过像是机器的一个附件,日复一日在被动地、机械地在重复着同一工作,那么,他对工作就必然是缺乏情感的,不仅没有兴趣,而且还会产生厌倦的心理。这样,他身上的知、意、情也就分裂了,因为他的知识和技能除了作为直接获得物质利益的手段之外,就不再有自身超乎物质利益的价值了,这就必然会使人的情感贬降为一种动物性的情欲,从而使得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机器生产条件下从事工作的工人,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对自身工作方面的兴趣反不及中世纪的手工业工人。因为中世纪的时候,“在城市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原始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作,凡是他的工具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这就使得他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还有一定的自主性,不像大机器生产那样,只是整个工艺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正因为如此,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练技巧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则远远超过对工作本身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9页。)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进步不仅没有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反而使人的理智、意志、情感进一步的走向分裂,使自己的一切活动都被眼下的欲望的关系所支配而不再有超越这种欲望关系的兴趣和爱好,这样,劳动对人来说也就必然成为一种负担,一种苦役,一种只是为了生存活命的强制的行为,结果使工人像是马克思说的:他们“只有在运用自己动物的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4、51、51页。)。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里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也指出:“奇妙的机器如果落在公正而有远见的人手里,就会用来减少令人生厌的劳动,给予人类以快乐,或者说丰富人类的生活,但是现在这些机器的用处却适得其反,他们把所有人驱向紧张、忙乱中去,因而从各方面来看都破坏了快乐,即破坏了生活;它们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却加强了劳动,因而在穷人必有的负担上又增加了更多疲倦。”(注:莫里斯:《艺术与社会主义》,《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第90~91页。)对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这种人的自身的丧失,罗丹则说得更加直白,他认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所缺乏的,在我看来,就是对于自己职业的爱好;他们仅以厌恶的心情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有意识地草草从事——自上至下,社会各阶层都是如此。政客们凭借他们的职权,所注意的无非是能获得物质的利益,他们似乎不懂得过去的伟大政治家把国家大事管理得很好的时候所感到的愉快。实业家不想保持自己创立的商业荣誉,只求伪造货物,得到更多利润;工人们,用了多少是合法的对资方的敌视态度,草率地做他们的工作。工作本应看作是我们生存的理由和我们的幸福,可是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视为可怕的强迫劳动,可诅咒的苦役。”所以他感叹道:“如果工作对于人类不是人生强索的代价,而是人生的目的,人类将多么幸福!”(注:葛赛尔:《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118页。)这都向我们表明,这种变目的为手段、变自由为强制、变享受为苦役的现象之所以在人的活动中普遍存在,从人自身来说,其原因就在于人对自身的活动普遍丧失了兴趣和爱好。
正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强制性出现的人在活动中兴趣和爱好的丧失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理智、意志、情感的分裂而使人的情感贬降为一种动物性的情欲,以致人的活动除满足于一些本能的、肉体的、物质性的享受之外,而再没有超越于物质的精神上的追求。所以,马克思、莫里斯、罗丹在指出异化劳动的罪恶的同时,都主张要改变这种状况,从主观的、心理的领域来说,就必须从拯救人的情感、使人摆脱强制而重建对自己工作的兴趣、爱好入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同时,就提出劳动应该属于“人的专有物”,“应该以自己的内容和方式来吸引劳动者”,应该“把劳动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来享受”(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8页。)。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游戏”的概念来自康德。康德在谈到艺术与手工业的区别时,认为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被“雇佣”的;前者好像“游戏”,它使“自身愉快”,而后者“作为劳动”只是为“结果”所吸引,它对自身来说“是困苦而不是愉快的”。所以他把那摆脱强制,建立在对事物的自由爱好的基础上人的活动称之为“游戏”(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9~150、46、146页。)。莫里斯在试图改变工业文明使人的劳动变成“生厌的负担”时,也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艺术与劳动混合的主张”,认为这种艺术与劳动混合的标志就在于在劳动中人人“做值得做的工作”,“做高兴做的工作”,“做条件保证下的、既不致于过分疲劳、也不致于过分紧张的工作”,“凡不值得做的工作,或必须使劳动者堕落然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都不应该用人的劳动去完成”,他所说的“艺术”实际上也是“游戏”的同义语(注:莫里斯:《艺术与社会主义》,《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第90~91页。)。罗丹在同样的意义上强调为了使工作成为“人生的目的”,唯一的途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变成艺术家”。他这里所说的“艺术家”指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是“游戏”那样,“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愉快的人”。如“木工艺术家,熟练地装配榫头和榫眼而感觉快乐;泥瓦艺术家,心情愉快地捣烂泥灰;驾车艺术家,由于爱护他们的马匹,不撞路人而感到骄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造成一个可赞美的社会”(注:葛赛尔:《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118页。)。这些言论所表明的,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把劳动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来享受”的意思。由于这时人们在工作中都超越了利欲关系的束缚,成为自己的意愿和情感所向,这样他们的活动也就由手段变为目的,强制变为自由,苦役变成了享受,理智、意志、情感在人身上的分裂也就重新回归统一,对活动的兴趣和爱好也就失而复得,人在活动中也不再是奴隶、“打工者”而是主人翁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解放,也就是这样一个人性得到复归,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理想获得最终实现的过程。这种解放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一个社会的、现实的问题而非只是意识的、精神的问题;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可能会变成空想的、不切实际的“审美救世主义者”。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不能否认在人的意识和精神上所反映和折射出来的说到底也是一个社会、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以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为主导的社会里,对于人的意识和精神的提升,更应该被看作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维护人自身的健康生存和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方面一个突出问题来加以重视和解决。而在这当中,审美教育就有着为其他精神力量所无法取代的意义和作用,从对个人的、心理的领域的意义来看,它不失为是一种对“自我”的拯救。
三
美为何具有这种功效?这就得需要从美的性质说起。虽然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讨论了两千多年,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在19世纪以前,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都比较着眼于美与真和善的内在联系,而很少注意到它自身相对的独立价值。如狄德罗认为“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注:狄德罗:《绘画论》,《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第393页。)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美与真和善并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而只是表现形态上的不同。于是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出现了布瓦洛的根据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真理观提出文艺作品“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注: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第290页。),以及伏尔泰的“悲剧是一所道德的学校。纯戏剧与道德课本的唯一区别,即在于悲剧教训完全化作了情节”(注:伏尔泰:《论悲剧》,《伏尔泰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这样的观点。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都认为美是没有什么自身目的的,美的价值就在于它载负了真与善,这无疑等于把美当作是一种达到真与善的工具和手段。这样,艺术也就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了。因而这种观点出现不久,就遭到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批判。如马克思指出“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诗一旦变成了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注: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第一篇文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这当然不是说美应该像后来“唯美主义”所主张的它与真和善是绝缘的。因为美虽然是一种情感的对象,但是人的心理是一个知、意、情的统一体:所以通过审美对于人的情感的陶冶和提升,也必然会辐射到知和意的领域,有助于人的整个心理素质以及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这就决定了真、善、美三者总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辨证统一的。但这是以我们承认美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为前提的,绝不能理解为它只是真与善的工具和手段,而没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价值指向。
美的这种相对独立的性质直到康德才开始有所发现和认识。康德在“美的分析”中通过对审美判断的质和量的方面考察,提出对美的鉴赏是不以利害关系和凭借概念而普遍使人愉快的。这样,在判断形式上就把审美判断与真的判断和善的判断区分了开来。虽然这三种形式的判断都能使人产生愉快,但是在这些愉快里,只有对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愉快”;因为它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康德把这种愉快称之为“惠爱”,并强调“真爱”是“唯一的自由愉快”(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9~150、46、146页。)。这样,它就把超越欲望和理性强制的“自由愉快”当作审美判断不同于真的判断和善的判断的质的规定性提了出来,从而确定了美在整个人的对象性关系中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就像后来弗·斯雷格所宣称的:“美有别于也应该有别于真和善,与真和善有着同等的权利。”他认为艺术理论亦即诗的哲学就是“始于美的自主性”(注:弗·斯雷格尔:《雅典娜神殿的断片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9页。)。所谓“美的自主性”,就是说美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的某种工具和手段,它是自己做主的,它有它自身的目的。关于美的自身目的,奥·斯雷格尔又吸收了康德“美的分析”中关于关系和情状项目分析中提出的美是具有“合目的性”而必然使人产生愉快的对象的论述,认为审美的愉快之所以是必然的,就在于它有一个“目的性”的观念作为内在的依据,这种目的性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只能从“在那构成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道德使命”中去寻找(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9~150、46、146页。)。相对于这个终极目的,其他一切外在目的都是有限的、偶然的。所以他根据康德伦理学中“人是目的”的思想,把“美的自主性”与“人是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人的目的有些是有限的,偶然的,有些又是无限的、必然的”。美的艺术不是“为一个有限的目的服务”,从这意义上说,“美的艺术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面它又有它自身的绝对目的,即以“人为目的”,相对于人自身这个绝对的目的,原来我们称之为目的者(如借艺术来进行教训、劝善、娱乐等等),都“不过是知性的一种有限任务,是对绝对目的的一种否定”(注:奥·斯雷格尔:《关于美文学和艺术的讲座》,《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页。)。由此可见,他通过把“美的自主性”与“人为目的”联系起来,为的是进一步强调由审美活动所带给人的“自由愉快”的这种超验的、亦即超越一切利害关系的束缚、强制和奴役的性质,对于构成真正人的生存状态来说,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它最终完成了对人的本体建构,表明人不同于动物,因而审美境界也就被人看作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
审美为人们所创造的这种自由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使人的活动超越利害关系而就像游戏一样建立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的基础之上,凭自由愉快与对象发生关系,这对于克服现代社会由于异化加剧、由于物对人的奴役所造成的人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厌倦和痛苦,使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来说,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种情感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摆脱异化劳动所造成的手段与目的、享受和劳动的脱节,使劳动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种“人的专有物”,一种“体力和智力的游戏和享受”。真正人的活动总是在知、意、情等心理机能全面参与下而进行的,它不仅具有意识性和目的性,而且还总是以自己强烈的兴趣和高昂的情感去激发和推动的。休谟认为“理智是冷静的超脱的,所以不是行动的动力,……趣味由于产生快感或痛感,因而就造成幸福或痛苦成为行动的动力”(注:休谟:《论人的知解力》,《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页。)。因此审美鉴赏那种不带物质占有欲望而仅凭感性外观所带给人的“自由愉快”,尽管对人来说是没有实际利欲可言的,但它却可以激活人的情感、培养人的兴趣和爱好,促使他把自己全身心都调动起来,以轻松的姿态,高昂的情绪,愉快的心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所以康德认为与“痛苦是生命力受阻的情感”相反,“快乐则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情感”(注: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页。)。惟其具有这样一种积极高昂的情绪,他才有可能会在劳动中排除一切艰难险阻,不折不挠地坚持到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其次,审美活动所激活人的情感和培养人的兴趣爱好,还会使劳动者感到劳动是他的生活必需,从而使自己在劳动中排除那种单纯的物欲考虑,把自己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自身的意愿的基础上,甘愿为它牺牲,为它付出一切代价。这样,劳动对他不仅不会感到是一种强制、一种苦役,而且是一种享受,他在劳动中是居于“主人翁”的地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在进行工作,而不再是为雇主卖命的“打工者”了。惟其如此,他才会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对象,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一种痴迷,感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乐此不疲。这种痴迷不仅会减轻他的压力,提升他的劳动的功效,而且还会使得他永远不满足于现状而无休止地去追求完美、追求自我超越,从而使自己的智慧、意志和一切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在工作中才会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一个人工作成绩的大小,往往就是与他对于自己工作的这种痴迷的心态、执着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劳动也就成了他自身聪明才智的体现,他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自身价值的一种证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劳动所具有的特性。
再次,为审美活动所激活和培养的人的兴趣、爱好,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情感指向,它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营造一个精神上的家园,使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情感和精神生活有所寄托,从而可以使他的紧张、繁忙的生活有所调节,现实中的缺失有所补偿,被物欲所支配的心灵获得解脱。这不仅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而且还可以使得他摆脱和超越物欲的强制,进入一片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的自由天地。因为在人的生活中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有精神世界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惟有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他才有可能对自己当下的生存状态有所反思,这种反思能力使得人不只“感觉到自身”,而且能“思维到自身”,去思考什么才是应该真正属于它自己的生活。这样,才能使他与一切动物区别开来,把自己“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注: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页。)。鉴于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焦虑和现代社会的社会弊病都是由物对人的支配和奴役而使人迷失真正的生存价值、丧失自身的自由而来,这种审美所带给人们的自由愉快,对于人自身的本体建构的意义和作用也就不言自明了。因而,美也就被雪莱视作为“神圣的东西”、比作是“世间的上帝”(注:雪莱:《为诗辩护》,《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它可以取代宗教起到拯救人的灵魂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把审美看做是现代人的自我拯救之道的理由之所在。这些理论可能是“乌托邦”,但正如卡西尔所说:“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文精神淡化、价值观念迷失、一切都以功利原则来计算和衡量的时代,作为马克思所说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的哲学,包括美的哲学在内尤其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标签:判断力批判论文; 文化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