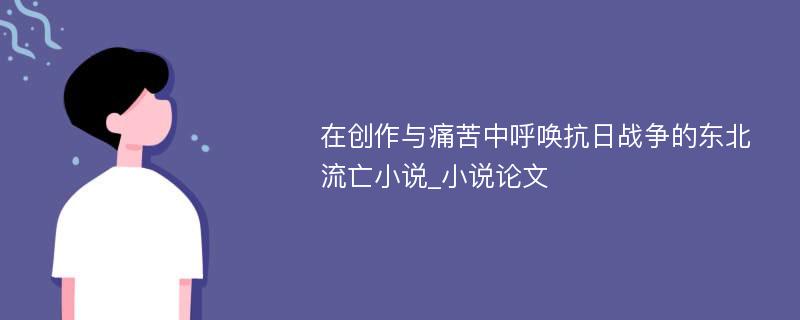
创痛中呼唤抗战的东北流亡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痛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有一个被时代潮和个人切肤创痛造就的独特小说群落,这就是东北流亡小说,它在历史的创痛和流亡的间歇里孕育,其新鲜而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东北生活题材,浓厚的思乡情绪,强烈的抗日态度,年轻而率真的生命意识,都被纳入一种历史选定的结构形态和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整体中的一部分,东北流亡小说因其独特的品格,内在的文学精神获得了相对的自足性、完整性和流派命名定性的意义。
一
“东北流亡小说”是“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寇投降期间(约14年)由流亡的东北作家群所创作的小说。其代表作家是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马加、李辉英、罗烽等。东北流亡小说是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九·一八”日寇的侵略、东北的沦陷,没有痛楚的流亡生活,就不会有这一取材新颖,意蕴独特,迅速崛起,而暂领潮头的小说群落。从这一群创作主体的才性和能量释放方式看,这是一个成长着的青年作家群,东北故土的文化风俗营养,时代的创痛,被放逐的青春生命意识的痛苦体验使他们顺势而生。因此,东北流亡小说有一个在流亡中成长的动态过程。
现代小说在东北的起步较迟。由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诸原因,1906年东北才出现作为大众新闻媒介的报纸;1907年《盛京时报》率先开设“小说”专栏,但多为文白杂糅之作;1920年底到1921年初东北开始响应新文学运动[①],《盛京时报》等副刊登载属于东北地域性的新文学作品。1921年到1930年东北出现了启蒙的新文学,但总体上讲,由于受制于东北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因素,其影响并不显著。值得提起的是1928年到“九·一八”之前,沈阳、吉林、哈尔滨都出现了有自己刊物的文学团体和青年作者群。小说方面出现了白晓光(马加)、三郎(萧军)、悄吟(萧红)等小说新人新作,虽多为幼稚的习作,但初步表现了自觉的追求。这时他们从东北的文化母体中汲取着文学营养,为后来流亡小说的形成准备了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小说作者和在关内工作或求学的小说作者合流,初步构成流亡小说作家群规模。1932年李辉英发表与法国作家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同名的短篇,以同样的模式表达反帝爱国的主题。次年他又出版长篇《万宝山》,这部几近纪实的作品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民族败类汉奸郝永德的形象。这两篇作品形成东北流亡小说的先声。
1935—1937年是东北流亡小说第一个丰收时期,也是该作家群声势最大,最引人注目的辉煌时期。萧军、萧红辗转到新文学中心上海,投师鲁迅,发表了各自的长篇《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鲁迅分别为之作序,肯定了他们的成绩。通过鲁迅的强信息输出,二萧轰动文坛,一举成名。从而使滞留北中国的东北流亡作家相继南下,汇聚上海。一时间,群集的东北作家将他们的群体意识,大体一致的文学观念,乃至主体感知和思维方式倾泄而出,形成题材、形式、语言叙述、风格等相近的小说作品群。如二萧之外又有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大地的海》、《憎恨》,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马加的《登基前后》,罗烽的《呼兰河边》,白朗的《伊瓦鲁河畔》,李辉英的《丰年》等。这批小说蕴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是反帝爱国的创作基调。流亡小说刚刚出现在文坛上时,几乎整个左翼文学界都不约而同地将其概括为“反日(反帝)爱国文学”。然而,它决非等同于近代以来具有普泛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反帝爱国文学,在大规模表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血与火的生活方面,它空前深化和拓宽了表现领域,而且就亲历目睹、切身感受来说,情绪和倾向也更为炽烈、尖锐和直接。
救亡和忧患意识是流亡作家的主导心理。它根源于故土灾变和被迫流亡的残酷生存状况,是30年代国破家亡的巨大厄运最早落在他们身上的结果。他们被从故土连根拔起,被放逐和流亡,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对共同受难的命运体验和感知,使其超越了个人乡土情结的狭隘性而升华为民族的、时代的情感。由于特定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态度,流亡小说张扬了作家们的强烈责任感,侧重于社会效应的实现。诸如揭露“王道乐土”的罪恶,从乡土的变故到都市创败,写出了东北沦陷之后日伪的罪状和父老乡亲的血泪苦痛,从而表现出悲忿、哀怨、呻吟和讽喻的特征。同时也更多地写出了东北人民的血性和骨气,他们在痛苦的咀嚼中觉醒,进而投入不屈的抗争。《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大地的海》、《边陲线上》等作品直接或间接地描写人民的奋起抗争,是抗日救亡文学中不愿做奴隶的最先呼声。
其次是在人物塑造上的引人注目。端木蕻良笔下雄强犷悍的大地之子——东北的农民和妇女形象曾引起人们的好奇,并将其与欧洲文学中的吉卜赛人相比较。流亡小说在充满紧张、刚毅、强悍,乃至原始、残忍、疯狂的画面中站立起一群单纯、粗犷、豪放的受难者和反抗者形象,有着浮雕般的感受效果。
这批不可多得的群像在现代小说中有着特殊的价值。农民在经过一个苦难的历程后,从已往麻木、愚昧、逆来顺受中渐渐觉醒并发出反抗,如《生死场》的“二里半”、《大地的海》中的艾老爹、《第七个坑》的耿大、《八月的乡村》的李七嫂等等。在军人形象中既有像《八月的乡村》、《边陲线上》中的陈司令、铁鹰队长、李三弟、崔长胜、梁兴、刘强等革命英雄主义式的新型军人;也有像《八月的乡村》、《遥远的风砂》中的唐老疙瘩、刘大个子、煤黑子等出身于旧军队和“胡子”(土匪)的抗日战士。流亡小说人物群像突出体现的共性就是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是流亡者精英对其生活意义、目的以及民族前途的文学思考。其明确的教育感化指向性,对民族抗日情绪的高涨,推动全民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流亡小说人物群像的传奇性、超常性、雄强阳刚的特征使之充实了以往反帝文学形象的不足。至此反帝爱国的思想情绪找到了坚实的文学载体,改变了“五四”反帝作品只停留在浅层情绪化的诅咒呐喊和抗议的情形。于是广大的反抗和搏战所构成历史性行为以闪光的群像方式大规模出现在现代文学中,表现了文学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
再次是色彩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流离他乡的作家们都有强烈的故乡恋情,因而创作中除用家乡的村名、地名、河流山川作为作品的篇名或故事的地点外,还大量绘制家乡的自然景观,给作品抹上了浓重的乡土底色:故乡可爱的蓝天白云,草长莺飞,桦木松林,马队羊群,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端木蕻良是一位长于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家,他追求“三分风土能入木,七种人情语不惊”[②]的小说境界,把民俗、草原和土地当成有生命的整体来写,赢得了拜伦式的诗人和“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赞誉。此外如舒群的“蒙古之夜”、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白朗的“伊瓦鲁河”都各具特色,特别是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给人以深刻的田园印象,边地的晓风残月衬托着生活的斑斓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流亡小说的自然风物景观的描绘不是客观性的,不是为了自然而自然。由于风格和地方语言的加入,特别是将人物塑造、社会关系、内容主题等与上述自然景观相融,自然景观也就成为情绪的表征而纳入了小说意蕴的总体结构中,所以流亡小说亦可看成是一种发展了的,特殊的乡土文学。在自然描述中渗入主体情绪,而且使之与总体氛围相和谐,与乡风民俗、时代、社会内容相交迭,于是流亡小说获得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七·七”事变后,流亡小说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作为流派它暂时失去了自足独立的群体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它震聋发聩、动员救亡的基本功利目的已经达到,作家的观念和审美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调节。原先由流亡作家独唱的思乡曲已汇合到由全民族同唱的,与时代交响的大合唱之中,“思乡”的唤醒基调向怒吼的基调变奏了。但应看到抗战初期由于文学生态的被破坏,作家们忙于救亡宣传和诸多事务性的工作,审美距离太近,功利目的过切,再加之作家们无暇坐下来宏构细作,小说创作陷入了低谷。仅有的少量作品明显是生活的浮光掠影,马背征程中的急就之作,虽然在精神或形式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艺术上多较为苍白。
1940年后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流亡小说家分流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部分。萧军、罗烽、白朗、舒群等辗转到延安后面临新环境下的选择、改造和整合。由于一时难以与延安文艺的内在机制相适应,更由于烦杂的事务性活动和思想政治运动的冲击,事实上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滞留在延安的流亡小说家们没能恢复和保持原有的群体特征,《狱外记》、《第三代》、《满洲的囚徒》等本应有分量的长篇失去了原有的文本内质,以余音的形式宣告了衰落。
继续流亡重庆——香港——桂林的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仍然凭着“乡关之情”的创作内聚力继续呈现出流亡小说特征,而且迎来了第二个丰收时期。例如端木蕻良的《大时代》、《科尔沁前史》、《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初吻》、《早春》;萧红的《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骆宾基的《人与土地》、《蓝色的图门江》、《北望园的春天》等等。
对这一次创作上的丰收,评论界并未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多年以来被视为“脱离政治”“脱离时代”是“小资产阶级个人情调的渲泄”。实际上,这些作品尽管有的断残不全,与时代的怒吼拉开了距离,题材转向非政治化,但它的确是流亡文学合逻辑的发展,是由功利性目的向审美性目的转向。这根源于作家孤寂艰辛的流亡生涯的加剧,根源于更个人化的生命苦痛的体味。狂热的呐喊、怒吼之后,激流般的外在认同情绪退潮,回归追忆的主体领域随之打开。由于审美机制的调整,小说家听任表现性手段的引入和强化,以便使心灵和情感直奔“呼兰河”、“科尔沁旗草原”、“松花江”、“珲春”、“图门江”等象征式的情感精神的家园,于其中得以亲近、慰藉。这样他们便把小说推向似传非传、诗化和散文化的境界。所以转向后的丰收值得重视,其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内蕴,尤其是个性生命体验的审美强化是其魅力所在。
二
流亡小说有着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双重主题,即抗日主题和怀乡主题。在第一个创作盛期抗日主题是主调,它受制于唤醒民族救亡的强烈政治功利要求和浸润着时代色彩的群体性共识。《八月的乡村》等体现了这一共同的主题。怀乡主题是第二个收获时节的硕果。《呼兰河传》等更多揭示沦陷前的东北人情生存状态,更细地触摸东北人的情绪和心灵的律动,富有文化韵味和较高审美品位。
回忆性是流亡小说共同的文本特征,但是由于这个流派的无组织的松散开放性特征和最初艺术追求自觉性缺乏,使“回忆”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见出差异而且由于不同时期的追求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呈现价值的偏离或文本的变化。
首先是“载道”与“言志”的矛盾和差异。仅就具代表性的二萧来说,萧军是男性度极强的载道作家,萧红则是极女性化的言志作家。萧军把艺术作为追求社会功利的工具,因从军未成而不得已为文。其小说虽视角开阔,但因急于贴进现实显得开掘不够,学识胜过文采,小说往往深刻而不动人,但《八月的乡村》却是一个较好的粗犷激昂又充满激情的写实作品。萧红则借助人物故事的框架来抒写性灵,实现自我,有极强的个性和内向性,文化意味较强,《手》可说是现代短篇小说的佳作之一,端木蕻良与萧红相仿,是位以才性见长的作家,尽管他偏于理智,但也不时地陷入迷狂式的抒情中。流亡小说的写实性描写中常常伴生着昂扬的浪漫气质,到了后一时期回忆性使之愈加呈现出“恋乡情结”的凸出和“自叙传”式的叙事风格,“言志”、抒情压过了“载道”。
其次是内容价值选择和艺术呈示上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偏离。前期的抗日主题倾向于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批判与反思。解剖和探寻东北悲剧的构成根源,从而滤出值得张扬的有着积极意义和雄强生命力的东北精神。鲁迅称道《八月的乡村》提供了酷烈的强力感受:“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③]端木蕻良早就倡导“力的文学”。其创作表现过“农民”的力,“土地”的力,“大江”的力,“草原”的力。第一批流亡小说无不以血和泪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并体现了坚韧不屈和顽强搏战的民族精神和伟力。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现实造就了东北人近现代以来的生活方式,逐渐“衍化、形成了以强悍、野性、互助、悲凉等为价值取向和外部特征的东北区域文化的结构形态。”[④]大田耕种、伐木垦荒、挖参狩猎、淘金泛海是集中体现了东北人以发财梦想的狂热冲动,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同时又充满艰辛和冒险的典型生活方式。在这些动荡而有力度的东北生活方式中最能体现生命强力的意志实现的生活是“土匪”和军旅生活。如果说上述诸劳作生活方式使东北人的生命力得到积极发挥和实现,是正向的选择和顺势的追求,与之相对,“兵”“匪”生活则是生命在野蛮强力的挤压下迸发的人性强力向社会斗争的表现,是负向选择,逆势追求。选此以险治险、以“恶”抗恶、以乱应乱的人生出路,对许多青年男子是最捷近、最省力的生存方式。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兵”“匪”生活集中于清末民初的动乱岁月和30年代外患沉重时期。“九·一八”前后几十年间,“兵”“匪”一面对社会生活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民众的求生意识和生存状态而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斗争的悲壮性。流亡小说将这一独特的历史存在置入尖锐化的民族矛盾参照中,写出了一批较成功的“兵”“匪”形象。他们既有正直、善良、劫富济贫、同情弱小的一面,又有乱中偷生,险中求夷,烧杀掠淫的否定性一面,这又往往使其人格精神中野蛮的兽性常压倒健全的人性。如果小说对此有清醒冷静的认识,写出“兵”“匪”的历史所规定的复杂性、两重性、可变性,那么将会呈现更精致高级的“原始的犷放的野性的美”。然而由于作家们的审美判断频繁地被严酷的现实所冲击(这在当时必然如此),过多地掺入功利成分,急就间仅凭一腔热情就使形象生辉,对“兵”“匪”大都采取肯定的正面描写,将其作为正直、正义、高尚的代表来歌颂,以至有许多失度的美化,直到萧军的《第三代》才给出历史层次的较全面的把握。这是前期“兵”“匪”问题上的一个普遍偏颇。
从艺术上说,前期初登文坛的流亡作家毕竟年轻,在生活阅历和文学素养上不仅不能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甚至与30年代同时的一些作家比也存有一定距离。这使前期的小说文本普遍出现显明的缺陷和幼稚。与李辉英模仿都德的《最后一课》一样,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不论是叙事角度、文体、意象,还是总体风格都明显模仿了法捷耶夫的《毁灭》。[⑤]由于艺术上的不够成熟,语言“有时甚至生涩”,“缺乏的是修辞的内在的清醒”,甚至“作者在替他的人物说话”和出现“读书人的白话文章”等瑕疵,使之不能成为一部审美意义上的小说杰作,但因其应时合潮而得到广泛的民族心理上的认同成为一个“光荣的记录”。萧红的作品艺术性较强,但《生死场》充满了“越轨的笔致”,也有些生硬的欧化语言。端木蕻良的几个长篇有时竟粗糙到令人难以卒读的地步,而李辉英的人物缺乏个性化……。
流亡和战乱的骚扰等因素致使流亡小说家在艺术素质上大都是先天不足,后天未补。战时生活的紧张和变动影响到相当一些作品成为急就篇或断残物,虽不乏振撼之美但也留下不足和局限。另外,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流亡小说也充满了功利化和意念化的东西,这种缺陷随着时间差距的加大显得更加清楚。
同时也应承认一部分流亡作家诸如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又的确在小说体式上有独特的追求,其功绩在小说史上不可低估。在前期的流亡小说中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有较丰厚坚实的文化历史价值,艺术上属上乘之作。该作品完成于1933年,被称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巴人语),“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郑振铎语),但因未赶上机运,迟至1939出版,未能引起轰动效应,但确实是一部具有史诗特点,结构奇特,内容庞杂的优秀佳构。它有似《家》、《四世同堂》、《京华烟云》等现代世家小说的视角,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社会变迁,揭示民族生活的趋势上取得成功。同时它的独特价值又在于大幅度地、以强烈浓厚的主观抒情方式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灾难厄运史诗般呈现而出。在表现手法和形式上端木蕻良倾向于情感倾诉式的、汹涌狂放的写法,不受传统或惯常的叙事限制,常常是淡化或忽视情节过程,而专注于画面的凸现,抓住最鲜明的情景和瞬间以构成小说的意象。在结构表面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有序构成,以情感意象为经纬来组合人物和事件。端木蕻良采用了与小说情致相适应的跳跃性强、有旋律感的语言。为了使感情鲜明强烈,当人物或意象不能充分表达作家情意时,作家自己就打破叙事者和被叙述的界限,以超乎小说叙事性特征的抒情主人公站到前台。此外,大众口语式的北方方言俗语的准确而明快的运用与电影语言简洁句式的借鉴以及与传统典雅色彩语言的融合,这一切就构成了端木蕻良独特的小说语言艺术。
后期流亡小说成就卓著的是萧红,她用《呼兰河传》的模式表明了自己的“小说学”。她是第一个在本世纪小说发展中以似传非传、虚实相间和开放性超时空的散文式笔触充实长篇小说获得成功的作家。她率先在文坛引起了一个关于“不像小说”和“像小说”的观念转化。这种变化或许在当时的意义还不够明了,但在今天多元变化了的小说形态中其意义就极为明显,其影响也是非常广大的。
《呼兰河传》的审美属性在于由审美接受主体所感知出的艺术世界:一幅多彩的风情画,一篇感伤的叙事诗,一部苦涩辛酸的小城故事[⑥]。观察者、叙述者和人物的混一是《呼兰河传》的叙事视角。这不同于一般小说尽可能客观化的展示性叙事。作家采取一种主体参与性极强的“讲述—品评”式的叙事。萧红在回溯历史,反刍回味自己所熟悉的故土生活中自然灵活、游刃有余地缩短了审美距离,强化了其情感性讲述—品评的真切感。《呼兰河传》分为三部分:小城风情(一、二章)、作家自传片断(二、四章)、小城故事(五、六、七章)。风情部分无情节,无人物(出场者均为无名无姓的泛指),无明确的场景,呈现为全景式的宏观扫瞄,叙述展示了呼兰河城乡的风土人情,它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又有开放组合的可待性,它属于散文化小说的肌质。自传部分由作家、叙事者、人物三位一体的“我”出场。在时间序列上显得外在而客观,空间上行云流水,忽内忽外,变幻频繁,相应的事件自然而散漫。这一部分属于纪年式的小说。故事部分中三位一体的“我”虽仍存在,但已退于一侧,让位于诸小城故事。小城故事、风情背景和自传透露的整体文化氛围相辉映补充,构成了一种独特审美意指性的小说文本。
三
1931年到1945年是中国本世纪中一段特殊的岁月,东北流亡小说家以庄重合度的节奏与时代同步,写出了只有在这个时空才能出现的一批小说,自有属于它的人文价值。在整体评价流亡小说时,一些学者已充分褒扬了洋溢其中的民族意识、反帝主题和社会责任,但对小说文本的细部分析、审美构成认识不足,甚至忽视了作家艺术素养和小说中存有的幼稚、缺陷与败笔。再补充两点如下:
首先是对“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被称为“历史和文学的辩证法”[⑦]的看法。文学的发展取决于相应的文学意识的张扬。流亡小说是先被动而后主动形成的文学意识。它产生的窘迫性、无可选择性都说明它不是文学进程中循序造就而成的衔接环节。作为一次强制的打断和硬性的插入,这恰恰是在国家不幸之后随之而来的文学的不幸。那种认为只有置一个民族于水深火热,国破家亡之中才能激发起高度的审美创造力,成就艺术杰作的观点实在令人难以苟同,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并不是文学自身的规律,它意味着文学发展的曲折性是由内在与外在、主观和客观因素,各种条件等合力作用所造成的,而处于不同的动荡时代的文学发展究竟如何,需就具体的文学史实作辩证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其次是对功利性与审美关系的评价,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之际,流亡小说的大部分不能不是痛苦的哀号或热情的赞美,甚至是战斗的鼓动、匕首和投枪,不能不是这个时代民族精神和情感倾向的表现以及作家社会良心的呼唤。这种小说也体现了该历史时期一种特别的悲壮之美。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它作为小说发展史上的特例,一种非常状态下的产物,未必达到了它所处时空审美价值的典范高度。一种困境下激起的表达欲望使它把社会功利性放在了首要位置,为了记录巨大的历史内容和认识价值,则需要付出相当的审美度和艺术质量为代价。
纵观流亡小说,它在题材、主题、地域文化特征、语象构成方式、叙述和文本特征上都有较稳定的内质。从规模和动态上也达到了流派的水准。从内容上它是一个在创痛中呼唤抗战的小说群落;从艺术上看,它虽无精品,却在价值选择和表达上无愧于所生存的时代。
注释:
①⑥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第4、65页。
②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
③⑤《鲁迅全集》第6卷,第287页。
④⑦逄增玉:《新时期东北作家群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0年4期,第75、70页。
标签:小说论文; 端木蕻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科尔沁旗草原论文; 读书论文; 呼兰河传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生死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