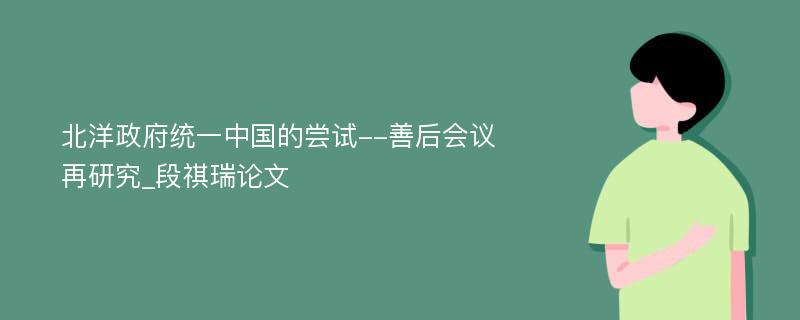
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中国论文,会议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既有学术话语中,“军阀”都是穷兵黩武的赳赳武夫,不可能与非暴力的和平会议发生关系。基于这一判断,直奉战争之后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一直被视为旨在对抗国、共两党倡导的国民会议,并且是在各军阀集团之间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对其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这次会议是段祺瑞政府在各派军阀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屡遭失败之后,改弦易辙,顺应时势民意,推进“和平统一”的一次尝试。就性质而言,国民会议是要诉诸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善后会议则偏重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两者并不矛盾冲突。从议程上看,善后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既有研究因否定北洋政府而否定其一切政治作为,不是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①
一、“和平统一”政治语境的形成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战败、反直军事同盟获胜而告结束。严格地说,直系之败并非败于军事,而是败于政治。从反直各方军事力量对比上看,江浙方面卢永祥的实力,不足与吴佩孚较量短长;东北的张作霖在军事上较之直系亦略逊一筹;广东方面相隔遥远,且因陈炯明及商团的“叛乱”,时有后顾之忧,难以抽出足够兵力北伐。直系之败实败在冯玉祥的倒戈上,而冯之倒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原因。直奉战争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宣告了北洋军阀“武力统一”政策的终止。随后,以政治手段致力战争“善后”问题解决,进而谋求“和平统一”提上了中国政治的议程。
中国政治家谋求“统一”的文武途径变化,与各实力派之间暂时的力量“均势”有关。北京政变之后,虽有反直军事同盟成功“倒曹”,但直系的军事力量并未被歼灭。段祺瑞念北洋旧情,对曹、吴的处置又难免手软:“有谓段顾全北洋统系,欲抚直系残部为己势力,以图国力之均势者。”②故吴佩孚虽败走,但仍手握重兵,“长江势力未损秋毫”,不久即成卷土重来之势。而奉、浙、粤“三角同盟”在反直军事行动结束后,内部矛盾急剧上升。广东方面欲将统治区域扩大到江西等省,与段祺瑞重新确认地盘的初衷相忤。奉系企图染指苏、浙,与复出后在江苏任职的卢永祥发生利益冲突。冯玉祥与奉张的关系也呈紧张态势。国民军势力逊于奉军,使冯时刻感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但国民军控制着北京,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广东方面响应,又反过来对奉系操纵中央政权造成阻碍。冯、段之间也存在矛盾:“段于地方势力久已根绝”,“非冯之所重”;段则利用奉张与国民军的矛盾压制冯,黄郛摄阁为许世英取代,即其明证。③被推至政治前台的段祺瑞与奉张不免明争暗斗,所谓“张作霖与段干木貌合神离”,是为符合两者关系实际的分析评价。④这就在各派军政势力之间形成可以相互制衡的“均势”,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方要用单纯军事力量来解决时局纠纷,实现统一,均难操胜券。⑤
武力自身不能统一,要实现“武力统一”自然成问题。而武力自身不能统一的原因,在于袁世凯之后陷于四分五裂的北洋各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⑥是以主张“武力统一”之军阀,屡致颠仆。当“武力统一”政策失败之后,段祺瑞曾表示:“纷争既久,渴望统一,革命告终,宜有建设,亦即全国憬悟,心同理同矣。而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⑦就连依恃实力,“仍思继承吴佩孚之武力政策”的张作霖,对于“和平统一”主张,亦不便公开反对。⑧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战后各方谋求“统一”的手段也只能是“和平”的。盖“倒直”获胜乃奉、浙、粤三方联合加上冯玉祥倒戈的结果,此役既以数方合作而获胜,善后问题当然只能由各方协商解决。从段氏个人的处境上看,他能够受到各方“拥戴”,除了再造民国“元勋”的旧招牌外,主要原因在于他体验了“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且已丧失实力,除实施“和平”之道,已别无选择。《申报》特约评论员写道:“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借,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段祺瑞之被推(戴)也,则以标榜和平之故。以各方信其前此武力之失败,足以醒其(武力)统一梦之故。则段之不能再谈武力统一,非独以道德信段,实亦于事实可以信段也”。⑨失败的教训与缺乏实力凭借,使段不能不谋求政治解决之道。被视为北洋“文治派”的王士珍对此看得最明白,曾规劝段说:“君之得各省之拥戴者,以不拥兵也;国民军之受人民欢助者,以标榜和平也。长江及吴既尊重君,君宜摒除武力,则统一可期。”⑩已经穷蹩到“手无寸铁”地步的段祺瑞,岂能拒绝劝告?这是段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原因。
“和平统一”在吴佩孚乘舰出走之后即已提上日程。当时急切解决的问题,一为收束军事,一为整理财政。军事问题虽因“均势”出现,暂无在全国范围内重开战火之虞,但局部冲突仍难以避免,时有发生。财政问题更加棘手。1920年代初期,战争连连,规模日大,军费支出急剧上升,其在地方及全国岁入中所占比例严重失衡,政府财政已困窘到连一个月薪俸都发不出的地步。(11)全国如仍处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财政上“入不敷出、举债养兵”的状况就不可能解决,实现统一遂成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先决条件。此外,执政府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国家的和平建设与发展问题,以及“倒直”之后新政权的外交承认问题,在在需要解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会议之后决定出山的段祺瑞,提出以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和平统一”。其于入京前发出之“马电”,宣布将召集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表示以三个月为准备期,会议条例一旦议定,即行公布。(12)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入京就职,宣言于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解决与时局相关的一切重要问题。随即谕令临时法制院院长姚震草拟《善后会议条例》,并在吉兆胡同宅邸召开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为保证善后会议如期召开,段氏将善后会议条例草案提交国务会议,与会者就善后会议权限及代表资格进行了磋商。最后商定的《善后会议条例》凡13条,分别就会议宗旨、会员资格及类别、会议拟议事项(包括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方法,改革军事事项,整理财政事项,及由临时执政交议的其他各案)及会期、会址、议长副议长选举、出席及投票之有效人数、秘书处之设置、议事细则等作了安排。(13)段在敦促各方出席会议的电文中,刻意表达了以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宗旨:“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备建设方案而设,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14)
由此可见,善后会议虽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主持推进,其中不免包含维系自己政治统治的考虑,但通过会议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谋求国家政治及军事问题的解决,实现统一,实为当时军政形势的客观要求,是明智的政治选择。至于善后会议能否“善”时局之“后”,则与段政府是否具备整合政治军事的能力及地方实力派的立场密切相关。
二、地方实力派及社会各界的立场
以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政治方针确定之后,地方实力派的反应成为各界首要关注的问题,亦成为段政府能否实现统一的关键。其中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立场,于事情之成败,关系尤为重大。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当然不是今日研究者心目中的“地方实力派”,事实上,孙此时尚未构建起真正的实力地位。然而,因其曾经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特殊经历以及与苏俄联络之后走民众路线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孙俨然成为左右政局变化举足轻重的人物。过去普遍认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对善后会议持反对态度。然而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孙中山是主张以会议协商方式寻求国家问题解决的,其当时的处境决定了他只能这样做;其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离粤北上,更表明了他对善后会议的基本立场。在领袖如此决策的情况下,国民党虽存在内部分歧,但基本立场仍是主张有条件参与。孙中山的这一立场是其参与“三角同盟”的逻辑发展,既已共谋反直,当然只能同商善后。正因为如此,段祺瑞才十分注意孙的态度。12月2日阁议,就决定善后会议组织大纲须待孙中山同意后公布。(15)依照这一决定,许世英将草拟的《条例草案》送往天津,呈孙中山“核阅”;接着段祺瑞又派叶恭绰等前往谒见,询其意见。大体而言,此时孙的立场,只是对段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对善后会议则未持异议。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趋于激进,对待善后会议的态度才最终改变。(16)
作为反直三角同盟执牛耳的人物,张作霖的态度是会议能否如愿召开的重要因素。张对善后会议最初并无兴趣,认为此种会议人数众多,“彼之有力主张不易实现,而疑段之有意缩减其发言权”。段则以召开善后会议的决定在就职前之“马电”中即已发表,不便自食其言为由,坚持己见。于是出现“六头会议”之插曲。所谓“六头会议”,即以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五人,连同唐继尧共同会议。(17)段试图“以六头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会议为形式之通过,则所谓善后会议者,又以六头为预备会”。但此议发出,孙中山首持异议,唐继尧复电又表反对,冯玉祥亦不愿参与。六头而去其三,所谓“六头会议”只好作罢。(18)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张作霖反对召开善后会议,实际上,张只是对段将其列入二、三类代表(即“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和“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的人事处置不满。对此,其身边人曾有所解释,“谓张作霖在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上,固居第一功,而在历次有意义之战争上,亦未尝无功,故应将其列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19)不过张作霖也有所顾忌:段系其领衔推出,在其力图控制段的同时,冯玉祥也很注意与段的关系,若过分与段为难,则段可能转而倚重冯甚至孙,这对自己显然不利。故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张作霖对段的安排不得不稍事迁就。1月12日,即《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后半月,张作霖致电会议筹备处,允派代表出席。与此同时,奉系另一核心人物杨宇霆致电许世英,称“善后会议东三省军民长官应派代表,日内雨帅回奉即行会商遣派,准于开会期到京,特先奉闻”(20)。奉系表态支持,为善后会议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及人事基础。
国民军当时控制着北京,故冯玉祥的态度于会议成败亦关系匪浅,但事情颇费周折。段祺瑞以“特别请书”邀冯玉祥与会,未得允诺。段嘱薛笃弼探其缘由,冯称:“此事吾不能与闻,吾今唯知五次、六次以至十次之辞呈,向段执政辞职耳。”冯氏自1924年11月25日起,七上辞呈,并致电吴佩孚,请同时下野。个中原因,或与冯当时的处境有关。盖政变之后,“社会上谅之者甚少”。天津会议上,“冯奔走段张之间,其中殆有不可告人之苦痛”。可见冯拒绝与会,系出于在政治上摆脱尴尬处境的考虑,并非对善后会议有何不满。时论称冯氏在观念上与善后会议处于“不即不离之间”,是为中肯评价。(21)后来冯派陈金绶为代表与会,证明其于善后会议,并不根本抵触。国民军将领胡景翼派代表与会,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22)
西南实力派乃段政府必须联络的政治势力。当时所谓“西南”,包括云贵川三省及广西、湖南部分地区,地域辽阔,难统易分,故其立场于实现“和平统一”关系重大。然西南方面的立场殊难捉摸。自段任临时执政以来,西南各省虽多沉默,但滇唐代表王九龄未就教育总长之职,此中消息,可见一斑。为争取西南实力派的支持,段曾致电刘显世,请求赞助。然刘之复电中,有“俟商取蓂赓(唐继尧)、陈竞存(炯明)诸公同意,即行通电表示”之语。嗣因陈炯明通电反对善后会议,刘遂与唐继尧、谭延闿、熊克武四人联名通电,示以反对。不过,西南方面立场并不一致,部分西南代表曾在上海集议,商量赴京与会。云南代表王竹村表示:“绝对赞成此项会议,现在被邀之列,自当扶病出席。”(23)另外,四川的刘湘曾通电赞成善后会议,刘文辉则慷慨解囊,汇出4万元,以示赞助。(24)甚至陈炯明也一度表示赞成善后会议。(25)后来,包括滇唐代表在内的多数西南代表都赴京与会。不过,由于内部步调不一,一些西南实力派人物与段、张立场难以协调,已露端倪。
与西南方面态度歧异不同,晋、鲁、苏、浙、皖、鄂、直、闽、赣、湘等省实力派对善后会议大多明确表示支持。阎锡山、郑士琦、王揖唐、萧耀南、胡思义、孙传芳、卢永祥、杨以德、萨镇冰、赵恒惕、方本仁、龚积柄、韩国钧等先后致电善后会议筹备处,承诺到会或派代表出席。张学彦代表萧耀南致电段,表示“鄂萧对中央服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萧本人慷慨解囊,更表明了对会议的态度。(26)尽管该数省的“支持”有附加条件,一些时候甚至被当成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他们的表态,无疑壮大了善后会议的声势。
依条例规定,除倒直有功者、各省军政领袖及代表之外,会议将邀请有特殊资望及学术经验的“特聘会员”,人数不超过30人,由临时执政聘请或选派。最初拟聘之30人中,10人为拒贿议员,其入选系奉张与各方妥协的结果。其余20人,或代表各实力派,或代表各政党,或为商学界之闻人。最后确定的“特聘”会员有王士珍、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严修、饶汉祥、汪精卫等30余人。相对正式会员大多具有军政实力而言,“特聘会员”似乎只是会议陪衬,但因具有“软实力”即社会影响,其言行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各界立场的风向标。
王士珍系北洋元老,与徐世昌一起被视为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27),赞成“和平统一”,且与段氏关系甚深,曾亲自到善后会议筹备处访许世英,允届时出席。蛰居上海的唐绍仪则不愿北上赴会,段派员持亲笔函至沪敦请多次,唐均表示拒绝,且抨击善后会议“用意不善”。曾在政坛显赫一时的岑春煊,接到段之邀请后致电段氏,称赞其和平会议决策,但岑在政治上有时又倾向西南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时人称之为“消极赞成”者。(28)章太炎一向标榜维护黎元洪的“法统”,政治上视黎之出处为进退,此时又因为与唐绍仪的瓜葛而拒绝与会。(29)梁启超在政治上曾与皖系合作,段召集善后会议,自然对其期待甚殷。但梁氏归国后历尽宦海风波,心灰意冷,早已发表宣言,“毅然中止政治生涯”,潜心学术研究与教育,不愿与闻政事,故婉拒段之邀请。(30)
最能反映各界态度的是胡适对会议所持的“实验主义”立场。胡适乃新文化健将,学界翘楚,在政治上亦不乏影响力。以其对于政治的理解,他并不认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乃方枘圆凿,故在受聘国民会议促成会,担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同时,又接受了段祺瑞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胡适的想法是作一番和平解决时局问题的“尝试”,他在给许世英的信中写道:“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毫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31)
综上可知,尽管目的不尽相同,响应方式与程度也存在差异,但多数受邀者对善后会议都表示赞同。就“实力派”而言,当时各派实力并不对等,曹、吴倒后,奉张最具实力,国冯最扼枢要,其次则苏、浙、直、晋、鲁、皖、鄂、闽、赣、湘等省或其分合不定的联盟,再其次则内部分歧的西南各省。按照这样的区分,可以说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都已明确表示支持善后会议。张作霖、杨宇霆、阎锡山、郑士琦、王揖唐、萧耀南、胡思义、孙传芳、卢永祥、杨以德、萨镇冰、赵恒惕、方本仁、龚积柄、韩国钧等或亲自莅会,或委派代表参加,使“和平统一”的会议宗旨有了半数以上省区的支持。而作为反直三角同盟重要一方的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意见未能一致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北上,冀与各方共商国是,更是对以和平手段谋求统一的认同。加上部分西南实力派的有条件参与,“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从社会各界的情况看,尽管反对呼声不断,但胡适所谓“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段政府对善后会议“颇抱乐观”,其通过会议协商实现“和平统一”的努力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32)
三、会员的派系构成与议案处置
从善后会议会员的派系构成及议案处置上,也可以看出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谋求“和平统一”的良苦用心及真正达成“统一”的不易。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后,段祺瑞特派与之有“金兰之交”的许世英办理筹备善后会议事宜。许受命之后,即着手设立筹备处,编定筹备处章程,并按照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开始邀请会员。(33)最初拟定的会员合计132名,由于条例细则规定兼省长之督办及兼督办之省长等会员可派代表两名与会,故全部应出席的代表为166名。(34)自1924年12月30日段政府发出致各军首领及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通电,“请躬自出席善后会议或派代表出席”,迄于次年2月1日,筹备处接各方函电“计有346件之多”,其中“函电答复到会及派代表与会者,共计148人”。(35)从“善后会议会员录”上看,登记的会员及代表共计181人,比条例规定的代表多15人。而会议实到人数,据会议秘书厅统计,截止到3月15日共计169人。(36)
就政治关系分析,善后会议列席者可以分为四大派系:其一为皖系。主要是段祺瑞系统的人,此外还包括段所欲拉拢或借重的人,计有赵尔巽、王士珍、熊希龄、乌泽声、周学熙、胡适、周作民等10余名,时人称之为“准段系”。其二为奉系。凡东三省直隶热河之代表,皆包括其中,总数约在30人上下,领袖人物为张作霖的秘书长郑谦及参谋长杨宇霆。东三省代表20余人曾先在沈阳集合,开一预备会议,然后来京,足证奉天方面对此会的重视。其三为国民军系。凡察哈尔、绥远、京兆、河南诸省区代表,及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部之军官代表,皆被视为该系,人数约有18名。至各人之行动,则大体以薛笃弼为标准。其四为西南实力派的代表,约有10余人,其进退行止大体视唐继尧的立场为转移。其他各省区代表,皆不能结合一致,往往附属于某一派。西藏达赖喇嘛以及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以西藏地区行政及宗教领袖代表的双重身份应邀,虽与内地派系无明显纠葛,但在国家分合不定的背景下,也十分引人注目。(37)
若单就“特聘会员”看,其派系关系又有所不同。时人曾将全部特聘会员的派系作了如下分析:1.民党派3人(汪精卫,新文化健者;杨沧白、彭养光,拒贿议员);2.段祺瑞派3人(刘振生、乌泽声、潘大道,拒贿议员,潘为章太炎弟子);3.张作霖派3人(赵尔巽、杨宇霆;邵瑞彭,拒贿议员);4.冯玉祥派2人(黄郛、张绍曾,原系直系,后因失意,立于冯系旗帜之下);5.黎元洪派2人(李根源,原属政学系;饶汉祥);6.唐继尧派2人(王九龄;褚辅成,拒贿议员);7.熊克武派1人(李肇甫,拒贿议员,亦属政学系);8.研究系3人(熊希龄、梁启超、林长民,准段系);9.旧交通系2人(朱启钤、梁士诒);10.政学系1人(杨永泰,拒贿议员);11.联治派1人(汤漪,拒贿议员,准段系);12.西南名宿3人(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13.北洋名宿1人(王士珍);14.遗老1人(严修);15.学界1人(胡适,新文化健者);16.商界1人(虞洽卿)。(38)
如此区分派系,尽管因判断标准不同会出现以领袖人物、政治观点甚至所处地域分类的淆乱,却也揭示了出席会议者派系众多这一事实。将分属众多派系的代表聚集一堂,共商国是,反映了段政府谋求“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当然,由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会员及代表复杂的派系构成在证明“和平统一”政策具有较为宽广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的同时,也预示会议达成共识将异常困难。善后会议期间,联治派的王克家拜见法制院院长姚震,姚曰:“这善后会议聚恩仇于一堂,哪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只要能把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议定,就是善后会议的好结果。”(39)所谓“聚恩仇于一堂”,或系对善后会议会员构成驳杂的批评,但段氏能将“恩仇”聚于一堂,洵属不易。
善后会议从1925年2月1日召开到4月21日闭幕,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多月。(40)除去休会期,正式会期约50天,其间共召开大会22次,谈话会2次。会议共收到临时执政府提交的议案14件,会员提议案25件,会员修正案62件,意见书31件。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的议案为15个,其中2个在会议期间由提案人申请保留,3个被撤销。有关国民代表会议的议案和修正案单列,共14个,放在“交付审查各案”一类。(41)在会议收到的各类议案中,整理军事大纲案、整理财政案和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关系政局最为紧要。从这三个议案的内容和议决过程,可以清楚看到段政府为谋求“和平统一”作出的艰苦努力。
段祺瑞谋求战争善后的最大难题是收束军事。为解决这一难题,卢永祥曾致电段,主张“废除督办,军驻军区,饷由部给,不干民政”的主张。(42)临时执政府则提出了《整理军事大纲案》,主旨包括:1.根据财政状况量入为出制定军费标准;2.依民国8年预算案以岁入1/3之比例为军费;3.暂定全国兵额为50万人;4.设立收束军事委员会,按照上列各条妥议办法,次第施行。(43)与会代表在讨论军事问题时,鉴于议案众多,且不少交叉重复,决定将各案合并,分为两类,以执政府提出的《整理军事大纲案》、《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为“讨论之标准”,融汇各修正案。(44)但讨论中意见歧出。西南代表反对将军事纲要并入有关军事善后委员会的议案,但“政府派”代表认为会议有制定军事善后纲要及军事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必要。东三省代表对此不满,“相率退席”,致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为应付局面,许世英请王士珍出面调停,未能收效。(45)
从4月2日起,大会召集专门委员审查与军事相关的议案,并指定11名委员组成特别审查会审查全案,并逐条议决审查修正理由。4月15日,召开第18次大会,决定将军事各案合并讨论,并采纳委员建议,将合并后的议案改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经逐条审查表决,获得通过。该条例共16条,确定了军事善后委员会的组织、应行议决事项、议事程序、会期、与财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事务处的设立等。(46)然而,对如何确保军事善后委员会解决收束军事的问题,会议并未讨论。事实上,在与会实力派各自为政、国家权势重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即便会议作出有关规定,也难以根本解决军事善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善后会议只是将收束军事这一难题移交给了军事善后委员会,至于该机构能否完成会议赋予的使命,则无暇顾及。
财政是“和平统一”能否实现的又一关键,政府财政的拮据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最早的议案共9项,均由执政府提出。在第9次大会上,9项议案归并为《整理财政大纲案》与《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两案。另外,熊希龄、任可澄、钟才宏、周锺岳等先后提出的新议案或修正案7项,也一并加以讨论。经初步讨论,决定将各案提交财政专门委员会审查。遂有专门委员会特别审查会的召开,议定以段政府所提两案为纲领,将各修正案中相关内容归并于该两案之中,其不能归并者,则另立为一类,以免重复。会上各方争执不休,直到善后会议召集最后一次大会,才采纳处理军事善后问题时将各案并入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的办法,决定将整理财政大纲案并入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与会者逐条审查议案,最后将全案表决通过。所通过的《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共16条,规定了委员会的组织、应行议决事项及议事程序等。(47)
从内容上看,会议通过的整理财政的议案堪称全面,既分析了国家财政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意见和办法。条例强调财政必须“公开”,这是针对民国以来“纷争不已,其重大原因,莫过于财政不能公开”而特别强调的原则,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不过条例也存在诸多局限,最明显者莫过于对军政关系的混淆。执政府最初提出的议案与会员修正案均规定财政整理委员为“民政长官”,条例将其改成“各省区军民长官”,声明是考虑到各省区的财政收支,均与军政有关。(48)这样的理由显然难以成立。盖民元以来国家财政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军政长官”造成的,要整理财政,就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军人干预财政的现状。善后会议无法改变这点,却迁就现实,寄希望于本不应该掌握国家财权的军人与之合作,结果事与愿违。但会议作此修改,体现了主持者不得已的苦衷,似不必苛责。
国民代表会议是段政府标榜制定宪法、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重要会议,故对临时执政府法制院起草、以段执政名义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与会者十分重视,争论也异常激烈。(49)关于国民代表会议的权限,条例草案的表述为:“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实施之附则,为其职权。”但是在讨论草案时,代表金兆棪认为,国民代表会议是“国家最高的及无上的机关”,是国家的“主体”,应否对其加以限制,值得怀疑。即便应该限制,谁具有这样的权利,亦属问题。代表寇遐对限制国民代表会议职权从根本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共和国家的主权在于国民,除了国民代表会议自身可对其职权加以限制外,其他任何人均无此权利。(50)
金、寇二人的意见反映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林长民则站在“政府派”的立场反对金、寇的主张,认为宪法问题乃国家的根本问题,宪法实施之附则应能包括一切,因而限定国民代表会议这一“职权”,实际上已规定了会议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与金氏所称国民代表会议系无上之机关,并不矛盾。林尤其不赞成寇遐的意见,斥之为“纯系一种理论”,认为要对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毫无限制是不可能的。林氏举例说,“试思本案规定之会期三个月、名额若干人诸条文,若依此说绳之,何尝非限制之意”,如果依寇氏之意,此皆不必加以规定,“则一切条文,皆无准据”。因此,林氏极力主张维持原案,双方就此争论不休。(51)
在宪法应由政府指定的专门人员起草还是由国民代表大会起草这一问题上,也可明显见到各方的分歧。林长民主张宪法案及实施附则应由“国宪起草委员会”起草,遭到寇遐等人反对。寇等主张“宪法之起草由国民代表会议互选委员若干人行之”,认为宪法具有“民约”性质,应体现主权在民之意,林氏之办法系“假政府官吏之手,根本上即违反民与民相约之意”。林长民反驳说,宪法起草委员会虽由段执政及各省区军民长官推举,但宪法之最后决定权仍属于国民会议,即便有不妥,亦“有纠正之余地”。而宪法的价值系决定于内容实质,不是决定于“起草之机关”。但寇遐坚持认为,宪法系国家根本大法,其起草权应操之于民,否则所产生的宪法只能名之为“政府宪法”或“官僚宪法”。双方互不相让,只好付诸会议表决,结果寇遐的主张被否决。(52)
1925年4月18日,善后会议召开第21次大会,在前一阶段会议对条例草案所作逐条表决的基础上,就业已修正之议案开“三读会”,并将全案付诸表决。(53)结果,“全场起立,主席宣告全案成立”(54)。《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通过标志以“和平统一”为宗旨的善后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政府派”副议长汤漪认为,善后会议虽议案众多,重要议案却只有5个,即(1)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整理财政案,(3)整理军事案,(4)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5)联省自治案。在汤氏看来,“二三两案较易通过,第一案虽多争议,亦有解决希望;惟第四案的进行,妨碍正式政府的成立,及宪法的产生;第五案则善后会议无权解决,须于将来国民代表大会时提出”(55)。经过各方努力协商,汤漪所列五项“要案”中,前三项至少在形式上已得到解决。这样,真正棘手的议案只剩下与西南联治派相关的联治案和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而这两个议案均涉及政体选择这一重大问题。
四、“和平统一”议题下的政体之争
通过会议联络各方共商国是只是段祺瑞实现军政统一的手段,而已呈分裂气象的各派政治力量应该“统一”到何种政治体制之中,或者反过来说,究竟什么样的政体才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统一”,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北京政变发生不久,唐绍仪接受《上海泰晤士报》记者采访,发表政见,明确指出,尽管时局混沌,难言究竟,但以往“借强有力人物解决国是”的办法,显然已不再适用,而“联省自治制”则“可提出试行”。对于中央政府,他极力主张实行“委员制”,以取代总统制。按照他的设想,委员制“与日本政府制度相若”,合22或29省区,每省区各举1人为委员,组织委员会,委员任期6年。由委员会中互选1人为委员长,行使总统职权,“但权力则较现在中国总统为小”。唐氏认为,这种制度,“深合今日(中国)之需要”,而国民厌弃“武力统一”的倾向,又为这一制度提供了“采用之机会”。(56)
当时在上海赋闲的章太炎亦不甘寂寞,力图指导国内政治潮流。紧随唐之后,章发表政见,同样主张“以委员制救时”,但想法更为激进。他申述道:“观曹吴所能为乱者,则北洋派之武力统一主义为之根本。今不去其根本,而徒以解决曹吴为快,后有北洋派之继起,则仍一曹吴也。是故归之行政委员制,以合议易独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非盲从瑞士苏俄政制也。”不过按照章太炎的政治理想,即便委员制也只是“救弊补偏之术”,只能算是“中策”。真正堪称“上策”的“根本之治”,是他在此之前便已提出的“分立数国”的办法:“或分为二,或分为三,或分为四五,悉由形势利便、军民愿望而成。譬如兄弟分财,反少内讧。此实今日观时立制之要点也。”(57)
唐、章二人在政治上与西南方面有深厚渊源,其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实力派的愿望,因而很快得到响应。但“委员制”主张“与段之素性,极端枘凿”;且除段反对外,其他多数人也不赞成,加之国外舆论颇以委员制将造成“多头政治”为虑,天津会议就政制问题进行讨论时,遂以拥段担任临时执政作为解决办法。对于“联治”主张,则未作决议。(58)
善后会议期间,被天津会议搁置的“联治”主张再度提起。如前所述,西南方面对参加会议颇为犹豫,其最终决定与会,主要理由便在于会议可能为其提供宣传联治的机会。故会议开始不久,唐继尧、赵恒惕就发出通电,主张联治。其代表锺才宏、萧堃、郭同等随即在会上提出《确立联治政制为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以解纠纷而谋统一案》。与此同时,在征得费行简、周锺岳、彭养光、马君武等12人连署之后,褚辅成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因不满现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褚辅成等人主张设国务院以执行国家最高行政权,并将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集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于一身的集权制,改为具有33位执政的“合议制”。(59)褚、熊等人的议案与联治案相互支持,该案的提出明显构成对段政府的挑战,要害在于以“分权”取代“集权”。诚如《晨报》评论所言,褚案“使果实行,则现当局地位直从根本推翻”(60)。
对于褚辅成的议案,政府派人士极为敏感,主张涉及改制的问题,与其由善后会议提出议决,不如由政府自动拟一大纲,提交该会同意,借以表示善后会议不能有此提案权。奉张对褚案亦不以为然。在善后会议第10次会议上,因褚案列入议程,东三省代表以不出席会议,加以抵制,致使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召开,这显然是贯彻张作霖意志的结果。《顺天时报》的文章称褚案为善后会议的“暗礁”,亦揭示出其间的利益关系。在善后会议第13次大会上,经政府派会员提议,按照议事细则第16条之规定进行表决,褚案以超越善后会议权限而被搁置。(61)
段祺瑞对旨在加强地方权力的自治运动本无不慊,其就职时的“马电”中有“促成省宪”之语,可为证明。(62)段既赞成省宪,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属于地方自治的“联治”。惟此次“联治案”之提出者“均为西南实力派代表”,也就引起了段祺瑞的警惕。(63)
为对付西南实力派,段祺瑞及其同僚可谓煞费苦心。西南代表共计9人,若不将褚辅成算在内,则西南代表只有8人。其人数虽少,“而段祺瑞视之,则不啻数千人,所以欢迎之者,较欢迎孙中山,殆有过无不及”。除饬沪宁、津浦、京奉三路特备专车迎迓外,并饬沿途军警加以保护。且令所过地方之长官如卢永祥、王揖唐、郑士琦等,于其经过之际,为之照料一切。同时安排齐岳英、沈成栻、任传榜与之同行,护送进京,以示优异。(64)
段祺瑞之所以“居滇黔桂代表为奇货”,据《申报》记者分析,原因有三点:第一,联治运动在当时发展迅速,其运动之起点,系以湘鄂粤桂滇黔川赣为之,其中最有可能被运动者,则为湘桂滇黔。为阻止联治运动之进行,必须竭尽全力以事拉拢。第二,滇黔桂等省,位在西南一隅,若不拥段,“则段氏虽有长鞭,亦不及马腹,驭之以刚,既非势之所能,则怀之以柔,情殊不能自已。今滇黔桂之代表,既应招联袂而来,自不能不加以异款,使其心悦而诚服。”第三,鄂萧(耀南)、川熊(克武)联滇唐以解决坐镇武胜关的王汝勤之风闻,则不可轻视。为阻止滇川鄂联络以倒王起见,亦不能不特别重视滇黔代表。(65)
段对联治的态度,从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善会期间与许世英的一席谈话中可以更清楚窥见。王问:“合肥对于联省自治的问题,意见到底怎样?”许答曰:“合肥对于联省自治四字,是很怀疑的。他的意思,说省自治可县自治可镇乡自治也可,惟于‘省’字头上冠一‘联’字,是不懂得的。怕的说联省,是省与省联变成兼并割据。怕的说联省自治,只管各省,不管国家,只管地方,不管中央。若说联省便是为国家为中央,可以办到统一,这个当做注解,说明白,不若用联自治,反为好些。”(66)可见段真正关心的只是“统一”抑或“割据”的问题。
鉴于与褚辅成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相比,联治案尚属温和,其对中央的威胁亦相对较小,故段对联治主张最初只是采取疏通的办法。3月29日晚,许世英、姚震、章士钊、王九龄、段宏业、汤漪、陈宦、张树元等联名邀请联治派在绒线胡同“某宅”会谈,表示政府方面亦赞成联治主张,“但以兹事体大,未便在善后会议中解决,仍留待国民会议较为上策,以为缓兵之计”(67)。
30日,段祺瑞复电唐继尧及赵恒惕,对其不主张在善后会议中讨论联治问题的原因作了解释,词气尚属和缓。(68)直接出面反对将联治案列入善后会议议事日程的汤漪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汤氏素主联治,曾与张耀曾等发起筹组联治同志会,但此时却站在“政府派”的立场。他在对电通社记者谈及此事时称:“第五案(联治案)为本人民国十一年以来所主持者,自欲早观其成。但本人以为现在之善后会议,无权议决此案。须于国民代表会议时,提出讨论,较为得当耳。”(69)汤漪虽未就联治案的内容作何评论,但他从会议权限角度提出的意见,对于否定联治案,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吴佩孚不合时宜的参与对联治案遭遇否决也关系匪浅。吴氏迷信武力统一,本不赞成联治,兵败之后,感叹壮志难酬,不得已接受赵恒惕等联治派的庇护,以谋再起。殊不知这一做法却与张作霖不甘只作“关外王”的野心发生了冲突。盖吴与湘赵联络,必然触及反直三角同盟首领奉张的利益,使他别无选择地站到与联治派对立的立场。而奉张的反对,则成为联治案在善后会议获得通过的最大障碍。联治案提出不久,奉吉黑热及卢永祥方面的代表立即公函大会主席赵尔巽,请勿提交大会议决,得到赵的支持。加之国民党方面不满唐继尧等借联治之名,“冀攘夺地盘,殊与民党主义背驰”,对其主张持反对态度,使西南实力派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70)
不仅如此,西南实力派尚存在军、政两系分野以及由此形成的内部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联治案虽提出,其在善后会议通过的前景已十分暗淡。为改变所处窘境,西南代表竭力疏通政府,但未能奏效。不得已西南方面作出政治摊牌,提出联治问题未解决前,不能开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甚至提出以联治案与国民会议条例交换的计划,即以通过联治案为条件,换取联治派对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支持,否则将不投票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奉天及段政府代表则合力反对,甚至不容联省自治案列入议事日程,致使联治案未能在善后会议获得通过。(71)
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和联省自治案被否决,意味着西南实力派未能实现参与善后会议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联治派一方面电催唐继尧在滇组织联治政府,对执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以退出善后会议相要挟。(72)组建联治政府的计划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退出善后会议的要挟,因为西南实力派的代表不过寥寥数人,即便全部退出,也不会对会议产生多大影响,故“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73)。显而易见,对西南实力派来说,怀着推进“联治”的目的参加善后会议,实在是参与了一场只会输不会赢的赌注。然而,对段政府来说,没有西南方面的参与,“和平统一”的政治内涵也多少打了折扣。
五、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
善后会议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谋求“和平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也是段氏整合北洋势力,试图建立新的权势中心地位的一次努力。然而,会议的人员构成及段祺瑞政府宣布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的抵制,使会议尚未召开便蒙上一层阴影。(74)另外,参加会议的地方实力派目的各不相同,顺其愿则设法维持,拂其意则竭力拆台。这样,开幕伊始,会议已遭遇暗礁,不用说通过会议实现“和平统一”,就是善后会议能否自善其后,也受到怀疑。(75)
善后会议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停止国内军事行动,另一难题是废督裁兵。正如事实业已证明的那样,这些都是段祺瑞政府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善后会议既面临如此棘手的问题,其主持者自不敢抱过高期望。汤漪曾表示,对会议收到的五项主要提案,只要其中的军事、财政、国民会议组织条例三项能通过即算差强人意。然而在其他政府派人士心中,就是这三项议案能否顺利通过,亦没有把握。故曾提出最低限度的设想,“即于延期二十日内无论如何须将国民会议组织条例通过”,将通过三项议案的目标缩减为一项。(76)段祺瑞在会议弥月之际,面对所提交各案迄无一项议决的局势,亦不得不知难而退,将临时执政府提交的议案,除正待集议者外,全部撤回。后经王揖唐、屈映光等多方疏通,奉天方面与政府派就军事整理案达成妥协,善后会议才出现转机。4月14日召开第17次大会之后,先后通过了汤漪所说的三个主要的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议程,正式宣告闭幕。(77)至此,被怀疑能否自“善”其“后”的善后会议才算有了一个结局。
对于善后会议,时人褒贬不一。从会议召开之日起,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评价。这与评论者的立场不无关系。一般而言,政府派人士对善后会议多褒扬肯定,非政府派人士则多批评贬斥,而尤以反政府派人士为甚。
龚心湛在为费保彦《善后会议史》作序时称,善后会议将天下之大兴大革,悉付舆论,深得民为邦本之义。会议五旬,议决众多议案,“自有代议制以来,未有若是之迅疾详慎者也”。叶恭绰称,善后会议与民更始,“一时海内贤达之士,靡然向风,相与挟策,来会兹土,阅时凡五十日,而内政改造之方,国家大法之的,罔不具备。虽其间论见不无异同,大抵出乎探讨之意,谋国之诚,非徒向之借邀功利者可比也。”田中玉称,善后会议旨在“结束十四年来争法之嚣呶,复以国宪之成,责之行将召开之国民会议。所以继往开来,致我国于升平之域,开后世专法之基,固莫善于此也。”(78)
与龚、叶、田等“政府派”人士的认识及评价相反,非政府派和反政府派人士则对会议展开猛烈抨击。批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议代表系执政府指定,具有“御用”性质,是一次“政治分赃”会议;二是善后会议非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却要越俎代庖,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三是违反民主制宪原则,将宪法起草权交与由各省军民长官推举之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四是所通过的议案对各方没有约束力,因而无法实施;五是派系之争激烈,致使善后会议无以自善其后。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研究者大多承袭了这些批评意见。
应该说,既有涉及善后会议的评说均有其道理,然而都不免“当局者迷”或受大革命时代激进政治影响的局限。从研究者的立场审视,在直奉战争结束、国家百废待举的形势下,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推进“和平统一”,应为顺应时势之举。作为“武力统一”的对立物,各方以会议方式谋求现实问题的解决,反映了当时多数国民及政治家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政治内涵。会议围绕议案进行,共收到临时执政府及会员提交的议案39项,修正案62项,经筛选合并,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的共15项,没有一项议案涉及权力分配,因而谈不上什么“政治分赃”,除非研究者将“政治分赃”的定义泛化到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的地步。批评善后会议系段祺瑞政府抵制国民会议的手段的说法也难以成立。因为国民会议在当时只是一种带有“民治”色彩的政治理念,其“优越性”尚属待证的假设,且国民会议并不一定与善后会议相矛盾。这一层,就连不愿直接参与会议的冯玉祥亦有所认识。冯在为费保彦撰《善后会议史》所作序文中写道:“共和而无宪法,非国矣;宪法而不出于民意,非宪矣。客岁以不得已之苦衷改组临时政府者,实欲得真正民意之宪法,以为遵循之正轨耳。盖国民代表会议者,民意宪法之母;而善后会议者,又国民代表会议之母。兹幸以短少之时间,克成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无此是彼非之私争,有和衷共济之公德,不可谓非会议诸君之热心毅力也。”(79)
从可行性角度分析,问题或更加明晰。人们指责善后会议行不通,认为惟有国民会议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其实国民会议在当时更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主张“联治”的王克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他在会议即将召开时指出:“善后会议尚未开,即开矣,能否解决时局纠纷,固非吾人之所敢深信。国民会议未知能否召集,即召集矣,能否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亦非吾人之所能前知。然使善后会议无良结果,则国民会议不能召集。国民会议不能召集,则吾此文中所述关于国民会议一切事件,固属梦话。而其时国内之纠纷,必且千百倍于今日,段氏政府非瓦解不可,此则吾人所敢断言者也。但段氏既去,继段氏而执政者,将用何方法以革新政治乎?即令从中山主张,改善后会议名称为国民会议预备会,第二步仍用国民会议为号召,吾恐如周幽王之再举烽火,诸侯救兵无一至者。彼国民深知政府无意与民更始,不过借国民会议骗取国民一时之信仰已耳。”(80)国民会议在近代历史上被当作政治口号空喊的命运,证明了王克家的推断。
历史研究不能只观察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还应该结合历史的客观结局进行考察。1925年9月,浙奉战争爆发,宣告了段祺瑞“和平统一”政治努力的失败。这一历史结局提示研究者,对善后会议不宜做过多的肯定性评价。但这样的认识只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得出,难以未卜先知。对会议能否产生积极的建设性成果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却应聘成为“特聘会员”的胡适,也是通过“尝试”,看到善后会议并不能制止国内战争之后,才获得“此路不通”的认知,表示不愿意继续出席善后会议的。他在《割据》一文中写道:“今日善后会议至少也应该有全国停战的条件作开会的基础,若各方的争执仍须靠武力来解决,则是各方参加善后会议为毫无诚意……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该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81)胡适与会时所抱“尝试”想法以及尝试之后感受的失望,是当时社会心理的典型反映,虽未遂愿,却说明在久经战乱之后“和平统一”主张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善后会议没能实现主持者初衷的原因,与段缺乏实力,未能形成足以控扼各方的权势重心有关。段祺瑞与皖系在政治上真正可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是在袁世凯死后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时期,以及讨伐张勋,再造共和,继续掌握政权的几年内。直皖战争败给曹、吴之后,其权势的巅峰期已经过去。第二次直奉战后段能复出,不是因为具有实力,而是因为奉张与国冯争执不下,拣了个政治便宜。然而依靠权力平衡冒出来的政治领袖,日子从来都不好过。奉军将领何柱国评论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那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82)所谓“罩得下”,是说其北洋元老的特殊身份使各方尚能有条件的接受他;所谓“吸不住”,是说自身缺乏实力的段祺瑞,已经不能臂使指应地调度指挥各路人马。故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段氏与徐世昌相比,指出他“已入十年东海境地”(83)。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政府要想成为袁世凯政府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通过和平会议来实现“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84)反过来说,段如果有了足够实力,以北洋军人的思维方式,或许又不会召开善后会议了。个中的悖论提示研究者,善后会议无所作为,或在事前已经决定,事后的论断只是为了说明事理而已。
然而历史不能简单地以成败来判断是非。北洋时期,中国政治呈分裂气象,人心思治,故“统一”总是被当成政治的至高准则。在谋求“统一”的方式上,“武力”通常成为政治家的第一选择。善后会议以和平协商方式谋求统一,是一次难得的例外,却招致失败。善后会议失败之后,“武力统一”再次被提上中国政治的议程。不过此时“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者已经不是经过第二次直奉战争激烈厮杀实力严重削弱的北洋各派,而是当初与善后会议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国民党。1926年夏秋之际开始的北伐是国民党这一不甘屈居“地方”地位的政治集团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一次尝试,却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然而国民党“此时”的军事成功能否证明“彼时”段祺瑞所作的“和平统一”努力一无是处,或者还值得认真思考。
注释:
①有关善后会议研究的学术成果殊不少见,但既有研究受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影响,在否定北洋政府的同时连带否定了善后会议。近年来,学术研究相对中性,出现了一些对于善后会议的客观记述,但大多仅摄取会议单一侧面展开,基本没有对善后会议作全面考察的学术论著。除了近代通史类的论著之外,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有胡晓《段祺瑞与善后会议》(《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鲍和平《胡适与善后会议》(《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王文玉《国民军与善后会议》(《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孙彩霞《军阀与善后会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华友根《略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条例〉与〈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纷争》(《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孙中山何时公开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刘敬忠《胡憨战争与善后会议》(《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政府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②《段祺瑞与张作霖意见之冲突》,1924年12月23日《重庆商务日报》,万仁元等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8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0页。
③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页;《西报论中国内乱》,《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3辑,第749—750页。
④古蓨孙:《乙丑军阀变乱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486页。
⑤西方学者Lucian W.Pye对1920年代初期中国军政力量之间形成的暂时平衡及相互制约作了细致的研究,可供参考。详见氏著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Washington,London:Praeger Publishers,1nc.1971)。该书第6章“the Warlords’ Balance of Power”比较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见该书第94—112页。
⑥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0—434页。
⑦1925年3月12日《重庆商务日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9辑,第141—142页。冯玉祥亦有所觉悟,他在给段祺瑞的信中写道:“当代军人,非有真正之觉悟,不能祈向真正之和平,即无由措国家于治理。觉悟维何?即武力终不可恃,当艰苦卓绝,就民治痛下功夫是也。”《冯玉祥函段陈时局意见》,《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8辑,第655—656页。
⑧余华心整理:《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⑨心史:《此后政府亦欲财政统一否》,1924年11月23日《申报》,第1张,“时论”;随波:《段祺瑞入京前之津讯》,1924年11月25日《申报》,第1张,“国内要闻·北京通信”。
⑩《国内专电·天津电》,1924年11月20日《申报》,第1张。
(11)[美]齐锡生著,杨云若等译:《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2)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3)《善后会议条例》(192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善后会议档案,1031(重并1029)/124(以下径注档案号)。条例第一条阐明了“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之会议宗旨。第二条对会员资格作了规定:一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为“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为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为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之“有特殊资望及学术经验者”。其中前三类有明显交叉,如“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可能同时是“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而被列为第二类则可能同时属于第三类。如孙中山既属第一类又属第二类,而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唐继尧、胡景翼、阎锡山、孙岳、李景林等则同属二三两类。见《善后会议会员暨代表姓名住址册》(1925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8页。
(14)段祺瑞:《致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卅电》(1924年12月30日),善后会议委员会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1925年2月,“公文”之“电一”。
(15)《时事日志》,1924年12月2日条,《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1925年1月,第205页。
(16)《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401页。孙中山态度如此,国民党的态度则十分暧昧。在孙去世前一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公函,号召实行国民会议并示威反对善后会议,被视为国民党不赞成善后会议的根据。但从所拟定的游行口号(“反对军阀包办善后会议”,“要求人民参加善后会议”,“善后会议人民代表应占三分之一”)看,国民党并不根本反对这一会议。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最大的时局问题,就是本党是否加入善后会议。因为善后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所以本党是否加入的态度,应该要赶早决定。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和大元帅研究过,总是主张加入的多。”黄昌谷:《大元帅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658页。孙中山去世后,善后会议曾宣布停会一次,以表哀吊,可见段政府方面很注意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
(17)《内外时评·善后会议》,《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1925年1月,第3页。
(18)《善后会议前途之暗礁》,1925年1月4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北京通信”;黄昌谷:《大元帅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657—658页。
(19)张氏自己亦曾公开表示不满,就在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张由京返津,“谒孙谒黎,且发出‘我系抬轿,任谁可抬’之语”,对段进行威胁。《善后会议之前途》,1925年1月10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二·北京通信”;《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1925年1月16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北京通信”。
(20)《实力派之赞成善后会议》,1925年1月13日《顺天时报》,第3版。
(21)《外电之北京政局》,1925年1月8日《申报》,第1张,特约路透电;《善后会议之前途》,1925年1月10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二·北京通信”;《冯玉祥辞职原因》,1924年11月13日《申报》,第2张;《段派激进之善后会议》,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善后会议昨日公布之电文》,1925年2月17日《大公报》,第1张第4版,“国内要闻”。按:冯氏先是派薛笃弼为代表,后因薛“政务殷繁,不能兼任,爰特改派陈君金绶接充斯席”。
(22)《胡郑龚虞与善后会议》,1925年1月11日《大公报》,第1张第4版,“国内要闻”;《又一批善后会议之各省代表》,1925年1月16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国内要闻”。
(23)《西南与善后会议》,1915年1月22日《顺天时报》,第4版。
(24)《关于善后会议之消息》,1925年1月12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国内要闻”;《筹备处所接之函电》,1925年2月21日《大公报》,第1张第4版,“国内要闻”。
(25)陈炯明最初对会议似持支持立场,其代表刘亮称,此次倒直成功,实南北统一之良好机会。现段氏召集善后会议,西南方面对此应竭力赞助,声明“陈总司令对此会议,十分赞成”。《西南与善后会议》,1915年1月22日《顺天时报》,第4版。
(26)《面对善后会议之态度》,《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75页;《萧耀南筹助善会经费四万元》,1925年3月1日《大公报》,第1张第4版,“国内要闻”。
(27)Wou 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3.
(28)《辞谢之各电》,《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76页;《善后会议筹备处消息汇录》,1925年1月13日《大公报》,第1张第4版,“国内要闻”;《唐少川对于善后会议之观察》,1925年1月10日《申报》,第4张,“本埠新闻”;《北京通信》,1925年2月5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岑春煊致段祺瑞电》,1924年11月26日《申报》,第4张,“本埠新闻”。
(29)章太炎:《致李根源等书(四九)》,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9页。
(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0、868页。
(31)胡适:《致许世英》,《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355页。
(32)《善后会议与国民党》,1925年2月5日《大公报》,第1张第4版,“国内要闻”。
(33)黄伯度编:《许世英先生纪念集·传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9),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页。
(34)《善后会议筹备处章程》,善后会议委员会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1925年2月,附录之章程部分;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5—6月,第27—28、51页。许世英称善后会议实际邀请的代表共171人,与此略有出入。参见氏著《善后会议经过情形述略》,转引自孙彩霞《军阀与善后会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168页。
(35)《善后会议秘书处发出开会通知》,1031/85。截至2月1日开会,善后会议筹备处公布的函电共计125件,其中电报122件,信函13件,数量有所不同。见《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1925年2月。
(36)《善后会议秘书厅联系文书》,1031/95;《善后会议会员录》(1925年2月21日)、《善后会议秘书厅关于到会会员人数报告》(1925年3月16日),《善后会议》,第49—56、91页。
(37)遏密:《善后会议会员一览》,1925年2月7日《申报》,第3张,“国内要闻二”;随波:《正式开会中之善后会议》,1925年2月12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北京通信”;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章第5节“会员”,第37—44页。
(38)与孙中山同列“有大勋劳于国家者”的黎元洪对段祺瑞的邀请明确表示拒绝,但措词委婉,自称“坠露”,不必附丽“龙、凤之会”,在流露出政治上的失落感的同时,力图表现自身的影响力犹在。遏密:《善后会议之特聘会员》,1925年1月11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
(39)《王克家读段祺瑞复唐继尧赵恒惕电书后》(1925年4月),《善后会议》,第126页。
(40)《善后会议开会纪事和闭幕仪式》,1031/87。
(41)《善后会议议事日程》、《善后会议议案总目》,1031/85、44。为让外界了解会议进行情况,善后会议秘书厅编辑出版了《善后会议公报》,每周出版一次,“凡京内外各部院署衙门及各省法团均须按期分寄,以广流传”。参见《善后会议函告》(秘书厅公报处函字第一号)、《公函邮政总局局长总办请特准本会议公报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函》(1922年3月12日),1031/95。
(42)《善后会议秘书厅联系文书》(第171号)、《朱绍文代电一件》,1031/95。
(43)《整理军事大纲案》,善后会议委员会编:《善后会议公报》第3期,1925年2月,“议案”部分,第1—2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19—120页。
(44)《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1029/2/122。
(45)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09—110页;《善后会议之第八次大会》,1925年4月1日《晨报》,第3版。
(46)《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1925年4月15日),1029/2/124。
(47)《善后会议议决之财政整理委员会草案底稿》,1029/2/119;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1、123页。
(48)《整理财政大纲草案》内容包括:(1)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就现实收入实数,支配用途;(2)编制中央暂行概算,其方针为:收入方面须专列属于中央的款项,支出除国债之外,以民国8年度预算为标准,所有各机关经费8年度预算已列者,参照该年度预算办理,其未列者按照现行实支数目分别核减;(3)调查各省区财政状况,作为编制新预算之预备;(4)公布历年财政状况,及临时政府每月实收实支状况;(5)筹划裁减军费;(6)筹备划分国家地方税及国家地方之支出;(7)商定中央与各省区协解款项办法;(8)统一国库,整理币制;(9)整理内外债款,并宣布历年所欠内外债确数及用途;(10)筹备裁厘加税;(11)厘定财政暂行法规。《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1925年4月20日),1029/2/116。
(49)会员王守中说:“窃维善后会议以议决国民会议条例为最重之案,国民会议条例以各省区代表名额为最重之点。”《善后会议秘书厅联系文书·王会员守中函及附件》,1031/95。
(50)《国民代表会议条例》(1925年4月18日),1029/2/116。此外,《法制院呈稿》亦称:“国民代表会议,既以商定国是为主旨,则制定根本大法,自为其唯一之职权。至其他政治善后问题,应委之与善后会议,普通立法事项,胥让诸根据宪法产生之立法机关。”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88—89页。
(51)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99—205页。
(52)《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审查报告及修正案条文汇览》(1925年4月8日),1029/2/115。
(53)《国民代表会议条例》,1029/2/116。
(54)《国民会议条例完全通过》,1925年4月19日《顺天时报》,第3版;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0页。
(55)《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1925年4月,第1—2页。
(56)《本埠新闻·关于北京政局之沪上昨讯》,1924年11月5日《申报》,第4张。
(57)章太炎:《改革意见书(一—二)》,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98页;《章太炎再发表改革意见书》,1924年11月15日《申报》,第4张,“本埠新闻”。
(58)《冯段张今日在天津会议》,1924年11月11日《顺天时报》,第3版;《东报对中国时局之悲观》,1924年11月10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二”。
(59)《褚辅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善后会议公报》第8期,1925年4月8日议事日程第13号。与褚案几乎同时提出的还有熊希龄的《提议国宪起草案程序》,主张“采取联邦主义以合民意而图统一”。见《会员熊希龄等关于国宪起草程序提案》,1029/2/106。按:连署会员包括胡适、马君武、江亢虎、潘大道等。
(60)《执政府将自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法》,1925年3月9日《晨报》,第2版。
(61)《联治派在京之积极搏战》、《善后会议昨日大会流会》,1925年4月3、5日《顺天时报》,均为第3版。
(62)不过王克家则认为段“素非主张联省之人,因鉴于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之不可能,一时联省派之学者政客,环聒于左右,始毅然有此表示”。《衡阳王克家撰著〈联省救国谈〉》(1925年1月),1031(重并1029)/85。
(63)《关于时局前途之联治问题》,1925年3月26日《顺天时报》,第4版;《联治案在善会形势》,1925年3月27日《晨报》,第2版。
(64)西南的9名代表包括:唐继尧的代表周锺岳、徐之琛、马骢,唐继虞的代表李华英,刘显世的代表刘燧昌,沈鸿英的代表岑德广,李德麟的代表严端,赵恒惕的代表锺才宏,褚辅成系以会员资格赴京与会。《善后会议会员录》,善后会议委员会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1925年2月,附录之“会员录”。
(65)《善后会议与西南代表》,1925年2月27日《申报》,第2张,“国内要闻”。
(66)《段祺瑞怕联省自治》,1925年4月13日《晨报》,第2版。
(67)《联治派与联治案》,1925年3月30日《晨报》,第2版;《政府仍疏通联治派》,1925年4月9日《益世报》。
(68)段解释说:“联治之论,实获我心,此次政局改造,其唯一途径,在使国宪省宪,同条共贯。祺瑞于去年十一月来京就职,即经马电明揭此义。今年二月,于善后会议开会之日,复经郑重宣言,并条举促成省宪方法,期于次第实施,与来电主张,初无二致。但盼制宪机关,早日成立,根本大法,早日观成,吾辈协力改造之精神,亦早日实现。则长治久安之局,将从此奠其始基。否则纵横捭阖,所谓联治者,非形同割据,即互相侵扰,末流之失,变本加厉,亦所当防。”《段合肥复滇唐湘赵联治电》,《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38页。
(69)《联治同志仍开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24页;《汤漪与联治案》,1925年4月4日《顺天时报》,第3版。
(70)曾经以记者身份采访善后会议的陶菊隐称:“我在北京采访善后会议新闻,发现张作霖反对‘联治’最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如今他又痛斥联治派为‘地方分裂主义者’,指使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此后‘联治建国案’如果列入议事日程,你们即以不出席为抵制。因此,善后会议出现了西南联治派与东北反联治派的斗争。”见氏著《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106页;《联治案之现势》,1925年3月28日《顺天时报》,第3版。
(71)《善会前途与联治案》,1925年4月7日《晨报》,第2版;《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1925年4月,第1—2页。
(72)《联治派之计划》,1925年4月13日《顺天时报》,第3版;《褚辅成之谈话》,《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66页。
(73)时人在评论西南代表退出善后会议一事时说:“惟闻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据其所计算会议中之确属联治派分子者,仅褚辅成周锺岳马聪等六人,即便全不出席,亦不生重大影响。”《西南代表将退出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50页。
(74)关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本人曾做过专题讨论,参阅拙文《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5)《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1925年4月,“内外时评”,第1—2页。
(76)《善后会议最近形势》,1925年2月23日《晨报》,第2版。
(77)《善后会议开会纪事和闭幕仪式》,1031/87。另参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29、242—244页。
(78)龚心湛、叶恭绰、田中玉各自所作《〈善后会议史〉序》,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序言部分。
(79)冯玉祥:《〈善后会议史〉序》,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序言部分。
(80)《衡阳王克家撰著〈联省救国谈〉》(1925年1月),1031(重并1029)/85。
(81)《马君武胡适等表示当执政府无力制止各方敌对行为期中不再出席善后会议来往函件》,1029/2/62。案:胡适不再出席善后会议一事,颇受世人关注。北京《晨报》曾报道说胡适已辞去善后会议会员之职,胡适本人则对《大公报》英文部记者否认此事,称自己只是考虑到若不能结束战争状态,善后会议实无继续开会之必要,意指不出席,并不意味着辞去会员资格。1925年3月7日《大公报》,第1张第3版,“国内要闻”。
(82)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冊第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83)《国内专电·北京电》,1924年1月7日《申报》,第4版。
(84)关于段祺瑞未能通过善后会议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拙文《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可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