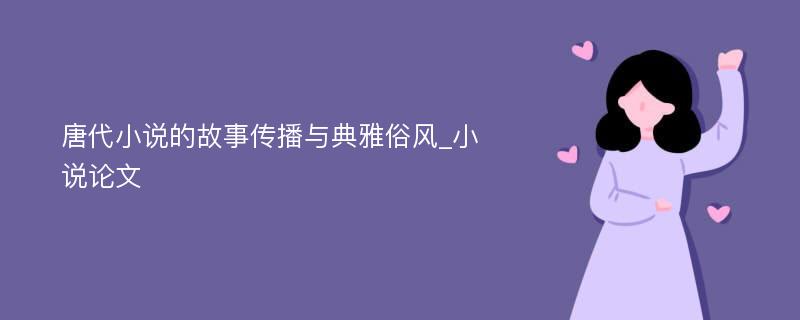
唐代小说的事、传之别与雅、俗之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之别论文,之体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小说内涵的确定,尚有分歧,侯忠义分为传奇、志怪、轶事三类①。周勋初认为:“但不管作品的性质属于志人、志怪,抑或属于学术随笔性质的著作,在古人看来,中间还是有其相通的地方,即对正经而言,都属‘丛残小语’;对正史而言,大都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学术随笔,则大都为纠正历代相传之讹误而作。因此这些著作都可在‘小说’名下统一起来。”②本文中的小说概念,也较为宽泛。从文学发生学看,小说一体,多起于民间,并没有得到文人应有的关注。唐代人也不太重视小说,举例来说,唐代文人的行卷可以用诗,也可以用散文,但鲜有用小说者。唐以小说行卷的记录只有一例,宋人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载:“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③且不说钱易的记录是否属实,即使如实,也只能说明李复言以小说行卷只是一种尝试,想以奇取胜,结果却遭斥逐。李景让知贡举在晚唐的文宗开成五年,“虚妄”成为李景让轻视《纂异》的理由,但这正反映了小说虚构的特点。一般而言,越是受重视的文体,其形式上的成熟度与纯净度就越高,越容易具有排他性。小说因其地位和受重视程度的相对低下,其结构具有较大的松散性与包容性。因此,对中古时期小说形式的研究更适宜采用平面描述的方式,注重同一时间序列上各种要素的组合形态。 在唐代小说中,有一种明显的现象,即“事”、“传”二体交叉兼行。究其内涵而言,唐人以口头传述之故事谓之“事”,而以文字记述者谓之“传”。唐代文人在小说创作中也自觉运用并区分着这两个概念,这在一些重要小说中留有痕迹。白行简《李娃传》云:“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④沈既济《任氏传》云:“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⑤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云:“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⑥《卢江冯媪传》云:“钺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⑦《谢小娥传》云:“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⑧陈鸿《长恨歌传》云:“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⑨可以看出,一则小说经由“事”到“传”的两个传播阶段。 “事”、“传”之别还体现在唐人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将口头叙述转变为书面叙述的记载,这些材料已为研究者所重视,并据以阐释唐人小说受史著影响的观念,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将荒诞真实化。如唐临《冥报记》中传递了大量相关信息⑩,其《释智菀》云:“殿中丞相里玄奖、大理丞采宣明等皆为临说云尔。临以十九年从车驾幽州,问乡人亦同云尔。”《大业客僧》云:“杭州别驾张德言前任兖州,具知其事,自向临说云尔也。”《东魏邺下人》云:“雍州司马卢承业为临说,云是著作郎降所传之。”亦有众人传说,如《北齐冀州人》云:“浮图今尚在,邑里犹传之矣。”《韦仲圭》云:“仲圭弟孝谐为大理主簿,为临说,更问州人,亦同云尔。”本为众人传说,而由知之最详者口头叙述的,如《陈严恭》云:“州邑共见,京师人士亦多知之,驸马宋国公萧锐最所详审。”《崔彦武》云:“崔尚书敦礼说云然。往年见卢文励亦同,但言齐州刺史,不得姓名,不如崔具,故依崔录。”还有直接来自于当事人的传述,《孙回璞》云:“回璞自为临说云尔。”在其他小说中也有留下类似传播的痕迹,如陈玄祐《离魂记》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11)这样的现象除了将荒诞不经的故事以来源有自而令读者听众相信外,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即它暗示了故事传播的过程。这一由口头到书面叙述的过程,其文本的形式必然包含有故事叙述者的口头语言风格和故事记录整理者的书面语言风格。 唐代小说中以“传”为题的篇目数量较多,一般研究者认为这是受史书中“传”体的影响,但从唐人小说的创作情形来看,“传”还不是史书中传记的原意。从传的含义来讲,可分两层:一为说明、解释意义。如先秦经书,各自有传,经传即因解释经义而生,史传目的也是阐发历史进程规律。《陔余丛考·史记一》云:“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12)《史记》中的列传虽以人物、故事次第结篇,但主旨一贯,并非仅以故事本身为宗旨,而始终与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旨相一致。除此以外,传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转述与转达。《史通·六家》云:“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13)上古时期经文授受,常以师徒相传的形式进行。老师将经文诵读告知弟子,弟子则背诵记忆,尽量保留原初样式向下传习,故有伏生传书的典故流传。因此,传一方面有解释、说明的意思,一方面又有转述、转引的意思。传的这两层意思进入文章、文学体裁后,各自形成“传注”体与“传奇”体两大类。前者以说理为要旨,后者以记录为核心,虽然形式上均以故事的方式展开,但本质上仍是有所区分的。从上引唐小说“事”、“传”诸例可以看出,小说的“传”是在口头材料“事”的基础上进行“传述”的意思,一经“传述”则成为书面文字。这一解释也能得到文献的支撑,白行简《李娃传》开头是这样的:“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结束时则云:“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传,即传述之意。 从“事”、“传”实例及析义来看,唐人对于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已有清晰的认识,并体察到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分:即前者为群体的,民间的创作;后者是文人的、个体的创作。唐代小说正产生于书面叙事与口头叙事的“互动”状态当中。文学叙事的两种形态,不仅为唐代小说的生成所反映,也体现在有唐一代其他“说唱—记录”体式当中,如敦煌变文中就经常有两种叙事形态交织、互动的实证。敦煌写本《舜子变》,记载了在《尚书》、《史记》、《孟子》等经典文本之外的舜的故事,追其源头,应来源于长期以来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对舜的形象记忆:“从变文中呈现许多与《史记》情节的歧异的现象来看:舜的传说,在太史公写成定本之前,应即有非常丰富的口头传说,敦煌本《舜子变》的依据可能有另一与《史记》不同的源头,有可能是《列女传》,也有可能是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舜子口头传说,而在民间可能也仍有一些口传形态的不同文本。”(14)除从材料来源上反映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之外,从变文自身形式上也能看出口语叙述与书面叙述的区别。由于口头表演具有即时性、即兴性,固定的故事形式、起承转合时的习惯性说法有助于艺人记忆与民间故事传播。这一特征体现在变文当中程式化的语言:“在敦煌变文中,说唱艺人在现场表演时,也常会运用一些重复的习套式词组和短语,来作为组织故事的方法。”(15)又如,在变文中描写人物外貌时不重视个体特征,而是程式化叙述:“比如《伍子胥变文》中,描写秦穆公之女的‘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方,耳似珰珠,手垂过膝,拾指纤长。’猛一听来,每一个部位都出奇地美丽,但仔细推敲,在我们的面前会呈现出怎样一个美女呢?恐怕和怪物差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能说,变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的‘并不是一副具体的人物肖像,而是凭借一套现成的公式捏合出一个美女的某种象征性形象。’”(16)这些套语的运用,有可能在变文文本内部造成细节的含混,逻辑的矛盾,但它对于主要意义的表达与传递不会构成大的障碍。相反,这种文本“缺陷”正凸显了敦煌变文与口语叙事的密切关系,正是直接来源于口语,在语词与细节上才未经仔细打磨与推敲,在结构上则体现为单一和固定化,这与书面用语的精雕细琢和富于变化是相对立的。同时,变文对口语“缺陷”或者说“特色”的记载,显现出被书面传统所遮盖的民间通俗文学传统,这对于深入了解唐代小说的生成方式,乃至文学经典文本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小说生成的角度不难看出,它结合了口头和书面两类叙述方法。尽管在现存的文献中故事多以文本为载体,但仍然可以看到口头叙述在文本中留下的诸多痕迹。由“事”到“传”的过程,也就是故事不断被“文本”化的过程,而文本中的“口头”叙事成分自然会混杂在“书面”叙述之中,“口头”叙述也不断被改造为“书面”叙述了。 书面叙述传统与口头叙述传统所直接作用的,是唐代小说中雅化与俗化并存、并用的倾向。雅化与俗化是在两个层面上分别体现出来的。首先是体式——即文体上。雅化与俗化带来的是不同的文体构成,比如唐诗与元代散曲相比,我们可以说唐诗雅而元曲俗,如果将元曲和当时民间流行的小调或明代的山歌比,元曲多出于文人之手,还是可以列于雅文学的范围,这体现出“雅”与“俗”的相对性。小说文本的“雅”和“俗”也是相对的。其次是体性——风格上,雅与俗对应着不同的审美趣味。《文心雕龙·体性》云:“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可见,体又可指文章的气韵、格调、风格。唐代小说雅化和俗化并存,形成了雅体和俗体的风格。它既是形式上的,又是内涵上的,这种雅俗的或分或合,正缘于唐人小说交织着“事”与“传”的两种叙事形态。由于口头叙事传统与书面叙事传统的共同作用,使得唐代小说在雅化与俗化方向上各自生成不同的面貌,更多的情形是在同一文本中夹杂着“俗体”和“雅体”的叙事方式,而成为雅俗共生的文体形态。 唐人小说多为文人整理加工过的文本,它在脱离民间说故事的场态后,“雅”成了小说的主导风格。小说的“雅体”,大致指叙事采用书面语,风格典雅,由此而形成的文人化的内容,讲究情调。其实,小说中大量的作品仍然是书面叙述的产物,它不是为口头传述而创作的。早期的作品如《游仙窟》其情节性不强,以雅致的语言叙述浅俗的内容,比如其中有以骈体形式写作的长篇书信,不适宜口述,其赠书云:“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虽复赠兰解佩,未甚关怀;合卺横陈,何曾惬意。”又如牛肃《吴保安》中有两大段书信,其一为“保安寓书于仲翔”,其一为“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这样的作品只能以书面叙述的形式而流传。有些作品只能阅读文字而不能口头传述,如韩愈《毛颖传》,此文收入《全唐五代小说》中(17),但就不具有口头传说的特点,故事性不强,要在说理,故柳宗元观其文,方能知其详细内容。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云:“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18)《毛颖传》只能“读”而不能“听”,其传播的范围应当是有限制的。 小说受史学影响,借鉴史著的评论风格,是其雅化的表现之一。唐代小说受史学影响,沈既济《任氏传》明显采用了史学叙述方式,如开头:“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祎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故事结束后,有议论:“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19)这和《史记》“太史公曰”的议论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人物的品德都从叙述中出,如写任氏的善良,当她为韦某所逼,则云:“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惟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20)深得太史公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撰史之法。《枕中记》:“明年举进士……是夕,薨。”这一段则为卢生的完整传记,并插入卢生临终上疏和皇帝的诏书。据《旧唐书》本传,沈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为史馆修撰,李肇《国史补》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真良史才也。”(21) 小说诗化,是其雅化的表现之二。小说的情节简单,而以诗歌创作为主体来表现诗才,这种雅化倾向在某些小说作家那里尤为突出。小说不以口头文学为特征,因为大量诗作的出现,不适宜向第二者或更多的人陈述,就连在文人圈中的口头叙述也已不再成为可能。如李玫的小说(22),以大量的诗歌来抒发情感或来表现人物的命运际遇,抒情性强。作者借小说或叙事作品来表现自己诗歌创作才华的欲望十分明显。首先是诗歌有一定的数量,差不多篇篇如此,可列举的作品有《嵩狱嫁女》、《陈季卿》、《刘景复》、《张生》、《蒋琛》、《韦鲍生妓》、《许生》等。如《陈季卿》,中间一段则全是诗作,“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如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这是一个很简单却很凄丽的故事,讲的是举子陈季卿苦于功名未达,遇终南山翁,山翁作法使其终能遂愿。上引之文即中间归家一节,反映了科举场中一般举子的辛酸和漂泊情绪。小说中陈季卿并非实有其人,李玫只是借此表现落魄文士的一段经历,更主要是表现才华,没有诗也不影响叙事情节的展开。 另外,作者有意在用多种体式来尝试表现诗才。在《陈季卿》中,诗体有所变化,有七绝一首,七律一首,五律三首。再看李玫其他作品,诗歌体式多样,《刘景复》中有长达三十二句的七言歌行,据作者说“歌今传于吴中”。有歌,《张生》中张生妻“歌六七曲”,写闺怨,凄楚动人,其一曲云:“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有骚体词,《蒋琛》中所唱《怨江波》:“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而且有意尝试用不同风格的诗作来表现作者写诗的能力。《蒋琛》中有楚辞体的哀怨,“歌竟,四座为之惨容”。吞声饮恨、溢眸恨血的内心情感倾诉,音乐曲调的幽深绵长尽在其中;《张生》中诗歌轻艳,“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写出闺中少妇的寂寞无可奈何的情绪;《许生》中诗歌较为沉着,六首七律,有如一组咏古伤怀的组诗,如:“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举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瀦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如果说一位作家能诗备众体,那是通过很长时间创作来体现和确认的。而小说作者在其写作中或有意运用不同诗体进行创作,或展现不同风格的诗作,其意图和期待非常清楚。这必然是在展示诗歌写作修养,结果就造成了小说的雅化倾向。 李玫小说的诗化倾向,在其他文人的创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虽然这不是唐人小说的主流,却反映了小说在文人圈传播时不断雅化的要求。如此,小说便渐渐远离口头叙述的特点,而成为案头摆设,成为以文字方式传阅的书面文学。 与唐代小说雅化倾向相对应的是对“俗”的接受,这是指叙事的口语化,风格俚俗,讲究情节,由此而形成的世俗化的内容,尽量让听者接受,这是小说受口头叙事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书面叙述中保留讲故事现场感的结果。小说俗化特征体现在小说中书面叙述的减少与对话内容的增加。李朝威的著名小说《洞庭灵姻传》,一作《柳毅传》,其中的重要情节就是柳毅为洞庭龙君小女传递书信,小说之妙在于没有写出信的具体内容,只在柳毅答应为其传信时,“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柳毅传书于洞庭君,亦未及信的具体内容:“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23)而书信中内容都在柳毅初见龙女时的大量对话中得到落实,这样的对话形式恰恰可以在口头进行传述。唐人小说经历由小范围的口述,到文人中间的书面传递,再到面对大众的口头叙述,这一过程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由于传播要求世俗化,内容也有了变化,如在日常人生、游侠复仇、婚姻恋爱等小说中,主人公身份的差距渐渐成了叙述模式,如贵族公子和妓女之间,其中妓女成了下层人的符号,正反映了底层百姓的愿望。真正的妓者进入叙事角色,爱情的女主角多与妓人有关,仙妓于此合流。 大众、市井文化对于小说的期待,还带来小说形式上的变化,体现在因口头叙述而要求情节的自然化,细节描写的生动形象,这都在适应大众心理。用真名实姓,并注意细节的真实可信,如地点方位的真实,这样可以吸引听众,以此为基础进行虚构,虚虚实实,也是为了吸引听众。 总体来看,叙述者对同一叙述对象的处理当兼顾雅俗两个层面,或有侧重,但从叙述形式和叙述内容来看,唐人小说的主流还是以雅为主,太俗的并没有流传下来。首先,唐人小说传播的范围大多是在文人圈内进行,这是唐人小说繁荣赖以存在的土壤。沈既济《任氏传》,得之于故事中的主人韦崟,“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崟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这时故事虽未形之于文字,但已形成于文人的记忆中,后来又在文人间传述,并最后定型。“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24)。即使故事最初来自民间,经过文士的记录、加工和改造后,大致就在文人群体中传述。其次,雅化还表现于对“俗”传统整体性的、全面性的遮蔽与取代趋势。小说的本质是使人在闲谈时获得愉悦,传播知识不是主要的任务。唐人小说中的俗的一面肯定被历史洗刷殆尽了,通常研究文化的学者都主张要注意下层文化运动,但不能进行下去的重要原因是文献不足征,特别是宋明以前的下层文化。下层文化肯定是复杂的,精华与糟粕并存。不管有无文字的记录,古往今来,谈“性”当不绝于耳,但即使将谈性视为最低俗的内容,文献中仍留下了流传的印记。就小说而言,被我们认定有色情倾向的作品是《游仙窟》,它着重写作文人群体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但对情色的描写仍是含蓄和保留的。然而,敦煌文献中发现一篇题名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其对色情场面的描写直接而具体,远非《游仙窟》中点到为止的“玉体横陈”等含混语气可比,作为唐代俗文学的代表,《大乐赋》的序文内容可使人们了解唐代底层人群对于性爱的观点:“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既足,莫远乎欢娱至精。极乎夫妇之道,合[乎]男女之情。情所知莫甚交接,其余官爵功名,实人情之衰也。夫造构已为群伦之肇、造化之端。天地交接而覆载均,男女交接而阴阳顺。”“始自童稚之岁,卒乎人事之终,虽则猥谈,理标佳境,具人之所乐,莫乐如[于]此,所以名大乐赋。至于俚俗音号,辄无隐讳焉,惟迎笑于一时。”(25)因此,《大乐赋》的作者是不是白行简已不再重要,它的出现让人认识到:现存唐人小说中原该存在的民间传述,并有文人参加的有关“交接”之事的叙事作品,已经消逝。今天在讨论唐人小说雅俗兼行的叙述方式问题时,应意识到大俗的文字已经散佚的事实。但像《大乐赋》这样大俗的作品集体散佚,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在文学审美价值尺度下选择淘汰的结果,换言之,是文人趣味与民众趣味竞争优劣的结果,是统治需求与民间消费、精英文化与俚俗文化抗衡和博弈的结果,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 唐代小说所体现的口头和书面叙述共存的形态特点,也是唐前小说的共同特征。唐人关注和有意使用“事”、“传”两个概念,是对小说特征较为成熟的认识。传奇小说的文本大多是从口头叙事而来,是对口头叙事的记录,又是对口头叙事的加工和润饰;作为文本的小说必然保留了部分口头叙述的原始成分,但经过整理的文本也自然成了口语化和书面化的综合体;书面语和口头语,民间的和文人的叙述在风格上就有偏重民间叙述的俗体和偏重于文人叙述的雅体,在一篇小说中又可能是“雅体”和“俗体”兼行的,如在文本整理中既注意对话中的书面语(例如书信内容)的省略,又刻意加入显示文人才情的史学叙述方式,以及用不同体裁和不同风格去展现诗人的才情和学养。 在历史叙述中,大量原本存在的真实淹没在零碎的史料中,甚至已隐藏到材料的背后,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唐人小说的产生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讨唐人小说流传的方式及其特点是有意义的,但却是很困难的。呈现在历史表层的材料、观点、趣味,从表象上看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只是部分的真实,是经过选择保留下来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却是以大量消失的、被遮蔽的历史形态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学术研究不仅需要解读显性材料的能力,更需要认知和发掘隐性材料的能力,以获得历史进程的纵深感与动态性。唐代小说,以及唐代说唱文学正好具备雅、俗双重属性,它是两种对立视野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小说可能具有报告的功能,它能将文化与文学未曾重视的各种人类状况带入人们的意识中。”(26)本文的写作试图在文化生态中去探讨文学的生成和演变(27),复原唐人小说的原生状态,探讨其在口头传述形态与书面传述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雅俗兼行的叙事形式和形成原因。 ①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第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③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第9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⑤⑥⑦⑧(19)(20)(23)(24)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4,第3991页;卷452,第3697页;卷475,第3915页;卷343,第2719页;卷491,第4032页;卷452,第3697页;卷452,第3694页;卷419,第3412页;卷452,第369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⑨李昉等:《文苑英华》,卷794,第4201页,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⑩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引《冥报记》诸篇见其书卷二,第27—6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11)李昉等:《文苑英华》,卷358,第2832页,原题《王宙》,出《离魂记》,中华书局1966年版。 (12)赵翼:《陔余丛考》,第85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1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15)刘惠萍:《在书面与口头传统之间——以敦煌本〈舜子变〉的口承故事性为探讨对象》,《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 (16)富世平:《敦煌变文程式化创编所带来的文本缺陷问题》,《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17)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 (18)柳宗元:《柳河东集》,卷21,第3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1)李肇:《唐国史补》,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2)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引李玫诸篇见其书卷四九、五○,第1357—1405页。 (25)伏俊连:《敦煌赋校注》,第24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We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p.18.转引自陈新著《西方历史叙事学》,第18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7)戴伟华:《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