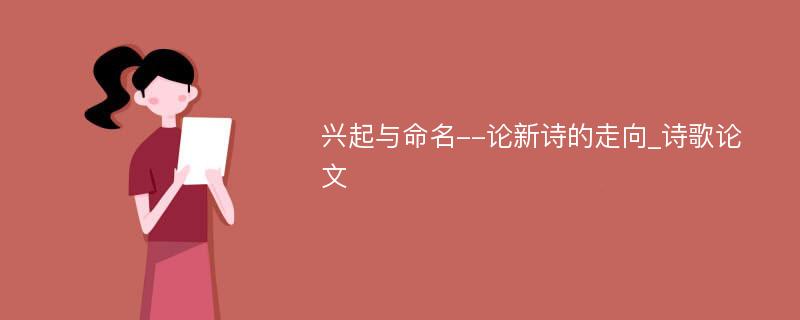
崛起与命名——再论新诗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12-0025-05
1976年,随着芒克最后一个离开白洋淀水乡,书写在历史进程中的白洋淀诗歌也便翻 过了她的最后一页。也正是在这一年四月,丙辰清明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似乎又开启了 一个新的诗歌时代,不过那仅仅是一个象征而已。毋宁说那更像一场政治行动,一场为 旧的黑暗时代送终的仪式罢了!果然,一个新的政治和文学的时期在这年十月登临了舞 台,并且渐次拉开了光明的序幕。正如徐敬亚在《复苏的缪斯》中所说的那样:“应该 感谢历史:正是在我们民族最迷茫、最窒息的时刻,新中国的诗神在清明雨中猛然惊醒 ,天安门广场上,爆出了愤怒的咆哮。之后,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沉默(那是黎明前的黑 暗),1976年10月,她睁开昏死沉沉的眼睛——”(注:徐敬亚《复苏的缪斯》,《崛起 的诗群》11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然而,历史的风尘并不是在这开眼闭眼间就可以倏然轻易抖落的,一个百废待兴的荒 原似的世界,几乎一切都处在新的出发点上甚至迷茫处。就中国文坛而言,最初的几年 间,就如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于彷徨与转型的关口。那时最慑人心魄、令人震撼的声音 莫过于刘心武《班主任》中“救救孩子”的呼唤。在一场民族的浩劫和人性的深度沉沦 之后,它似乎接续上了五四时期鲁迅“救救孩子”的启蒙话语,渴望从废墟中将人们拯 救出来。但真正具有这种启蒙价值和意义的,还是1978年底在人们的视野中崛起的新诗 潮,即所谓“朦胧诗”,这被人们称作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作为一种新诗潮,它可以 追溯到北京文化沙龙与上山下乡运动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诗人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落。但 那时还仅仅是一种存在于口头或传抄方式的隐秘写作,还不具有广泛的思想启蒙意义和 艺术价值。可到了1978年底,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作为引领时代思潮的思想启蒙 者和先锋写作者,他们重又集聚在一面旗帜下,并且创办了20世纪地下文学中最具有先 锋精神和文学价值的民间刊物之一《今天》——或许下面一段话最能够充分说明《今天 》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民刊的出现是民主自由舆论成熟的标志,它们由手抄本小说、诗歌、政治传单发展 演化而来,并遇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复出这么一个历史转折契机。如果当时公 开发行的国家出版物能与民间舆论同步成熟,与广大人民同样富有激情的话,长期处于 地下的文学作者们也许会放弃办民刊的想法,直接通过公开发表作品去产生影响——可 惜,历史不是设想……
现在,《今天》创刊的时代背景已凸现出来,那是一个人民积压多年的心声需要表达 而又在正规渠道得不到表达的特定关口。……”(注:《<今天>的创刊及黄金时期》, 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320-321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今天》就这样应运出现在一个历史的特定关口。在1978年10月的某一天,北岛、芒 克聚会在黄锐家喝酒,当他们感觉到需要寻找一种更有力的形式以“表达内心的声音” ,甚至参与历史的进程时,他们一拍即合,商定创办一份文学刊物。接下来他们便四下 联络,并很快组成了一个最初的编委会,其成员分别是北岛、芒克、黄锐、刘禹、张鹏 志、孙俊世和陆焕兴等七人。在商定刊物的名称时,他们当初曾分别给出了一个名字, 比如“无花果”什么的。芒克说当时他非常潜意识地想到了“今天”这个指称,并且获 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后来北岛起草的“致读者”中,把“今天”的内涵阐述得很是清 晰和深入: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 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再等待了……过去,老一代的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 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今天,作为一代 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注:《 致读者》,《今天》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
第一期稿件征集齐之后,困难的还是印刷。最后黄锐背来一台很破旧的油印机。这样 原始的手工作坊似的印制工序就开张了。第一期印刷是在现属东直门外使馆区的陆焕兴 家,那时是城市的边缘地区,比较隐蔽和安全。这也似乎成了中国处于地下、民间状态 隐秘写作者的一个基本象征,所谓“从边缘出发”(注:奚密认为:“从边缘出发”是 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所以她一部书的名称即是《从边缘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北岛在一次访谈中谈及《今天》创刊号的印制,说那是在一个边缘地区,谁也 找不着,“就如奚密说的,中国的诗歌是从边缘地区出来的。”(《沉沦的圣殿》332页 ))。1978年12月23日,这同样是一个标志和象征:《今天》诞生了!北岛、芒克和陆焕 兴骑上改了号码的自行车,在纪念堂、西单民主墙与文化部等一些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标 志区沿途张贴下来。翌日就又去了北大、清华等一些大学区,并获得强烈反响。可在取 得成功的背后,隐患、矛盾和尖锐的冲突也在孕育着。《今天》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在 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一直是一个问题,也是编辑部同仁所关注的聚焦点。北岛撰写的 创刊号“致读者”中这样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 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注 :《致读者》,《今天》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虽然同仁们曾就此达成保持纯文 学立场的共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似乎完全游离也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为此导致了 编辑委员会的严重分裂,其中五人退出,只留下北岛、芒克鼎力相持与继续着。不久, 新的编辑部重又组成,他们是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和周眉英。 其中北岛任主编,芒克任副主编。后来黄锐又回来担任美编,而赵一凡算是幕后编委, 他提供了大量在作者那里早已散轶的珍贵资料。刊物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及新人,并 且从第二期起便赢得了大量订户,也吸纳了一批为此甘愿献出自己而义务工作的热心人 。不管怎样,那时《今天》的同仁们隐忍着不安和阵痛,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很快产 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自1978年12月《今天》创刊,到1980年12月研究会自行消散, 他们坚持了整整两年时间,共出版九期《今天》和三期文学资料。在这期间,还刊印了 北岛的《陌生的海滩》、《波动》,芒克的《心事》和江河的《从这里开始》等4种丛 书。在刊物上发表诗歌的主要作者有北岛、芒克、食指、舒婷、江河、方含、顾城(古 城)、杨炼、多多(白夜)、田晓青、严力等。历史当然也不会忘记那些一直躲在幕后, 但却为《今天》的出刊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文学朋友,比如赵一凡、周眉英、鄂复明、徐 晓、王捷、李南、桂桂、小英、小玉、彬彬等,其中有许多才华横溢、目光高远,但却 并未从事创作,只是本着对《今天》的热爱以及文学这份事业,才聚首在这面旗帜下的 ,这几乎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本身。(注:参阅《沉沦的圣殿》第五章、第六章相关 部分。)
1979年3月,北岛的《回答》在《诗刊》上发表,这是第一首公开出现在国办刊物上的 “今天派”诗人的作品。继之舒婷发表了《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祖国呵,我 亲爱的祖国》,而顾城则发表了《一代人》等“抒情诗十首”。1980年是新诗潮全面崛 起的一年,“……在这一年,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现代倾向正式出现在中国诗 坛,促使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中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 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 期。)。然而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异样的声音与眼光,经过长时期思想与美 学的体制性禁锢,人们接收和感受新艺术的触角早已在一片片地剥落与钝化,从而形成 了一种守成意识与审美堕性,尤其当那种准意识形态色彩的艺术范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 时,那份坚守与拒绝就决不仅仅是一般艺术问题,它是一种立场,一种姿态,是与阶级 的本质生死攸关的。与此同时,一种伴随新事物与新艺术而一同兴起的开放的观念也在 成长,这些艺术的先锋与理论的前导者,尽管最初时或许显得有些孤高,但也同样不乏 掌声和召唤。因此在新诗潮涌动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事 实也果然如此,新诗潮一出现,就由此引发并展开了激烈、尖锐而又旷日持久的论争。
首先做出反映的是“归来”派诗人公刘。早在1979年初春,他就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 馆主办的《蒲公英》小报上,读到了青年诗人顾城的组诗《无名的小花》,这些诗“真 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随父‘下放’少年的畸形心理……”看着这些诗以及作者 的心灵独白,他感到了心灵的颤栗!随后他设法找来顾城所有能找到的诗作,默默地读 着和思索着!首先他不赞同以顾城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作者“是走在一条危险的小路上” ,或者说他们的诗仅仅“是一些个人主义的呻吟”。无可疑问,这一代人的主要特征就 是思索。即便他们的诗中“有着消极的甚至是颓废的一面”,究其所以,那一定会有“ 出现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因素”,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并充分理解他们,然后加以引导。 这是摆在诗坛和老一代诗人面前的“新的课题”。(注: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 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复刊号,1979年。)在公刘看来,像顾城那样仅仅有幻想 ,必然导致“病态的早熟”。加之个人经历和认识上的局限,就会出现偏差和片面性, 甚至“陷入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犹如搁浅的船只,“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拉纤、撑 篙,或者跳下水去用肩膀将这些小船扛出沙滩和礁丛。”(注:公刘《新的课题——从 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复刊号,1979年。)对此,顾工发表了《两代人》 ,试图在“理解”和“引导”的前提下展开平等对话,并且开始了对自我的反思:“我 们这一代观察事物感觉事物的方法,就是最完美无缺的方法吗?我们所习惯的反映论, 就是天衣无缝的最准确的反映方式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其他学说其他流派中,吸收到 一些新的光和热?”(注: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 10期。)从而在理解孩子的过程中理解诗,在理解诗的过程中理解这新的一代。
新诗潮之初反应强烈的另一位焦点诗人就是舒婷。她先是在福州市马尾区的油印刊物 上集中发表了《珠贝——大海的眼泪》等5首诗,继之从1980年2月号起,《福建文学》 开辟专栏,连续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后来舒婷有些伤感与 疲惫地说:“我的名字像踢烂的足球在双方队员的脚边盘来盘去,从观众中间抛出的不 仅仅是掌声、嘘声,也有烂果皮和臭鸡蛋”。(注:舒婷《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心烟》15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1980年4月,全国诗歌讨论会在南宁召开,有关新诗潮的论争也更趋激烈和深入。这年 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他在南宁诗会上的发言 ,“崛起”的字样也是第一次见诸报端。在他看来,这是一批新的探索者,他们给诗坛 “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因此人们要以史为鉴,对于这些崛起的新人,“适当容 忍和宽宏”,“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出来“引导”或“采取行动”。1980年 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作者从另一视角,表达了对 这类新潮诗歌的质疑与批评:有些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 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 。”他以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短诗《秋》为例:“连鸽哨也发出了成熟的音调,/过去 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这 是诗的第一节。他说开头第一句就叫人捉摸不定:初打鸣的小公鸡可能发出不成熟的音 调,大公鸡的声调就成熟了。可鸽哨仅仅是一种发声的器具,它的音调还有什么成熟与 不成熟之分?诗中“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信息又不是一种物质实体,它能被 扫描出来吗?这位批评家还说,他与一位写诗的朋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共同研究,才仿 佛猜到了作者的用意,原来“那阵雨喧闹的夏季”,指的就是十年动乱,而现在,一切 都像秋天一样明净爽朗了。接着他又举证和批评了另一位青年诗人的《海南情思》。他 指称这类诗让人感到气闷!但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便采取了一种温和的说法,姑 且以“朦胧体”称之。从此,这种新的诗潮便有了“朦胧诗”这个普泛性的共名,而围 绕着“朦胧诗”的论争也愈演愈烈。
论争的双方可分为崛起论者与否定论者。谢冕、孙绍振与徐敬亚因文章均有“崛起” 字样,因而被称为“三个崛起论者”。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之后,孙绍振于1981 年3月在《诗刊》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者在评价近一二年某几个青年诗 歌作者及其作品时呼应了谢冕的说法,但他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新的 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些新的美学原则主要有1)“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 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 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2)提出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3)强调艺 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则在更广泛的 理论层面上阐述了朦胧诗的诗学内涵,尤其是它的现代主义倾向(注:徐敬亚《崛起的 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吴思敬的《时 代的进步与现代诗》则从发展、进步的视角,进一步揭示了朦胧诗发生发展的合理性与 合法性的基础,确立了那个时代诗歌写作与内在性诗学的现代性特征(注:吴思敬《时 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诗探索》1981年第2期。)。“崛起论者”无论诠释、呼唤,还 是辩难、论争,他们均以激情与理性,既为朦胧诗推波助澜,又为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石;而另有一些批评家和诗人,则认为这类诗晦涩、怪僻,表现了阴郁、不健康的心 理,甚至是资产阶级沉渣泛起,因而采取断然拒绝与否定的态度。这部分“否定论者” 主要有丁力、郑伯农、陈涌,也包括艾青、臧克家等。就其论争所涉及的热点或诗学问 题,主要集中在传统与创新、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及懂与不懂等几个方面。
如何体认传统与创新的内在本质,赋予传统一种怎样的属性与内涵,这决定着诗歌创 作的逻辑起点、基本路向和最终归属。一直以来,中国当代诗学似乎本能地隐含着一种 本质主义的观念:建立在阶级或集团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意识是它的内核,现实主义是它 天经地义的必然的主流,而古典加民歌则成了发展与创新诗歌的唯一方向。虽然人们也 一致以为,文革期间的帮派文艺严重异化了诗歌艺术,但在不少人的本质主义观念里, 解禁之后的诗歌也仅仅只能是返回现实主义和古典加民歌的根本传统,因而不应有任何 僭越之想。然而中国新诗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难道这就是它的唯一方向吗?就如谢冕先生 所一再质疑的:“……新诗是否只能拥有一个‘基础’——‘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一个‘主义’——‘现实主义’,它是否应当拥有更为广阔的借鉴对象和艺术表现的方法?”(注:谢冕《失去了平静之后》,《诗刊》1980年第12期。)民族化、大众化、现实主义、古典加民歌……这种所谓的本质主义诗教传统,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成不变的陈旧僵化的教条与模式?就如谢冕所说:“其实,传统不是散发着霉气的古董,传统在活泼泼地发展着。”它就像一条河流,它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湾浅水,而在它经过的地方,却有无数支流汇入(注: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诗人江河也以河流作比,他说:“传统永远不会成为一片废墟。它像一条河流, 涌来,又流下去。没有一代代个人才能的加入,就会堵塞,现在所谈的传统,往往是过 去时态的传统,并非传统的全部含义。”传统就是“河流的自身或整体”,它含纳着过 去、现在和未来。(注:参阅江河《随笔》与《小序》,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24—2 5页,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从这些叙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的生命,它是 个不断被加入的成长着的事物,而不是过去已达致的某个点,一种范式或一片化石。它 既在过去,也活在今天,并指向未来。既然传统是一个不断被加入的事物,那就必然会 有超越、变革和创造,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颠覆,比如五四。其实,中国新诗最大的传 统就是五四诗体革命,它的精神就是创造和变革,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反传统就是一种 传统,是一种不断被加入的创造的传统。
朦胧诗的现代主义倾向,是这场论争的另一聚焦点,也是其根性所在。革新与加入传 统,必然走出一条超越“诗学原旨主义”或“本质主义”的传统创造之路。以一种开阔 的视野和多元的胸怀去借鉴和吸纳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及艺术方法,是具有时代与历史 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就如《今天》在发刊词中所申明的那样: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 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 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注:《致读者》, 《今天》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
一代新诗人的崛起,就是在“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 ”(注: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 果。事实上,这一代诗人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上与现代主义相遇,并适时地而又有所 选择地吸纳了它的合理因素,比如它的启蒙理性以及象征主义艺术手法,这在吴思敬的 《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文章中均得到了合法性的解释。 但在朦胧诗的反对者与本质主义或决定论者那里,“……‘崛起’者们是要承袭西方现 代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是要让我们的诗歌走现代主义的道路。他们呼喊要实行当代 西方的‘美学原则’,要步西方现代主义的后尘进行‘内容和感情的更新’”(注:郑 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诗刊》1983年第6期。),事实上他们就是要否定中 国的新诗所走过的道路及其现状,从而发展现代倾向。在反对者看来,既然现代主义属 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自然便在扫荡之列了。
“表现自我”或“向人的内心世界进军”,这是朦胧诗最为彰显的一面旗帜,也是当 时论争的焦点之一。徐敬亚说,从80年代起,“一个平淡然而发光的字眼出现了,诗中 总是或隐或现地走出了一个‘我’”,这群新潮诗人最主要的艺术主张就是“表现‘自 我’”(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 3年第1期。)。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将此看作是“新的美学原则 ”的本质要素,即所谓“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任何丰功伟绩”,而是深入到生活 溶解于内心深处的秘密之中。朦胧诗的崛起,意味着人的回归,使人们在诗中既看到了 自我的身影,也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开在内心深处的花朵”。但长期以来,自我作为 与社会、人民或群众对立的一极,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或唯我主义的代名 词,而内心世界也成了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形式。因而,当表现自 我情调的诗歌及诗学理论一经出现,就自然成了话题的聚焦点,也不可避免地会涌动起 反对的声浪。就反对者一方,他们认为,朦胧诗人的“自我”已成了最高主宰,这个自 我“忽而缩小到微观世界无法捉摸的极其琐小细微的‘心灵深处分子粒似的一颤’之内 ;忽而又扩大到凌驾于整个祖国人民甚至宇宙之上”,他反对神化别人,原来只是为了 神化自己。(注:柯岩《关于诗的对话》,《诗刊》1983年第12期。)
“表现自我”体现了朦胧诗人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主体性层面,而在艺术上,他们则采 用了以象征手法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艺术方式。象征、隐喻、通感、幻觉……这些在传统 和习惯修辞中已经陌生了的手法,现在开始大面积地出现在朦胧诗中,“他们好像在刻 意追求某种朦胧的意象,好像在照相时故意把焦距对得不太准确,使感情和意象的联系 比较模糊和隐秘。这样,诗的形象和思想便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但是它又是这样新颖, 许多诗作中还有很独到的、深刻的沉思乃至哲理。不过,他们厌恶直接说出来,他们把 它藏起来,让读者去找。”(注:孙绍振《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诗刊》1 980年第9期。)因而便使得习惯于在传统中阅读诗歌的读者感到了隔膜和困难。尤其象 征艺术本身所固有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更使得那些渴望获得明朗而又具确定性内涵的 读者迷茫、朦胧,如入五里雾中。就如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中的描述的那 样,“不懂”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然而诗人们并没有因“不懂”、“晦涩”而停下探 索的脚步,就如舒婷所说“先行者是孤独的”,可他们宁愿忍受这孤独,甚至牺牲自己 ,“只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注:舒婷《生活·书籍与诗》 ,《心烟》144页。)
这场论争最终以徐敬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一文 而告结束(注: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 。)。然尽管如此,朦胧诗的写作和影响还在,而且作为一条生生不息的脉流,已经汇 入了源远流长的文学之河,汇入了辉煌的历史与传统之中。
收稿日期:2004-08-18
标签:诗歌论文; 朦胧诗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北岛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徐敬亚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