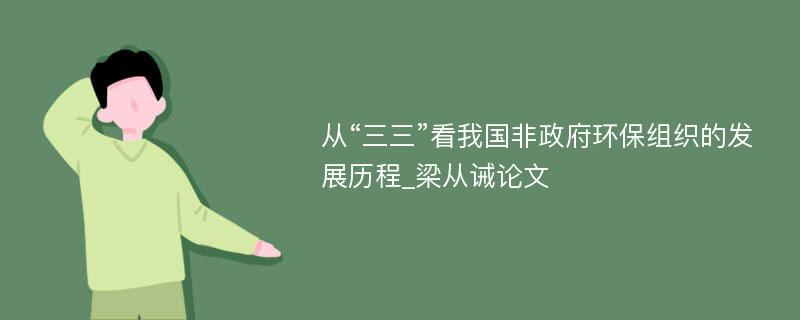
从“三个三”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历程论文,国民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6)03-0040-02
十年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迅速发展,她的发展已不仅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力量,而且正在成为公民社会形成的主力军。对这一宏大的发展历程,笔者仅选择了三个侧面给以浓缩,以期望反映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一、从三个组织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艰难起步
1.梁从诫破天荒创立“自然之友”
1993年之前国际社会NGO(非政府组织)已经大量出现,但国内却对其知之甚少。“自然之友”的发起人之一梁从诫也是从电视上了解NGO,看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在国际社会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大背景下,一群对中国环境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社会精英人士在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和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1993年3月,梁从诫带着草拟好的章程和“绿色环境文化协会”的组织名称来到国家环保局,希望找到一个主管单位。国家环保局拒绝了梁从诫,因为此时环保局下面已经有了一个半官方色彩的“中国环境协会”。之后,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梁从诫。他继续找“婆婆”,继续被拒绝。终于,中国文化书院答应“收留”他们,于是梁从诫又把组织名称改为“绿色文化分院”。当时文化部有关人员疑惑地问,文化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你们到底搞什么?“主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等等。”梁从诫搪塞了过去。带着文化部盖了章的文件,梁从诫终于过了最后一个关口——民政部。拿着崭新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friends of nature”公章,梁从诫感慨万千,为这一刻他奔波了足足9个月。
成立之初,“自然之友”经历了一段十分艰苦的日子,租了一间又小又破的办公室,连买纸的钱都没有。去大学演讲、开讨论会,学校也持怀疑态度,不予配合。就这样,“自然之友”在夹缝中生存壮大。时至今日,“自然之友”没花国家一分钱。经费来源于会费、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私人捐赠,特别是国际大型基金会、公益组织的捐赠。让其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所得到的资金年年递增,至1999年9月30日,已累计为252.6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63万元。而1998年,北京市合法社团的平均收入为26.4万元,远远低于“自然之友”。
2.廖晓义西方取经创办“地球村”
廖晓义,是自然的忠实敬畏者,她一直努力将东西方文化融合起来,用自己的方式在实践东方生态学。
1992年,廖晓义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知道还有一种组织叫做NGO,尤其是环保NGO几乎荟萃了全美的民间环保精英,以女性居多,主要负责监督环保执法,影响力足以撼动美国国会。
廖晓义深受启迪,并萌发了新的想法——采访国际杰出的环保女性并制作成片子,拿到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上播放,让中国有影响力的女性率先投身环保。为此,她罄尽在美国打工积攒的两万美元,采访了40多位国际环保女杰,其中有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主任微尔、《寂静的春天》作者卡逊的朋友等。廖晓义聘请专业摄像师精心制作,给该片取名为《地球的女儿》。这部片子成为中国在“世妇会”民间组织论坛的骄傲。
1995年,从美国回来的廖晓义着手创办“地球村”,那时很少有人理解这个“疯女人”。这时有一个朋友向廖晓义无偿提供了一间房,有了安放理想的栖息地,她注册了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199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这天,曲格平与廖晓义共同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第7套节目18∶50分首播的《环保时刻》。以后每周五的同一时间,廖晓义的声音传到了千家万户: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地球村,因为是非盈利性组织,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一些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除此之外,只有一些企业的零星捐助。
3.扬欣义卖专著成立“绿色江河”
现任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创始人杨欣,从1986年漂流长江开始关注长江源起,便投身于民间环保工作。他曾二十余次进入长江源和可可西里了解那里的生态环境现状,并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义卖他馔写的《长江魂》筹款,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中国民间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启动了来自中国民间的长江源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1998年12月杨欣等人成立了“绿色江河”民间环保组织,全称“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是经四川省环保局批准,在四川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民间团体,在“绿色江河”的努力下,如今,长江源的生态环境和藏羚羊的命运正在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也已基本建成,在协助当地反偷猎的基础上,环境教育和科学考察项目也都在逐步展开。
一位研究中国民间环保的美国人在采访“绿色江河”时惊讶地发现:这个民间组织的经费一半来自国内外组织和企业的捐助以及所获奖项的奖金,另一半则靠义卖自己写的书。
二、从三件大事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影响
1.“联名声援”让政府感觉到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力量
2005年1月21日,56个民间环保组织联名声援国家环保总局叫停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大型建设项目。
2005年1月21日起,各环保组织的网站和《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20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刊登了一封由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绿家园志愿者、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绿岛、北京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绿色北京、绿网等56个民间环保组织联名的声援信。
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司司长牟广丰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环保总局非常感谢民间组织的道义支持。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更多次热情地把民间环保组织称为“同盟军”。
2005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当天,到北京出差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正春偶然到圆明园参观,目睹了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这一“宏伟工程”。张正春认为,对圆明园的天然湖底进行如此严密的全部防渗处理无异为圆明园掘墓。此事件经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和普通民众纷纷对张正春的观点表示支持。正是这种高涨的民间环保意识推动了国家环保总局叫停这个项目,并举行了中国首场环境影响评价听证会。
以独立身份呼吁政府、监督政府的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不断地牵手,这一连串事件引起人们对环保NGO组织未来走向的关注。
2.“约堡+1”让世界听到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
2002年8月26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对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此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环保NGO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并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2003年11月17日,北京,“约堡+1”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论坛召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等均派代表参会,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来自祖国各地的环保NGO的代表,更有一些热衷于环保事业的群众也积极投入其中,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
中国环保NGO已经引起国际关注。北京地球村国际交流负责人赵立建这样回忆道:“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我们的声音是受到关注的。在联合国环境署组织的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计划的圆桌会议上,当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身着唐装起立提问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转头倾听,所有的照相机都开始闪烁。可能我们声音是微弱的,但是世界竖起耳朵在听,因为我们的背后有13亿人,可能我们说话是口吃的,但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强大的,任何人都不能忽视。”
就在“约堡+1”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论坛召开的第三天,第三届中国国际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接踵而至。来自世界各国160多个环境组织的代表、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代表、50多家媒体及其他关心环保事业的人士共计40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
自1999年9月起,每年一届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论坛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环保事业。中国环保NGO已经融入世界环保NGO的大家庭中。
3.“怒江保卫战”让国人看到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能力
2003年8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在中国仅存的两条原生生态河之一——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按方案,该工程比三峡工程规模还大,年发电量预计为1029.6亿千瓦时,是三峡电站的1.215倍。
此次会议后,“绿家园志愿者”、“云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多个环保NGO相继投入到“怒江保卫战”中。这些组织通过媒体和网络,以开展讲座、论坛等形式,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大坝的情况,取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还在2003年“两会”期间,将反对提案提交给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把意见传达至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联盟军的队伍还扩大到了海外。2003年11月底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上,参会的“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与此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也马不停蹄召开了一系列怒江流域生态调研和专家论证会。2003年9月3日、10月20-21日,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在北京和昆明召开两次专家座谈会,以云南本地专家为主的支持建坝派和以北京专家为主的反对建坝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在环保NGO组织的努力下,建设派和反对派的天平不再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项目暂缓实施,怒江的命运终于在国家环保总局和民间环保组织的联手扭转下拐了一个弯。
“怒江保卫战”是中国环保NGO发展的重要拐点。环保NGO组织的意见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此前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活动多局限在环境教育等边缘领域,“放鸟、种树、捡垃圾”老三样,而反对怒江建坝属于公共行动,在世界上也属于NGO活动的前沿领域。
三、从三则新闻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趋势
1.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的讲话表明中国政府希望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环境保护的同盟军
新华网北京2005年3月12日电: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全国环保系统厅局长工作会议上说,“环保总局将支持和引导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的环保事业。”“中国将在两年内建成一个包容全国所有合法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协作网,每年对成员进行业务培训和专业指导,并进一步推动环境信息公开,联合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共同应对中国日趋严峻的环境挑战。”“尽管公众在环保事业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中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处于自发、松散和各自为战的状态,整合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巨大潜能,采取具体措施引导其参与环保,已成为实现全民参与环保的当务之急。”“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环境信息透明化、环境决策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广大环保志愿者和一切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们来共同努力。”
2.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表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正在成为环保第三部门
2005年4月24日中国环境报报道:在北京召开了“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会发言,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国政府向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正式成立表示祝贺。他认为,成立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探索。中央和国务院高层如此重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这是从未有过的。
3.首次中国环保NGO搜索行动表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将会规范化发展
2005年8月2日中国环境报报道:首次中国环保NGO搜索行动日前在京启动。经国家环保总局、民政部等部门同意,受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从即日起到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社社调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搜索环保组织的通讯方式,以建立中国第一个环保NGO信息库——“绿页”,并完成中国第一份环保NGO白皮书。活动还将评选出最具活力的十大环保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