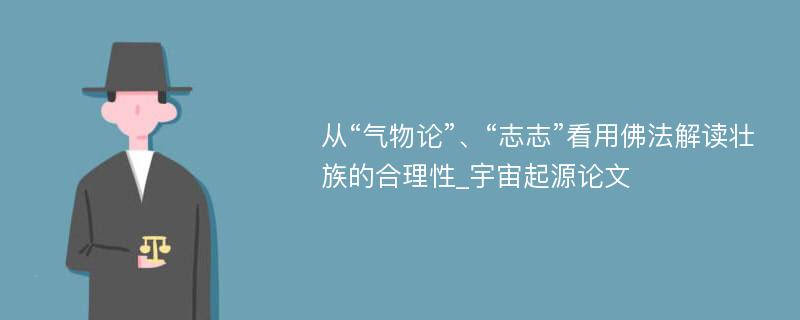
从《齐物论》论“至知”看以佛解庄之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齐物论论文,至知论文,佛解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108-06 一、解读“至知”的四种模式 庄子对“古之人”之“知”的论断①,见于以下一段话: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② 由上可知,“古之人”之“知”是“未始有物”,庄子将“未始有物”置于一个多层次的认知系统之中,在“未始有物”之下,“知”的层次逐渐降低,分别为“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和“有是非”。庄子仅以上述寥寥数语指点这一认知系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诠释空间。对于这段话,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做出了各种解释。概而言之,解释的模式大致分四种,即宇宙论解读模式、本体论解读模式、认识论解读模式和境界论解读模式。 宇宙论解读模式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解释庄子的这段话,采取这种解读模式者将庄子所言“未始有物”、“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视为不同认知水平的人对宇宙起源状态的猜想。详言之,认知水平最高的人——“古之人”认为宇宙的初始状态是“未始有物”,即“宇宙初始并不存在万物”③,认知水平稍逊的人认为宇宙的初始状态是“有物”“而未始有封”,即“宇宙初始存在万物,只是万物之间并不严分界域”④,认知水平更逊一筹的人认为宇宙的初始状态是“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即“宇宙初始不但已存在万物,并且事物之间有分界,只是不计较是非”⑤。陈鼓应先生、马恒君先生等多数庄学研究者均采取这种解读模式。 本体论解读模式的采用者以杨国荣先生为代表。他将世俗之人眼中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设定为非真实的世界,认为在种种假相背后,潜藏着某种真实的存在形态,“对庄子而言,真实的存在首先展现为本然的形态”⑥,这“本然的形态”也就是庄子所谓“未始有物”。在这里,所谓“真实的存在”或“本然的形态”都是指世间万物的本体,换言之,“未始有物”就是世间万物的本体。杨先生进一步解释这个本体说,“未始有物,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而是强调其超越时间上的先后及本体论上的有无之分”⑦,亦即“‘无’任何规定的存在形态”⑧。这就是说,“未始有物”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无任何具体规定性的存在者。杨先生还提出,庄子对存在的如上形态的追溯,“既展示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立场,也表现为逻辑的推论”⑨。这就是说,庄子是以哲学思辨或逻辑分析为方法,而逐步推演出世间万物的本体的。至于“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和“有是非”,依照杨先生的看法,它们虽然也是对于世界的存在形态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是不究竟的,因为它们没有通达本体之域。 认识论解读模式的采用者将“未始有物”、“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和“有是非”界定为由高到低的四个认识的层级,在他们看来,这四个认识的层级仅仅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而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具体言之,“至知是未有,即无;次知是有而不分,只是一种抽象的‘有’;再次是对物作审察区分的功夫,是是非的前提;而最次是对是非得失的计较,这是对‘道’或整体价值的损害”⑩。类似于本体论模式的解读,采取认识论解读模式者,如陈少明先生,将人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迁,视作“思辨”的功用,用他的话来说,“要化有为无,是一种思想的功夫”(11)。不过,尽管陈先生也觉得,“由众有导向纯有,而有与无又相互转化,有指向本体论的倾向”(12),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像本体论模式的解读者那样,认为庄子讲“未始有物”,就是要告诉人们“世界是怎样的”(13);他仅仅认为,“未始有物”是庄子通过将具体事物抽象化的逻辑分析和有无相互转化的哲学思辨而推导出的一种认识上的境相,庄子只是教人们“把世界看成怎样”(14)。这样一来,认识层级的高低就只是反映人的思辨深度的不同,而与客观事实无关了。 境界论解读模式也如认识论解读模式,视“未始有物”、“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和“有是非”为由高到低的四个认识的层级,只是,这四个认识的层级反映的不是思辨深度的不同,而是“修持境界”(15)的差异。思辨仅仅是分析、推理、辨别、审察的思维活动,而修持则伴随着全副生命体验的转化,二者间的张力在两种解读模式的采用者对“未始有物”的解读上有集中的体现。如前所述,陈少明先生认为“要化有为无,是一种思想的功夫”,而牟宗三先生却指出,“无为境界,是无可说、不可思议的”(16),他还说,“‘不可以加矣’,即不能形容,不能思议;故至人其知有所至之至,实是无至之至”,“无至之至,即不以分解的方式至”(17)。“思想的功夫”即哲学思辨的功夫、逻辑分析的功夫,而“不可思议”“不以分解的方式至”则意味着不能采取思辨的方式、分析的方式。“未始有物”是个人修持的最高境界,这是境界论模式解读者的共识,然而,对于这境界是否切合客观实际,在境界论模式的解读者内部却又存在着分歧。牟宗三先生认为,“道家不以客观情调说之,故无存有论的建立,而收摄于主体的感触,遂借喻于古之人”(18),意谓庄子借“古之人”来烘托的“未始有物”境界纯系主观的体验,而并非对外界境况的如实反映。与此致思路向不同的是,章太炎先生以佛家名相阐释“古之人”一段,从而赋予了“未始有物”以存有的意义。章太炎先生称“未始有物”为“无物”,他指出,“无物之见,即无我执、法执也。有物有封,有是非见,我、法二执转益坚定”(19)。我执指凡夫以为包括自我在内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态都是具有实体性的真实存在者,换言之,以为有情众生的身心安立在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不变的实体之上;法执指凡夫以为一切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以为一切事物都各自以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不变的实体为其基础或本质。哲学上的“实体”是一个多义词,这里所谓实体,特指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存在基础的存在者。“无我执、法执”,即已经破除了我、法二执,依照佛家的理论,破除了我、法二执,便能够见证诸法实相,即一切人、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本来面貌便是空。所谓空,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无实体性,亦即在一切人、事、物的背后并不存在着相应的承担者,一切皆是幻相。由此可见,章太炎先生所谓“无物之见”实际上也就是“空”见。这个空,既是佛教徒通过持戒、禅定等修行方式所证成的生命境界,又是世界真相。“未始有物”以下的“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和“有是非”,据章太炎先生所说,则系凡夫因“我、法二执转益坚定”而越发远离真相的“愚妄”(20)之见,这三种见解均偏离了诸法实相,仅仅是不同层级的生命境界。 二、境界论解读模式 以上四种解读模式各有其合理之处,但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加倾向于认同境界论解读模式。理由如下。 首先,庄子认为宇宙起源的问题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基于此,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理解“古之人”之“知”的做法殊难成立。庄子对宇宙起源问题的看法主要见于这样一段话:“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21)庄子采用的是一种“遣之又遣”的方法,在否定的基础上再否定,从逻辑上讲,其对宇宙起源的追溯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换言之,庄子的话讲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和“未始有夫未始有无”并没有结束,依照他的逻辑,还应当继续对“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和“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进行否定,“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之前还应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之先还可以再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无”……庄子采用的方法本身已经向人们昭示了,他认为宇宙起源的问题是说不清的。更何况其后的“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明显是庄子对自己先前说法的质疑,这种质疑也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质疑,在庄子看来,宇宙的初始状态究竟是“有”还是“无”,完全是“未知”的。既然庄子已经明确了宇宙起源的问题不可知,那么他便不可能再以“未始有物”为宇宙的初始状态了。 其次,有关外物、坐忘的寓言表明,对庄子来说,认识层级的跃迁实质上喻示着生命体验的升华,而本体论和认识论模式的解读者仅仅视之为思辨深度的逐步加深,这与庄子本意实难相应。“古之人”一段将人的认识的层级做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排序,而《大宗师》中的两则寓言则由低到高地排列了人的认识层级,这两则寓言,一是女偶教卜梁倚修道的寓言,二是颜回与孔子论“坐忘”的寓言。在这两则寓言中,主人公认识水平逐层提升的轨迹清晰可辨,前者为“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后者为“忘礼乐→忘仁义→坐忘”。这二者与“古之人”一段所展示的认识演进之迹——“有是非→‘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有物’‘而未始有封’→未始有物”,无论在表述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的侧重上,都有所区别,但它们无疑共同表明了,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古之人”一段没有揭示这种改变是何以发生的,而《大宗师》的两则寓言却略示端倪。在第一则寓言中,从女偶闻道后的表现——“年长”“而色若孺子”来看,既然道对人的生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能够变易其心,转化人对自我和外物的看法,而且能够润泽其身,使人返老还童、青春永驻,那么,要领悟这样的道,所需要的也就不仅仅是高超的智力水平,还应包括深厚的生命体验。在第二则寓言中,颜回通过一系列“忘”的活动而最终转迷启悟,“忘”的活动显然不同于分析、推理的思辨活动,彻底的遗忘也不是分析、推理所能够达成的;而且“忘”的最高境界——“坐忘”更是显然有别于古希腊哲人式的沉思,而颇类似于佛徒打坐式的修持。在坐忘的状态下,人已经“离形去知”,即超脱了形体和知识的束缚。通常意义上的“知”,若非来自于感性认识,则必来自于理性认识,庄子否定了“知”,也就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一同否定了。分析、推理的思辨活动属于理性的认识活动,故此,庄子的一句“离形去知”已经标明,在认识的最高阶段上,逻辑、思辨是停止了作用的。在“离形去知”的前提下,人才能够“同于大通”,“同于大通”即“同于道”——“和大道融通为一”(22)。与大道的融通不能仅仅指对道的认识或理解,因为仅仅认识了道或理解了道,道还仍然只能作为认识的外在对象而存在,而不能成为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融通”必须是全身心地认同甚至合一,这就是一种生命体验了。既然认识层级的跃迁等同于生命体验的升华,那么,在从“有是非”到“未始有物”的认识演进过程中,促使人的认识水平逐步提升的也就应当是修持之功,而不是思辨之能。 综上可知,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解读模式均存有弊端。反观境界论解读模式,它把不同的认识层级释之为不同的修持境界,从而免于宇宙论解读模式的诠释困境;而且,它以生命体验的深浅来界定“未始有物”与“有物”“而未始有封”等认识层级间的高低,从而又与庄子在有关外物、坐忘的寓言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保持着协调一致。总之,在四种解读模式中,境界论解读模式最具合理性。 三、章太炎先生的以佛解庄模式 在境界论解读模式中,笔者又更加认同章太炎先生的以佛解庄模式,这主要是因为,庄子的有关论述表明,“古之人”的境界不仅是其对世界的一种看法或感触,而且这种看法又完全符合世界的真实状况,一言以蔽之,“未始有物”既是最高境界,又是世界真相。 庄子在谈论不同的境界时,往往将其与相应境界的人对“道”的体悟或修证相联系,比如,庄子称卜梁倚因“闻道”而渐次悟入“不死不生”,称“坐忘”境界中的颜回能够“同于大通”,称世俗之人的是非之辩是“道之所以亏”的原因。总之,充分地悟道或证道,人才能够达至极致之境,遗忘或损伤道,人的境界则会不断下堕。依前所述,“古之人”之“知”——“未始有物”是最高境界,据此,“古之人”对道的体悟无疑最为彻底,“古之人”已“同于道”。“同于道”对庄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绝对真理或世界真相了然于胸。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庄子的“道恶乎隐而有真伪”(23)的诘问上。世俗之人总会认为某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某些事物是臆想出来的,某些观点是反映现实的,某些观点是脱离实际的,这应当就是所谓的“真伪”之分。这样的真伪之分是庄子所厌弃和否定的,它就像猴子对“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所做的分别一样,完全是虚妄的。“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之说表明,这种虚妄的真伪之分是在大道被遮蔽之后才产生的;倘若大道不被遮蔽,人们便不会做出这样的真伪之分;而只有世界真相清晰地呈现出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才不致虚妄,所以,“道”应当就是世界真相,毋庸赘言,“同于道”者正可一览无遗地看到世界的真相。由此推之,“同于道”的“古之人”,其对世界的看法——“未始有物”就应当是其所看到的世界真相。 庄子还有一些暗示性的话也隐约表明,“同于道”就是洞彻了真理或真相,比如《大宗师》中有关“道”的论述。庄子的“道”是一个多义词,在《大宗师》篇,庄子用这样的语言表征“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即“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24),从道的这一特质来看,它所指称的应当是某种抽象的、高深的道理;庄子还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道,“自本自根”“在太极之上”“在六极之下”“先天地生”“长于上古”,这应当是喻示道凌驾于时间、空间之上,庄子又说,道能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应当是喻示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由此看来,道既永恒存在,又无所不在,这样的一种道理应当就是绝对真理。不仅如此,庄子还较为明确地提出,“夫道,有情有信”,“情”犹实也,“信”者,信验也,这应当是说,“道”这样一种道理与物之实情完全吻合,且能够得到事实验证。总之,《大宗师》篇的“道”论将道诠释成了一个如实反映了世界真相的绝对真理,觉悟或证成了这样的“道”,自然也就明了了绝对真理,认清了世界真相。 最高境界与世界真相之间的同一性不仅以“道”为中介而得以体现,在《庄子》内篇中,这种同一性还隐现在其他一些文字中,比如《应帝王》篇对“至人之用心”的描写:“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将至人对外物的观察体验比作明镜照物,用镜子来鉴照外物,外物自然会如实地映现在镜子之中,在庄子看来,至人之心之于外物同样如此。郭象注“至人之用心若镜”曰:“鉴物而无情”(25),“鉴物”即照物,“无情”喻不加主观偏见,“鉴物而无情”即谓至人之心对外物的反映是客观的;成玄英释“应而不藏”曰:“来者即照,必不隐藏”(26),无所隐藏地映照外物譬喻至人之心对外物的反映是真切的。总之,至人对外物的反映既客观,又真切。至人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至人之“至”在于他的境界至精至纯、至真至上。至人的这种特质正与“其知有所至”的“古之人”相一致,“古之人”所获得的“至”“知”其实就是一种“至”上的境界。因此,“古之人”即为“至人”,“古之人”之心对外物的反映——“未始有物”即为客观而真切的反映。 综上,牟宗三先生的解读与庄子的有关论述不相吻合,相比之下,章太炎先生的解读更为可取。 四、以佛解庄模式的合理性 尽管章太炎先生的解读相对可取,但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文本上的直接证据,用来证明章太炎先生以“空”解“无”——“未始有物”的正当性。即便如此,基于以下三点,笔者仍然认为,以佛解庄乃至以空解无有相当的合理性:第一,庄、佛在世界观上的相近性;第二,庄、佛在修持工夫上的相似性;第三,“未始有物”与“未始有回”在内涵上的相通性。 首先阐述第一点。诸法皆空是佛教徒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与此相关的看法还有缘起、无常等。所谓缘起,是指万物都只是由于各种条件的临时聚合而产生的。正因为万物都只是条件聚合而生的,所以,万物的存在就只是假相,在假相之中,并没有与其相对应的本质或实体,这就是诸法皆空。同时,既然万物都是条件的聚合而产生的,那么万物也就会因为条件的分离而消亡,没有什么事物能够永久地维持某种状态而不发生改变,这就是诸行无常。佛家的上述世界观与《齐物论》中许多文句所体现的思想十分相应,例如“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在这段话里,庄子先是列举了人生的各种情态;继而又以“乐出虚,蒸成菌”为喻说明,上述种种情态完全是无根的、没来由的,这就是“莫知其所萌”。这“莫知其所萌”可以被理解为各种情态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本质或实体:正是由于各种情态都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与之相对应,都是空的,所以它们才不能自始至终地显现于人身,而是“日夜相代乎前”,生生灭灭,流转无常。再如“罔两问景”的寓言,这则寓言可以从缘起、无常的角度加以理解:影子的状态变动不居,无恒常之操守,这是与诸行无常之说相合的。而影子之所以变动不居,是由于它的状态被外在的条件所决定——“有待”,这又完全符合缘起之说。此外,庄子还表示,决定着影子状态的人的状态也是由自身以外的条件决定的,谁都不能够独立自主,这似乎是在暗示,一切人、事、物都被外在的条件所决定,一切人、事、物都是缘起之物。又如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寓言,笔者以为,这则寓言借喻着一种诸法皆空的境界:如果说庄周在梦中的“不知周”,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暂时性遗忘的话,那么庄周在惊奇地发现自己是庄周之后,仍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就应当别有深意了,这恐怕是以怀疑的口吻来表达对实体性观念的否定。用世俗之人的眼光来看,庄周是有实体性的,蝴蝶也是有实体性的,二者都是真实的存在者,所以,二者的界限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可是,庄子却有意地混淆了二者的界限,这应当是暗示,事物的实体性并不存在。事物的实体性不存在,则诸法皆空。 再看第二点。相对于对“未始有物”境界的不置一词,庄子对心斋、坐忘等修持工夫的阐释相对清晰,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其与佛家止观工夫的相似之处。止的梵文音译为奢摩他,指妄念除尽,专注一境,观的梵文音译为毗婆舍那,指在“止”的基础上,观察思维各种事相,以求认清其本来面貌。一般认为,止也就是定或禅定,观也就是慧或智慧,止观之法也就是定慧二学,定慧二学是佛教修持的主要内容。达到定的方法有多种,但总归都是要人把各种妄念排除掉,收摄注意力到一个方面。心志专一、妄念止息,定的这两种特质刚好也表现在庄子“心斋”“坐忘”的修持工夫中。《人间世》篇讲了一则关于“心斋”的寓言,其中提到的“一志”即为心志专一之意;“无听之以耳”意近于《大宗师》篇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喻指摆脱掉感性认识,“无听之以心”意近于《大宗师》篇所谓“忘礼乐……‘忘仁义”“去知”,主要喻指摆脱掉理性认识,“听之以气”则比喻一种空灵的状态,在此空灵的状态中,修持者的一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停止了,这也就意味着妄念的止息。总之,在止或定这个方面,庄子与佛家的相似度极高。不过,仅仅在止或定上相似,并不足以证明庄子所悟的无就是佛家所证的空,这就像禅定是古印度各宗教的共法,但佛教认为诸法皆空,而婆罗门教却相信有最高实体——“梵”的存在。所以,庄子的无是否是佛家的空,关键取决于庄子与佛家的观法是否具有一致性。对佛教来说,将妄念平息下来并不是修行的目的,平息妄念、专一心志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观察思维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而要观察真相、思维真理,就必须在修定的基础上修观,即,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对各种事相或道理进行观察思维。观察思维要依据一定的方法,这就是观法。在这里,笔者不拟对佛教的观法一一做介绍,其原因不仅在于佛教的观法种类繁多、极其复杂,有限的笔墨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在于庄子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明确的观法,其与佛教观法之间的比较无从进行。在关于“心斋”的寓言中,“虚而待物”意谓空虚而能够容纳外物,这似乎是在暗示修持者在妄念除尽之后,方能以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观察识别外物;“唯道集虚”表明空虚之中含藏着道,道有绝对真理的含义,这“唯道集虚”之说似乎意味着修持者在止的状态下,方能对绝对真理进行思维、省察。这也就是说,庄子似乎也认为,止后还要起观,不过,究竟要如何观察外物、思维真理,庄子却没有明说。由此看来,从观法上找出庄子与佛家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庄子的修持工夫至少与佛家相似。工夫相似,则境界便存在一致的可能。“定生慧”,修习禅定者可以在定中以智慧观察事相,从而最终契入诸法空相;“虚室生白”(27),空灵状态下的修持者也可能凭借类似的智慧,证成类似的境界。 最后说明第三点。“未始有物”与“未始有回”存在两个共同点:其一,二者的表述方式完全一致,这一点一目了然;其二,二者都是修持而来的境界。“未始有物”是修持境界,这一点前文已述,兹不赘言;在关于“心斋”的寓言中,颜回提到,他是在实践了“心斋”之法后,才达到“未始有回”的状态的,这显然也是一种修持境界。既然这二者具有如此重要的共同点,那么,厘清“未始有回”的含义,对理解“未始有物”自然有莫大的助益。“未始有回”的含义不难厘清,这是因为,“未始有回”是颜回自己言说自己的存在状态,既然如此,那就可以排除对“未始有回”的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颜回认为自己完全不存在;第二,颜回忘记了自己是谁。因此笔者所能想到的唯一一种解释就是佛家意义上的空,具体言之,“未始有回”指的是破除了我执的我空境界,即打掉了对于自我的实体性的执着,认识到自我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者。基于“未始有物”和“未始有回”在表述上和实质上的共同点,笔者认为,这二者在内涵上也应当是相通的,具体言之,“未始有回”之说从自我存在的真实与否的角度着眼,否定了自我的实体性,即破我执,而“未始有物”之说就很可能是从万物存在的真实与否的角度着眼,否定了万物的实体性,即破法执。这也正是章太炎先生所给出的结论。 由于《庄子》语言的隐喻性、暗示性,庄子的本意难以为人所知,由此而形成了庄学诠释史上歧见纷纭、千人千解的局面。然而,庄子的本意虽不为人们所知,我们却可以尝试着接近他的本意,接近庄子本意的最有力抓手应当是《庄子》内篇的文本和逻辑。在对“未始有物”的解读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佛解庄的结论不仅与《庄子》内篇在文本和逻辑上不相抵牾,而且十分相洽。这一个案启示我们,历史上支遁、释德清、章太炎等人以佛解庄,虽不免附会之处,却仍有其合理性;对于这一解庄传统,学界仍需重视。 收稿日期:2015-09-22 注释: ①在《庄子》杂篇的《庚桑楚》中,亦有一段论及“古之人”之“知”的文字。不过,鉴于学界普遍认为外杂篇系庄子后学所作,故笔者对庄子论“古之人”之“知”的研究,仅从内篇的《齐物论》着手。 ②(21)(23)《庄子·齐物论》,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 ③④⑤(22)(2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第79、79、79、228、201页。 ⑥⑦⑧⑨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55、54、54页。 ⑩(11)(12)(13)(14)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3、24、118、118页。 (15)(16)(17)(18)牟宗三讲述、陶国璋整构:《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第111、111、111、114页。 (19)(20)章太炎:《齐物论释》,刘凌、孔繁荣编校:《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25)(26)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第314页。 (27)《庄子·人间世》,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标签:宇宙起源论文; 齐物论论文; 庄子今注今译论文; 文化论文; 寓言论文; 大宗师论文; 庄子论文; 章太炎论文; 坐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