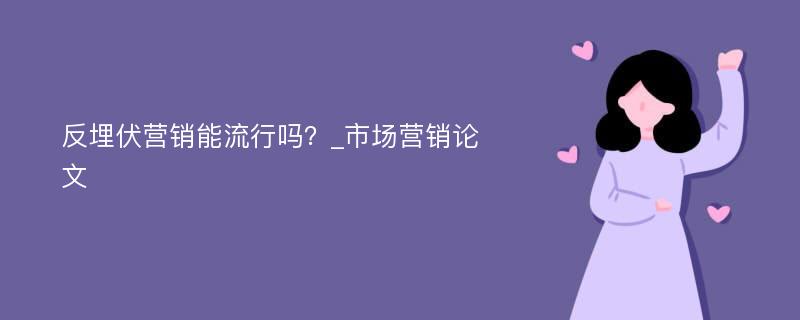
反埋伏营销能否大行其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行其道论文,埋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口可乐是1980年第22届奥运会官方赞助商,然而其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在开幕前两个月便在各比赛场地竖起大面积广告宣传牌,并在多处地方设点推销,在运动会期间向各国运动员和大会工作人员散发赠饮券,给获奖运动员赠送纪念品,又多次举行酒会招待各国运动员及名流贵宾。结果,其借奥运会宣传的效果超过了可口可乐,其间盈利比可口可乐超出约1/3。
北京2008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愈行愈近,埋伏营销会否大行其道?赞助商该如何对其进行有力阻击?
高门槛儿低围墙——怎能不埋伏
就以2006年德国世界杯为例,“国际”赞助商有权通过世界杯赛事来独家宣传和销售企业的系列产品。国际足联从每种商品中选择一家生产企业作为赞助商,总共有15家企业最终与它签订了合同,但门槛儿高得惊人——赞助金额为6000万欧元。
联想成为奥组委TOP计划成员付出的是6500万美元的高昂代价,而这仅仅是获得赞助资格的费用,联想还必须另外预算一大笔广告费去传播作为TOP成员的产品、品牌以及企业形象。
高额费用让相当数量的企业望而却步,转而寻求其他途径“搭便车”。这种搭便车的营销活动并没有得到组委会认可并支付相应费用,无疑是对组委会和正式赞助商利益的一种侵害。而中国现行法律对于埋伏营销没有明确、直接的规定。上海世博管理局为了保护世博会的标志,专门出台了《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但是,这些规定仅是对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补充,并不能有效针对埋伏营销。
但也并非完全无法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些法律上的“兜底”条款严格说也是可以适用到埋伏营销之中的。只是,在中国现有司法环境与人员结构条件下,完全依赖于一般条款进行判案并不合适。
软挤压硬法条——手段难拿捏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
首先需要认清的是,埋伏营销是无法根本性杜绝的。埋伏营销方式多样,按照一些学者的总结,包括活动模仿、直接拦截、暗渡陈仓、搭便车等等方式,让活动主办方防不胜防。但是,对于一个大型活动而言,即便不能完全禁止,只要能够很好地限制埋伏营销的空间,其实也足以让活动成功举办,这有赖于活动主办流程安排。
可以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流程来认识一下世博局的招商工作。招商工作可以分解为两个过程:获得授权与进行授权。首先,包括世博会在内的大型活动,如足球世界杯、奥运会、亚运会等,实际上都是垄断性活动。世界杯、奥运会每4年一次,并且只有一个法定机构可以进行运作。活动的主办方获得这种活动主办的垄断地位之后,就可以通过收取赞助费的形式,将这一垄断地位再卖给各大厂商,让赞助厂商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垄断地位,并依靠这种垄断地位创造超竞争的利润。这也就必定吸引赞助商的竞争对手追逐这一利益。这是各种大型活动埋伏营销无法禁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是活动主办方的垄断性权利,而组委会实际上需要得到的授权不局限于此。作为活动主办方需要得到的一系列权利可以包括:场馆的经营权、相关标识许可的权利、转播整个活动过程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的范围、大小是决定世博会商业价值最为直接的内容。因为这些权利的获得一方面表明了赞助商可以从中得到的权利,同时也决定了埋伏营销可能采用的方式与可能获得的收益。
在可乐大战事件中,如果活动的主办方获得了比赛场地的垄断性权利,使得只有作为赞助商的可口可乐才能在比赛场地竖起广告宣传牌,则百事可乐就无法通过这一方式来实施埋伏营销。因此,只要主办方得到足够多的授权,埋伏营销的空间便会受到压缩,赞助商的利益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其次,世博局要将其获得的授权经由一定的程序再授权出去,也就是指定赞助商的过程。虽然世博会本身并不是一个赢利活动,世博局也不是一个营利机构。但是,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商业赞助,无疑可以极大地缓解资金问题,将世博会办得更好,拓展世博会影响。而再授权的价格——也就是赞助能否得到赞助商的青睐,取决于活动的主办者能够得到多少授权。当活动的主办方出售的“包裹”内容丰富时,必然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如果囊中羞涩,则温饱也无法解决了。
对于活动主办者来说,获得授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合同谈判的方式得到各种授权。例如,与独立的场馆经营者达成协议,获得场地的独家使用权;与电视台合作,独占电视台的广告时段;或者与酒吧协商,得到在酒吧内的排他性权利,与活动的合作伙伴无关的一切行为都予以禁止等等。另一种形式则是通过立法游说,颁布法令而直接获得相关的授权。
如澳大利亚政府曾在《澳大利亚2000年悉尼奥运会法案》第67、68节中分别对某些空中广告和以营利为目的的节目制作与传播予以禁止,最高处罚金额达到250000澳元。伦敦成为2012年奥运会东道主后,英国政府欲颁布法案以减少埋伏营销的发生。据称该法案禁止对奥林匹克字样及奥运五环标志进行任何非官方的使用和贩卖,并在原奥林匹克规则上追加条款,除了“金、银、铜”等容易让人联想到奖牌的词语外,连奥运的宗旨“更快、更高、更强”等语句也受到严格的使用限制。这些法案的推出,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主办方获得权利的成本,提高了活动的商业价值,将更小的埋伏营销空间留给竞争对手。两种形式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私”与“公”方式的区别。第二种形式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活动主办方在一些领域无法通过合同谈判的方式得到授权,例如要禁止打着广告的飞艇通过体育馆上空,就无法通过一般的商业谈判予以实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可以大大节省谈判成本——因为一立法,主办方就自然而然得到了权利。
中埋伏因失误——保护需有度
实际上,过分保护对赞助商也无好处。这往往意味着更加高昂的赞助费用,而成本的提高,一方面让厂商无法再在相关广告上有效支出,给埋伏营销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也让厂商收回成本成为难题。奥运会的赞助商和广告是分开的,获得赞助之后仍然要支付巨额费用来打广告,当赞助商因为自己的广告不到位而让竞争对手埋伏时,实际上是其自己在营销上出了问题。
事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埋伏营销并不意味活动对于赞助商没有商业价值。在权衡制止埋伏营销所需支付的成本与获得的利益之后,只要埋伏营销的负面影响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则活动的价值仍然是可以得到认可的。而对于世博会来说,获得立法的支持,是将取得授权的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的有效而必要的方式,但立法授权的范围必须有效地予以控制。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世博会带有很强的公益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公共产业所必然具有的“外部性”也体现出来。因为要求立法确保商业利益而完全扼杀埋伏营销,也会让世博会失去被更为广泛传播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