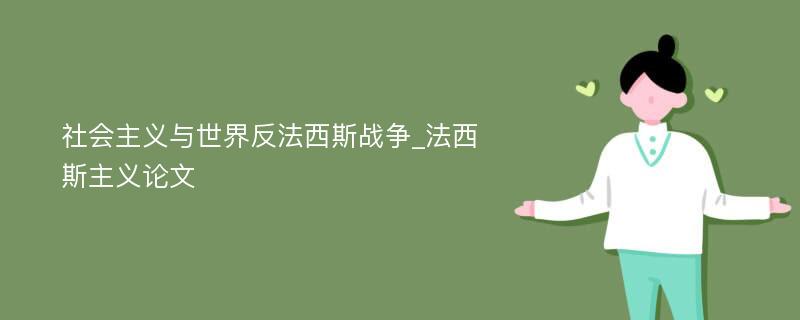
社会主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法西斯战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已半个世纪了。时间激流对它的冲刷,时代风云对它的拂拭,使得这次大战的那些最引人注目、最发人深思、最催人警醒的部分,格外清晰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其中那些在火海里、在血泊中冶炼浇铸出来的沉痛的启示,人类将永志不忘。
一、一次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易制止的”战争,为何竟变成“非打不可的”大战?是历史捉弄,还是“恐共病”作祟?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中,有两个耐人寻味的说法:这次大战,是一次“非必要的战争”;可以说,“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制止的了”。
乍一看来,两个说法都还在理,细思索却颇有疑义。众所周知,酝酿这次大战的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全面危机的冲击之中。伴随危机的扩展和深化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猖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的日趋尖锐;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对抗的日益激化。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两种态势。我们先从被矫饰、被曲解较少的第二种态势讲起。大战全面打响的前夜,相继发生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人民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入侵;西班牙人民抗击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叛乱,抗击德、意法西斯为支持这一叛乱的武装进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进攻的焦土抗战和敌后挺进。这一个又一个的战斗,打得十分英勇、极其壮烈,有的战场辽阔,使敌人难以自拔。但就与全球法西斯力量对比来说,悬殊很大,难以制止或推迟大战的爆发。再着重说说假象、认识误区较多、莫衷一是的说法较多的第一种态势。那些曾在瓜分殖民地时捷足先登而占了大便宜的国家,为保既得利益强调矛盾可以缓解,大战并非必要;那些自认为在瓜分殖民地中滞后一步而吃了大亏的国家,则声言矛盾无法缓解,大战非常必要。一边不想打,“和为贵”;一边想打,“打为高”。不想打的国家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想打的国家,它们只要下决心,使大劲,不耍权术,不玩花招,是有可能遏制对方的扩军备战,制止,至少是推迟大战的爆发。可是这种可能性没有转为现实性,大战最终还是爆发了,而且是提前爆发了。丘吉尔不无遗憾地承认:一次“非必要的”、“易制止的”战争,竟成了“非打不可的”战争。而且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破坏最烈、伤亡最重、最残酷、最悲壮的战争。
事情为什么会闹成这样?是历史老人的捉弄,还是某些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的自我捉弄?在丘吉尔看来,这次既“非必要的”又“易制止的”战争所以变成“非打不可的”战争,原因是英国“太诚实”、“太忠厚”;“英语世界 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听任恶人重整武装”。这种背离事实的说法太离谱了。事实很清楚:听任恶人重整武装,甚至帮助恶人扩军备战;听任恶人今天偷袭这个地区、明天攻占那个国家,甚至帮助恶人逼迫受害者低头就范;听任恶人对奋起自卫的国家肆虐,对苦战中的军民冷眼旁观,不但不帮忙,反而帮倒忙;听任恶人在“反共”的幌子下到处为非作歹、倒行逆施,而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者、左派社会党人和进步人士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紧急呼吁则当成耳边风,甚至以冷落、奚落这方面的任何倡议以换取法西斯魁首的好感。这种种令人心寒的表现,仅仅用“太诚实”、“太忠厚”、“好心肠”能说明得了吗?其实,这全是那些患“恐共病”的列强纵容、支持的结果。
这次大战的酝酿期间,美、英、法等国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苏联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突破性的胜利,与正陷入大危机泥潭中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较,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吸引力。二是德、意、日等加速法西斯化的国家的咄咄逼人,或威胁要凭借武力夺取“生存空间”、“占有全世界”,或叫嚣要不惜代价重建“新罗马帝国”,或扬言要运用铁腕确立“大东亚新秩序”,暴露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蓄谋。在美、英、法当权者的心目中,来自左的方面的挑战,是环绕根本制度提出的挑战,是谁战胜谁的生死问题;而来自右的方面的挑战,则是自家人之间的权益再分配的问题,是谁活得更宽裕、更舒畅的问题。使它们忧心如焚的是左的方面的挑战,至于右的方面的挑战一时还成不了大气候,构不成严重的威胁。一句话,根深蒂固的“恐共病”使它们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和仇恨大于对法西斯的畏惧和仇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的既定方针是扶植法西斯主义以遏制进而消灭共产主义。具体说来:用德、意这股祸水去祸害欧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和一切进步力量,同时,“祸水东引”,摧毁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主要的根据地;用日本这股祸水去祸害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和一切进步力量,同时“祸水北引”,与欧洲那一大股祸水配合,夹击社会主义的苏联,并由此导演出“慕尼黑阴谋”、“东方慕尼黑阴谋”。很显然,这些都有其深刻的根源,而不能简单地仅仅看成是个别人物的个人罪孽的产物。的确,把纳粹的眈眈虎视从英、法身上引开,唆使德苏互相厮杀,待其两败俱伤,自己再出来收拾局面,英国前首相张伯伦是这套“谋略”的主要设计者。“只要我们能和德国人坐在一张桌子边,用铅笔对他们所有的抱怨和要求圈划一遍,整个紧张局势就能大大缓和。”②这个奇谈怪论也的确是出自张伯伦之口。然而,这样说、这样主张的在英、法、美的权贵中大有人在。丘吉尔也曾以内阁大臣身份多次声明:对于英国唯一的政策是同德国结盟。他说:“使德国在东界方面有较大的满足,这个念头,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断过。”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艾伦也说:美国的政策是要把德国扶植起来,允许德国向东扩张,“我们预料这样做一定会造成德国同俄国发生冲突,其结果会大大削弱德国在西方的势力。”④美国前外交部长哈·伊克斯则在《秘密日记》中写道:“英国对希特勒奴颜婢膝,害怕共产主义”。⑤真是一言说到要害。
英、法、美等国的当权派由于“恐共病”作祟而搞什么“慕尼黑阴谋”、“东方慕尼黑阴谋”,正中德、意、日等国的下怀,为其所用。希特勒极力投其所好,不仅叫嚣“反对马克思主义”、“根除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在《我的奋斗》中宣告:国社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方突进,俄国必须从欧洲国家名单中划掉。”对这样“难得”的反共急先锋,美、英、法当年是奖赏有加,竭力扶植。为此,推出了“道威斯计划”(1924年)、“罗加诺条约”(1925年)。英、美资本用于恢复开增强德国军事经济潜力和强化军队的存款达200亿金马克。德国为实现经济军事化而得到的外债总额超过310亿金马克(当时应付的赔款只有110亿金马克。在1932年洛桑会议以后,实际上已免付赔款)。德国军事经济所需的原料和物资约50%得自英、法、美三国及其控制的地区。美、英、法等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格外积极。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英国石油大王载特林、法国军火康采恩施奈特-克勒佐等都是希特勒的主要施主。希特勒为报答福特早在1922年给予他的30万美无的赏赐,特颁发给他最高等级的法西斯勋章。
对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美、英等国也同样采取“绥靖”政策。正当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亚边境运兵,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中立法,禁止把武器卖给交战国家,这等于拒绝帮助阿比西尼亚。战争打响前几个月,墨索里尼让大使向英王传递口信,请英国对意大利即将在阿比西尼亚采取的行动表示最友好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表示:“对意大利友好并帮助它,一向是英国政府的目标”⑥,暗示意大利可以放手进攻阿比西尼亚。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美国国务院竟主张国际联盟应给日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安全感”,不仅不要制裁日本,还必须“为日本保障原料和市场”。美国说到做到,据日本官方统计,美国对日军需品贸易占其全部对日贸易的比重在1937年为33.5%,以后逐年增大。仅1937年上半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钢铁,废钢就达130万吨。“7·7”事变后一年,美国运往日本的军事战略物资竟达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华盛顿邮报》在1937年8月29日的报导中承认:“美国的废钢铁在远东起了可怕的作用。日本用它在降血雨。枪炮、炸弹、军舰都是用旧金属制造的。”⑦这些令人发指的“绥靖”,目的都在于或把亚洲那股祸水北引,或把欧洲那股祸水东引,以淹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淹杀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和革命力量,以实现其“铲共”、“灭共”的宿愿。
在英、法、美等国的一再“绥靖”、多方扶植之下,德、意、日的军事力量膨胀,侵略的胆量加大,主宰世界的胃口扩张。还以德国为例:飞机产量在1932年只有39架,到了1935年年产量就猛增至3183架,1939年年产量又翻了一番多,约7300架。空军在1933年已训练好飞行员2500人,至1938年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已达33万8千人。陆军,按凡尔塞和约规定,数目不得超过10万人,可是大战爆发前夜常备军有60个师,约85万人。海军,在英德海军协定签定前,德国舰队仅有78600吨,到了1939年,德国已拥有2艘战斗舰,3艘万吨级钢甲舰,2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22艘驱逐舰,20艘鱼雷艇,32艘扫雷艇,35艘近海潜水艇,27艘远洋潜水艇,17艘快艇,其全部装备,是当时第一流的,成为一支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
德国法西斯秉性如此:如果它的军事实力膨胀四分的话,那么,它的侵略胆量至少也得加大到八分。当德国在1936年3月间进军莱因非军事区时,色厉内荏的希特勒提心吊胆。事后他说过:“在进军莱因兰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因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⑧但是,拥有一百个师兵力的法军按兵不动,未作任何反应。英政府则忙于表示理解,洛提安勋爵认为:“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⑨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说:“幸而,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德国目前的行动有引起敌对行动的危险。”⑩这一切既使希特勒喜出望外,庆幸自己铤而走险得手,又使他从“恐共病”患者的心态行为中得到启发,再来几次走险又何妨。继续走险,走向何方?结论是:你搞“祸水东引”,我搞“声东击西”。因为布特勒自身也染上“恐共病”,视奉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苏联为硬,视奉行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英、法、美为软。“雷公打豆腐,挑着软的欺”。就近、就软,先动手收拾法、英。希特勒认定:“在数年之内将首先对付西方,然后再对付东方。”“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11)进军莱因非军事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口喊向东、向东的德军,铁蹄却是向西、向西。英、法眼睁睁地看着祸水西灌,绥靖政策破产,德军大军压境,只得全国紧急总动员,仓惶应战。这样一来,“非必要的”、“易制止的”战争,不但没能制止,不但没能推迟,倒是提前全面爆发,成为“非打不可的”大战了。事情闹成这样,怪谁呢?作为当时拥有制止战争或推迟战争全面爆发实力的美、英、法的当权者,如有自知之明,自责之德,理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恐共病”给人类造成的重大祸害。正如前苏联外交家安·葛罗米柯所说:“他们冒然试图在法西斯瘟疫流行期间寻欢作乐,想去出席追悼第一个、也是他们所希望的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亡灵的酒宴,甚至叛卖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将其推向深渊,而想首先把苏联推到深渊的边缘。”(12)然而事与愿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中有些人挨砸即瘫,再也站不起来,为历史所淘汰。有些人忍痛奋起,基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既得利益不受法西斯损害的立场,着手纠正错误的国策,并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联苏”、“联共”,参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总算也还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做了一些有益的、应该写上一笔的事情。
二、这次战争的性质、进程、结局空前复杂,并存竞争的两种社会制度在大战中的相互关系极其微妙,历史在特定的环境里以特殊的方式再度昭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人类。
在20世纪的上半期,竟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大战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条件下发生的。第二次大战则是在“一球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的条件下爆发的。两相比较,既有类似之处,又各有各的特色。就战争的性质讲,一个简明,一个复杂。前一次大战的作战双方,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是为争夺或为保持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战,打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争霸战。其中,被卷入战争旋涡的一些弱小国家和民族,拿起武器是为了反侵略、反奴役,但这种义战只构成战争整体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改变不了整个战争的性质,甚至连局部质变也谈不上。后一次大战,就英、法、美和德、意、日作战双方的国策来说,为争夺或为保持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战的成分仍占据主要的位置。但英、法、美三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和勇气参战,则带有明显的反法西斯性质。就这次大战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日战场来说,中国举国上下抗击日本的亡国灭种的入侵,则完全是大义凛然的反法西斯义战。再就这次大战作为欧洲主战场的苏德战场来说,社会主义苏联全国军民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为保卫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为战胜德国纳粹的亡国灭种的进犯,同样是大义凛然的反法西斯义战。于是,在这次大战中,出现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广泛而密切的交织。这是前一次大战无法比拟的。就战争的进程讲,帝国主义争霸战这种色彩与人民反法西斯义战这种色彩并排或交错出现。时而这种色彩浓一点、突出一点,时而那种色彩浓一点、突出一点。从阿比西尼亚人民抗意之战,到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的抗德、意之战,再到中国人民抗日之战,反法西斯义战的色彩越来越浓烈,越来越突出。然而,当英、法向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全面爆发,这霸与那霸、老霸与新霸在西欧大打出手,帝国主义争霸战的色彩又显得浓烈、突出,颇有淡化、掩盖人民反法西斯义战色彩的趋势。到了苏德之战打响,反法西斯义战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水平。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蓬勃发展,西欧、东南亚等敌占区的人民抵抗运动和人民游击战争的浩大声势,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准备反攻阶段再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胜利实现等等,更是加大了反法西斯义战在这次大战中的比重,从而淡化、掩盖了帝国主义争霸战的色彩。就战争的结局讲,两次大战都出现过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催生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历史事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烈火中,胜利的俄国十月革命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新生的但还比较嫩弱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开始老朽的但仍有相当稳固根基的资本主义制度,几经较量,大体是打了个平手,双方都取得了各具特色的“相对稳定”,出现了一球之内两者并存竞争的局面。与上次大战相比,这次大战的结局,就坏事变好事而论,具有更多方面、更为丰富的内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欧洲、亚洲的一些地区和国度深化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革命催生的新社会制度,已不是胜利的十月革命后那种“一枝独秀”,而是东欧数国、东亚数国人民相继翻身解放的“一片锦绣”。这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由一国胜利的阶段进展到多国胜利的新阶段。此乃一大特色。另一大特色是:作为这次大战的战胜国,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满想重温上次大战后的美梦,“凯旋”并继续管辖原有的殖民地附属国和扩张势力范围。然而美梦破碎了,战后民族民主运动如春潮澎湃,民族民主国家相继建立,殖民体系彻底瓦解。这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与上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社会主义潮流相伴而行,蔚为壮观,举世瞩目。
这次世界大战在性质、进程、结局等方面具有这种种特色,有其多种多样的缘由。亟需深一层考察、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球之内并存竞争的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它们在战前(前夜)、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极其错综复杂和颇为离奇微妙的相互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是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列宁清醒地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郑重地告诫俄国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3)并且科学地判明:“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4)基于这一科学判断,列宁确立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以及一切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原则。
列宁逝世后,这些思想原则和方针,得到了坚定不移的贯彻。当德、意、日法西斯迈出征讨世界的最初步伐,公然践踏国际法、蹂躏“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原则时,苏联立即作出明确的反应,提出一系列直接间接有助于约束法西斯的侵略行径、维护世界和平的措施。它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出全面彻底裁减军备的方案,继而又提出关于对侵略一方(侵略者)下定义的宣言草案,这种种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苏联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重申自己坚持各国人民和平相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的原则,力求实现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经济合作。可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对此依然置若罔闻。眼看法西斯对世界和平、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日益严重,苏联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进而又强烈呼吁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时,英、法、美的“恐共病”者想的是如何东引、北引“祸水”的问题,德国纳粹主义者想的是如何“声东”以“击西”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想的是如何“声北”以“击南”的问题。英、法、美关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安全问题,哪有心思去过问什么“集体安全”、什么“统一战线”。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走一条迂回曲折的抗击法西斯之路: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达到击破“祸水东引”阴谋的政治目的;建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达到挫败“祸水北引”阴谋的政治目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15)
事情很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苏联、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以及团结在它们周围的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法西斯是威胁人类文明、危害社会进步、破坏世界和平、敌视共产主义、挑动民族仇恨的主要危险;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应统一行动反对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应联合奉行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制止奉行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侵略、掠夺,制止它们把新的世界大战强加给人类。可是,英、法、美的当权者却视此为异端,并把在特定的条件下本来可以成为难得的盟友的苏联当成仇敌,力图“借刀以杀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则推行了颇象“攘外必先安内(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政策,弄得嫁祸者得祸,借刀者几乎被杀。大敌当前,社会主义苏联以联合抗击法西斯为重,力争同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由可能变为现实。而对已成为人类公敌的德、意、日法西斯则是武器批判加思想批判。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在最后战胜法西斯主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保卫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帮助了英、法、美等国家,也保卫了人类的文明成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特定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起了支援、维护受到法西斯主义严重威胁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社会主义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抹煞不了的。丘吉尔说:“敲碎德军骨头的是俄国人”(16);“与英国和美国的巨大资源相比,尤其是与俄国的巨大努力相比,我们所实施的一切战役规模都是不大的”(17)。罗斯福说:“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很难抹煞这样明显的事实,就是俄国军队所消灭的敌军士兵和武器数量,比联合国中其他25个国家所消灭的敌军总数还多”(18)。乔治·凯南(美国驻苏大使)说:“当1939年夏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欧洲上空时,西方政治家的困难和处境是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的。当时,除非取得苏联的帮助,要战胜德国是毫无希望的。”(19)仅此三段话,就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佐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确确实实帮了奉行自由主义的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忙,甚至可以说,救了它们的命。如果再加上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保卫人类文明成果的贡献,对维护社会进步的贡献,那么,可以说,历史再次昭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人类!
历史一再昭示的这一伟大的真理,并不因为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而褪色,并不因为苏联东欧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而消失。可以相信,再过五十年,当人们隆重庆祝战胜法西斯一百周年时,这个伟大的真理定将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辉。
①参见《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伦敦,1962年英文版,第513页。
②⑥⑦(11)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93、63-64、26、111页。
③④转引自《祸水东引话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页。
⑤哈罗德·丁·伊克斯《秘密日记》,1954年纽约版,第2卷,第574页。
⑧⑨⑩《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威廉·夏伊勒著),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卷,第412、413页。
(12)安·葛罗米柯:《为了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演说和论文选集),莫斯科,1978年版,第98-99页。
(13)(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67页;第42卷,第33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3页。
(16)摘自德新社汉堡1995年3月20日电。
(17)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51年版,第4卷,第613页。
(18)摘自1955年11月25日《纽约时报》。
(19)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标签:法西斯主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