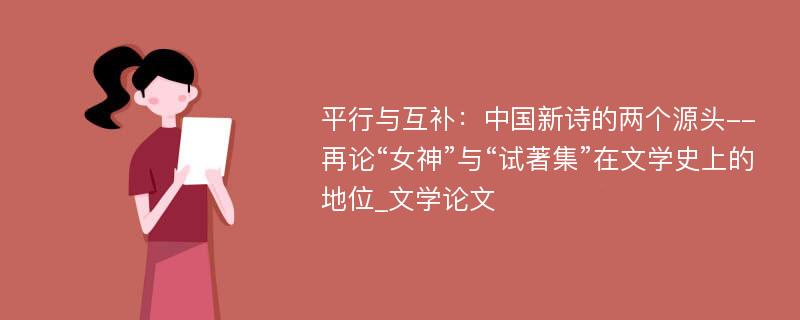
平行与互补:中国新诗的两大源头——重评《女神》与《尝试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两大论文,史上论文,源头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女神》和《尝试集》进行比较研究时,人们常常面对着一种困惑:《女神》的艺术价值和对中国新诗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尝试集》,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但从出版时间来看,《女神》在《尝试集》之后,那么新诗的“开山之功”就只能归于《尝试集》。同样郭沫若在新诗创作方面只能算作胡适的“响应者和追随者”。尽管这一结论与实际的阅读感受及文学史上的发展状况难以吻合,研究者也想出了种种办法来为《女神》辩护,如把它称为“奠定我国新诗的基础”、“开一代诗风”(刘元树)的“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周扬)等等,但由于出版时间这一“铁证”无法改变,人们也就很难修正这一成为史界共识的结论。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对《女神》和《尝试集》进行比较研究,以便重新认识这两部诗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认为,《女神》和《尝试集》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和前后相继的关系,它们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平行发展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两大发展源流——抒情的浪漫主义和说理的写实主义;从创作过程看,郭沫若不但不是胡适的“追随者和响应者”,而且是作为胡适的否定者出现的。过去学术界对这两部诗集哪个是“第一”的争论,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因为这两部诗集根本不在同一跑道上,并且有着各自的起点,所以把他们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安排座次,那是徒劳的行为。从史的眼光来看,《女神》与《尝试集》之间存在着对立与互补关系,它们就像两个支架一样,支撑起了新诗的第一座殿堂。也正是这种互补关系,显示出新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有了一个极为稳定的内部结构。
如果单从出版时间上看,《尝试集》初版于1920年3月,《女神》初版于1921年8月,《女神》比《尝试集》晚一年多。但出版时间并不代表诗歌的创作时间。《女神》在出版以前,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已公开发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诗歌的创作时间来看,胡适的第一次“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是1916年7月22日。由于他提倡白话,喊出“文学革命”的“狂言”遭到他的朋友梅觐庄的反对,为了“和他开开玩笑,所以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答他”。[①]这首“一千多字”的白话诗其实是一篇“顺口溜”,胡适称其为“打油诗”,是有自知之明的。这首诗引起他两位朋友(任叔永和梅觐庄)的极大不满。为了证明白话可以作诗,这年的7月26日,他下决心“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②]开始了一个白话诗人的创作历程。同年8月,作《朋友》一诗,表达单枪匹马的孤独心情,后改名为《蝴蝶》。《尝试集》出版时,《蝴蝶》成为首篇。但胡适并不孤独,当他在美国吟完“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不久,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死的诱惑》,随后又创作了《新月》、《白云》等,这些诗后来都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死的诱惑》并被译成日文,发表在大阪的一家日报上,得到厨川白村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③]这说明郭沫若的初试之作,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女神》初版时《新月》和《白云》合为《新月与白云》和《死的诱惑》一起成为《女神》的重要篇目。因此可以说,胡适和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胡适是一位自觉的诗人,他从事新诗创作是为了证明白话作诗的可能性,是其“文学革命”活动的一部分;相反,郭沫若是一位自发的诗人,他从事新诗创作没有丝毫的文学或社会功利目的。只是因为他那时正在与安娜恋爱,初恋的甜蜜与分离的痛苦使他不能平静,加之他自幼爱好文学,诗歌自然就成为他倾吐内心情感的方便之门。郭沫若有着很深的古典诗词素养,到日本后也一直没有停止写文言诗歌,那为什么这时突然想到用白话写诗呢?我想这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对民间歌谣的迷恋。民间歌谣一般是口语,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郭沫若对此一直情有独钟。他六岁时主动要求进家塾读书,一个主要原因是“一则母亲口授的唐诗(按——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歌谣)‘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的情景令人神往;到日本后,“对当地民间歌谣颇感兴趣,很爱唱《待康晓》,进入大学后还时常挂在嘴角。”[④]民间歌谣在古典诗词之后为郭沫若开辟了新的诗歌园地;二是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诗歌的自由体形式及其清新明快的风格,给郭沫若留下很深的印象,并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年以后,郭沫若回忆自己的作诗经过时,仍对初读泰戈尔诗歌的那份激动难以释怀:
民国四年的上半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从学校里带了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回来,是英文的课外读物。我拿到手来看时,才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The Crentmoon)上抄选的几首。是《岸》(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和其它一两首。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⑤]
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首次面对泰戈尔诗歌的那份欢娱会对他由创作古典诗歌走向白话诗歌起决定性的影响;三是黄遵宪及近代诗界革命的影响。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祧之祖”。他们提出的白话文运动、提高小说地位的口号,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在诗歌方面,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体现了“诗界革命”的实绩。他提出的“我手写吾口”的口号,对五四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郭沫若在谈到黄遵宪时说:“黄公度可以说是近代的大诗人,他的诗我大概都已念过。”并把黄遵宪与陶渊明、王维并举,列为最喜欢的诗人之一。[⑥]可见他并不以黄遵宪诗歌的口语化而有所鄙薄,也许在他看来,只要是好诗,用文言或白话并不重要。对黄遵宪的仰慕及其开放的胸襟,自然也会成为他转变的因素之一。当然,以上三个方面只能是他从事白话创作的外部因素。从他个人的因素来看,他那天生浪漫型的青春人格,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的思维方式,及其吞吐八荒的才情,都成为他向白话转变的重要条件。对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来说,初次试用白话做诗,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如社会舆论的压力,思维方式的调整等,但对郭沫若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他最初甚至没有意识到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只是本着内心的需要,自由挥洒他的天性。因此,郭沫若和胡适虽然同时进行新诗创作,但其动机存在着很大差别,我们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在五四诗坛上,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不管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胡适有多大差距,但都程度不同的受到胡适的影响,他们都是在《尝试集》的影响和启发下,走上新诗创作之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尝试集》是当之无愧的先锋和表率。作为一部诗集,《尝试集》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但以此来否认它在新诗史上的筚路蓝褛之功是不公平的。对《尝试集》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表现在艺术水平的高低上。胡适本人对此有明白的表示:“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⑦]相比之下,《女神》与《尝试集》的关系就相当疏远。郭沫若在日本着手白话诗创作时(1916年秋天),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最早在国内公布他文学改良的“八事”,是1916年10月,在《新青年》2卷2号发表《与陈独秀书》)还没有发表,国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开始。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国内学界正式发难,而此时郭沫若正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学习(郭沫若从1915年7月进入该校),对此一无所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刚开始的时候,“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⑧]。为了扩大运动的影响,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在4卷1号上,发表了白话新诗九首,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正式诞生;4卷3号上,发表著名的“双簧信”;4卷5号上发表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初步显示了文学运动的实绩。这时郭沫若仍在日本冈山高校学医。本年3月,他与安娜同居,父母有“哀痛之情”,郭沫若在家信中表示“悔之罔极”,又由于“有日本老婆”被归在“汉奸之列”[⑨]使其内心痛苦不堪,而对国内的文坛巨变,知之甚少。正是在他与国内文坛近乎隔绝的情况下,他还创作了小说《骷髅》(故事梗概见《创造十年》,当时投向了《东方杂志》,未刊)和诗歌《解剖室中》(后刊于《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2日)。这与国内新诗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只是当时没有将作品发表,因而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也正是在同年,他与张资平筹划出版专发文艺作品的白话刊物。这一想法与《新青年》改用白话不谋而合。
郭沫若第一次与国内五四新文坛的正面接触是1919年。这年6月,他与朋友成立夏社,为了与国内文艺界交流,他们选定了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9月,在该报的“新文艺”栏内读到康白情的白话新诗《送慕韩往巴黎》,“不觉暗暗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作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以发表了。’我便把我在1918年在冈山时作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是郭沫若首次发表新诗。[⑩]我们不能否认康白情这首来自国内五四文坛的新诗对郭沫若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影响是很微弱的,他只是坚定了郭沫若写白话新诗的自信。就目前资料来看,这几乎是唯一的一次郭沫若表述五四诗歌对他产生的影响。而在这次正面接触之前,《女神》中的许多作品已经写成,其风格也已露出端倪,郭沫若此后完成的《女神》中的其它诗作,也基本上是沿续着最初的风格。在《女神》初版之前,郭沫若可能没读过其它的五四新诗和《新青年》,这说明,《女神》基本上是在一种与五四诗坛较少交流的情况下写成的,在郭沫若与五四诗坛接触之前已基本定型。那么,《女神》与国内的白话文学(包括《尝试集》)只能算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没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女神》充分显示了五四时代精神,这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尝试集》等其它五四诗坛的作品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但这不能成为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关系密切的证据。我认为,《女神》的精神渊源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它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交相辉映的结果。郭沫若在谈到对他产生影响的诗人和思想家时,他列了一长串外国诗人的名字:泰戈尔、海涅、惠特曼、歌德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谈到其思想来源时说:“我在未转换之前(1924年前),在思想上是接近泛神论,喜欢庄子,喜欢印度的佛教以前的优婆尼塞图的思想,喜欢西洋哲学家斯皮诺沙。”(11)他几乎没有谈到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诗人对他产生的影响。因此,《女神》与五四精神之间的一致,反映了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反封建问题上的默契和共同要求,也反映世界文学(包括文化思潮)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中国新文学产生的影响。郭沫若也曾多次表白《女神》与五四运动之间的依存关系,但他说的五四运动主要指的是1919年5月4日的学生大游行,当时日本的报纸对此作了歪曲性的报导,为了向国内传送日本反华的信息,他与朋友成立“夏社”。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那场政治运动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从当时的历史史实来看,在《女神》的创作时期,郭沫若对国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知之甚少,而且心存不满,甚至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创造社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他们计划成立创造社的最初动机就是因为不满国内文坛和《新青年》。1918年8月下旬,郭沫若在日本博多湾海岸邂逅张资平,谈到了对国内文坛的看法。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是三年没回国的人了。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并提到了对《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的反感。他这时似乎没有读过《新青年》,但肯定知道这份刊物的存在,因为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们提到了这份他们认为“浅薄的杂志”:
隔了三年的国内文化情形,听资平谈起来,也还是在不断地叹气。
——(张资平说——引者注)“中国真没有一份可读的杂志。”
——(郭沫若问——引者注)“《新青年》怎么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章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起来还要多。”
在这次谈话中,他们酝酿仿照日本的样子,办一份纯文学杂志,专门发表文学创作,“不用文言而用白话”。这一决定,正与国内的白话文运动同步(从《新青年》也在同年全部改用白话),很显然,他们这一决定与国内的白话文运动无关。其实1918年正是《新青年》的黄金时期。除了白话诗歌和鲁迅小说外,还有大量的反封建檄文。但由于他们对“纯文艺”的追求,在文学观上与国内文坛有较大分歧。郭沫若将这次谈话作为创造社的“受胎期”,结合后来成立的创造社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文学活动所具有的双重性;在变革封建文学传统、反对旧《小说月报》式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方面,与国内文坛是一致的,客观上,成为五四文学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新兴的启蒙文学也颇为反感,心中不无取而代之的打算。鲁迅的小说无疑是五四文学的最为杰出代表,但在郭沫若看来,“感到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12)郭沫若这种感觉可以推广为对整个五四文学的看法。后来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对鲁迅小说的批判,也体现了创造社成员对五四文学的不满。正如一位论者指出:创造社“尽管在精神上体现着‘五四’新文学的方向,显示了这个文学运动的新的实绩,但至少在形式上却并不直接表现为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正面冲突,创造社与外界的论争更多地表现为新文学营垒内部的斗争。”(13)郁达夫在其起草的《创造》季刊出版广告上,(14)说“自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引起与文学研究会的冲突,后来将这冲突解释为彼此之间的误解。但我认为,这句话倒真实地反应了他们要与国内文学一争高低的雄心。这对一群初出茅庐而自恃才高的年轻人来说是正常的,也是很令人佩服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把郭沫若看作是对胡适的“响应和追随”,并把《女神》与《尝试集》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并且仅仅根据出版的时间,就判定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
《女神》与《尝试集》之间这种人为焊接的密切关系一旦被解除,我们就能够较为客观地来对这两部诗集做出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胡适对白话诗倡导与宣传,是得风气之先的,《尝试集》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新诗的重要起点;但它并非是唯一的起点,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也同样为新诗的诞生提供了一个起点。胡适的意义在于以其权威话语,奠定了新诗的正统地位,而在艺术经验上,除了失败的教训外,没有能够为新诗提供艺术的武库和成熟的范本。而这一必不可少的工作,是由郭沫若来完成的。《女神》与《尝试集》有着惊人的发行数字,但那蹒跚的幼稚的步履,没有能够像胡适期望的那样证明白话作诗的优越性,而这一历史使命也同样是由《女神》来完成的。在新诗的草创时期,这两部诗集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如果没有胡适的鼓吹和亲身实践,光有《女神》,那么白话新诗很难赢得公众的认可;同样,没有《女神》的协助,《尝试集》蹩脚的艺术手法,也很难使新诗在短时间内走向成熟。
注释
①②陈金淦《胡适研究资料》第142页、145页。
③④⑨(12)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第50页、第38页、第59页、第90页。
⑤⑥(1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第51页、第39页、第40页。
⑦《尝试集·序》。
⑧鲁迅《〈呐喊〉自序》。
⑩《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卷64页。这几首诗的发表时间作者自述有较大出入,此处只摘引原文。
(13)王富仁《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第170页。
(14)载《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
标签:文学论文; 郭沫若论文; 诗歌论文; 女神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尝试集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胡适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