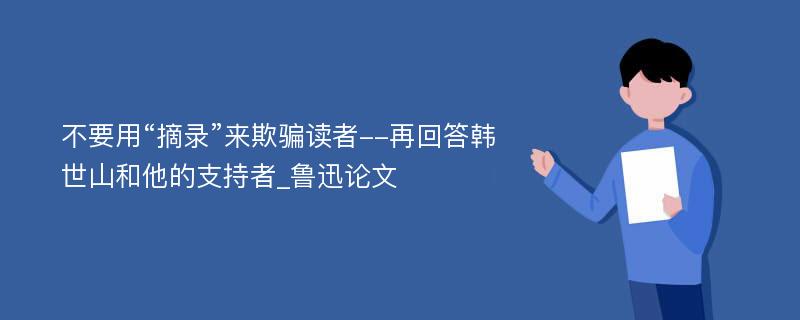
不要用“摘句”欺蒙读者——再答韩石山及其支持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山论文,支持者论文,不要用论文,读者论文,再答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十年前,也就是鲁迅临终前不久,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精品力作:《题未定草》,对文艺批评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其中第七部分一开头就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鲁迅强调:“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去年以来,“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再起风波,笔者有幸成为了“众矢之的”。发难者是资深酷评家韩石山,矛头是2003年12月28日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的一次讲演:《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被韩右山精心挑选出来做靶心的是以下这句话:“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韩石山认为,这样说是无常识,昧良心;是在说“大话”,说“空话”;是在摆出作政治报告的架势对当前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像我这样的人,“打上一顿,他也不会明白”,“真是没救了”。还有更加用心良苦的人,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与此类比,将我影射为“以柳宗元知己白命的”一再“出丑”的章士钊。
这样的抨击和讥讽是否得当呢?我认为,要评论我文章的得失,首先要读完我的全文(网上随时可查),要读懂我的原意。韩石山是没有勇气在他主编的刊物上披露我讲演全文的,也有意不向读者全面介绍我的观点,而只是抓住其中可供他利用的一小段话大做文章。一般读者不可能一一去查阅我的原文,于是就难免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了。
我果真是在对当前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吗?请大家以公正之心认真读完我讲词中的相关部分: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对于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会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鲁迅同样会持肯定的态度。这并不是强加于鲁迅。五四时期,有形形色色的主义在中国传播,除开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一起涌进了思想的自由市场。鲁迅当时并没有服膺什么主义,也没有宣扬什么主义。1925年3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回信中坦率地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但到1927年之后,鲁迅已经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不但能从鲁迅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证实,而且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也能得到证实。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在现存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回忆公认为最真实生动,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无疑是可信的。另一位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在他的回忆文章《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中也提到,鲁迅“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萧红回忆的一个旁证。
有人说,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中国也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见鲁迅的看法过时了,他当时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鲁迅有一篇杂文题目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实际上受骗的是鲁迅本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表面的看法,不足为训。鲁迅在文章中对苏联的肯定主要是两点: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消灭了农奴制。千百万奴隶从地狱里涌现出来,成为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二、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由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而苏联的小麦出口,煤油出口,使世界震惊。我认为,鲁迅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尺主要是这么两个:一看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权的尺度;二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生产力的尺度。这两个标尺今天也完全正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前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平等的原则,另一条是发展的原则。所谓平等也就是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对公民幸福和福利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关注。所谓发展就是要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来谈平等就会流于空想,其后果就是全社会的普遍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像格鲁吉亚,人均月收入才23美金,前总统月薪才200美金,这就会引发所谓“天鹅绒革命”。但离开平等讲发展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然,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在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然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不过不能差距过大,以致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方向。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但是,“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所谓贫与富是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扩大是一种世界性趋势。目前,全球1%的富人已经占有全球80%的财富,富国跟穷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达到了430倍。在不同国家,贫富的标准也并不一样,但粗略划分,贫可分为赤贫与贫困。所谓赤贫指生存性贫困,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生活费每天低于1美金者为赤贫,这类人在全球有15亿;生活费每天不足2美金为贫困,这类人在全球有30亿。也就是说,目前全球有一半人口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可分为先富和暴富两个群体,他们致富有合法与非法两个渠道,他们的财富因而可分为可以公开来源的“阳光财富”和来源不可告人的“肮脏财富”。
我国贫困线是根据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项指标之和确定的。根据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927万。因此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成为了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城市贫困群体也不少。据统计,今年下岗职工有600万,登记失业人员有800万,新增劳动力有1000万,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形势也相当严峻。
今年夏天,我去东北进行了一次考察,重点视察了那些煤炭、石油、木材进入枯竭期的城市,发现那些地方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小兴安岭的林木资源已经减少了98%,林场42%的职工处于闲置状态。抚顺西露天煤矿经过数十年开采掘,只遗留下两个6.6公里长、2公里宽的大坑。鹤岗煤矿区发生大面积沉陷,每年下沉一米三,时有事故发生。比如王治发等三人开会,房屋下沉5米,无一幸存。付成友到室外大便,地面突陷10米死亡。李桂花推车行走,发现一小洞,好奇观看,连人带车掉进15米深的井巷,未见尸体。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生前曾蕴酿写一篇关于“穷”的杂文,大意是:“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比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1937年上海《宇宙锋》十日刊第50期。)鉴于我国目前地区、城市、行业、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中间层收入相对下降,三农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形势,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决策时强调城乡的统筹发展,区域的统筹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统筹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发展。根据鲁迅的思想实际,他对这些举措肯定会由衷拥护的。
在同一篇讲词中,我还尝试运用鲁迅思想剖析了当前的职业道德和官场道德状况,愤怒谴责了不容忽视的腐败现象。文中还以相当篇幅谈到了令人忧虑的青少年犯罪和文艺世俗化等社会问题。如果读者真正站在客观立场,听完我的陈述,读完我的引文,难道不会从中感受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吗?难道还会误认为我只是在说“大话”说“空话”吗?如果我真是在对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那么韩石山有本领指出我谈成绩的数据或事例有哪一条是虚假的吗?再说,我在用鲁迅观点联系当代中国现实的时候,就连一点成绩、一点进步也不能讲吗?讲了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要群起而攻之吗?
但韩石山却振振有词地说,我讲演的那年,如果鲁迅还活着,已经有122岁。一个中国人活不了这么大,至少他没听说过。这不是废话吗?须知,我所作的是“假言判断”。凡“假设性命题”,都不可能一一坐实。正因为鲁迅已经在1936年逝世,人们才会假设他活着会如何如何。如果进行文艺性假设都必须有准确的年龄限制,那韩石山能否规定一个法定年龄让普天下做假设的人都来遵循?比如过去有一句诗:“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请问韩石山先生,哪年哪月牺牲的先烈有回眸笑慰的资格,而哪年哪月牺牲的先烈则无权笑慰呢?
被韩石山攻击的还有上述讲词中的一组文艺性的排比句:“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鲁迅肯定会含笑九泉。”这在韩石山看来更是无视中国现实的“大话”、“空话”。他狂妄地要作这样的修订:“如果看到闰土的一部分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一部分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这真是把诡辩当雄辩的典型例子!我们都知道,鲁迅在作品中剖析了中国人的种种精神痼疾,但就在当时,他笔下出现的“中国人”三字就从来不包括四万万同胞的全部。如今是否有必要请韩石山出山,在鲁迅作品所写的“中国人”之后通通加上“大部分”或“小部分”的限定词呢?又比如,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是否应该请韩作家修改成“咱们老百姓,今儿有人高兴,也有人不高兴”呢?
其实,像我这种被韩石山藐视的退职之人,原本不值得他如此大动干戈、大兴挞伐的。有不少好心的读者给我来信或来电话,指出韩石山进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而是在借题发挥,别有深意所在。这使我明白了许多事理。本来,“假设”是一种十分轻松的话题,可以为提出假设者提供一个神思遐想的广袤空间。你思念爱人吗?那你把自己假设成一屑月光,就可以立刻偷偷匍匐在她的枕边。你想要造福人类吗?那你就可以把自己假设成为一切人类的必需品:返乡民工的一张车票,贫穷学生的一沓学费,救济印度洋海啸灾民的一箱面包或一个帐篷。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质问人如何能变成“月光”,又怎么会成为“帐篷”,那一定是这个质疑者的智商发生了问题。
对历史人物身后命运的假设原本也可以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轻松话题。比如鲁迅推崇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为帮助希腊独立,于1824年病逝于梅索朗吉昂沼泽地,至今已有181年。对于“如果拜伦他还活着”的问题,不同人历来各有不同的假设。据马克思的女儿回忆,马克思认为拜伦如还活着,很可能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但马克思的研究者柏拉威尔教授却怀疑这一回忆的真实性。有些英美学者认为拜伦如不死于1824年,他有可能成为希腊的国王或总督,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位行走诗人会浪迹天涯,移居南美或到神秘的中国旅游。这些假设从不同角度丰富着拜伦的形象,增添着拜伦的魅力,使之成为说不尽的拜伦。提出不同假设者之间决不会出现剑拔弩张的关系,也从未有人说这种假设“无异于痴人说梦,过过嘴瘾而已,屁意义没有”。
然而一旦涉及“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气氛就会立即变得凝重起来,就变成厂有些人所说的以韩石山为代表的“觉悟者”与以我为代表的“不觉悟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交锋。韩石山一定要我在同一篇讲演中谈假如鲁迅活在1957年或者活到文革期间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要求是无理取闹,因为我论述的是当下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全面总结历史教训。任何一次讲演都有一个中心,任何讲演者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阐述所有问题。但我可以明确表态:如果有人假设鲁迅在1957年可能错划为右派,或者假设鲁迅在文革期间会被迫害,我决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出自某人之口则是另一问题),因为这类“假设”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假设”,说鲁迅活到今天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而欢欣鼓舞,同样也应该被允许,跟前一类假设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它性。我提出后一种假设的依据有两点:一、鲁迅是一位平民作家,毕生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他如果看到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的确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怎能不发自内心的高兴呢?二、鲁迅后期是一位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如果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怎能不发自内心的高兴呢?当然,假如他活到今天也会对当下的种种社会弊端表示关注和忧虑,这一点我在讲演中阐述得更为充分。只不过韩石山不敢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因为一旦全面介绍我的观点,就不可能达到他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的目的了。
这场风波发生之后,有些好心的朋友规劝我今后多谈学术,少谈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这种关心善意可感!也有人激烈攻击我的讲演“不是学术研究”,是在“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上的真理”。这种批评又使我感到十分困惑。我感到,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武器的鲁迅著作,本身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因素。因此,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鲁迅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的过程中,要完全回避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对鲁迅当代意义的理解上发生观点分歧更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可以断言,从1946年至今,围绕“假如鲁迅活着”的讨论,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我在讲演中提出了七、八个假设,韩石山单选出其中的一个进行批判,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香港《动向》杂志去年6月号刊登了一篇“大陆来稿”,说“假如鲁迅活着”,一定会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这就更反映出作者的一种政治倾向!
我在同一次讲演中作过声明:“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地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冲击,终止其垄断地位。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的地位又被重新确定。不少学者(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考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儒家思想的应有作用。如在市场经济中讲‘诚信’,在人际关系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敌面前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讲‘尊师重道’,等等。我想,只要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这种现代阐释就不会导致牵强附会。基于这种理解,我今天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
既然是带探索性的“尝试”,当然会有不成熟的地方。这是在谈政治?还是在谈学术?抑或学术当中有政治,政治当中有学术?我说不大清楚。所以对这种尝试进行任何批评都是允许的,我一律表示衷心的感谢。但这种尝试决不是“用政治上正确的言论来冒充真正的学术探讨”,更何况“政治上的对与错”跟“学术上的真与伪”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情。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对人的羞辱,特别是政治性的羞辱和诽谤(比如在彻底否定我的前提下又说我“三个代表”学得好,甚至不顾事实说我有违反政协纪律的“诈行”),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学术争鸣的规范,超越了文艺批评的道德底线。尽管被羞辱者可以将羞辱化为激励自己继续奋斗的动力,但对人的羞辱毕竟是一种邪恶,决不是一个健康和谐社会所应该产生的现象。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论争中韩石山不仅对我个人进行了羞辱,而且对整个鲁研界进行了群体性羞辱:先是由他本人宣布“鲁研界里无高手”,鲁研成果多废品;而后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宣布“鲁研界里高手如云”——但多为“大内高手”,即官方打手。像这种极端的做法,在中外文艺批评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在这场风波的过程中,我不禁又思考了一个问题:一贯主张“人各有己”,提倡“张扬个性”的鲁迅,为什么会对以陈西滢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恶痛绝呢?我想,鲁迅所反感的并不是他们的“特立独行”,并不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而是厌恶他们的虚伪性——他们“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五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他们满嘴“宽容”、“大度”、“多元并存”,但实际上搞的却是思想专断和党同伐异。只要有人的观点跟他们相左,他们就会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合力进行“围剿”,企图一统舆论,使文坛成为他们独霸的天下。比如《天津老年报》为此组织了一场“讨论”,但事前事后都不跟我打招呼,发表了几篇“围剿”我的文章之后就匆匆宣布“鉴于某种考虑讨论终结”。该报在“编后”中还说:“有读者来信要求本报转载陈漱渝《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讲演全文。鉴于该文太长,而且亦无必要,本报不再转载。”这种做,法难道是公正的吗?难道对我进行准确的批评没有必要了解我的全文吗?该报既对我的文章进行“围剿”又两次宣称“不拟介入这场争论”,这难道不是极端的虚伪吗?然而辨别真理和谬误终究要看事实,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用一时一地的“人气指数”虚张声势决封不住别人的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