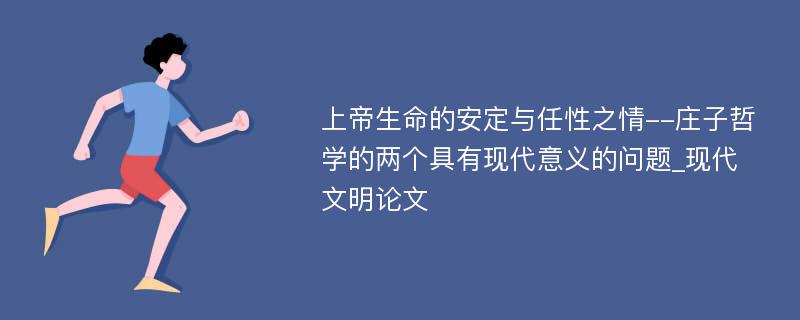
神生安定与“任其性命之情”——庄子哲学的现代意义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情论文,庄子论文,性命论文,安定论文,任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4-0018-05
在两千二百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和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舒适和无数的好处的时候,当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们都在不厌其烦地讨论社会、文化、哲学以及文学的种种现代性的时候,重读《庄子》,我们发现,两千多年前庄子哲学中所关注和讨论的诸多问题,在现代社会重新又成为我们所关注和苦恼的重大问题。时光已经流逝了20多个世纪,人类社会已经从古典的农耕社会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然而,庄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没有解决,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焦虑和必须面对的问题。诸如:关于人类社会的前途和走向问题、对机械技术的评价问题、对待人的欲望的态度问题、历史进步与伦理道德的矛盾问题、生态问题等等。于是,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问题有意无意的凸现出来,由此,我们不由得感叹这位古典圣人的高瞻远瞩和伟大。庄子哲学的现代意义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神生不定——对机械和技术的社会后果的警惕
自近代社会以来,我们日渐生活于一个被机械和技术所包围的世界之中,机械和技术已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的东西,并且机械技术的广泛使用及其所形成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机械和技术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推进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机械和技术的广泛使用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愈来愈被现代社会所认识。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说:“人类社会在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增长上得益于机械技术,但另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剧毒、枪支、战争机械和这类摧毁性发明形成的行业已远远超过了迈诺特尔所具有的残酷。”[1](p4)不仅如此,机械和技术的广泛使用及其所形成的观念,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制度、秩序以及人们的心理意识和价值观念之中。这种由于机械技术和使用机械技术所带来的后果人们无法全面预料到。到目前为止,科学技术的未来和人类社会的前途仍然是一个谜。更为严重的是,技术已成为一种控制人类的力量和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可能最终与人类发明创造机械技术的目的背道而驰。有学者指出:“技术的发展似乎并不是自动把人类导向一个幸福的天堂,相反却可能是把人类导入一个阴霾的地狱。”[2](p18)勃兰特·罗素也说:“我认为,科学最终将赐福还是伤害人类,这还是一个充满疑问的问题。”[1](p6)
极为有趣的是,对于使用机械技术的社会后果,生活于科学技术还非常不发达的年代的庄子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和警惕。这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
《庄子·天地》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报壅而出滑,榾榾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为,羞而不为也。’”[3](《马蹄》,p193)
庄子借一老者之口说出了他对使用机械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警惕。庄子并非不懂得机械的用处,然而,他更注重的是使用机械以后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天下人机心存于胸而“纯白不备,神生不定”,在庄子看来,这是很可怕的。
庄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孤立的看待机械技术的使用问题,而是把机械和技术问题与伦理及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他更注重机械和技术的伦理和社会后果,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学术文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如何看待机械技术的作用问题是现代学术文化争论的焦点之一。毫无疑问,机械技术的使用对我们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和获得方便、舒适等等方面的好处是难以尽述的。然而,正是这些好处掩盖了机械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和危害。
庄子的深刻在于,他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看到了机械和技术对人的“纯白之心”和“神生安定”的扰乱和破坏。而且,庄子的推论是难以推翻的: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神生不定。
我们只要看看现代社会的状况,就得承认庄子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仅就运输机械而言,现在世界上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在数十万以上,还不计由交通事故带来的财产损失以及医疗、诉讼等其他事项。这就是由机械所带来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人们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对于纯朴、纯真无限向往。然而,这种纯朴的面貌和纯真的人心,我们只能在那些机械技术相对不发达的偏远乡村才能找到。越是在那些机械技术发达的地方,则纯朴和纯真越少。也许这就是庄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机械技术,人民素朴愚昧,人兽同居的社会的原因之一。庄子说:
夫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可系羁而游,鸟雀之巢可樊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乎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3](《马蹄》,p193)
庄子所描述的这种原始素朴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机械技术因而也没有机事和机心的社会。有机事必有机心。现代人被机械技术和机巧所累是人所共知的。现代人都说很累,是什么原因?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事累,二是心累。机械技术的广泛使用推进了文明的发展和人的智力的发展,但也使我们“机心存于胸”而失去了纯朴、纯真的天性。由机心所带来的狡猾、奸诈、阴谋等机巧、机关、玄机又使人们陷于相互猜疑、相互戒备之中。在人人都具有了机心的文明社会,人们以机心对机心、以聪明对智慧、以阴谋对奸诈,哪能不累?
或许会问:机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那些人性中的不良品质不一定要由机械技术负责。在古代那个机械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不是也有许多极有机心甚至比现代人更聪明或狡猾的人吗?使用或懂得机械技术的人就一定不纯朴、天真吗?
从总体上看,凡是机械技术和现代文明越不发达的地区,则民风越是淳朴、人们越是纯真,而机械技术和现代文明越是发达的地区,则淳朴、纯真越稀少。这种现象令人深思。在庄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庄子已从很有限的机械技术的使用中,看到了发明、创造和使用机械技术需要以人的智力去从事这些事业,其结果是使人“纯白不备、神身不定”。故而,庄子也反对智慧。
最为重要的是,庄子是从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机械技术的使用的。他看到了使用机械技术的背后所隐含着的灾祸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连串我们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后果,至少这会使人“纯白不备”、“神生不定”。庄子对机械技术的反对是和他的人生理想以及他的审美理想相关的。
首先,庄子主张人是自由的。在庄子看来,技术往往限制人的自由。在《天地》和《应帝王》中,庄子借老聃之口说道:“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3](《天地》,p73)“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3](《应帝王》,p133)
庄子认为,有技艺者因技艺而被束缚,并且劳形苦心,因而是不自由的。这样也会改变人的天性,故而庄子又说:“功利技巧必忘乎人心。”(天地)所以,庄子反对一切机械技术、技艺乃至聪明、智慧、仁义等等。同时,庄子从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出发,反对技巧和工匠。庄子说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3](《马蹄》,p58)
庄子认为,原始素朴是天下最高的美,而工匠、技巧会毁坏器物的素朴之美,圣人推行仁义会毁坏道德,所以都是应当抛弃的。
庄子反对机械技术、技艺、技巧、工匠以及仁义、智慧的目的是让人过一种保持着纯朴天性而神生安定的幸福生活。而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也是使人类幸福吗?然而,现代科技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虽然在物质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在保持淳朴之心和神生安定方面,现代人却离这个目标愈来愈远了。
本杰明曾经这样描述过现代人的城市生活:“害怕、厌恶和恐怖是大城市的大众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中去了——这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这种机器主义的每一点进展都排除某种行为和情感的方式。安逸把人们隔离开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使醉心于这种安逸的人们进一步机器化。19世纪中叶钟表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革新只有一个共同点:手突然一动就能引起一系列运动。这种发展在许多领域里出现。……就像报纸的广告版或大城市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进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4](p146)
在本杰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机械化和工业化给现代人带来的惊恐和不安,再加上现代人无处不在的机心,人们哪里还能神生安定。
在高度崇尚机械技术和工具理性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我们无法回答,但是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告诉我们:它使人“纯白不备”、“神生不定”。至少从人类社会目前的状况来看,庄子没有瞎说。
自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对机械技术的评价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一是科学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观念;二是科学技术中性论;三是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至上的批判。庄子对机械技术的全然否定当然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把机器看作恶魔,主张“返归自然”,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文明和机械技术的批判、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对技术社会的揭露和控诉,以及现代学术文化对把技术和技术产生的后果分离开来的技术中性论的怀疑、对工具理性至上的警惕和批判,都显示出庄子对机械技术的后果的深刻认识仍然具有深远的现代意义。
二、“任其性命之情”与人性的完善
庄子不但对机械技术的使用及其后果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而且,庄子对“仁义”、智慧、聪明、礼乐和人的欲望也持否定的和谨慎的态度。在庄子看来,这些都是或扰乱、或改变、或残害人的自然天性的东西。庄子说:
“自虞氏招仁义以扰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数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3](p55)
庄子认为,自从上古时期的尧、舜以后,天下人都被“仁义”、“名利”等东西改变了其自然的天性。无论是以身殉利的小人,还是以身殉家国的士大夫,都是伤身残性的。而所谓的“仁义”、礼乐、名利都不是人的天性中原有的东西,所以,所谓“仁人”总是有许多的忧愁:“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骈拇》)而以“礼乐”、“仁义”去规范人,就会使人失去其本性:“曲折礼乐,眗愈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骈拇》)也因为“仁义”不是人的自然本性中原有的东西,所以就得费力去推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骈拇》)既然仁义不是人的天性中原有的东西,是圣人强加给人的,那么,“仁”与“不仁”都是违背人的本性和伤生残性的东西。故而,庄子说: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丧生残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财货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期间哉。(《骈拇》)[3](p55)
庄子认为,伯夷(仁人)和盗跖(不仁之人)虽然死于不同的目的(名或利),但在伤生残性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不一定伯夷就对盗跖就错,又何必区分什么君子或小人呢?在儒家思想看来,仁义、礼乐、艺术等等都是能够陶冶人的性情、使人向善的东西,而庄子从顺任人的自然天性出发,认为扰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就是仁义。正因为圣人推行仁义而扰乱了人的自然天性,所以才又反过来需要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去规范人性。庄子说:
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乱,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马蹄》)[3](p153)
道德、仁义、声色、工匠、技巧都是扰乱人的自然天性和破坏事物的自然质朴之性的东西,所以应该否弃。不仅如此,庄子认为,所谓视觉上的“明”、听觉上的“聪”以及能言善辩和仁义、技巧等东西一样都是扰乱人的性情、祸害天下的东西。庄子说: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声,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矣。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骈于辨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至正也。(《骈拇》)[3](p53)
在庄子看来,所谓“明”、“聪”和善辩都不是好东西,是扰乱人的视听和人心的旁门左道。它们会使人沉溺于声色犬马、沽名钓誉之中,所以,离朱、师旷、杨墨都是歪门邪道。那么,什么是正道呢?在庄子看来,就是顺任自然和人的自然天性,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用庄子说法是:“彼正正者,不失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
庄子认为,“任其性命之情”就是遵循自然的德性,不用外在的“仁义”等东西去束缚人的自然天性。
“吾所谓藏者,非仁义之谓也,藏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藏者,非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
在这段话中,庄子说的“藏”指的是“善”,[5](p55)而庄子说的“德”,是指顺任天道自然和“任其性命之情”,故而在《庄子》一书中,有德之人都是顺任自然天道和性命之情的人。庄子为什么反对“仁义”、“明”、“聪”?因为在庄子看来,这些外在于人的自然天性的东西都是扰乱人心、妨碍人对事物的真正认识,所以,庄子认为,“善听者不为聪”(如师旷),“善见者不为明”(如离朱),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聪明呢?庄子说是“自闻”、“自见”、“自适”、“自得”者。
“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3](《骈拇》,p56)在庄子看来,所谓聪明并不是去闻见那些“仁义”、声色等外在的东西,而是去体悟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内在本性,即所谓“自闻”、“自见”,这样才能“自适”和“自得”。如果我们不是去闻见自己的内在本性而是去“见彼”、“得彼”等外在的东西,那就等于是“得人之得”、“适人之适”,所得到的不是你自己本性中想要的东西(如同我们做什么事总是考虑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高兴,适不适合社会道德等外在的规范等等)。这样的话,即使虽然盗跖和伯夷有区别,也同样是邪道,因为他们都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
从顺任人的自然天性出发,庄子对于人的欲望也同样持警惕的态度,主张“恬淡”、“虚静”、“无为”。庄子所推崇的理想社会中的人都是“恬淡寡欲”,人们不被欲望和外在的声色诱惑所束缚的素朴状态。
“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也可,亡也可;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脔卷獊囊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3](p62)(在宥)
庄子认为,过度的沉溺于外在的声色欲望和被“仁”、“义”、“礼”、“乐”“圣”、“知”等外在的社会规范或知识所束缚,就会扰乱人的心灵的安宁,使天下人不能安其性命之情和使天下人困惑不安甚至天下大乱。所以,庄子主张人应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
庄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性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性,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将守性,性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为所败。[3](p65)(在宥)
庄子认为,人应该不去闻见外在的声色和知识才能使人清心寡欲,不劳形苦心,得到心灵的安宁。庄子为什么反对知识,也是和他对欲望的态度有关的。
冯友兰先生在评价老子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为寡欲故,老子亦反对知识,盖(一)知识本身即一欲之对象。(二)知识能使吾人多知欲之对象,因而使人不知足。(三)知识能助吾人努力以得欲之对象,因而使吾使人不知止。[6](p156)
冯友兰先生评价老子的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庄子,因为在对知识和欲望的关系的理解上,庄子和老子是一致的。故而,庄子才说“心无所知,女神将守性”,“多知为败”。
总的来说,庄子反对“仁义”、“礼乐”、“聪明”、“智慧”以及对人的欲望持警惕的态度,目的都是一个,即使人保持人的自然天性,达到“任其性命之情”的理想状态。而庄子要人“任其性命之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人的自然天性不被扭曲,人性得以完善。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自然天性早已经被文明社会的种种制度和规范所压抑和扭曲。我们的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以及人的聪明智慧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我们的文明的种种进步是以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为代价的。现代人被聪明智慧和科学技术等等理性化的东西所异化,我们的内心被欲望和外在的物质所束缚,我们的自然天性被文明社会的种种规范所压抑。我们不仅不能“任其性命之情”,而且,我们离人性完善的目标也愈来愈远了。虽然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不可能存在没有压抑的文明。但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要远远甚于古代文明和原始文明。这也许是众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设计他们的乌托邦社会时总是以古代文明社会为模式的原因之一吧。
毫无疑问,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现代社会的种种病症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孙志文所说:“许多成就都是利弊兼具的。因为这些成就主要基于唯理式和机械式的前提,而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物质方面的不断进步,忽略了人心理和文化的需要。结果造成现代人愈来愈以无理性的态度来处理生命,导致现代人和自然、社会、上帝疏离。”[7](p15)在现代社会的种种病症中,最大的和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观念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残害和扭曲。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我们享受着无数的好处和舒适,然而,我们却“神生不定”,不能安身立命,更不能“任其性命之情”。[8](p31)在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所形成的唯理化观念统治下的现代社会,庄子所说的那些“仁义”、“礼乐”、聪明智慧、外在的物质欲望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扰乱和残害等等现象,无不以现代的方式在现代社会重演。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以民主、自由等名义发起的种种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科技理性和机械把人作为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在愈来愈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愈来愈无法满足的欲望,愈来愈聪明智慧的现代人却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人类社会极力推崇仁义、礼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费尽心机所要获得聪明智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竭尽全力地创造财富以满足欲望的目的又是什么?当我们人类艰难的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不就是努力使我们人类集体及其每一个个体有一个完善的人性和身心吗?不就是让我们人类有一种幸福和谐的生活吗?
庄子对仁义、礼乐、聪明智慧和知识的反对,对欲望的警惕、对理性和机械技术的态度,这些似乎与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观念背道而驰的观念其实并没有过时。庄子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应该过一种顺应人的自然天性而且人性完善的幸福生活。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仁义、礼乐、聪明智慧和知识的负面作用,看到了机械技术和唯理化的理念对人的压抑和异化。在庄子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仍然是我们所考虑和没能解决的问题。庄子的焦虑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共同焦虑。
庄子,一个知识丰富而充满智慧的人却极力反对知识和聪明智慧,在现代看来,这是大有深意的!
[收稿日期]2006-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