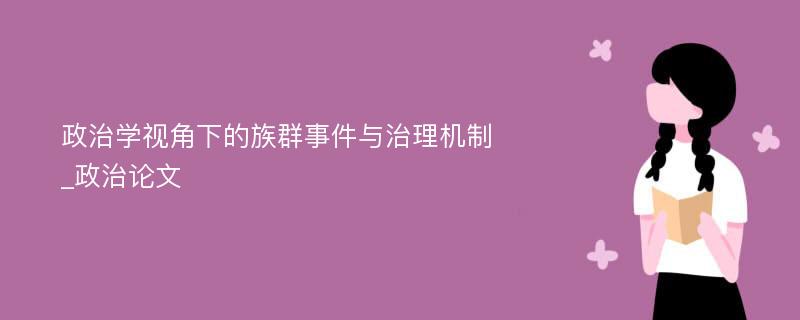
政治学视野下的民族群体性事件及治理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视野论文,机制论文,民族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少数民族或者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趋突出,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作为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不仅事关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事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重要性不容忽视”。①
本文通过深入、有针对性的田野调查,在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②的研究上做一些新的尝试,力争突破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理解误区,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形态和成因,探求群体性事件的一般规律,为正确处理此类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提出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回顾
中国正处在体制变革、社会转型的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民族问题与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交织在一起,引发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因此,将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纳入到转型中国的大背景考察,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经济、民事、刑事等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这些矛盾和纠纷主要是不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民族关系问题。比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来自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城经商、务工日益增多,其中有一些是无证开业;有些流动商贩则在商业中心区集中沿街摆摊,强买强卖,违章经营。有的还以民族风俗习惯为由携带管制刀具,制造事端。③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源头和性质往往都是经济、民事纠纷,不能认为是民族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及时或方法不恰当,也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第二,宗教因素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伤害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宗教感情引发的纠纷,教派之间或教派内部矛盾引发的纠纷,一些少数民族信教群众违反相关规定引发的纠纷,跨地区非法传教引发的纠纷,外来信教群众擅自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引发的纠纷,涉及宗教团体权益的纠纷等。如2006年乌鲁木齐市某回民清真寺,因阿訇的人选问题产生争议,后又因教产问题发生矛盾,引起教徒之间的冲突。④还有就是在城市城镇改造过程中,一些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被拆迁,由于未得到妥善安置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三,触犯少数民族感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报纸、杂志、图书、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上出现违反民族宗教政策、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内容,引发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一本读物由于伤害了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感情,引起一些地方上千人游行抗议。媒体具有传播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使得此类事件极易在较短时间内扩散,导致事态扩大和升级。
第四,清真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有的是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了解不够而误用了清真标识,有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故意冒用清真标识,也有部分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事端。这类事件虽然数量不多,但容易引起部分地区穆斯林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引发为群体性事件。
第五,历史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历史问题引发的事件所占比重不大,但由于矛盾蓄积较久且多为深层次原因,如果不能得到充分重视、研究和有效化解,容易演化为群体性事件。例如,云南省普洱市、玉溪市、红河州交界的黑树林地区,是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山林、水利、土地等权属纠纷。各个村寨对山林等资源的争夺,常常是以民族纠纷的形式出现,使普通的利益争夺与民族间的利益纠纷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和矛盾具有更大的复杂性。⑤有些历史问题还反映为现实社会的经济利益问题,如2004年甘肃、青海交界处少数民族群众因草场放牧问题而引发冲突。
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社会流动等方面。但是,如果简单地把这些诱因归结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那么这种认识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有误区的。举例来说,如果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是由于得到的选票超过麦肯恩,这句话没有错,但从这句话中得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和有用的结论,这句话就成了“正确的废话”,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他为什么能得到超过麦肯恩的选票。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与中国其他群体性事件发生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却又往往有着更为复杂的因果机制。“在我国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的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作为我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在实现其利益要求方面受到自身条件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由此产生和加剧的矛盾”也就成为“我国民族问题最广泛、最普遍的表现”。⑥更需要关注的是,随着下岗、拆迁、征地、外出务工、拖欠工资等问题逐渐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众,可以预见,类似的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有可能会形成新的高发期。一旦这些问题与传统的诱发因素交织在一起,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将会更加复杂。
在我国,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政治、社会生活中众人关注、非常敏感但又缺乏充分讨论的问题,需要理论界给出理性的认识和有因果机制的解释,特别是对所涉及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要有深入全面的分析。中国学术界对群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刚刚起步,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山西大学陈晋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教授、于建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相关研究等。⑦这些研究对群体性事件的现状、诱因以及相应的处置策略都有所阐述。比如,在利益表达方式上,认为主要特点是:被动型表达多于主动型表达,群体性的表达多于个体性的表达,自发性的表达多于组织性的表达,制度外的表达多于制度内的表达;在诱因分析上,主要有体制缺位论、结构冲突论和制度封闭论三个观点;在处置策略上,主要包括预防保障法、应急处理法、政府控制法、社会调整法等。另外,国内研究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在城市业主维权、下岗工人维权、村民集体上访等,对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目前还缺乏有深度、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而且,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较多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民族文化,较少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解释现实社会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
与此不同,美国在1969年就有题为《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认识美国的暴乱:向国家暴乱起源和预防委员会报告暴乱的原因和预防手段》的著作,旨在向政府报告如何管理和控制美国当时正在兴起的各类社会运动。⑧可以说,西方学术界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研究起步较早,且取得了较多成果。威尔逊认为,“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⑨而戴维·波普诺则认为,“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社会运动”。⑩在因果分析方面,首先回答的问题是群体行动、社会运动乃至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最早期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的解释,比如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都强调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在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心理学成为主流方法,基于“挫折—反抗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强调对个人进行微观分析,认为个体的不满与抱怨使人们参与群体行动,且往往是没有计划、自愿、非理性的行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源动员论(resource mobilization)和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逐渐成了主要研究范式,除了强调社会心理与非理性的层面外,更将其分析单位由个人移转为组织结构的动力(dynamic),采用利益、兴趣等带有理性选择意涵的概念,甚至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其主要观点是: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梯利的动员模型就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权力。而且,这些因素通过特定的组合而对集体行为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11)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进展,是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乃至革命这三类政治行为看作是一个连续统,并提出了“对抗性政治”这一概念,指的是权利声称者(makers of claims)与其抗争对手之间发生的一幕幕公开的和集体性的互动活动,在这一类互动活动中,一是至少会涉及某个政府行动主体,它或者作为权利声称者出现,或者作为权利声称的目标对象出现,或者作为第三方出现;二是一旦该权利声言得以实现,将至少影响到其中某一方的利益。(12)而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领袖等一些因素也逐渐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13)这些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学术成果,为研究中国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由于转型中国有一个充满地域差异、状况复杂的社会生态,这些解释框架均有适用它们的研究对象,且往往是以不同的程度交织在一起的。
当然,由于许多看似中性的描述性概念都预设了历史背景,很难横向地移植至不同的社会脉络,直接借用西方的理论是危险的。因此,要在充分学习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开展本土化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本研究通过有针对性的调研,在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研究假说,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意愿的形成”与“能力的获得”互动作用的结果,即Incident=Perception*Capacity,亦即I=F(P,C)。
二、意愿的形成:为什么会诉诸群体性事件?
所谓意愿,就是要解释人们为什么想参加或组织群体性事件。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生活的幸福度评价较高,同时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可以预见他们是很难有动力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也就是说,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们需要有参与的意愿。
(一)经济上的贫困是重要动因
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地区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多层次的互动,大量少数民族群众进城务工,形成了经济利益驱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只是社会变迁因素的一个方面,但它有可能启动其他社会机制并推动“社会运动”的发生。(14)“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族际交往密切和人口流动以及经济利益的交织,会通过文化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等因素表现出民族问题增多的趋势”。(15)正如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冲突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在经济起飞阶段有可能会阶段性增加。进入市场经济的少数民族民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收入,但收入上的相对差距并没有缩小,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弱势地位没有根本改观,还承担了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较多代价。民族地区整体落后、少数民族群众的相对贫困,以及现代化的冲击等因素(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汇合在一起,往往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因经济利益引发的冲突,在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可以认为,经济上的贫困,是解释中国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变量。
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常用的解释,然而经济学的解释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是生活贫困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那么就应该是改革开放前经济不发达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的群体性事件多,而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改革开放前发生的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很少,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却日趋增多。同样,如果遵照经济学的解释,就应该是越穷的人、越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与现实情况也有不吻合的地方,甚至好的经济条件更增加了抗议的能力。因此,不能一味以扶贫政策或致力于当地GDP增长等经济手段作为解决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灵丹妙药。
(二)心理落差导致抗议意愿的产生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决定人们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外部原因只有进入主体的认知范围才具有现实意义。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个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心理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们不断升高的期望,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比较的进行,人民向政府要求更多的东西。据此,有学者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的概念,(16)即强调人们的物质财富增加在横向社会对比下显得更少,人们所想要的东西(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与人们实际能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差距。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这一观点是有启示意义的。当今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部分民族政策执行不力,少数民族群众原有的一些优惠受到影响;一些企业在利税返还、招工、环保等方面,考虑民族地方利益不够,没有尽到合理的社会责任;一些政府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心理特点考虑不周;在拆迁安置中,对少数民族群众经济补偿不到位,对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考虑不足等等。以上诸多情形的存在,往往会造成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多是文化、政治、教育、宗教、情感等上面的。有些虽是许多个体的孤立事件,有类似困难的人多了,就容易形成群体性的不满,如果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就容易引起上访、串联、聚集等情况的发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某种情况下,所谓“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也包括外部势力灌输、调唆、煽动的作用。
(三)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激发了抗议意愿
关于社会变迁对群体抗议、社会运动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关于社会变迁对自杀率影响的分析。他认为,欧洲现代化的过程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导致失范(anomie)的形成和自杀率的提高。(17)涂尔干的理论对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发的。(18)
近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前工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重要转型,群体性事件正是中国社会重要转型的反映。伴随着社会变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不再大包大揽,少数民族群众虽然大体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环境保护、资源补偿、移民安置、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传承和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各种新型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问题,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价值形成冲突,往往就会增加群体抗议的意愿。而且,民族差别及其产生的民族问题,扩大到民族与民族的整个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使民族问题产生之源变得更加广泛,而且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更加复杂”。(19)如回族群众多聚居在城市的老城区,围清真寺而居,长期以来在生活上,特别是在清真牛羊肉等供应上自发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生活比较方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城区改造需要拆迁一些回民住宅或生活设施,有时处理不善就会引发矛盾冲突。另外,在急剧转型的现代社会,少数民族群众寻求通过自身努力,为子女创造更加稳定、富裕的未来生活。因此,人们参与群体抗议,往往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条件,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
(四)有意愿并不必然导致参与抗议行为
人们有了参与抗议的意愿,并不一定就会参与抗议的行为,可以选择沉默、自暴自弃、注意力转移、合理化现状等。(20)事实也表明,群体性事件也只是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场合,并且与发起者和参与者手中掌握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可支配时间)紧密相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个体的参与意愿如何导致群体的抗议行为。
三、能力的获得:群体性事件何以可能?
所谓能力,就是要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参加或组织群体性事件。毕竟如在个人层面去“走后门”,向政府申诉、上访,相对而言可操作性是较强的,而要动员或者参与组织他人一起去向政府申诉、上访却需要更为复杂的条件,诸如枪打出头鸟的顾虑,搭个便车的心态等等都会有影响。因此,不仅要了解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还需要分析其参与能力。
(一)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力量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各国民众普遍把包括自身历史和艺术、文学、英雄人物等在内的文化成就,而不是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作为民族自豪感最重要的来源。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被主流文化所包围,容易为主流文化所淹没,因而这些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处境更为敏感,对语言和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需求更为强烈。为了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少数民族群众将来源地、民族、语言和宗教等话语因素作为凝聚群体、感受亲情的最常用手段。(21)即使是原来素不相识的人们,只要是同一民族就会倍感亲切,关系自然就会融洽,同一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民族意识得到加强。这种民族意识的加强,容易引起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共鸣,他们往往将发生在本民族个体成员身上的矛盾和纠纷,简单等同于“本民族的事情”。如果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引发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民族身份和联系纽带的影响
人们因为拥有某种共同经验或者特征就更容易形成一个群体。而少数民族群众不仅是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有着多重的联系纽带,形成了重要的关系网络。(22)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多重互动的人群,“同质化”程度高,内部意见容易统一,正是群体抗议的一个主要来源,也就是说人们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系而组织起来。另外,宗教领袖、知识分子、社会活动者等非正式领导也会是重要的组织力量来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一些城市已形成一定的聚集地,构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例如维吾尔族,最著名的有广州三元里、上海民族饭店一带和北京的甘家口、魏公村的“新疆村”。少数民族群众利用族缘、亲缘、地缘和职业的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交往空间,有相对固定的生活和交往圈,凝聚为一个紧密的整体。学者认为,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聚集在同一社会空间下,为群体抗议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3)另外,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场所也容易形成一个组织空间,人们在这些宗教场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关系网络。在中国,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虽然受到有关法律的限制,但国家政策绝无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或动员。事实上,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之下,从而促进了主动的人际交往和被动的直接接触。(24)因此,以地缘性为基础的动员方式是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促成因素之一。
(三)手机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推动
手机、互联网、3G技术等新兴媒介的兴起,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促使各种信息迅速传播、广泛覆盖和产生深远影响。一些涉及民族方面的信息,通过上网或发短信被公开乃至被歪曲后,往往引起众多群众以跟帖或者互发短信的方式扩散,使信息的受众群和影响力加倍扩大,甚至成为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通过调研发现,一些进城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人员,不仅与同一城市的同民族成员和本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其他城市的本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着包括民族关系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
另外,群体性事件是公共事件。新闻媒体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公共的判断和大众支持度产生重要影响。(25)群体性事件、新闻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中国,记者出于新闻责任感、报刊发行量、收视率等复杂原因的影响,往往以所谓探寻事件背后的真相为由,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26)而广大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又往往容易听信谣言,这就会使得舆论和民众在发生群体抗议时往往倾向于激进。
四、替代选择的缺失: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方式?
所谓替代选择,就是指通过群体行为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实现权益诉求。毕竟,相对于人民调解、行政复议、参加听证会等合法方式而言,参与群体行为的风险和成本更高,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诉求的首要选择。也就是说,存在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群体行为并不是必然选择。
(一)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限制
社会由体制内成员和体制外成员组成。体制外成员往往是一般民众、民营企业等等,他们缺乏充裕的政治参与渠道。因此,他们要么设法进入体制内,或者设法改变体制以便把自己包容进去,或者以群体抗议的方式挑战现有体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府深度地介入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过程,并为此相应承揽了过多责任。少数民族群众遇到了困难,或者有什么不满,都把政府作为自己利益的保护者,利益实现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也就把利益诉求指向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通过群体性事件进行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府或者说上级机关的信任。另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寻求解决问题时,存在利益诉求的迫切心理以及一蹴而就的观念,如果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对政府的信任将下降,采取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将会提高。
(二)有效利益诉求渠道的缺乏
政府总是告诫民众应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不能采取极端手段,更不能挑起群体性事件。然而问题是,这样的合法渠道在哪儿?中国的政治参与面临着两难困境: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是以满足国家政治体系的要求而设置的,无法充分体现不同利益群体具体的利益要求;而不同利益群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要求而进行的参与,又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参与渠道的支持,缺乏合理合法表达自己诉求的手段。即使存在一些渠道,但往往程序复杂、时间漫长、经济成本高、公信力不强,成本高昂的纠纷解决或权益诉求渠道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显得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分散的、个别的诉求无法有效地表达,逐渐地积累、汇聚、发酵,到一定时间就演进为一个群体的诉求。这个时候,借助于某个偶然事件的导火索,许多被压抑的利益诉求被集中表达出来,从而形成制度外的参与,伴随着非理性的冲动,甚至会引起暴力冲突。
(三)与政府的非良性互动
群体性事件发生与否,国家或者说政府角色的作用十分重要。如果国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强,某个具体的群体抗议就会推迟、减弱甚至避免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群体抗议很可能会接踵而至。在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中,就存在着群体行为参与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动辄采取过激行为。某些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意愿不强,能力不够,倾向于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正好契合了群体行为参与者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实现,又相应地对类似的情况产生示范和激励作用,造成恶性循环。因此,不仅要强调国家的管治能力,更需要关注政策的统一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等,不能简单化处置。
五、治理机制与对策研究
面对群体抗议,不同类型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承受能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决定的。在某些国家—社会关系中,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能够被边缘化;而在另一些国家—社会关系下,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化,起初是改良性的运动也会被推向极端。(27)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命是任何性质的政权都不会允许的,但在西方国家,像工会等以前处于体制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为体制所不容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被全面或部分地纳入了体制轨道。这样,西方虽然社会运动很多,被描述为社会运动社会,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则趋近于零,这对中国治理机制的完善是有启发的。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可以从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等入手,构筑和谐稳定的国家—社会关系。
(一)实现群体性事件的规范化预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广大群众将越来越希望对自己的事务有发言权、参与权,不仅关心政策执行,同时也关心政策制定,要求参与政治。这是许多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共有的经验。而且现在要面对的少数民族群众,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出生的,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甚至高中以上教育,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长大,他们这一代的打工经历和政治意识与他们的父辈差别非常大,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和期待,希望享受到更多改革的实惠。然而,当这种期待和实惠越来越难获得时,行为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偏激。因此,要坚持和完善民族政策法规,尊重合理的利益诉求,拓宽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把各种合理的利益诉求整合进政策之中,维护有序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降低少数民族群众进入体制内的成本并提高体制化的成效。另外,斯科特教授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中提醒要密切关注弱势群体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一些没有形成群体性事件的积怨与日常抗争。(28)这样的举动,多数情形下避免了群体性的、直接公开的反抗,但不能草率地认为“闹不出太大的动静”,因为在一定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这些日常抗争同样可能演变成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因此,要认真排查可能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引导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化存在
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准确定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避免夸大民族因素,从而影响执法公正。要通过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将调整民族关系、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首先,要坚持法制原则,畅通政府和社会的信息交流、沟通和互动渠道,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组织和制度上保障群体性事件的合法规范,引导少数民族群众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民族利益。其次,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事件时,无论哪个民族的成员,只要触犯了法律,都要依法处理,坚决反对和制止采取非法手段解决问题的行为。再次,要在各族干部群众和行政执法人员中广泛开展法制教育,不断增强民族团结观念、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其中特别要重视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使他们既严格执法、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又文明执法、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三)形成极端事件的边缘化格局
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往往伴随着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乃至暴力行为。首先是要依法进行处理,不能把一般性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当作民族矛盾,要通过协调民族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争取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支持。对卷入非法活动的大多数群众,要通过宣传、教育,示之以法,使他们懂得无论什么民族,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对不听劝阻,继续非法活动的,应当依法处置。对插手事件的敌对分子和民族分裂势力,对借机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则要依法予以坚决打击。同时要及时、全面地公开有关事件的处理情况,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另外,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等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加以引导,促使他们为化解纠纷、协调关系、促进团结作贡献。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就是增进和谐因素,控制和减少不和谐行为。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增强国家对社会冲突体制化的能力,建立一个能在将大多数社会抗议体制化的同时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科学构建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治理机制,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真谛所在。
注释:
①郝时远:《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世界民族》2000年第l期。
②本文中的“群体性事件”也可以称作“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参见Meyer,David S.& Sidney Tarrow,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8,p.12。以中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为例,该县在一项行政法规中确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群体性事件:(1)参与人数在200人以下,影响社会稳定的;(2)在国家重要场所、重点地区聚集人数在10人以下,参与人员有明显过激行为;(3)可能引发跨地区、跨行业的影响社会稳定的连锁反应;(4)根据情况,需要作为一般群体性事件对待的其他事件。
③参见陈乐齐:《我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④参见曹修伟:《浅析新疆城镇少数民族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⑤参见云南大学课题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协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⑥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⑦参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陈晋胜:《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李培林:《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第3期。
⑧参见Graham,Hugh Davis & Ted Robert Gurr,Violence in America: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Washington:Task Force o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1969。
⑨J.Wilson,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
⑩[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11)参见Tilly Charles,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p.147-150。
(12)参见Doug McAdan,Sidney Tarrow & Charles Tilly,Dynamics of Conten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76。
(13)参见Ronald R.,Aminzade et al,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3。
(14)参见Goldstone,Jack A,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47。
(15)郝时远:《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16)1970年,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一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参见Ted Gurr,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87-88。
(17)参见Durkheim,Emile,Suicide,New York:Free Press,1951,p.42。
(18)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9)郝时远:《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20)参见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98-102。
(21)关于话语对群体抗议或社会运动的影响,19世纪的社会学家多有论述。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阶级觉悟的强调,以及他本人在建构无产阶级意识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都清楚地表明他对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地位的重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以及他关于权威的分类和分析等等,均可视为话语理论的源泉。
(22)斯诺等人在1980年首先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参见Zurcher,Snowand Ekland-Olson,"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Movements: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5),1980,pp.787-801。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地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后来被统称为动员结构。参见Doug McAdam,John D.McCarthy & Mayer N.Zald 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3-154。
(23)参见Francesca Polletta,Freedom Is an Endless Meeting:Democracy 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76。
(24)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5)参见Ruud Koopmans & Susan Olzak,"Discursive Opportun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Right-Wing Violence in Germa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4,p.138。
(26)参见赵鼎新:《社会与社会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l页。
(27)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8)参见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110。
标签:政治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