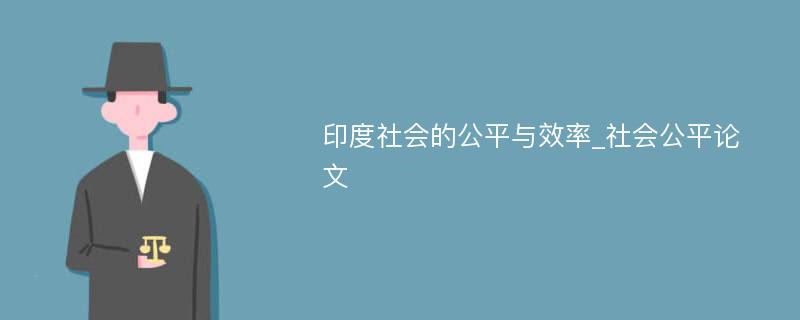
印度社会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平与效率常常仅被理解为一个纯经济学问题。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公平与效率实际上应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问题。美国学者迈克尔·P.托达罗认为:“在众多社会关系中,人们不可能真正地把不平等的经济表现和非经济表现区分开。在复杂的、常常是相互关联的因果过程中,每一因素的不平等往往会加剧其他因素的不平等。”(注:万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笔者认为, 公平与效率问题应被置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基地上去加以理解,而文化从根本上讲乃是某个民族或社会群体面对生存在世所形成的(包括宗教、政治、经济、技艺、艺术、哲学等)诸种生活方式。因此,笔者倾向于从广义上来考察公平与效率问题。
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其公平与效率问题在文化传统的类型上极为典型;作为一个第二人口大国,这一问题在非发达国家中亦有代表性。探讨印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无疑有着借鉴作用。在印度社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精神、理念层面的力量,是如何渗透和作用于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之中,从而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基本格局的。
一、印度社会的公平问题
尽管人们的行为首先与通常是由世俗利害关系的动机所推动,但我们在考察印度社会时,却完全不能不看到宗教动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印度80%多的人所信奉的印度教教义,被局内人认为是为印度不平等的种姓制度提供了“合理的”甚至“神圣的”根据。尽管印度教最古老和权威的《吠陀》经典并无明白具体的对于种姓的规定,而只是在一首颂诗(原人歌)中区别了世人的分别出自“原人”之口、臂、腿与足的不同来源。但这种本身还只有一种区别倾向的表达,后来被夸张解释并被实施为高低贵贱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这一制度成为大约3000年来印度社会结构中的一块磐石。在印度教的《摩奴法典》中,就已公开确认四种原始种姓以至派生的各个种姓的等级差别,把保护婆罗门、刹帝利两个特权种姓的地位和权利作为其宗旨。在今天,当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在西方式现代化潮流中纷纷瓦解、消蚀之际,印度社会依然令人惊讶地保持了传统的等级制,这除了有其政治、经济上的根由之外,我们也不可否认印度教对人们从灵魂深处到日常行为的影响、支配力量。
从社会的制度文明来看,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不同等级的种姓明确制定了不可逾越的行业规范。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婚姻上的内婚制,只能在同一种姓内通婚,禁止种姓之间的婚姻。为了照顾高种姓者,后来允许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为妻。但是低种姓男子与高种姓女子之间的婚姻及子女则为社会完全排斥。2.种姓地位的高低与其职业性质具有直接的联系。从事宗教活动的婆罗门被视为地位最高,在其他职业中,从事务农、经商、手工业等所谓“洁净”职业者的种姓地位高于从事捕鱼、狩猎、屠宰、接生等所谓“污秽”职业者。3.种姓地位与生活习俗直接联系。在种姓制度中,素食者的种姓地位高于肉食者,实行童婚和禁止寡妇再嫁者的种姓地位高于不遵守这类习俗者。
从社会的物质文明层面的不公平现象来看,在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上,非公正的两极分化十分突出。
独立之前的印度就是一个举世闻名的饥荒之国,大多数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据统计,仅1900年到1947年,印度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就达2650 万人(注: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9页。)。当时土地逐步集中到地主手中,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了印度的工业命脉。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宣称要以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为目标,印度政府也在五年计划中把实现“社会公正”、“消灭贫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然而,虽然独立以后的印度经济有所作为,但正如有的印度学者所指出的,印度“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先进技术的、奢侈的、垄断的和剥削的富裕世界与贫困世界。”(注:〔印〕《德干纪事报》,班加罗尔,1980年12月10日,转引自上书。)当代印度不仅贫富悬殊,而且两极分化的局面始终不减。据统计,居民中收入最高的10%在全印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50年的40%扩大到1985年的50%。70年代初,仅塔塔和比尔拉两个最大的集团所拥有的财产,就超过1亿印度人的财产总和。据印度一些专家估计, 印度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独立初期为40%,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始终保持在50%。
二、印度社会的公平问题对效率的影响
独立以后的印度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农业方面,印度政府从1965年开始推行“绿色革命”的战略,到1991年,印度稻谷产量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二位。此外,在科技方面, 印度在原子能技术、计算机软件、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印度在某些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事实,不能掩盖其社会总的效率低下的不良状况。仅就与条件相似的中国同时期相比而言,印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大为逊色。50年代初,中国除了在粮食、棉花和煤产量上略高于印度外,其余均低于印度。而今天,中国除了在科技人力上不如印度外,其他方面都全面超过了印度。中国在综合国力、竞争力的排序上,现都已远超过印度。
究其原因,印度社会效率低下的状况,显然受到了以下几种不公平现象的影响:
首先,种姓歧视所造成的民族的分散与隔绝状态,使印度民族缺乏创造高效率所必需的动力。
种姓歧视使印度人被分隔为众多地位不同的社会群体,它们彼此间缺乏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应具备的起码情感和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使印度社会特别难以团结成一个富有强力的协作整体。印度独立后,低种姓为了免受歧视,拼力为改变种姓地位而奋斗,高种姓为维持其既得利益的稳定又竭力阻挠低种姓的这种努力。这样种姓之间把许多精力消耗在争取他人的承认与尊重中去,而不是在一种平等协作的氛围中达成公正的谅解,这显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背道而驰。现代化大生产本来就需要人们在各个环节的分工与合作,而各种姓之间互不信任与配合,这势必使现代化生产难以较好地组织起来,规模经济难以形成,全社会的总体效率难以提高。
其次,种姓职业的世袭制,使激励机制难以形成,人们缺少充分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欲望。
种姓制限制了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度,它较严格地规定了不同种姓的职业范围。从效率的目标着眼,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应首先由其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来决定。然而种姓制使人不是按才能而是凭出身来选取有限范围的职业,必然导致许多人都不能或不愿从事与自己的特长及才能相适应的职业。一方面高种姓者不愿“低就”宁愿失业,另一方面低种姓者本可胜任高种姓职业的,也不能实现职业期望。这样的社会既难以充分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使人们尤其是低种姓者打消了提高能力改进工作的期待,在被限定的职业范围内,难以有主动的、创造性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激情,从而造成人才的不必要的浪费。这应是为何印度号称第三科技人才大国却未能创造出与此相应的综合国力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严重的分配不公,使少部分富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得利者,大量财富为他们奢侈的生活所消耗掉,这不仅造成发展资金的短缺,也打击了穷人的致富期望,从而延续了印度社会效率水平的提高速度。
瑞典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了长达15年的实地考察后指出: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政权都属于“软政权”,在其治理的国度里,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守政府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与其本应管束的人们和集团串通一气,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违反和抵制法规为一己的私囊进行相互交换(注: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年。)。这样的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将对国民的道德心、正义感、国家观念以及辛勤劳动的热情造成难以扭转的败坏。印度的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分配不公甚至贪污腐败所造成的,这使印度社会难以充分形成健康、正常的生产活力,难怪反腐败也是印度政府历久常新的一大口号。
印度前能源部长瓦桑特·萨蒂这样描述80年代的印度:“我们不能不看到,增长与发展仅限于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贫困的大海中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拥有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福利。”(注:转引自《国际经济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这也基本上是今日印度的真实写照。
三、印度公平与效率问题对我们的启示
印度与中国同属东方文明,且具有很多相似的国情,印度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后者有明显的借鉴作用。
首先,印度的教训表明,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足够高效的增长,就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克服只重效率忽略公平的倾向。
印度独立以来,虽历届政府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发展目标,但由于其社会结构以种姓制为基础而构成,因此在公平问题上难有根本性的转变。印度政府希望绕过这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常常难以如期完成其计划。
改革以来,我国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对于调动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多年以来,社会公平状况呈每况愈下之势,已到了反过来影响效率的地步。据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 这已经都超过了发达国家通常的指标。近几年我国贫富差异还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从印度的教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不公平现象,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明显不利的。我们不能因为否定绝对公平的错误又走向另一极端,让过度的不公平损害社会效率。
其次,印度的教训表明,加强法制建设对于克服社会的不公正和增进效率具有重大作用,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中国和印度传统上都不是法治国家。今天,印度社会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首推种姓制度。中国的社会关系中,由自然人延伸所及的社会圈子也通常超越了普遍性的国民意识。这样的社会中自发地倾向于人治而非法治,尤其是一些掌权者缺乏法律约束,过度地徇私舞弊,最容易导致大量的社会腐败和不公。因此,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严惩各种形式的违法、腐败,才能避免长期困挠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消极现象在中国肆虐。
再次,印度的情况表明,增强国民的公正、平等意识,是培育国民素质、改善社会状况的重要前提。
把种姓制视为天经地义的印度教徒,大多只知种姓和等级差别,何知什么公正与平等。因此,高种姓者可以侵犯低种姓者和贱民的人身权利,却没有罪恶、愧疚感。这种民族主体素质是妨碍印度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公平观念曾被片面地理解为政治上平等和收入上绝对平均等。但是同时,传统社会所遗留的等级观念、圈子意识仍然势力强大,讲特权、拉关系、以私人标准来区分对待圈内人与圈外人,常使社会正义难以伸张,社会信任度亦随之很不理想。近年人们目睹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明显跌落,其实问题早就存在,只是市场经济使之更加充分地暴露。从印度的教训来看,只有从树立国民应有的公平观念这一本原问题入手,才能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从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