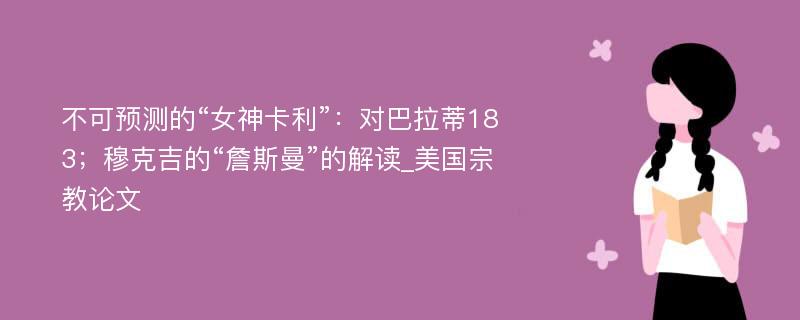
变幻莫测的“卡莉女神”——解读芭拉蒂#183;穆克尔吉的《詹丝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尔论文,变幻莫测论文,女神论文,拉蒂论文,卡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7) 03—0093—05
芭拉蒂·穆克尔吉(Bharati Mukherjee,1940—)是继奈保尔和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美文坛上熠熠生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但是,至今为止,除了《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寥寥几笔外,国内学术界并未对这位美国印度裔女作家进行过介绍和论述。穆克尔吉1940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1969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并定居美国。自197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老虎的女儿》(The Tiger's Daughter)以来,穆克尔吉致力于创作“新移民文学”(new immigrant literature)。1988年,她凭借短篇小说集《中间人》(The Middleman and Other Stories)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国家图书评论界奖”的流散作家。
《詹丝敏》是穆克尔吉的代表作之一,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介绍和解读具有牵强附会之嫌。在《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一书中,任一鸣和瞿世镜两位学者只强调小说女主人公詹丝敏的无根和“林勃”状态——詹丝敏“始终行走在一个圆上……处在这个圆周上的人便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文化的困境”(2003:150),并未梳理女主人公的多次流散经历以及其中蕴涵的反话语策略。
美国学术界对穆克尔吉的评论和接受分为两派。印度裔批评家从印度民族主义出发,谴责穆克尔吉对印度文化传统的消极描写,以及对殖民话语的妥协。而美国一些主流批评家也对《詹丝敏》颇有微词。他们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出发,认为穆克尔吉在塑造美国移民传奇时,应把第三世界移民的种族、文化等纳入美国身份政治中,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服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评论却有着共同点:流散者的主体性是建立在极端的文化差异基础之上的。在本质化主体性观点的影响下,大部分学者没有认识到:对于许多流散作家,特别是“新流散”一代来说,主体性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概念。
事实上,《詹丝敏》体现了穆克尔吉崭新的第三世界女性流散诗学的特点。从印度的“乔蒂”和“詹丝敏”到美国的“简”,再到永无止境的以“J”为首字母的新名字,小说女主人公詹丝敏试图挣脱印度“属下”阶级女性的本质化身份,并呐喊出通过不断变化的方式来反击殖民主义、男权主义和资产阶级剥削的反话语。她是流散中的“卡莉女神”,以鲜血来毁灭各种权力话语强加的僵化身份。詹丝敏的族裔身份、女性意识和阶级观念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她在困境中寻找变化的身份的政治诉求。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来剖析詹丝敏逆境求生的心灵轨迹,并论证穆克尔吉倡导的新流散诗学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其他“属下”阶层女性流散者提供了有效的斗争策略。
一
流散理论(diaspora theory)以其对当下移民现象的关注在20世纪文化批评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流散理论中最关键的概念是“根”(root)和“路径”(route)。“前流散者”操民族主义话语,深切关注民族身份或“根”。但是,这种族裔身份政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过分强调族裔身份会忽略流散者的性别、阶级、性取向等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其次,过分强调族裔身份有重建西方/东方、宗主国/殖民地等二元对立之嫌。再次,族裔身份政治把身份等同于静止、僵化的概念。最后,他们未意识到流散者身处的主流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文化。流散理论家维杰·米什拉和詹姆斯·克里夫等认为,“新流散者”强调“路径”以及身份的非线性和流动性,并以此来摆脱主流文化强加于他们的“他者”身份。同时,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对宗主国的身份政治提出了挑战。
穆克尔吉的流散诗学也反映了“新流散者”打破地域束缚,摆脱僵化族裔身份的美学理想。她认为,流散主体性的变化是一个从“无家”到“重铸家园”的过程,涉及“脱离出生地的文化”并“在新的文化中重新扎根”。(Hancock,1987:39)她强调:“在这个流散时代,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份并非他的唯一身份,破坏、成长与迁徙是如影随形的。”(Mukherjee,1997:4)詹丝敏在从印度到纽约,再到爱荷华州的迁徙和移居中,颠覆了印度族裔身份和印度民族宗教的束缚,反击了虚伪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强加的少数族裔身份,追求在不断流散中重新塑造自我的理想。
宗教信仰是印度民族身份的最好体现。詹丝敏出生于虔诚的印度教家庭,她的身份即是一位笃信印度教的乡村姑娘。但是,印度教的某些腐朽教条和繁文缛节以及与其他宗教派别如锡克教的宿世矛盾却制约着詹丝敏的身心发展,导致詹丝敏放弃宗教信仰和印度国籍,走上了“重铸家园”的流亡旅程。印度教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并已成为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印度教施行种姓制度,把人分为从高到低的四等,并宣扬避世论、因果报应论等。这些落后的教条严重制约着印度的发展。詹丝敏一出生就笼罩在“寡妇和流亡……我什么都不是,只是太阳系中的一块斑点”(1)② 的印度教预言中。她必须尊重并实践占星家的预言;她必须随家人离开拉浩村以让给更高一层种姓的人居住;她必须为自己的嫁妆烦恼,因为印度教中女方嫁妆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等。
锡克教是印度年轻的宗教,因崇尚宗教保护而经常与其他宗教发生流血斗争。锡克教在与印度教的斗争中提倡纯洁宗教,惩罚印度教徒。这些宗教矛盾给詹丝敏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也是她宗教身份觉醒的契机。锡克教徒为了给放弃“肮脏和邪神崇拜”的教徒建立“纯洁之地”,要禁止像詹丝敏等“妓女一般的女人”上街,因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纱丽是妓女的标志”。(58)结果,詹丝敏的丈夫在一次宗教流血斗争中被本来要丢向詹丝敏的炸弹炸死,使她成为象征着厄运和罪孽的寡妇。詹丝敏意识到封建宗教的危害,她诅咒道:“我要放弃神明。我要向神吐口水。”(87)宗教上的觉醒标志着詹丝敏摆脱印度宗教的束缚、弃绝印度国籍的决心。
詹丝敏初到美国的第一个身份是纽约福拉新(Flushing)印度移民聚集区法德哈拉家的借住者,美国政府虚伪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又使她在异国他乡保持印度性的梦想彻底破灭。法德哈拉先生曾是詹丝敏丈夫的老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民族差异和分裂使他无法踏上美国大学的讲坛。他为了养家糊口而背着家人做起了贩卖头发的买卖(头发属于人身体的废弃物,贩卖头发在印度教中被认为是贱民“不可接触者”的职业)。而法德哈拉夫人整天沉溺于有关印度的幻想中,生活在“天堂的小角落里”(127),例如她不断租借印度电影, 在印度电影的浪漫世界中寻找慰藉。这种林勃状态——身在美国,心在印度的“古老世界的忠实”几乎使詹丝敏窒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是要把少数族裔流散者限制在为他们划定的“文化飞地”(cultural enclave)中。穆克尔吉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控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种族传统的差异。对于差异的强调也常常导致差异双方的非人性化。非人性化会导致歧视,而歧视最后会导致屠杀。”(Mukherjee,1994)
经历了泰勒家的保姆、银行家巴德的妻子等身份之后,詹丝敏虽然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并怀上了巴德的孩子,却毅然选择与泰勒先生到加州,寻找新的身份和生活。她想“重新创造自己成千上万次”。她发誓:“我对盘腿飘浮在我家厨房火炉上的占星家低声地说:看我可以重新摆放星星。”(214)
詹丝敏对印度宗教文化的舍弃及其印度性的不断褪色和消减暗示了穆克尔吉流散诗学的局限性,即忽略了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印度性对詹丝敏反击殖民话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蒙昧的宗教教条和虚伪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重重包围中,追求族裔身份的流动性是一种无奈但行之有效的策略。詹丝敏自由身份的不断变化和显现彰显出“新流散者”以变化身份来反抗权力话语的魄力和雄心。
二
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因对“边缘”人群的共同关注而渐渐相互借鉴和影响,二者矛盾和融合的焦点是“第三世界妇女”。众多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强调,“第三世界妇女”是“毫无疑问的受害者——帝国意识和本土、外来男权主义的被忘却的遇难者”。而以莎拉·苏蕾莉为代表的理论家认为,“第三世界妇女”这一术语使这些女性陷入“对‘边缘性’的伤感而投机性的迷恋中”③。这种“新东方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女性描写成无知、贫穷、蒙昧以及墨守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因为它忽略了现实中第三世界女性的物质和历史差异,同时陷入了西方妇女将第三世界女性他者化和奇景化的殖民视野中。
第三世界女性为了摆脱本质化身份的束缚必须“说话”。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C·T·莫汉蒂在其后殖民批评经典《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学识与殖民话语》(1984)中不仅对西方妇女的女性帝国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同时还描绘了第三世界女性的“抗争版图”,以“流散版图”说明女性流散者身处帝国中心的尴尬位置,鼓励第三世界妇女应结成政治联盟,从阶级、宗教及性别的层面考察女性问题,打破“第三世界妇女”的刻板形象。詹丝敏通过挑战印度教极端男权和西方帝国主义男权,挣脱“受害者”的女性身份,努力解除制约女性自由生活的障碍,追求“属下”阶层女性的解放。她的“说话”是反抗东西方男权主义的最强音。
詹丝敏的女权主义意识在印度早已觉醒,她已经踏上了改变自己身份——没有嫁妆的印度教乡村女孩的道路。她英文出色,并常常代她的哥哥写信,掌握了为男性所垄断的表征能力(笔是隐喻性的男性生殖器)。她勇于追求理想:“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并在大城镇里设立自己的诊所。”(45)她放弃“殉夫”习俗(印度教妇女在丈夫的葬礼上自杀以显示其贞洁)标志着她反抗印度教男权主义、追求女性解放的勇气。除此之外,詹丝敏婚后还与其他家庭主妇加入推销洗衣粉的行列,有了一些积蓄。她追求女性解放和经济独立的斗争正好与西方女权主义者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的宣言不谋而合。
“属下”阶层妇女不仅是本民族男权主义的受害者,还是西方帝国主义男权的牺牲品。詹丝敏杀死强奸她的船长“半脸”标志着她拒绝“受害者”的角色,颠覆西方帝国主义和男权的双重压迫,同时也是她女性身份转换中的最关键步骤。她没有因失身而自杀并屈从于女性受害者的身份政治,而是使用刀(象征男性生殖器)刺人船长的身体。这标志着詹丝敏从懵懂走向醒悟,是一种逆转性、策略性的反抗。詹丝敏即是印度教中的毁灭女神——卡莉女神,她“展开我的舌头,在上面划了一道口子”(105)。卡莉女神詹丝敏的破坏和重组力量彰显了一种革命性的女性政治——对男权的反抗需要积极摆脱本质化的女性身份,并转换性地挪用曾为男性中心主义服务的武器来反击。
在美国这个西方女权主义的发源地和战场,詹丝敏从女权主义的支持者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泰勒先生的妻子薇丽离开泰勒先生,与她的真爱斯图亚特到巴黎生活。这使曾在泰勒先生家做过保姆的詹丝敏充分理解了女性追求自由的权利。在经历她的另一种身份——银行家巴德的妻子时,她把这种权利发挥得淋漓尽致。她虽怀着巴德的孩子,却拒绝嫁给他。在小说的结尾处,她接受了泰勒先生的爱,并和他一起走上了通往加州的路。詹丝敏的决定并不是仓促的,相反,过去的经历和对女性身份的崭新理解使她充满信心:“我并不是在男人中选择……我并不感到耻辱,而是解放。”(214)
虽然穆克尔吉对詹丝敏的塑造一味强调女性的解放,忽略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后女权主义者提倡的男女互补性。但是,詹丝敏确实为第三世界妇女提供了女性解放的可行模式。她们再不是“白人父亲”眼中温顺、贞洁的“殉夫”女,也不是“白人母亲”眼中无知、守旧的家庭妇女。第三世界妇女要获得女性自由,必须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精髓,通过不断摆脱女性僵化身份的途径达到对东西方父权制和西方帝国主义男权的解构。
三
第三世界女性的经济压迫和阶级地位常常与种族和性别一起决定着她们的文化身份。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加亚特里·斯皮瓦克认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许多国际跨国公司把工厂开在具有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第三世界。这种经济剥削引起了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合理,而其最严重的受害者恰恰是妇女。以印度“属下”阶层妇女为例,她们不仅是印度统治阶级的剥削对象,更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受害者。
斯皮瓦克借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重新阅读马克思,认为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忽略了第三世界殖民地臣民的困境。作为“属下”阶层的殖民地女性,必须通过颠覆和积极改变霸权意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抹杀人的真正物质、经济状况的“错误意识”,采取激进的破坏活动,才能彻底改变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妇女的命运。詹丝敏的阶级地位经历了从农家女儿、无产者的妻子、社会底层的流散者、白人的保姆到美国大学的印度语言教员和银行家巴德的妻子的过程。从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妇女到美国中产阶级们的精神支柱,詹丝敏的改变颠覆了充斥着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打破了传统国际劳动分工的局限。
作为印度的农家女儿和无产者妻子的詹丝敏虽无法摆脱天生的阶级地位,但她不囿于自己传统阶级的决心已经初见端倪。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殖民,首先是从改革农村的土地田赋制度着手改变印度农村古老而稳定的村社制度,掠夺财富,使印度农民愈加贫困,加剧了印度农村的贫富分化。家庭贫穷的詹丝敏每天必须做繁重的家务,生活条件与家有私人厕所和电灯的朋友相差千倍。她甚至没有印度教中决定女方地位的嫁妆。但詹丝敏改变自己阶级地位的决心没有停止:她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她想与丈夫建立属于自己的“维杰&妻子”商店; 她在丈夫死后发誓“不再爬回哈斯那普尔和封建主义。那个乔蒂已经死了”(87)。逆境中的詹丝敏已经建立了弃绝农家女儿和无产者妻子的阶级身份的决心。
在泰勒家做保姆是詹丝敏(已改名为嘉斯)阶级意识的转型期。在主流社会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她开始意识到“属下”阶层妇女与美国资产阶级应是平等的:“乔蒂会积蓄钱财。但乔蒂现在是殉夫女神;她已经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用栅栏围起的汽车旅馆后面的葬礼柴堆上自焚了。詹丝敏只为未来,为了‘维杰& 妻子’而活。嘉斯上电影院并为今天而活。”(156)她称自己是“白天的妈妈”而不是保姆;她凭自己的意愿挥霍浪费或积蓄钱财;她想要成为一个“幽默、聪明、文雅、柔情”(151)的人,即与白人资产阶级平等的公民。詹丝敏的改变不是对白人资产阶级的刻意模仿或崇拜,并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而是为摧毁白人眼中的“属下”阶层刻板形象所做的努力。
作为美国大学的印度语言教员和银行家巴德的妻子的詹丝敏在反抗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进入美国资产阶级心脏的她解构了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和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突显出美国资产阶级对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依赖性。詹丝敏在哥伦比亚大学印度语言系兼职教授印度旁遮普语时,甚至有一位拥有福特基金、研究旁遮普地形变化的人找她担任导师。在银行家巴德的家里,詹丝敏扮演着巴德夫人的角色,但拒绝嫁给他。而当巴德双腿残废,生活不能自理时,詹丝敏又成了他的支柱和依赖。詹丝敏进入以银行家巴德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并逆转性地成为他们的导师和精神支柱,标志着詹丝敏彻底打破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女性的陈旧形象,是对美国资产阶级的嘲讽和重重一击。
虽然詹丝敏阶级身份的改变具有模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渴望成为美国资产阶级一员之嫌。但是,詹丝敏最终放弃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体现了少数族裔女性不愿与具有剥削本质的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正直品质。在“美国的希望与古老世界的责任”(214)之间,詹丝敏选择了后者,即改变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女性“受害者”,反击美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在近40年的批评和创作生涯中,穆克尔吉一直致力于重新界定第三世界女性流散者的形象。她们的生命是“不平凡并且常常是英雄式的……虽然她们受到新生活或职业的挫折和伤害,但她们并没有放弃。她们为了解决问题而甘冒在古老而舒适的世界中从未冒过的险。当她们转变国籍以后,获得了重生”(Mukherjee,1988)。在族裔、性别和阶级等因素交织的权力网络中,穆克尔吉把詹丝敏这一典型的第三世界女性流散者塑造成为“斗士和改革者”(40)。她坚持着破坏即创造的理想:“世上没有无害而温柔的重塑自我的方法。我们杀死曾经的自我,以梦幻的意象获得重生。”(25)
虽然在穆克尔吉新流散诗学观照下的女主人公流露出浓厚的个人主义的色彩,即一味强调个人自由,忽略了第三世界女性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殖民主义、男权主义和资产阶级剥削等重重包围中,变化是一种无奈却有效的反话语策略。卡莉女神詹丝敏打破了第三世界女性守旧、无知和贫穷的刻板形象,并以不断变化的文化身份(神灵显现)来反击文化霸权(恶魔)。她的毁灭即重生的生存哲学无疑为众多“全世界受苦的人”,特别是流散女性,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收稿日期:2006—04—02
注释:
① 卡莉女神(Kali)是印度教中湿婆神的配偶神,是毁灭的象征。卡莉女神变幻莫测,时而形态优美,时而变化成具有黑色身体、四只手臂,吐着血淋淋舌头,以驱除恶魔的女神。穆克尔吉曾说道:“詹丝敏就是卡莉神,毁灭女神。”
② 以下凡出自Jasmine一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另注,参见Bharati Mukherjee著Jasmine,1989年出版。
③ 莎拉·苏蕾莉在其专著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中的原话。摘引自莉拉·甘地的Postcolonial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8年出版,8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