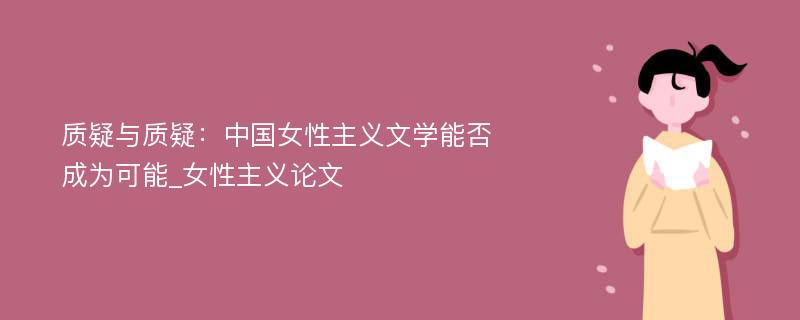
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的印象中,对于女性(女权)主义文学与批评这种西方的他者话语,中国的作家与批评家一开始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的。但是近年来,女性主义却在中国突然受到了青睐:一些女性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聚集在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大旗之下,一些批评家则乐观地宣称,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已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诞生在一片绯红的霞光之中。然而,伴随着欢呼与喝彩,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却也布满了一些疑点。下面,笔者仅从中国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女性作家的写作策略出发做一简要剖析,以期引出问题并且就教于大方之家。
妇女解放:走出异化与走进异化
众所周知,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是妇女解放进程中的直接产物。由于伍尔夫、波伏瓦等人的前期理论铺垫,也由于60年代以来知识阶层精英妇女的加盟和倡导,使它最终成为席卷欧美全社会的、三十多年来方兴未艾的政治文化运动。这么多年来,无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如何更迭嬗变,其逻辑思路却是基本一致的。她们都认为,在这个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世界上,女人从来都是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从来都没有与男人“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1〕。 既然“女人在本质上并不低下,而是后天的文化使之低下(Women are not interior by Nature but interiorised by Culture)”〔2〕,所以,积极行动起来,挣脱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锁链,粉碎千百年来已经成型的男性话语机制,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事。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成为了一种“行动的美学”,写作既是对文化、政治的强有力介入,也是对菲勒斯中心语言的摧毁,同时还是对女性自身的自我拯救。
如果从表面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女性面对着的是一个基本相同的文化语境。因为在西方有女人是由男人多余的肋骨制造而成的文化神话,在中国也有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儒家思想的经典命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先在地把女人置于了一个从属的、卑贱的地位。但是从20世纪开始,尽管在中、西方的历史舞台上都上演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大型剧目,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又使得中国女性面临着远比西方女性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肇始于“五·四”时期。由于受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和启迪,当时的知识女性大都意识到了她们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因为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浸淫,女性已经由人而被异化成了物。于是,“玩偶”便成了描绘女性自身处境的一个形象、贴切的词汇,如何摆脱玩偶的命运便成了她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这种觉醒的意义是重大的。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走出玩偶角色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行动也往往以离家出走的消极反抗为主,反抗的结果又往往是鲁迅所说的要么回家,要么堕落,但是,这种反抗所构成的姿态却第一次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大写的人,既然女人也是人而不是物,那么就应该还女人以人的地位和尊严,使女人和男人处于同一条精神的地平线上。其后,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文学本文中,都时隐时现地回荡着这个主题。直到70年代末,舒婷还在执着地重复着这种声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3〕没有人认为这种声音陈旧、飘渺不切实际,相反, 女性反而从中受到了莫大鼓励,获得了莫名的激动,从而也仿佛回忆起了被岁月尘封多年突然又被释放出来的种种往事。
必须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其实是一场抽去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运动,亦即女性的觉醒仅仅意味着她们意识到了自己如何才能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人,却没有使她们意识到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女人。这也难怪,当女性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终于有了解放的希望时,她们完全有理由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自己的性别。于是,淡化而不是强化自身的性别意识,否定而不是肯定自己的性别角色便成了妇女解放运动之初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然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起点上的,这意味着它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补充、需要具体、也需要否定之后的否定。那么,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究竟又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命运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49年之后。如果说妇女解放在“五·四”时期还只是一种口号或理想,那么,在1949年之后则是演变成了千百万妇女的实践行动,而行动的依据便是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论主张,它生动浅显地阐明了妇女的地位、作用以及在新的时代里妇女所应该具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于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便成了一声响亮而迷人的召唤,“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便成了一种富有浪漫气息的理想典范。由于时代新风尚的熏染,女性开始在服饰、发式等方面抹去自己的性别特征,并以茁壮结实的体魄取代杨柳细腰的生理特征而趋近于“铁姑娘”的模型,以坚贞不屈的铁石心肠取代风花雪月的满腹柔情以使自己更有李铁梅似的心理特征。经过时代熔炉的锻打,女子终于由女性而中性,由中性而男性,完成了自身意味深长的一次蜕变。
按照我的理解,妇女解放的本质除了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外,还应该具有开发自身性别潜力、擦亮自身性别魅力的特征。即女性必须清除长期以来渗透于她们身心中的男权意识,矫正和释放被男性社会压抑已久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僵硬走形的女性意识,从而为自身开辟一块独立而富有诗意的存在空间,以健康舒展的生命活力给这个坚硬而冰凉的理性世界带来暖意和柔情。于是,女人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女人便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然而,纵观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否定之否定,恰恰相反,而是加大了第一次否定的力度,从而使其消溶于人为的片面性之中。从长远的情况看,这种负面作用对妇女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当那个可悲的时代结束之后,尽管女性可以意识到这种变异并且可以佐以洁士苗条霜和太太口服液还原自己的生理特征,但是由于滞后性,她们却无法马上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无法马上清除投射于自身心理当中的男性因素。于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多见那种动辄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急便粗声大气、撒泼骂街的女性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在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本文实践中,我们也多见那种操练着改装过的男性话语,在思维方式和表情达意方式上都让男性自叹弗如的女强人形象;而在近年来的肥皂剧和电视小品当中,编导们更热衷于以夸张的喜剧化手法把那种满脸横肉极富阳刚之气的大女子和干精疲巴极富阴柔之美的小男人组合搭配到一起,让他们制造噱头,换取掌声。仔细想想,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吗?这难道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流风遗韵”吗?在这些真实和基于真实而虚构的历史场景中,隐藏着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残酷荒诞的东西,而所有这些却都被一声阴盛阳衰的慨叹给轻巧地遮掩了。在这个定理面前,我们失去了探究的兴趣。
假如以上的分析大体准确,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妇女解放的正常逻辑演进路线本来应该是摆脱物化——获得人的尊严——还女性以本来面目,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条“物——人——非女人(女性男性化)”的奇怪线路。这种现象表明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最终已滑离了它既定的运行轨道,而演变成了两性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女性充分运用了“以毒攻毒”的战略战术思想,所以便很快冲垮了男性阵营的防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注定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女性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们本来是要走出异化,还原自身,不经意间却走向了新的异化之途;她们本来应该敞开自身,使健康活泼的女性意识释放出来,但是长期以来,女性意识却被遗弃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蒙上了越来越厚的灰尘,处在了种种遮蔽之中。而她们自己却戴起了愈来愈强大的人格面具,游走于自己为自己设计的喜剧情境中,既悲凉,又滑稽。
我以为,这便是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所探测到的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语境,当我们来谈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时,把它置于这样一个语境之中是很有必要的。
女性话语:诞生的艰难与存在的尴尬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经不起理性追问的。因为它并不是妇女解放运动逻辑演进中的必然产物,也不是像西方那样经过了女权、女性主义两个阶段,通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才终于理清了自身的逻辑走向。回顾20世纪初期、中期中国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我们基本看不到女权或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或者即使有,它也只是融入了女性解放的这场大型的政治话语中而无法显示出个人话语的清晰。事实上,在那个非常的时代里,女性话语与其说没有价值,毋宁说它已被剥夺了自身价值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十多年前,当一些女性在文坛上叫响了自己的名字时,她们也仅仅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的。跟她们的前辈一样,她们也没有意识到写作时自己所扮演的性别角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新的时代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需要她们动用的是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是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而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妇女解放运动已在许多方面划上了句号,女性作家缺少现实经验的刺激,其性别意识的激活便也显得不太可能了。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她们所叙述的故事,使用的话语与男性作家大同小异,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事实上,她们的话语也确实汇入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新写实等文学思潮的主流话语中,成了这种文学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部。90年代以来,只是由于女性主义这种他者话语的渗透和启迪,大多数女性作家才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写作身份,但是她们写作的动因和最终目的是什么,似乎却仍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为什么会模糊不清呢?我以为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在中国,妇女解放主要是被纳入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操作之中的,这意味着女性在面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时,已由原来主动争取的革命热情逐渐变成了被动提升的心理满足。而当男女平等的思想被卓有成效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之后,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文化运动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便在中国丧失掉了某种先锋的姿态,它无法在公众层面激活女性的兴趣和热情。女性主义如入“无物之阵”,自然显得尴尬。第二,中国多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没有松动男性话语的根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因为女性男性化的潜在含义是女性首先肯定了男性话语的价值和合法性,并进而与男性一道分享了男性话语的权力、威力和魅力。由于这两个原因,女性作家在借用这种西方的他者话语时便没有多少充分的理由;同时,缺少公众的支持与配合也意味着她们并不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女性主义读者群。于是,她们的写作走向了空洞,显出了孤单。
因此,当中国的女性作家选择了女性主义姿态进入写作时,不管她意识到没有,她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中国,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女性意识的稀疏和淡薄,也正是由于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扭曲和强奸,所以才激起了一些女性作家擦亮女性意识、建立女性话语的冲动。如此一来,我们便为女性主义写作找到了一个崇高而神圣的理由。这样,我们便有必要对建立女性话语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作出分析。
考察中国作家女性主义写作的逻辑起点,她们大都对伍尔夫那个通俗易懂的经典命题发生过兴趣:“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4〕然而,仔细思考这句20 世纪初的名人格言实际上并不怎么适合于20世纪末的中国女性作家。因为伍尔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时,她想说明的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写作环境对于女人的重要性。因此,只有先有了钱和屋子,女性才可能平心静气地写小说。按说,这种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新鲜,而且,就大多数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而言,她们通常好像是在既有钱又有屋子的情形下开始自己的写作的,要不就是她们刚写小说不久便有了些钱也有了自己的屋子。如此看来,她们似乎没有必要边写小说边念叨屋子问题,因为她们拥有了写作小说的前提条件。可是事实上,她们又确实对这句名人格言发生了兴趣。那么,为什么她们会发生兴趣,她们与这种表述的共鸣点又在哪里呢?
我以为当中国的女性作家在重复着伍尔夫的命题并呼吁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时,其象征意义是远远大于其现实意义的,尽管中国的女性作家并不具有全盘接纳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但是,女性主义的激进姿态毕竟照亮了中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点透了她们写作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因此,作为女人说话便成了一种诱惑,成为她们写作的一个动因。于是,虽然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屋子,但是她们仍然希望这间屋子能延伸到自己的心理生活中,把它作为表达自己的屏障或掩体。作为一种心理意象,这间屋子具有隔断喧哗的男性世界声音的功能。所以,面对世界,它不是敞开,而是关闭。唯有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里,女性才可能潜思默想,收心内视,清理自身异己的经验内容,打捞自己的女性经验,寻找那种业已稀疏的已经被社会理性层面掩盖和遗忘的东西。在这种寻找中,与其说她们想证明什么,毋宁说她们首先想获得的是一种冒险的乐趣、破禁的快感和给自己带来假想满足的心灵陶醉。
然而,当女性作家以写作的方式说话时,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肖珊娜·费尔曼的疑问:“作为一个女人,就足够可以讲女性的话吗?‘作为女性说话’(Speaking as a woman)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某些生理条件决定的,还是由一种策略和理论上的立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女人的话语是由解剖学还是由文化决定的?”〔5 〕如果从心理分析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疑问也许不难回答。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被我们所发明的语言操纵着,或者说主体被一种无形的但却是强大的客体力量所诱导、所塑造,主体因而失去了阐释自己的能力和资格。因此,作为个体的人,表面看来是他在自说自话,他说着自己的话,而实际上他被一种意识不到的文化话语程序的深层结构所控制,于是话被他说着变成了他被话说着。如果这种理论是合理的,那么任何人都难逃这种规则的“法网”,男性如此,女性亦如此。
如此看业,女性作家要想真正表达自己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她们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如前所述,女性作家在心理上拥有了自己的屋子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寻找与打捞自身的女性经验,但是按照弗洛姆的观点,任何经验要想成为经验,它必须首先被语言所固定,然后才能被我们所察觉。“语言由于它的用字、文法、结构,以及其中所含藏的整个精神,决定了我们如何去体验,以及何种体验能透入我们的知觉。”〔6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语言是被千百年来的男性文化为核心的内容所浸泡、修剪、润色的语言,如果我们也承认任何人必将被语言支配而自己没有主宰语言的能力,那么,女性作家将凭借什么去开掘自己的经验呢?女性存在一种属于自己的经验吗?因为很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女性并不拥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的话语意味着她们并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经验。语言的压迫“使妇女处在沉默的状态中。妇女好像哑巴一样,不管她有多么复杂的经验,到头来连一个字都说不清楚”〔7〕。 而一旦开口说话——以写作的方式打捞经验,她们势必会陷入新的尴尬中。因为她们打捞的经验终究不过是变形走样的经验,她们所说的话在其深层上依然不过是男性话语的一种变体。在此意义上,女性写作透露出了某种宿命的味道。
事实上,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也早已意识到了女性的这种困窘,然而与此同时她们又认为,要想摆脱这种困窘又只有依靠写作。可是既然女性写作在男性话语中存在着被异化的危险,她们将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去保卫女性写作的纯洁性呢?埃莱娜·西苏认为,妇女在通常的意义上进行写作是无济于事的。要想摧毁菲勒斯中心的语言体系,“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如此才能横扫原有的句法学,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无法被攻破的语言。这样,如下领域便成了女性话语的核心内容:
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地和逐渐地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8〕
很显然,在埃莱娜·西苏看来,通过身体写作首先是女性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它试图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示威和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在被中心话语放逐的边缘地带,女性正在倾听着来自自己身体的神秘声音,并且通过这种倾听,女性正在建构着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这是女性写作的希望之光。
由此来反观中国的当代女性写作,我们对以自恋和私语为其基本内容和形式的叙述话语便不再会感到陌生。表面看来,自恋可能是一种姿态或象征,因为它表明了对男性文化的拒绝和对男人为她们设计的“反自恋”〔9〕模式的逆反,而且通过自恋, 女性也显示了一种优雅的精神情调;但是实际上,自恋的内驱力却显然是来自女性身体的与性有关的幻想内容和经验内容。于是,我们才会在《与往事干杯》(陈染)中看到肖濛常常脱得一丝不挂,对镜顾影自怜;才会在《一个人的战争》(林白)里看到多米在自身欲望的煎熬中,走向了“来自自身的虚拟的火焰”的爱情;也才会在《双鱼星座》(徐小斌)中看到卜零宁愿在性的焦渴中自慰,却不委身于世俗的男人。这些来自生命本能骚动的、非理性的、黑暗的、以往羞于示人的、白日梦般的女性经验构成了自恋的巨大底座,于是,中国女性作家的本文实践也正好暗合了埃莱娜·西苏的理论呼吁。
另一方面,以自恋为其核心内容的女性叙事话语又不可能进入主流话语之中,这样,私语便成了表达这种内容的唯一形式。所谓私语,首先意味着女性写作失去了假定的接受对象,她们在那间属于她们的“自己的屋子”里喃喃自语,独自享用。自己既是话语的生产者,又是话语的消费者,写作因此成了一种孤芳自赏,成了为自己的写作。同时,私语的形式无疑也是对自恋的一种强化。
当一些女性作家在一个新的基点上以自恋和私语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旅并企图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时,我很怀疑她们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进而也怀疑女性写作的纯粹性和女性话语的真实性。因为男性文化既然可以侵蚀语言,它同样也会渗透到人的无意识深处,这样,通过身体写作所做出的拒绝和反抗将难免显得徒劳。退一步说,即使这种经验内容是一块保存完好、未被男性文化开垦的处女地,这里面结满了非理性的欲望之果,只有女性才可以绕过语言的围墙以超常规的方式把它们采摘下来,那么这种采摘下来的内化于文学本文中的非理性之果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当今中国,显然不存在一个庞大的女性阅读群体,女性写作因此常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即便有了这样一个群体,已经被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修理过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异的女性读者能认同她们的话语吗?另一方面,对于男性读者,我相信他们的阅读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动机。于是,女性作家所公布的具有私人档案般的女性经验在男性读者那里演化成了一幅幅极具观赏性的画面,在合法性的窥视中,男性读者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并享受到了窥视本身所带来的乐趣。
因此,对于真正的女性主义文本而言,也许所有的男性阅读都是误读。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女性文本的阐释权和评价权往往又操纵在男性的手里,于是,一种女性作品的问世,我们最先听到的往往是来自男性世界的喝彩。在这种喝彩声中,通过身体的女性写作走向了荒诞。
结束语:问题与担忧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只是想指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并不想对女性主义本身进行什么价值判断。事实上,当人们使用“女性主义文学”这一称谓来指称“后新时期”所出现的一些文学事实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它表明了我们的文学理论界已失去了某种命名的能力和兴趣。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批评家,或许正是作家的首先挪用才为批评家的挪用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不过,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情形:中国作家挪用西方的写作套路写小说,中国的批评家又挪用西方的批评话语对这些小说作出评论。作家的生产刺激了批评家的消费热情,批评家的品评与定位又增添了作家的生产豪情。如此循环往复,却原来都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之上。这种生产与消费的竞赛活动持续久了,可能最终会耗尽作家与批评家原本就不多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使写作成为复制,使批评变成复述。
因此,当许多人面对中国目前的女性主义文学采用了鼓吹的姿态时,我却以为有必要为它担忧。
注释:
〔1〕西蒙·波伏瓦《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P9。
〔2〕见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P228。
〔3〕舒婷:《致橡树》,见《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P16。
〔4〕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92年版,P2。
〔5〕〔8〕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50,P200—201。
〔6〕见《禅与心理分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P158—159。
〔7〕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P134。
〔9〕埃莱娜·西苏语。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P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