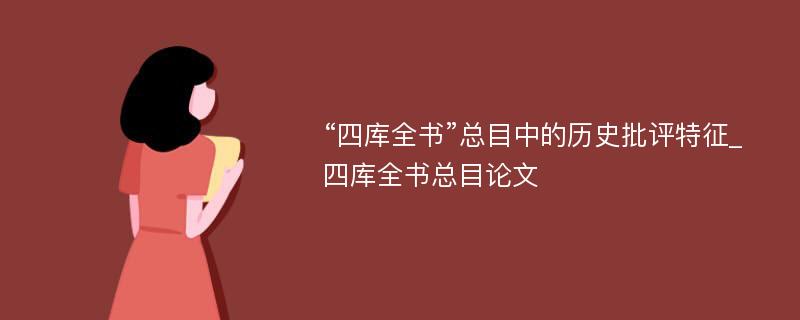
《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目论文,史学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样,由于《总目》以书目形式,“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指陈得失,比较优劣,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故而在史学批评史上也有着不能忽视的地位。
区分类聚以示史法
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撰写《史通》,对唐以前史籍及史学发展进行评述,所常用的方法就是“区分类聚”,以类相从,评其流变。刘知几的这一做法,深得《总目》赞赏,称“刘知几深通史法”,并受其影响,在评论史书时使用了这一方法。《总目》史部的《纪事本末类小序》、《别史类小序》、《杂史类小序》、《传记类小序》中多次讲到“以类区分”、“必以类分”、“皆得类附”、“著书有体,焉可无分”、“略为区分”等,足见《总目》对这一方法的重视。《总目》的分类还体现出一种批评的原则,也是评论史籍的一种方法。
《总目》把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将所有的史书全部纳入这十五类中进行评论。每类中又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分类,如传记类著作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类。《总目》这样做,决非仅仅是把历代典籍按类划分,便于编录而已,它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在里面。
一是尊正史、重编年的思想。《总目》特重正史,在《史部总叙》中说:“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注:《总目》卷45《史部总叙》。)明确指出正史是“大纲”,其它类别在地位上与正史是不平等的,编年至载记参考了正史的纪传,时令至目录参考了正史的志,史评参考了正史的论赞,皆受正史启发而分类。《总目》还进一步指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注:《总目》卷45《正史类小序》。)将正史提高到与经并列的地步。尽管《总目》推尊正史,但对编年也特别重视。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将纪传、编年作为中国传统史书最为重要的两种体裁进行论述,《总目》深加赞赏,以为“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只不过是纪传体历代相续,记载不断,而编年体时断时续,没有贯穿历代而已。(注:《总目》卷47《编年类小序》。)
二是寓经世思想于分类之中。如史部“地理类”之下划分为若干小类,其分类就体现了正宗思想,“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注:《总目》卷68《地理类小序》。)这种分类明显地体现出两种思想,一是拱卫王室,天下一统的思想,二是分辨方域、经世致用的思想。再如“职官类”下分官制和官箴两类,其目的一是“稽考掌故”,以备文献,二是“激劝官方”,(注:《总目》卷79《职官类小序》。)以肃清吏风。体现的同样是经世的思想。
三是分类以明通变,在分类的基础上分析著述流变。所谓“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叙,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如“史钞类”,从孔子删《诗》、《书》讲起,其后有卫飒的《史要》、张温的《三史略》、葛洪的《汉书钞》、张缅的《晋书钞》。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史钞不断发展。到宋代,史钞更加发展,有“离析而编纂”者,有“简汰而刊削”者,有“采摭文句而存”者,有“割裂词藻而次”者,名目繁多。到明末,编纂史钞之风更盛,“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注:《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经《总目》这样探源考流一分析,“史钞”的源流、得失就清楚了。
历史考察以见褒贬
《总目》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评论历代典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宏观把握学术流变,进而确定史家史著在这其中的位置。二是辨章学术,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而确定各流派、各思潮在本学科演进历程中的位置。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总目》在评论这方面的问题时,就是通过宏观把握史书体裁的流变来确定史家史著在这方面的成就的。比如,《总目》指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形式,除最古老的记言、记事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最早是编年体史书,及至司马迁出现,创立纪传体,遂有编年、纪传共同发展的趋向。所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编年、纪传各有弊端,“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到了宋代的袁枢,又因《通鉴》旧文,排比史事,详其始终,创立纪事本末体,该体裁“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其优点是“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注:《总目》卷49《通鉴纪事本末》条。)此后,仿效之作层出不穷。通过这种纵向的动态考察,确立了袁枢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开风气的地位。
由于《总目》运用了历史考察的方法评论史籍,故而凡在史书体例上有创新的史著,都得到了佳评。宋人倪思作《班马异同》,比较《汉书》、《史记》书法与内容的异同,是一部史学比较的专书,《总目》称为“创例”。(注:《总目》卷45《班马异同》条。)司马光作《通鉴考异》,《总目》认为“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注:《总目》卷47《通鉴考异》条。)马骕撰《绎史》,在体例上进行了很多革新,他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吸收了各种编纂体例的优点,创造了一种“新综合体”。对于这种崭新的体例,《总目》极加赞赏,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注:《总目》卷49《绎史》条。)清初官修《明史》,打破旧史历志无图的成规,根据晚明科技发展的新态势,在《历志》中增加了图,《总目》认为《明史·历志》的体例创新是“时异事变”的当然产物。“历志增以图,以历生于数,数生于算,算法之勾股面线,今密于古,非图则分划不清”。(注:《总目》卷46《明史》条。)
《总目》在评论典籍的价值时,不仅注意到流变中的创新,还特别关注“源头”上的开辟作用。如评《晏子春秋》,“《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注:《总目》卷57《晏子春秋》条。)如评价《孙子》,“(孙)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注:《总目》卷99《孙子》条。)再如评价《伊洛渊源录》,“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注:《总目》卷57《伊洛渊源录》条。)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情况。中国古代学术批评,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总目》中的不少地方,也显示出这样的批评思路。尤其是在评述古代学术分合以及古代学者的治学风格和学术风貌时,用得更多。如《闽中理学渊源考》条云:“宋儒讲学,盛于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辗转授受,多在闽中。”(注:《总目》卷58《闽中理学渊源考》条。)几句话就点明了从二程到朱子间递相传承的学脉联系,从而确立了各人在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又如元代吴澄撰《春秋纂言》,其中吉、凶、军、宾、嘉五例与宋代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相似,遂被人疑为蹈袭张氏,《总目》分源别派,从门户出入中辨明吴澄未袭大亨,“盖澄之学派,兼出于金溪、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于苏氏。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注:《总目》卷28《春秋纂言》条。)《总目》通过辨析学术源流,不仅为吴澄辨诬,而且指出其书优长之处,可谓评论至当。
《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固然很重视分源别派的学脉辨识,但又不把这一方法模式化,它能注意到学术传承中的“承”与“变”,这样,就使得自身的评论更接近合理。如在《明儒言行录》条中指出:“(沈)佳之学出于汤斌,然斌参酌于朱陆之间,佳则一宗朱子。故是编大旨,以薛瑄为明儒之宗,于陈献章则颇致不满。虽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弟子则删汰甚严,王畿,王艮咸不预焉。”(注:《总目》卷58《明儒言行录》条。)《总目》通过对汤斌、沈佳师生不同的学术趋向的辨析,指出沈佳《明儒言行录》的著述要旨,同中辨异,清晰明朗。
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史家、任何史著都不可能独自具备完整的意义,他(它)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在对他(它)们进行评价时,也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认识。《总目》穷源竟委的历史考察方法,就是在发展演变中把握全体中的个体,进而确定个体在全体中的位置,从而发现批评对象更为深刻的内在本质。
比较异同以论得失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的方法有着长久的渊源和广泛的运用,许多史家通过比较历史、辨析史学,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物的看法。《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自觉继承这一传统,通过比较来判定史著的得失、史家的高下。
对于比较批评的功能和意义,《总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所谓“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注:《总目》卷186《坡门酬唱集》条。)“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 与遣词之巧拙”,(注:《总目》卷195《优古堂诗话》条。 )也就是说,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看出作者的才气的大小、文章笔法的拙巧以及作者著述旨趣和著作思想内容的异同。也正因为此,《总目》对倪思撰《班马异同》,比较《汉书》与《史记》,“以参观得失”的做法极为推赏,认为倪思将“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焉”。(注:《总目》卷45《班马异同》条。)
《总目》运用比较方法评论历代学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比较作品的价值,二是比较学识的异同。
比较作品的价值,是《总目》最常见的内容。如《总目》在评论王称的《东都事略》时说:“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称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已,固宜为考宋者所宝贵矣。”(注:《总目》卷50《东都事略》条。)将《东都事略》与李焘、李心传之著作相提并论,以见其价值之大小。又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条中说:“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注:《总目》卷4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条。)通过比较突出了李心传著作的史学地位。再如《总目》将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与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进行比较,指出士奇之书“以列国事迹,分门件系,……大致亦与冲书相类。然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则以国为记,义例略殊”。(注:《总目》卷49《左传纪事本末》条。)将两书在编纂形式上的异同讲得非常清楚。又如宋人章如愚著《山堂考索》,《总目》将其置于同时代的著作中,通过比较揭示其价值,指出该书“在宋人著述之中,较《通考》虽体例稍杂,而优于释经;较《玉海》虽博赡不及,而详于时政;较《黄氏日抄》则条目独明;较吕氏《制度详说》则源流为备。”这样的横向比较,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山堂考索》及与之有关著作的优长短缺,即所谓“武库之兵,利钝互陈”。(注:《总目》卷135《山堂考索》条。)
《总目》利用比较方法评论作品价值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认识。《总目》认为,在记事上,《旧五代史》是“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而《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该具,而断制多疏。欧公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在体裁上,《新五代史》“止述司天、职方二志,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征”,“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于文献”。在风格上,《新五代史》“其词极工”,“文章高简”,《旧五代史》“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但无论两书多么不同,其价值不能互替,“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注:《总目》卷46《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条。)《总目》对新、旧《五代史》的这种详密周全的比较,将两书的特点清楚明白地揭示出来,而且又不抑此扬彼,反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
比较学说异同,以见不同学术流派的意旨,是《总目》史学批评的又一方面。比如,《春秋》学中,左氏古文派与公羊、谷梁今文派水火不容,长期攻讦,《总目》运用比较方法进行评析,辨析学说异同,归纳学派特征,“《春秋》三传,互有短长。……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谷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谷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于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注:《总目》卷49《案语》。)在这里,《总目》通过比较,将左氏征实而肤浅,公羊、谷梁穿凿而难通的学术特征归纳出来,并进一步将两派风格歧异的原因揭示了出来,使批评更深入了一步。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所谓汉学、宋学之争颇为激烈,主汉学者重考证,主宋学者重义理。《总目》在梳理这两大学术发展时,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异同,评析其优长短缺,极富启发意义。所谓“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讲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注:《总目》卷1 《经部总叙》。)“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于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注:《总目》卷22《读礼志疑》条。)“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注:《总目》卷35《四书集注》条。)将汉学“具有根柢”的实证笃实的学风和宋儒“具有精微”的长于思辨的风格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出来,指出两种学说各有短长,互有得失,见解允当。
比较批评方法是一种开阔视野,更准确、更深刻认识对象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克服史学批评的狭隘性,有助于揭示史学现象的同异,从而为深入探求史学现象创造条件。《总目》比较典籍优劣,明人之所未明,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论世知人以见批评用心
史学批评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在批评过程中,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势必要影响到评论的结果。为使主体不致于过分曲解客体,中国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早就提出知人论世的学术批评原则,即考察史家及史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中讨论史家和史著的价值,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多次宣明要“寓论世知人之义”,(注:《总目》卷190《甬上耆旧诗》条。)“俾读者论世知人”, (注:《总目》卷58《东林列传》条。)“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注:《总目》卷首《凡例》。)并广泛使用了这一方法。
《总目》的论世知人的批评方法,十分着意于从时代环境的制约与社会风尚的趋会等共时性方面对古代典籍的风貌或缺陷作出合理性说明,体现了一种设身处地的历史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考察制约史著优劣的政治文化因素。如《总目》指出,《北齐书》之所以“文章萎恭,节目丛脞”,是由于北齐“立国本浅”,“纲纪废弛,兵事俶扰”,那些被倚为立国之士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再加上作者的才、学不及古人,其缺陷自然难以避免。(注:《总目》卷45《北齐书》条。)史书质量的高低,史家固然首当其责,但政治文化的因素也极为重要。又如《辽史》之所以“重复琐碎”,是因为有辽一代,“书禁颇严”,“凡国人著述,唯听刊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这样的文化政策,就使得辽代典籍无法“流播于天下”,战乱一起,便“旧章散失,澌灭无遗”,“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无米之炊,足穷巧妇”,后世修史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其间左支右离,痕迹灼然”。重复琐碎也就在所难免,“不足怪也”。(注:《总目》卷46《辽史》条。)这就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揭示了造成史著出现偏失的深刻原因。
其二,考察制约史著优劣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总目》指出,《南齐书》多“附会纬书”,“推阐禅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萧子显“牵于时尚,未能厘正”。(注:《总目》卷45《南齐书》条。)社会文化风尚影响到史著的思想内容。又如宋人杜大珪撰《名臣碑传琬琰集》,“一代钜公之始末,约略具是”,一些被后世视为奸邪的人物,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亦被收录,“并得预于名臣”,对此,《总目》虽认为“去取殊为未当”,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知人论世”,分析了制约史家思考和认识的社会文化因素,“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注:《总目》卷57《名臣碑传琬琰集》条。)这样的评析让人看到了史学批评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其三,“原情准势”,体察史家著史之苦心,以见史著之真实面目。如魏收修撰《魏书》,有“秽史”之称,历代史家均攻评《魏书》不已。《总目》从论世知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抨击魏收的种种言论,提出不同看法。如《魏书》完稿后,“前后投诉,百有余人”,其中攻击最力者为范阳卢斐。卢斐认为自己的父亲仕魏官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但与魏收无亲,遂不列传,而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因是魏收外亲,故立佳传。《总目》经过一番考证,指出卢斐之父卢同党附元义,多所诛戳,后来被罢官职,并非“功业显著,名满天下”,崔绰官位虽低,却是“贤俊功曹,冠冕州郡”,自然应当立传。卢斐以官位大小作为立传的标准,“未足服(魏)收也”。对于那些认为“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的说法,《总目》也一一批驳,认为杨愔先世杨椿、杨津,高德正先世高允、高祐,均是“魏代闻人”,必须立传,并非魏收阿谀权贵。通过辨析,自然就推翻了《魏书》为“秽史”的说法,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与此同时,《总目》在力辨《魏书》非“秽史”时,也不护其短缺,指出它“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魏)收恃才轻薄”也不足取。但《总目》是以关注著史者的苦心来做出这些评价的,“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注:《总目》卷45《魏书》条。)
《总目》不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具体史家、史著进行评析,而且从这一角度考察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思潮,向人们揭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如陈寿作《三国志》,奉魏为正统,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一反陈寿之说,以蜀为正统,于是开始了中国史学史上的魏、蜀正统之争,持续不休。尤其是到了宋代,争论更加激烈。北宋以魏为正统者多,南宋以蜀为正统者多,并出现了一股改作《三国志》的风气。对于这个问题,《总目》尽管主张以蜀为正统,但没有简单就此评判,而是以“论其世”的态度,揭示了其中的奥妙,“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注:《总目》卷45《三国志》条。)《总目》从魏、蜀正统之争这一史学思潮的背景考察,清楚地向人们揭示出:任何一种史学观念、史学思潮的出现或变化,总有时代政治的需求在背后起作用,陈寿以魏为正统,是因为他所生活的西晋是承魏而来,伪魏即是伪晋,这是统治者所不允许的。而习凿齿生活的东晋,恰如三国时的蜀汉,正蜀汉即是正东晋,这是统治者所欢迎的。北宋的正魏和南宋的正蜀,也大致如此。《总目》尽管赞成以蜀汉为正统,但对于魏、蜀正统之争能“以势而论”,没有断然作出结论,而是提出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观点,这样的评析,可谓公允平实。
具体评析,折衷至当
《总目》评论史书,有时通过分析、归纳以后,对整部史书的优劣作出一个结论,有时又注意通过史书各部分不同价值的分析,来评价史书的价值所在。
从整体上评价史书,可以给人一种总体的、明确的印象,使人获得对整部著作的大致把握。比如,《北狩见闻》一书,《总目》通过分析后给出这样的评价:“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注:《总目》卷51《北狩见闻》条。)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总目》给予的总体评价是“于史学殊为有助”。(注:《总目》卷50《历代史表》条。)杜佑的《通典》,《总目》的评价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注:《总目》卷81《通典》条。)司马光作《稽古录》,《总目》认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注:《总目》卷47《稽古录》条。)这种总体性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确立一部史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看,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写得处处精彩,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无懈可击。那么,指出这些史书的优长之处和短缺之点,对于人们正确把握该书的价值,尤显必要。对此,《总目》有自觉的意识。如《总目》评《通志》,指出《二十略》是“全帙之菁华”。(注:《总目》卷81《通志》条。)评《文献通考》,指出“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也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有过之”。(注:《总目》卷81《文献通考》条。)评《隋书》,指出“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注:《总目》卷46《隋书》条。)评《方舆胜览》,指出该书虽在地理考证上不太详尽,但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注:《总目》卷68《方舆胜览》条。)等等,都是从局部入手评论史书的。
《总目》从局部入手评论史籍,是有所侧重的,综合起来看,它特别看重史书的功用、史书的体例、史书的取材和史书的考证这么几个方面。
《总目》重视史书的社会功用,认为史著“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鉴”。(注:《总目》卷55《钦定明臣奏议》条。)因此它在评论史书时,那怕其它方面一无是处,只要该书在借鉴历史经验方面有可取之处,也要特别指出,加以肯定。明代杨士奇奉敕编修《历代名臣奏议》,“名目太繁”,“区分失当”,“踳驳失伦”,在体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由于该书能够反映“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因而《总目》认为它“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注:《总目》卷55《历代名臣奏议》条。)给予了肯定评价。明季宦官吕毖所撰《明宫史》,在《总目》看来,内容“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但之所以将它收入《四库全书》,全在于它记载了为害严重的宦官的活动,向人们表明了宠任宦官乃明代“致亡”之一端,“足以炯鉴”,(注:《总目》卷82《明宫史》条。)引起后人警醒。
《总目》继承传统史学重视史书体例的传统,在评论史书时,特别注意体例的完备。元人修《宋史》,矛盾抵牾,书法不一,《总目》一一将其列举,指出“纪传之互异”,“志传之互异”,“传文前后之互异”等,认为“舛谬不能殚数”。(注:《总目》卷46《宋史》条。)唐人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体例严密,被《总目》评为“舆地图经……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注:《总目》卷68《元和郡县志》条。)
《总目》极其重视史书的取材,在提要中对史书取材作了许多评论分析。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广泛占有资料,《总目》在史部提要的叙中率先指出这一点,认为该书“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正是因为有了这浩博的材料,司马光等人才能“先为长编,后为考异”,成此史学“绝作”。(注:《总目》卷45《史部总叙》。)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广泛,《总目》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官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注:《总目》卷4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条。)由于《总目》重视博采史料,故而对那些取材稍嫌冗杂的史书,也不过多苛求,而是给予合理评价。明人徐应秋撰《王艺堂谈荟》,“嗜博爱奇”、“兼及琐屑之事”,资料以“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但《总目》指出:“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注:《总目》卷123《玉艺堂谈荟》条。 )清人张尚瑗撰《三传折诸》,有“支离曼衍”的缺点,但《总目》认为其“取材既广,储蓄既宏。……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粃遂尽弃其精英”。(注:《总目》卷29《三传折诸》条。)同样,对那种取材不备的史书,《总目》都给予了批评。如明人沈越撰《嘉隆两朝闻见纪》,有人称为“野史之良”,但《总目》认为该书取材“未为赡备”,不足以当“野史之良”,(注:《总目》卷48《嘉隆两朝闻见纪》条。)等等。对取材不精的史著,《总目》也给予了批评,它认为:“即系史名,事殊小说。……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若夫语神怪,供恢啁,……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注:《总目》卷51《杂史类序》。)这段话很清楚地指明了史书取材的范围与性质,那些虚幻荒诞、怪异神说、里巷琐语、稗官所述、小说杂言等,在取材时当慎之又慎。
由于《四库全书》成于乾隆时期,参与四库编修的又大多为汉学考据家,因此,《总目》特别注重考证。综观整个《总目》提要,几乎每一条评论之中,都灌注了作者辛勤考订的心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审的考订,才为评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提高了史学批评的学术价值。《总目》提出“考证则欲其详”,认为作史必须做到“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这样才能“得其精”。(注:《总目》卷45《史部总叙》。)故而凡是史学上以考证见长或在考证上有成就的史著都得到《总目》肯定,反之则给予尖锐批评。这又是《总目》批评的一种倾向。
援据纷纶以说史意
余嘉锡先生在论《总目》的学术批评时,曾说《总目》的一大特色是“援据纷纶”。确实,在《总目》的批评系统中,博引前人之论的归纳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总目》总是自觉地将诸家议论系统化,纳入到自己的史评体系中,以佐证自身的论断。如许嵩所撰《建康实录》,《总目》认为“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证”。(注:《总目》卷50《建康实录》条。)为说明自己的评价正确,便引征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郑文宝在《南塘近事》、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对该书的引用以为佐证,使人们真切感到《建康实录》确乎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再如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总目》深加激赏,认为“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为此,引用了王应麟《玉海》、《宋史·袁枢传》以及朱熹的话以为佐证,使品骘更有分量。(注:《总目》卷49《通鉴纪事本末》条。)
对于前贤的评论,《总目》并非只引来以佐己说,有时它还要对这些评论加以驳难,推翻旧说以立新说,这也可看作是《总目》博引前人之论的归纳方法的另外一面。如宋人宋敏求撰《长安志》一书,司马光认为其书“精博宏赡”,程大昌认为“其引类相从,最为明晰”。《总目》在征引了这些评论后,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其书“不免时有驳复”。(注:《总目》卷70《长安志》条。)等等。可见,《总目》看重前人的评价成果,但它又有自己的见解,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总目》所运用的史学批评方法是多样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历代典籍,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古代典籍的价值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总目》带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所谓“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注:《总目》卷首《凡例》。)所谓“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自然是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不符合名教的著作;所谓“怀作挟私,荧惑视听者”,自然是对清统治者有抵触情绪的作品。对此,《总目》就失去了评价的公正性,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完全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攻击。可以说,浓重的政治色彩障蔽了《总目》的批评眼光,使得自身的批评带有先天的局限,自觉充当了清代文化专制政策的马前卒。当然,任何学术批评都难于逃脱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都不可能没有自身的价值观念,对此,我们也要从“原情准势”、“知人论世”的角度进行理解,不能一味苛责。另外,《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尽管运用了多种方法,但它的批评仍然是保守的,它并没有像章学诚那样,自觉地通过评论向人们指出一条传统史学的发展出路。
标签: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班马异同论文;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 魏书论文; 三国志论文; 东都事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