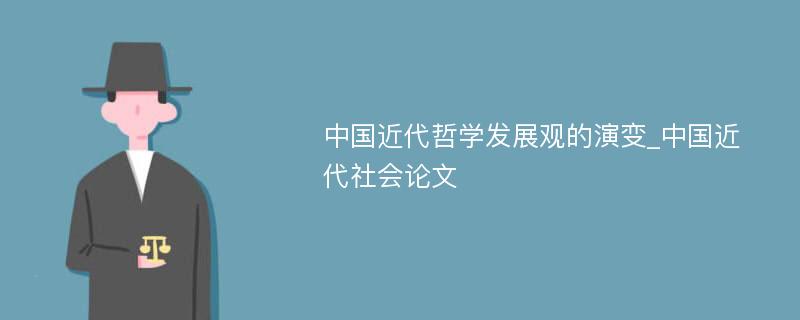
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观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之论文,哲学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发展观问题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他们构造各自的哲学体系时,不是作为次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般世界观意义的中心原则,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道德原则、政治理想。他们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呼应着对现实的看法,他们对发展的理解方式牵连着他们的实际行动方式。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观之嬗变,对于把握中国近代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
翻开浩繁的中国典籍,确实不乏变易的观念;检视众多的中国哲人,确实不缺变易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创立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易经》的“阴阳为易”,史伯的“和实生物”,孙子的“奇正相生”,范蠡的“赢缩变化”,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墨翟的“兼以易别”等,都表达了革新鼎新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观上辩证思想的活水源头。
但是,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来看,这种变异思想大都走向了形而上学不变论的归宿。从方法上看,走向这一归宿基本上是通过两条途径。
一是始终循环论。先秦哲学家邹衍在深观“阴阳消息”,研习“变化始终”的基础上,将先秦的阴阳对立、五行相生的变化发展观念演化为“五德始终”理论。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五行生胜”思想凝固化、公式化,将其看作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封闭之环,牵连附会地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这样,始终限制了发展,循环扼杀了变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流行的一种基本思维定势,并泛化为了一般人的那种“文质交替”、“治乱交替”的社会历史心理,把人世间事物的变化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
二是常道不变论。最为典型的是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学说。他也承认事物包含阴和阳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而引起变化,但把这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固定化,并依此规定了变化的内容。他从“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1],得出“天道无二”的结论,这样,变化只是名号,不变才是本质。人类社会,虽有“易姓更王”,“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但“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2]最后的结论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用“常道不变”去消融“万物之变”,这种观念后经宋明理学的发展,构建了“天理不变”的理学体系,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如“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等世俗社会的生活信条正是这种常道不变发展观的真实映照。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现实,更强化了这一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即使到了近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之时,还是有不少的人仍然觉得“纲常实千古不易”,“三代虽有损益,百世不可变更”[4]。然而,内乱外侵的社会现实所体现出的变革与发展要求,毕竟还是使“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失去其昔日的光彩。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曾对它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情感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其理论深度,所依仗的武器还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因此,不可能真正走出循环论和常道不变论的阴影。
真正动摇“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发展观走向近代哲学形态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进化论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威力,之所以一下子就摄服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之心,一方面在于伴随着进化论而来的是一个与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对现实的惊叹使得他们对理论产生信仰;另一方面还在于进化论自身显而易见的科学优越性。
进化论送来的是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发展观。中国古代的变易观念,不是出自贤哲的天才设想,就是出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笼统意识。而进化论发展观是依托在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在这种充满了科学力量的发展观面前,那种凭借主观臆测、依赖天人比附、通过内心反省才能理解的常道不变论当然显得软弱无力。
进化论用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并把这个结论推广到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长期演化、优胜劣汰被看作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天为天演之一境,人为天演之一境,社会为天演之一境,“是故天演之事,不独具于动植二品之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5]进化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6],从而获得了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这种“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进化论,使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新颖的发展观。它肯定天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既不是五德终始,也不是三世轮回。“其变无境,其途无境,其时无境”[7]。“后起者胜于先起者”,“后人逸于前人”。(康有为语)这就根本上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促使人们脱离陈旧的阴阳五行论和公羊三世论。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还会启示人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领域进行广泛的思考。如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都曾用进化发展观来论证变法图强的合理性、来论证新文化、新制度代替旧文化、旧制度的必然性。
任何一个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都会加进自己文化和自己时代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武器。体现在中国近代发展观的形成上,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用“善变应天”来理解进化,来注释进化。
所谓“善变”就是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力辅天行”,促进社会进步。他们认为:社会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有一根本不同点。动植物进化“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即以新”[8]。而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精神有意识的,“大抵天之生人也,其一周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它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于以成天之所不能”[9]。人类自身,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人治天行”的交互作用。从人类自身看,作为进化产物的生物器官,特别是人脑的发展,是人类“查物穷理”、“自治治人”积极使用的结果;在对环境的改造上,人们主动地去认识、变化自己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使之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具体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所谓“善变”,其根本点就是要将“变之权操在己”。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已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境地。是主动地变,还是被动地变,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蔽;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10]前者是将变化的权力操在别人的手上,后者是将变化的权力操在自己的手上。“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逐之”,只会灭亡。波兰人将变之权操在人,“国分人奴”;日本人将变之权操在己,“国强种兴”[11]。以此为鉴,他们号召人们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变革中国社会的斗争。
所谓“应天”,就是要适合客观世界进化发展的要求。“有志竟成”还必须顺应天理,这个天理就是事物自身进化发展的必然性。“顺天者兴,兴其变而顺天”,“逆天者亡,亡其不变而逆天”[12]。“善变”即是“应天”的内容又是“应天”的要求。
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他们认为只有“善变应天”,才能由弱变强,免受灭种亡国的危险。他们毫不忌讳的承认,自称中央大国的中华帝国不是强者是弱者,内处混乱:土地荒芜,饥馑连年,盗贼蔓延,兵勇老弱,官吏昏庸;外遭逼拶;列强虎视,突我边陲,通我口岸,掠我财物。他们指出:中国虽于今日为“奕国”,只要振奋国民精神,增进国民智力,“善变应天”,发奋图强,就一定会兴旺起来,“终为外人所严惮”。(严复语)还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强国。
用“善变应天”来理解进化发展,使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观具有不同于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新内容。这个新内容与近代先进思想家们的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和社会变革主张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二
因此,进化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观的基调。围绕这个基调,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对现实的反思中谱写了不同的思想乐章。
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空前大变革,洋务派思想家们主张“器变道不变”。从丧权辱国的事实中,与封建皇权紧密联系的部分当权者也深感西方国家的先进性,深感局势的严重性,深感天朝大国并非“事事在人先”,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相形见绌矣”。(张之洞语)他们也深感中国要变,但在如何变的问题上,得出的是“变器不变道”的结论。他们坚信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是不容怀疑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13]。要变的是器械,文武制度是万万不能变的,只能取“西人器数之学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4]。充分体现这种“变器不变道”思想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作了精要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中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5]。由此表露出的是一种想变又怕变的复杂心态。
维新派提出了“全变”的观点,这种观点建立在对“变器不变道”的批判上。与维新派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就曾困惑于“中体”与“西用”、“器变”与“道不变”的矛盾对立,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进一步他还分析了“中体西用”论的变器不变道的本质,指责中学“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6],必须根本改变。
于是,在发展观上就有了“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结论。“今日不变新,则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17]。“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8]。所谓全变,就是要“变法、变政、变道”,首当其冲的是“变法”。被奉行两千多年的封建大法太过于陈旧了,“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19]。因此,应“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20]。中国只有变法,改造典章宪制,改造科举制度,改造文化教育,改造专制政体,“百废更新”,才能“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康有为语)。
这种“全变”发展观包含了一些辩证思想因素,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变法维新运动也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出了光彩夺目的一页。然而,这种全变思想又与另一种观念结合在一起,后者显示出的历史局限性伴随它走向了令人深思的归宿,这就是“渐变”的观念。
这一观念原本就存在于西方进化论的母体中。达尔文在创立进化论时,曾批判过居维叶的“灾变论”,但他自己也走到了自然界没有飞跃的另一极端上。把物种的任何一种习性之变化都理解为经过无数连续细微的变异而形成、经过多次积累而确立、经过逐渐过渡而产生的。从方法论看,这种观念不仅抛弃了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抛弃了按辩证飞跃来理解的发展。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运用进化论分析社会时,更是扩展了上述观念。严复在译著《天演论》时,也将这一观念介绍进来。
维新派的发展观也停留在这一水平上。主张逐渐进化,否认突变革命。其主要方式是构造一个确定不移的进化系列,把事物的发展理解为在这个系列中的“因循渐进”。最典型的是康有为的三世进化理论。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又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三统原则把每一世划分为许多阶段,“由一世分为三世,由三世分为九世、由九世分为八十一世,由八十一式世分为千万世,以至无量世”[21]。把人类社会归结为三段过程,然后又进行一分为三的无限分割。这是一种“恶的无限性”,不同质混同在无限量的分割中,发展最后被湮没。
在这种“义取渐进,更无冲突”(梁启超语)的发展观看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可图“遽变”,更“无一跃飞越之理”[22],只能因循渐进,“不偏不蔽,点滴改进,难能躇等”。知识和道德的变化也是这样,“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23]。自然界的变化还是这样,“宇宙有至大之公例,曰万物皆渐而无顿”[24]。推而广之,渐进成了进化的一般原则,“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亦有渐进,此皆圣人无可如何,欲骤变而未能者”[25]。
“渐变”观念给维新派发展观留下了缺陷,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缺陷日益明显起来。维新派人物最后大都走向保守、反对革命的结局,虽不能说是这种缺陷导致的直接结果,但两者之间至少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至少可以从中窥见其思想根源。
三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895年的《马关条约》宣告了求自强的洋务运动破产,1898年的戍戌变法失败意味着“渐变”方式在中国行不通。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所造成的严重危机激发起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高涨,呼唤着新的变革观念。整个形势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描述的:“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国人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矣,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从此萌芽矣”[26]。
与此相应,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摒弃了维新派的“渐变”理论,将进化原则注入了革命飞跃的新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用“狡猾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
这种“哲学灵感”是从对严重政治现实的反思中获得的,凝炼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的中心命题。它最先出现在“少年英才”邹容那震惊近代的《革命军》一书中,第一次论证了革命是世界进化的普遍规律。“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27]。革命派热情地歌颂革命,鼓吹革命。他们指责“循序渐进”的发展观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不知文明之真价”[28],认为革命是进化的基本内容,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西方各国之所以走在中国的前面,就是因为社会革命的作用,“宇内各国……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 亦其一端也”[29]。正是这种“争自由、打平等”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使得“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我们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文明,才主张革命”[30]。
为论证革命飞跃的发展观,针对维新派的“难能躇等”,革命派提出了“后来居上”的理论。他们认为,天下之事,不只是“渐渐更新物”,而且还有“破天荒的突驾”。进化之秩序不只是“因循渐进”,还有“踵事增华,变本加利,而后来居上”[31]。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们可以向先进学习,效法他人的经验,少走或不走弯路,从而后来居上。孙中山以火车在中国的应用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发展思想。“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新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按渐进发展观,“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间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32]。
进一步他们指出,中国要后来居上,因序渐进是断然不行的,唯一的道路是革命。因为中国社会已到了陈腐不堪的地步,封建三纲五常严重桎梏了人们的思想,封建政体积弊丛生,残腐将死,文明古国屡遭侵略,面临瓜分。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于此时此地的中国来说,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药”(陈天华语)是“补泄兼备之良药”(章太炎语)。其功效:
一是破旧立新。他们承认,革命是有一些破坏,但这种破坏是对腐朽统治的进击、抗争。如果不破坏掉旧的,就不会有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革命是破坏的事业,好比拆房子一样,我们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旧房子拆去;想建设一个新国家,便不得不把旧国家破坏。这个破坏就叫做革命”[33]。因此,与革命相联系的破坏,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而是要清除阻碍人类社会进化的障碍物,破坏掉清朝的封建政权。破坏的同时是为了建设新国家,为了建设“四万万人民的民主共和”。革命是有流血,但这个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因革命流血,“犹龈龈于杀人流血之惨怵焉不敢为,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34]。
二是开启民智。维新派反对革命,还以民智未开为由。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行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35]。对此,章太炎严正指正:“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持他事以开之,而但持革命以开之”[36]。他历数了外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列举了中国的李自成、唐才常,认为他们的思想觉悟都是在革命中提高的,他们最的结论是:革命能开民智、去旧俗、明公量、立新潮。
以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发展观,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批判推向了新的高度。与此相应,他们以强硬的态度猛烈地抨击了专制皇权、宗教神权和封建道统。这种批判既有理论的,又有实践的。既表现在“引刀”、“革天”等辛辣的言词上,又体现在一大批革命志士的狂放行为中,如邹容的“就义”,章太炎的“剪辨”,陈天华的“自沉”等等。这种批判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为其后人所仿效或继承,并随着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展开而走向深入。
四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制度。但这场血和火的革命,换来的却是一个徒具其名的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果实先是被袁世凯后是被封建军阀所篡夺。一个严重的发展观问题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
面对这种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中,奋起而来的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掀起了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成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先驱。
从本质上看,他们的发展观也许没有走出进化论的思想范围。但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民国初年的反复,对发展观的理解仍然跃向了新的高度,表现出比其先驱者们更为强烈的进化意识、更为浓厚的主动精神和更为广泛的社会思考。
他们更为强烈的进化意识体现在满腔热情地盛赞宇宙的进化和发展上。从宇宙的无限性、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无限性上,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去描述宇宙的生息绵延。“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因此,“整个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37]。客观事物、人类社会无时不在“演进之途”,新陈代谢是进化的普遍法则,“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38]。这种新和旧的对立又具体地表现为生死、盛衰、阴阳、吉凶、祸福、否泰、消长、屈信、盈虚、青春自首、健壮颓老等,两者息息相攻、息息相守、相摩相荡、相克相复,而最终结果将是新的总是代替旧的,青春总是战胜自首。此乃“天演之公例,莫或能逃之者也”[39]。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40]。“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41]。于是,他们呼唤着中国来一番将腐朽化神奇的“彻底之变”,向往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青春之中国”。
与这种强烈进化意识相呼应的是发展观上浓厚的主动精神。这种在中国古代就很丰富的哲学观念,在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的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认为,宇宙虽是一个自然的大实在,但社会的进化、国家的发展却离不开人的思想,离不开人主动精神的发挥。因为人是有智慧的、有思维的,他们可以认识客观实在的变化,主动遵循进化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促进事物,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种主动精神在李大钊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有两种主张“任其进化”、反对发挥人主动精神的观点。一是生物学者之言,认为人类发挥主动精神是反乎自然和人类之生活;二是宗教信士之言,认为“宇宙一切皆为神造,维护之任神自当之,吾人智能薄弱,惟托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42]。对此,李大钊认为,前者只会使人“瞑心自放,居于下流”,后者“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43]。人类只有依人为之功夫,顺自然之生活,就能促进自身、民族、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人类就有“无尽之青春”、“回首再造之功效”。他还认识到,人类对社会进化的促进不是单靠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靠千万个民众的意愿。“国家之大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可莫持”[44],只有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对这种主动精神的理解,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进化,封建专制之所以不能根除,关键在于没有破除传统陈腐思想,没有提高国民觉悟,没有开通国民智慧,没有焕发国民激情。毛泽东激动地说:现在的中国“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45]。陈独秀则近乎愤怒地指责国民对辛亥革命“隔岸观火”、“袖手旁观”,他大声疾呼,中国社会的进化“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必须“发挥人间具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留于脑里。利刀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46]。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与民族解放呼声,使他们发展观的理论兴趣更注更于与民族存亡相关联的社会问题思考上。人进化的原则出发,去设想社会发展的模式。陈独秀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暴虐”、“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李大钊则相信,是由“君主政治”到“官僚政治”再到“民主政治”;孙中山则以地道的哲学方式将人类进化历程划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等相继递进的四个时期。他们的表述虽不相同,但着眼点是一致的,希望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化到民主社会。
只要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关联的问题,他们都纳入了发展观思考的范围,把进化发展的模式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调。关于道德,他们认为,“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47]。所以中国古代道德乃“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陈独秀语),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若不彻底根治,则中国社会“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48]。关于文学艺术,他们认为,“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49]。据此,他们猛烈抨击封建的贵州文学、山林文学甚至一切古典文学,指出中国社会要进化,要唤起国民精神,必须推翻雕琢阿谀的、陈腐铺张的、迂晦艰涩的、陈陈相因的旧文学,建立起平易抒情的、新鲜立诚的、明了通俗的新文学。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文学革命、道德革命,并试图将这种革命推广到教育、文化、民俗、时尚乃至生活方式、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领域。
五
总之,自进化论传入以后,中国人的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告别了中国古代哲学而走向了近代形态,取代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辩证法而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演观念在近代舞台上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理论深度和完整性上也许还比不上有两千年发展历史的古代朴素辩证法,但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毕竟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在近代短促多变的历史行程中,近代发展观大致经历了维新派的全变论、革命派的革命论和激进民主派的进化观,它们环环相关扣,步步逐浪高,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内容,是近代发展观一大特色。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近代思想家们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并不是在抽象理论圈子中,而是在社会动荡和民族存亡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不是在书斋里,更多的是从社会现实中,去获得理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发展观思考中所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哲学智慧不如说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许多陈述发展思想的命题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气息。(如革命是天演之公例等)由此,给近代发展观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使近代发展观获得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极受人们的关注,具有社会思潮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动方式和对社会其它问题的理解方式。从近代许多思想家的理论体系和毕生经历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明显存在。另一方面,对社会内容的关注也导致了近代哲学发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形式系统。在这一点上,它最终未能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窠臼。把达尔文进化论提升为一以贯之的哲学发展原则的方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习惯采用的类比方法。从生物界类比到人类社会,结论的时代先进性却依赖于陈旧的思维方法,这大大地削弱了其理性的力量和哲学的严密性,给人一种零碎、杂乱及浅芜的感觉,以致于我们今天在进行研究时只能从近代思想家的时论、政论中去察会他们关于发展的思想。
脱胎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观所表达的主导思想是“由旧到新、不断变化”。这一简单的发展模式以它的鲜明和简洁,唤起了近代中国人的极大热情,成为他们批判旧的封建专制、追求新的理想社会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简单的发展模式毕竟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它把发展简单地规定为对旧的抛弃和对新的追求,但对旧和新的关系缺乏辩证的理解,对新的内容,对新陈代谢的动力及复杂过程,对量变与质变、渐变与飞跃、连续与间断缺乏认识。这些缺乏在对发展问题的理解上易于造成虚无主义、形式主义乃至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就是明证。
面对这些现象,一些思想家由衷地发出了“新的是否一定就好”(鲁讯语)。“什么才是新的”疑问。这些疑问促使他们进行新的理论反思与探索,由此,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观必然会离开进化论而走向新的阶段。
注释:
[1]《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2]《春秋繁露·楚庄王》
[3]《对策三》
[4]均见《翼教丛编》
[5]严复《天演论》
[6]《天演论》
[7]《天演论》
[8]《天演论》
[9]《天演论》
[10]梁启超《变法通议》
[11]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
[12]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1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14]李鸿章《同治八年初一日奏折》
[15]张之洞《劝学篇·会通》
[16]严复《救亡决论》
[1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
[18]康有为:《上皇帝第六书》
[19]康有为:《上皇帝第六书》
[2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
[21]康有为:《论语注》
[22]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23]严复:《原强》
[24]严复:《政治讲义》
[25]康有为:《论语注》
[26]《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页
[27]邹容:《革命军》
[28]《孙中山选集》第66页
[29]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
[30]参见《孙中山选集》第753页
[31]《孙中山选集》第160页
[32]参见孙中山:《驳保皇报》
[33]《孙文全集》第4卷第113页
[34]寄生:《论支那立宪必以先革命》,《民报》第2号
[35]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36]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37]《李大钊选集》第95页
[38]《李大钊选集》第97页
[39]《李大钊选集》第70页
[40]鲁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41]鲁讯:《热风》
[42]参见李大钊:《青春》
[43]李大钊:《青春》
[44]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45]泽东:《陈独秀被捕及营救》
[46]陈独秀:《敬告青年》
[47]《李大钊选集》第79页
[48]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4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