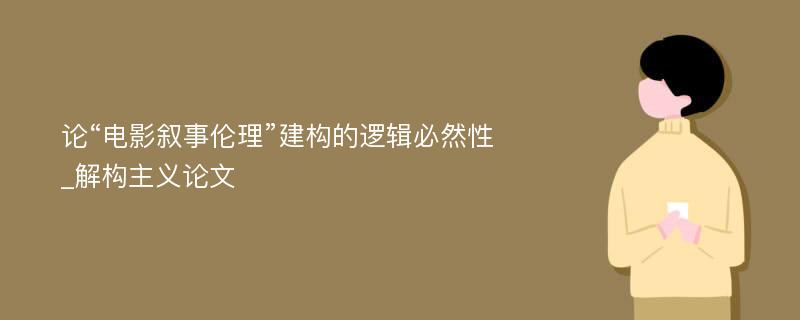
论“电影叙事伦理学”建构的逻辑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必然性论文,逻辑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叙事伦理的提出与电影叙事成为一门学科一样,都发生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叙事学研究转向以后,但由于电影语言的特殊性以及电影语言的不断发展,在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叙事伦理进行概念厘清并对其理论与实践的两方面价值给予充分认识后,理应建立一门属于电影学的“电影叙事伦理学”,旨在讨论作为一种伦理实践的电影叙事与相对伦理之间的关系,并思考如何运用日新月异的电影语言、借助电影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功能,实现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叙事伦理”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政府学生运动,此次运动虽然最终被强制打压,但却直接促成了法国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向。在西方学者的普遍认识中,1968年的这次法国学生运动正是导致法国思想界、学术界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的重要契机,因为在他们看来,解构主义思潮所独有的反传统、反权威、反逻辑、反理性等特征大体上缘起于此。然而正如特雷·伊格尔顿所言:“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①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现存语言体系实际上正是当下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一种能指,而通过对语言结构的破坏恰可以实现对传统秩序结构的全面颠覆。 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期《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和《文字与差异》的相继问世,解构主义理论被正式确立起来。德里达认为,“解构”并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这个词所关涉的,实际上是意义、惯例、权威、价值等本质上莫须有的问题。②由此,解构主义将挑战的对象锁定为由索绪尔等所奠定的语言学理论,以文本本身潜藏的自我瓦解的本性否定了语言学所讨论的结构模式、语法规范等存在意义,并随着后期罗兰·巴尔特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又经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发展,最终演变为一场带有消解一切的极端虚无主义意味的桀骜宣战。 虽说解构主义理论思潮脱胎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科技、经济加速发展的大工业生产社会,然而与人们对程式化的生产与千篇一律生活状态的厌恶情绪极其一致,它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叛逆心理,并怀着誓将打破所有刻板范式的革命豪情。无疑,这种挑战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例如它对逻辑中心主义和人文学科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对所谓恒定不变形式的批判、对终极意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凸显等等都强有力地撼动了形式主义妄自尊大的躯壳。然而,它的理论缺憾却也是明显的。从德里达以“无休止的延异”来驳斥“逻各斯中心主义”,到哈特曼对语言意义不确定性的重复强调,再到后来者对所有以语言为能指符号的事件意义的武断消解,结构主义理论的惨遭质疑和解构主义理论的强势出击,无疑是从一种对形式主义无限信赖的极端迈向了另一种对虚无主义毫无警惕意识的极端。同时,因为解构主义理论的生产机制与现实社会语境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所以其颠覆力也顷刻间渗透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最早由托多罗夫③正式提出、直接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叙事科学,这种相当于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使得经典叙事学业已取得的看似行之有效的全部探索成果和研究意义瞬间灰飞烟灭。然而更加严重的后果是,解构主义者对语言文本意义的层层瓦解则在更深远的层面上掀起了一股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范围的对一切现存事物的价值、秩序的怀疑和弃置,且此种情绪延续至今并依然发生着对当下社会多方面的消极作用。 但是正如那次来势汹汹的“五月风暴”终被平息,解构主义在经历了一番由动能向势能的纵横驰骋并迅猛却不乏畸变的壮大后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驻足已无路可走的理论崖边被迫勒马。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理解:此次对于语言学及建立其上的叙事学理论的血腥屠杀或许正是止于人类社会对某种秩序价值的模糊重识和再次寻唤,以及叙事学理论发展本身对新语境和新机制的必然关涉和必要探讨。 对象征着秩序社会和结构(关系)社会的语言王国的冲动拆解造成了眼前世界的一片混乱和现世芸芸的“无家可归”,因而,解构之后,便期待着新一轮回的建构。而以秩序问题和关系问题为根本讨论对象的“伦理”问题此时自然被重新纳入人们对生存空间以及从来都体现着生存空间结构的“叙事”问题的思考,当然,它本来也就一直深埋于亟需重建的这片土地。所以,从“伦理”与“叙事”的依存关系来看,叙事伦理的建构不仅不愧为经典叙事学绝境逢生的一次重要转机,更担当着重建人类文明家园的繁复重任。然而,究竟是谁首先在确切的时间地点命名了“叙事伦理”这一学科却难以考证,但这似乎已不再重要,因为伦理命题实则伴随总难排除逻辑关系并总象征社会秩序的叙事行为的始终,也因为“叙事伦理”至今仍没有一个明朗、权威的定义,更毋庸说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完全把握,它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但这并非意味着,“叙事伦理”是叙事学发展的唯一救命稻草或其定能将所有社会怪相一并拨乱反正,然而,它却恰似各味苦口良材中的一颗红枣,以“药引子”的身份独立其中,其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至此,我们仿佛已经大体上还原了“叙事伦理”的多重生成语境,但不容忽视的是,与叙事学的伦理转向同时发生的,还有叙事学对跨学科和不同媒介的关照,电影,适逢其中。 二、“电影叙事伦理学”的建构 (一)去谬 在这里,须要迂回重述的是,当叙事学“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意识到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④后,并没有直接催生出可以独立成为一种批评范式的“叙事伦理”,而是在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潮中,不断探讨诸多与“伦理”问题紧密相关的话题并不断延展出一系列如“女性主义叙事学”、“电影叙事学”、“社会叙事学”等文化研究范畴的课题。有学者将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进行了比较,认为,“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与方法。”⑤将这种对立研究的思维方式体现得更为彻底的则是文化研究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的忽视。在文化研究中,“‘文本’不再由于自身的缘故而受到研究,也不是由于它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而是为了实现使其成为可能的主体或文化形式而进行研究。”⑥正所谓“文本研究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个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个流通时刻的主体形式的社会生活,包括他们的文本体现。”⑦这里,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和其理论缺失都相当明显:合理性在于它对语境和机制的充分考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当代文化、当前社会就可以遗忘历史经典;不意味着研究大众文化、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就可以模糊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客观评价和基本态度;也不意味着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是万能的;当然,更不意味着对“文化”的重视就必然要忽视“文本”的价值。但转向后的叙事学的确又一次陷入了“走极端”的误区。此时,文化研究就像一个万花筒,经典叙事学的各种研究成果皆作为被绞碎其中的一片花瓣,混杂在文化研究的“圈套”内,在与周遭多棱镜的相互碰撞中不免晕头转向,然而正是这不断的碰壁,却意外地萌发出一束束看似生机盎然的新枝,而事实上,其中必然不乏一些以牺牲经典叙事理论精华为代价而生成的随机式命题,它们虽明媚一时,却也因异彩纷呈而终无定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种忽略文本规律和特征的文化批评必将导致叙事学研究又一次地濒临绝境。因而,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文本的形式审美研究和文本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⑧其实,即便是率先否定“语言中心主义”的德里达,质疑的,也不过是语言学对“终极意义”的迷信,而他对“人的主动性”的提出、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批判等至今也仍然适用。事实上,如果真正理解德里达,便不会出现其后的“耶鲁四人帮”,更不会出现后经典叙事学对“文化”的单向度研究。 现在,我们不妨回到“叙事学”概念本身。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而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对“叙事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显然,“叙事性”作为叙事学研究范畴的一种,理应成为叙事学理论的一个关注向度。而正如前面所述,既然任何叙事都是一次伦理实践,那么,“伦理”也就应是“叙事”的内在属性之一,进而也理应进入叙事学理论的研究视野。同时,因为“伦理”和“叙事”的依存关系,对“叙事伦理”的讨论则必须建立在对“叙事”和“伦理”这二者间充分必要关系的完全理解之上,也正因此,如果将“叙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一门课题并正确认识与有效实践,则更加能够在肯定文化研究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合理借鉴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成果,避免重蹈人文科学研究二元对立思维的覆辙。 对此,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已经对“叙事伦理”展开了较为正式的讨论,例如Adam Newton由哈佛大学于1997年出版的著作《Narrative Ethics》⑨,在作者看来,“narrative”,“remains an open and unfinalized form”,并且,“ethics”,“does not neatly reduce to a simple matter of apologue or moral example”,因此,十分有必要来探索“coefficient relation between narrative fiction and ethics”这一几近被忽略的问题,此外,在一些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研究的论文中,也散现出部分学者对“叙事”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关注。 在国内,“叙事伦理”一词首先出现在学者刘小枫于1999年由大陆出版的著作《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当中,此后,“叙事伦理”一词便频频亮相于中国文学批评领域。虽然刘小枫同样认为“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的伦理构想”,并提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没有的”⑩,但是在这本以“叙事伦理”为关键词的随笔式学术著作当中,在刘小枫对毕希纳、昆德拉、卡夫卡、基斯洛夫斯基这些卓越的文学叙事思想家和艺术叙事思想家的叙事文本进行复叙事的过程里,作者却仿佛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对“何谓所叙之事之伦理”与“所叙之事之伦理的分类”等问题的追问上,但不可否认,他的确成功地为伦理的叙事呈现和伦理的差异感觉这些饶有意味的话题开辟了一条新径。 沿着这条道路,国内一些学者便敏锐地将刘小枫的论述框架转而挪用在自己对中国叙事文本的分析当中,其中,较早进行如此实践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谢有顺完成于2000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该论文直接借鉴了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将其引言部分对“所叙之事之伦理的分类”分别作为该博士论文正文部分各章节的话题旨归,并将“叙事伦理”一词追溯到Adam Newton的《Narrative Ethics》。但遗憾的是,《Narrative Ethics》这部著作在谢有顺的博士论文中只是作为“文献综述”的一部分而被一笔带过,甚至还“不求甚解”地误读了其所具备的重要涵指和多元意义(11)。 当然,从《Narrative Ethics》还没有出现中译本这一现象或可看出,“叙事伦理”在当时其实并不流行,因此,在关于“叙事伦理”的早期研究中存在着不甚明晰的认识便是情理之中。但是,新世纪以来,对“叙事伦理”这一问题的讨论热情日渐高涨,虽然目前来看,“误读”仍然存在,并占据多数。但是正好像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叙事学的伦理转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所以,尽管“叙事伦理”之于传统叙事文本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但它在电影批评领域已然是难耐寂寞了。 其实,“电影是一种语言”早已毋庸赘言,而经典叙事学的现代双重转向虽说必要而及时却仍间有裂隙与缺憾,因此,“电影叙事伦理学”的提出似乎是必然且可行却依然不得不予以审慎之后的悉心建构,从而避免再次跌入理论的迷雾。 (二)建构 当被认为是引导了语言哲学新走向的《哲学研究》一书使得维特根斯坦几乎成为了叙事学研究的新英雄以后,他的后期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日常语言哲学”所主张的“日常语言分析原则”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而这一理论原则对于“电影叙事伦理学”的建构不无借鉴意义。 虽说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研究中出现了哲思上的剧变,他从受缚于封闭自足的语言逻辑世界主动转向喧闹的日常语言交流社会,认为语词、语言和话语并非有独立的概念,它们的意义是由人们日常习惯中的语言规则所设定的,但这样一种拒绝形而上的分析哲学却难说其彻底甩掉了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子,正好像他自己所言,“两年前,我有机会再次阅读我的第一本(《逻辑哲学论》)并解释其思想。这时,我突然想到,应当将那些旧的思想与新的思想放在一起出版:这些新的思想只有在与我的旧的思想方式的对照之中并在后者的背景之上才能得到其适当的阐明。”(12)只不过,这是一种自设语境的语言分析,在否定了语言逻辑的形而上意义的同时却承认其“特定位置”上的“约定俗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将语言的工具及其运用方式的多样性、词类和命题类别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们就语言的结构所说的话加以比较是饶有兴趣的。(也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13)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研究中,他将语言比喻为一场“游戏”,尽管“我们玩游戏而且——‘边玩边制定规则’,甚至于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在其中我们边玩边改动规则”(14),但因“游戏”也好或者具体到“语言游戏”本身也好,个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像“差异性”一样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因而我们也理应在反思将之进行形而上的统一命名的同时“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并通过“综览式表现”“看到诸关联”、认识到“中间环节的找到和发明的重要性”(15)。此外,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中,他认为,“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语词具有一种运用的话,那么它们当然必定具有一种像‘桌子’、‘灯具’、‘大门’这些语词的运用一样卑微的运用”,而这些“日常的、模糊的命题”并非“完全无可指摘的意义”(16),加之“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17),且“在存在着意义的地方必定存在着完善的秩序。因此,即使在最为模糊的命题之中也潜存有这种完善的秩序”(18)。 虽然就像维特根斯坦短暂一生中所做出的每一个令人捉摸不定的决定和到过的每一个不可定位的处所,维特根斯坦闪烁的智慧总是有如飘零的落叶,插着或称之为比喻或称之为臆想的翅膀,又总是很肆意地落脚在随便哪一个地方,因而他的思想总是显得琐碎而凌乱,但有一点却仿佛格外明了,那便是后期的他并不排斥对语言叙事的逻辑分析,只是这种分析终归要回到现实情境中来;分析并非是为了获得一个终极理想中的“经验”,而如此这般类似于“语法考察”的分析却必须建立在对其特定语境中特定意义的肯定之上,同时,还应当肯定,即便是相对自由的意义也仍需秩序和规则的保障。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简单归纳,我们似乎捕捉到了他分析语言哲学中无处不在的伦理意识,而就这层连他自己都无意揭示的“叙事伦理”意义,却可以从他1929年的一次关于伦理学的讲演当中窥见一斑。他在讲演中表示,“伦理学是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探索”,之后,他又通过大量的举例并依循分析语言哲学的研究原则来试图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价值”、“绝对的善”这种说法,而“只有相对的价值和相对的善与相对的正确等等”,因为,“没有任何事实陈述可以是或包含关于绝对价值的判断”,“尽管所有的相对价值判断都可以表现为纯粹的事实陈述”,这就好像是说,任何叙事都无终极意义,但叙事却可以使相对意义的话语呈现成为可能;也因为,我们所说的“伦理”必定是建立在具体的、可描述的或可感知的事实之上,而“我们可以想到或说出的东西都不是这个东西”。如若果真有真正的“伦理”,“那么它就是超自然的东西”(19),那是一种像水晶般纯净的理想。维特根斯坦对此类境界做过一个物理学的比喻,“我们走上了结在地面上的薄冰层,在那里没有摩擦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恰因如此,我们也不能行走了。”(20)而这个比喻正是出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分析语言哲学研究当中,用以批判早期逻辑语言哲学对语言终极命题的向往。事实上,在维特根斯坦并不多见的著作或论述中,将语言叙事与伦理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分散,但能够触发我们关于“叙事伦理”想象的起码有以下明确的几点: 1.所谓“伦理”即所叙之事之伦理,所谓“叙事”即必然遵守着某种相对秩序的语词和语言,因此,“叙事”与“伦理”实为“互文关系”; 2.所叙之事之伦理正如叙事必需之语词和语言,虽无形而上学层面的绝对意义,但却有具体语境中的相对价值; 3.所叙之事之伦理的相对性,正如语言游戏规则的相对性,虽相对自由,但不可或缺; 4.对所叙之事之伦理的分类讨论,正如对叙事语言的“语法考察”,应极力避免多种层面“二元对立”的研究。 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推论:对“伦理”的研究必然不能忽视其“叙事”条件,而对“叙事”的研究当然也一定关乎“伦理”问题,这既对“叙事伦理”这一批评范式提出了要求,也促使“叙事伦理”有资格成为那个寻求中的、包容了传统叙事学研究和现代文化研究的批评范式,从而再一次化解叙事学发展中遇到的危机。此为其理论价值。 当然,维特根斯坦还做出过这样一个类比,“将这片树叶看成‘一般而言的树叶形状的’样品的人是以不同于将它看成比如这个特定的形状的样品的人看他的方式看它的”,并且,“从经验上说,以特定的方式看树叶的人于是便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运用它,或者按照某某规则运用它。”(21)在这里,与“样品”对应的是“语词”,他假设此情境是想说明,语词意义缘于其运用的方式,怎样的运用便会产生怎样的认识,并依此方式循环生成与之对应的意义。而出于前面对“叙事伦理”的理解,这一比喻无疑将在另一层面引发我们的关注,也即“叙事伦理”的实践价值。 但是,即便清楚了上述的种种,然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来得及或根本无意为我们廓清和构架出或将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批评范式的“叙事伦理”所需要的概念和体系,他只是通过自己充满哲学思辨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并提供了一种建构的可能,但具体到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必然不会比证明其可以被建构的过程轻松,因为语言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生发出新的样态,正如叙事学研究的发展一样,总是在行进中不断逸出新的枝芽。 试想如果“叙事伦理”能够被正确理解并因之建构出一门与其相对应的“叙事伦理学”,它无疑将施惠于当下的叙事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领域,那么,既然伴随着叙事学转向的还有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尤其是对电影的关注,那么,“何谓‘电影叙事伦理’”,又将“如何建构‘电影叙事伦理学’”这些问题的提出则显得顺理成章,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显得迫切而必要。毕竟,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电影之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甚至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学对世界文明的意义,以致当代叙事学研究在被迫由经典向后经典跨越之时不得不将视野转向它的存在;毕竟,电影除了有着类似于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以外,还有着传统语言文字所不能的叙事方式,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数字新媒体的惊人发展下,电影语言也发生了堪比有声片出现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基于传统的叙事学将文学文本视为研究对象所建立起来的相关理论,针对电影叙事学研究的著作已有不少:例如挪威学者雅各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美国学者西摩·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法国学者弗朗西斯·瓦努瓦的《书面叙事·电影叙事》以及由加拿大学者安德烈·戈德罗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若斯特合著的《什么是电影叙事学》等,此外,在爱德华·布兰尼根的《电影中的视点》、戴维·波德威尔的《故事片中的叙述》、弗朗塞斯科·卡塞蒂的《注视的注视:影片与其观众》、安德烈·戈德罗的《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和弗朗索瓦·若斯特的《眼睛-摄影机:影片与小说的比较》等著作中,也早就印证了电影叙事学的存在。虽然在马尔丹看来,“我们是无法从文字语言的类目出发去研究电影语言的”(22),但建立在“既关注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又关注为分析电影叙事提供所需工具的必要性”(23)认识之上的“电影叙事学”不仅显得极为巧妙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像叶尔姆斯列夫以不同的参考工具将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符号学用以研究电影叙事,他借图表来说明,例如在同样以“叙述、情感、思想、主题的结构”等所指形式来关涉“真实或想象的事件,在历史、传奇、神话、社会、人类……的基底中汲取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所指内容的过程中,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则是借用不同的能指实体、不同的能指形式来完成这一表达的(24),也即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是利用不同的语词和语言形式来形成话语的。 可以说,充分借鉴了经典叙事学理论范式的电影叙事学发展到今天,就“语法考察”层面显然已经足够成熟,但电影叙事学如果不像经典叙事学一样适时寻找别的突破,那么,它必将遭遇并难逃经典叙事学曾经深陷的困境;然而,如果另辟新径的电影叙事学研究也像转向后的叙事学研究那样严重忽视文本的存在,或者未能实时更新电影语言发展的新动态,那么,它的发展想必也是不健全的。 基于前文的既有论述,将“电影叙事伦理学”进行一种建构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或将有利于电影叙事学的发展,而就“叙事伦理”的“实践意义”来讲,这种建构又是如此的必要。 当然,也有学者做过相关尝试,就国内而言,这显然与出现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叙事伦理”相关,同时,与文学批评领域对“叙事伦理”存在的诸多误解一样,国内的“电影叙事伦理”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对“电影所叙之事之伦理”的讨论上。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将电影所叙之事之伦理与电影的叙事行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例如上海大学曲春景教授近年来的论文《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就是在有意识地将电影叙事伦理从以往涡旋于故事伦理的周遭摆渡到叙事行为上来。但是,由于作者明显地将“伦理”等同为了“道德”,因而使得其论述更似一种文化批评,而非典型的电影批评,此外,作者虽然强调了叙事行为的伦理性,但因其对电影叙事行为的分析缺乏对电影语词和电影语言独特性以及电影语词和电影语言伦理性的凸显,也同样使得其论证存在着明显的“电影性”不足。类似的问题也体现在河南大学徐娟2013年的硕士论文《贾樟柯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当中,例如她对贾樟柯电影叙事空间和叙事伦理的分析,就明显缺乏对电影语词、电影语言独特性的敏感,而恰恰是这种电影理论方面的欠缺导致本应该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电影语词及其运用下的空间展示与伦理性呈现”没能被充分说明,反而使这种讨论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空间分析。 那么,何谓“电影叙事伦理”,又该如何建构“电影叙事伦理学”呢?这里,我们不妨再次回顾维特根斯坦分析语言哲学中对“叙事伦理”的某些启示。 首先,应该肯定“电影叙事伦理”既不是电影叙事学的延伸,也不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正像“叙事”与“伦理”实为“互文关系”一样,“电影叙事”与“电影所叙之事之伦理”相互共生; 其二,电影故事的相对伦理伴随着电影叙事的发生,而电影叙事离不开供给相对价值意义的电影语词和语言,因此,应全面理解电影语词和语言的独特性并准确把握电影语词和语言的动态发展,而这一点,对于“电影叙事伦理”来说则显得至关重要。比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可以作为一种语词并因被使用而被赋予日常价值的“灯具”,在文学作品中,它也许只能成为一种能指符号,在纸页和笔尖之间被书写出特定语境下的意义,然而同样的“灯具”在电影中却不仅可以作为意象的一种,发挥着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发挥的作用,它还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语词”,在影像师或照明师的调控下,成为一种电影语言,有助电影叙事及其伦理性的表达。再比如,同样展示一个相貌平凡却心灵高尚的人物,文字语言似乎不会选择对其长相做过多的描述,但却需要一定时长的书写对其言行做出说明,同样也需要读者花费一定时长的阅读来了解人物的品格,但即便运用接二连三的语词或语言也无法穷尽的东西,电影却可以通过镜头的仰拍或音效的烘托一下子让人看到并读懂,而诸如这些,才是“电影叙事伦理”的主要落脚点; 其三,对电影所叙之事之伦理的讨论和对不同的电影语词和语言的分析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境; 因此,在力避“二元对立”思维的研究方法下,应充分考虑影响特定语境中电影所叙之事之伦理和电影叙事语词与语言之间关系的多重机制。例如,要分析第六代摇滚青春片,则必须认识到像《头发乱了》和《长大成人》等影片中的“声景叙事”展示的正是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亚文化——对秩序的破坏,这种亚文化催生了摇滚,而摇滚又被运用到电影叙事当中,成为了第六代电影中独有的“电影语词”,并与文学领域的“底层叙事”情绪和第六代导演明显的西方电影语言风格糅合在一起,共同营造出一个电影当中的亚文化。 总之,由于“电影叙事伦理”讨论的是作为一种伦理实践的电影叙事与相对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应当对“电影叙事伦理学”做出这样的定义,即它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伦理实践的电影叙事与相对伦理之间关系的学科。当然,必须要指出,以上所有的这些论述,都只为阐明应如何理解“电影叙事伦理”并试图对“电影叙事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一些粗浅的设想。事实上,关于“如何建构”这一问题,它需要一个长时而系统的研究过程,因为,电影的叙事问题包括电影语词和电影语言问题及其相关的伦理问题皆为动态变化中的存在,并且还会在变化中发展下去。但是,这一过程显然应当建立在对“电影叙事伦理”概念的廓清之上。唯有此,它方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批评话语。此外,正如“叙事伦理”同时兼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们也同样期待着“电影叙事伦理学”能够在成为一种电影批评的同时更能指导电影的实践活动,使“电影叙事伦理学”不仅能够推动电影叙事学的理论发展,也能够在重建人类文明家园这一任重道远的过程中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英]特雷·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②参见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4页。 ③托多罗夫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④⑧参见[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引文部分出自申丹主编《新叙事理论译丛:修辞性叙事理论》总序,《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为该译丛之一。 ⑤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⑦参见[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参见Adam Newton:Narrative Eth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在这本书的背景介绍中,“in the wake of deconstruction,the ethical question has been freshly engaged by literary studies,and on this approach Adam Newton focuses.His book makes a case for understanding narrativeas ethics.Assuming an intrinsic and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Newton explores the ethical consequences of telling stories and fictionalizing character,and the reciprocal claims binding teller,listener,witness,and reader in the process.”一段话对作者关于“叙事伦理”的生成机制理解、重点讨论对象和主要研究视角等做了简要概括。 ⑩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前言,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11)参见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绪论部分,在其对该论文所涉及问题的研究现状的梳理中,他指出,“遗憾的是,美国学者亚当·桑查瑞·纽顿曾出版《叙事伦理》一书,但因国内尚未有中译本,我只能零星了解一点他的观点”,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2000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2)(13)(14)(15)(16)(17)(18)(20)(21)[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编译前言第xxiii页,第25页,第71页,第65、62、90页,第80-81页,第39页,第81页,第84页,第64页。 (19)参见[英]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的讲演(1929)》,出自[英]维特根斯坦著《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江怡译,张敦敏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9页。 (23)[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中文版前言第3页。 (24)参见[法]弗朗西斯·瓦努瓦:《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