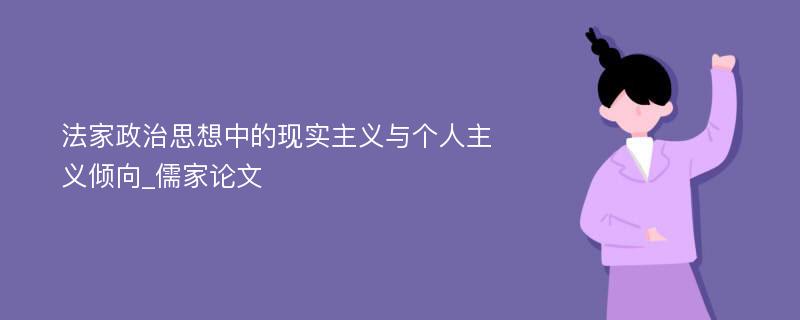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家论文,个人主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4-0030-05
冯友兰在谈到儒、法之异时曾指出:“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1] (P142)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确实,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是儒、法之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其政治思想中,法家的现实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力论。法家人士大多生活在战国时代。在其时国与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他们认识到,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原因是实力。他们看到,竞争的胜利者总是有力之人,而不是有德之士。法家确实有轻德尚力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儒家的尚德论在当时的现实面前完全是软弱无力的。韩非子别出心裁地按道德、智谋、气力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 (《五蠹》)跟上古和中世之争不同,当今之争乃实力之争。既然实力如此重要,那么,衡量一个国家实力高低的指标又是什么呢?法家人士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农(耕)和军这两方面的指标。在他们心中,农力和军力就是最基本的实力。因此,农人和战士就是最有用的人。浮夸的言谈者、文学之士、游侠等等,皆为无用之人。韩非子猛烈地攻击他们,称他们为“五蠹”(五种虫子)。
在农业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为农力,这是不错的。但是,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经济实力却远远不限于农力,而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如果法家人士生活在当代,相信他们一定会与时俱进,把农力这方面的指标调整为一个更宽的指标,比如说综合经济力的指标。在当代社会中,这一调整后的指标,再加上军力的指标,二者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最基本的指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直都在追求富与强。富事实上就是综合经济力的提高,强事实上就是军力的提高。在外敌屡侵,割地赔款不断的近代中国,最严峻的问题是贫与弱,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实现富与强。在这种情况下,2000多年前以提倡“富国强兵”而著名的法家,被人们日益重视。法家地位的上升,是很自然的事。对于饱受因贫、弱而挨打滋味的中国人来说,富强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以实力立国,看来不会有任何异议。
陈启天在20世纪40年代初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处于“新战国时代”。他说:“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家竞争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入于新战国之大变局中,将何所恃以为国家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惟有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3] (P1)2000多年前的旧战国时代和近代的新战国时代,都是求强求富特别重要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主张富国强兵的法家,都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又为时代所需要的学说。
陈启天的话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说的。在半个多世纪过去后的今天,我们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但可以说我们仍然处于“新战国时代”。现在,国与国军力上的竞争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力上的竞争。此即郑观应在19世纪后期所说的“商战”。
有一个问题值得在此讨论:法家是否因推崇实力而走向非道德主义?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到,韩非子的术,“毁坏一切伦理价值”。[4] (P353)这意味着法家主张非道德主义。近半个世纪以后,朱贻庭和赵修义详细阐发了韩非子非道德主义说。[5] 我个人认为,不能把法家说成是非道德主义者。[6] (P58-62;P77-82;P264-265)韩非子和其他很多法家人士确实是轻德的。但是,轻德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德。在法家眼里,德当然不如力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德失去了任何价值。轻德并不等于非德,不看重道德并不等于非道德主义。韩非子指出:“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夫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2] (《奸劫弑臣》),很难想象,说出以上之言的人会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这样的治世,绝对是一个道德完善之世。在追求此治世方面,法家和儒家并无不同,不同者只在于手段:儒家认为,通过德即可得到此一治世,而法家则认为,只有通过法方可达之。韩非子对奸的谴责(《韩非子》一书充满了对“奸臣”、“奸人”、“奸事”的责难),也说明他不是非道德主义者。奸,无疑是道德上的恶。韩非子之非奸,反映了他不能容忍道德上的恶。韩非子还强调守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支持他不是非道德主义者的明显证据。从法家的为人方面看,也不适宜给他们带上非道德主义的帽子。我曾把法家人士称之为“文侠”。[6] (P20-23)他们有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侠一样的侠气,但比武侠更聪明:他们设计出了一套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历代论者大都只注意到他们少恩苛严的一面,而忽视其刚直不阿、坚持公正、是非分明的一面。
第二,中君论。由于受其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影响,儒家向往圣君,并以圣君的标准要求每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执政的君王。法家认为,这样想和这样做是很不现实的。韩非子说:“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世治也。”[2] (《难势》)
法家的治国方案,都是为中君而设的。中君既非暴君,亦非圣君,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圣君实在是太难得了,“千世而一出”。如果只能靠圣君治国,那么,在没有圣君的九百九十九世,怎么办呢?确实,圣君难觅,而中君比比皆是。法家立足于中君的治国方案,是现实主义的治国方案,而儒家立足于圣君的治国方案,则太理想化了。
第三,现世论。作为现实主义者,法家人士不注重历史的承袭性,不看重过去,亦不看重将来,而专注于现世。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实情,切莫以古套今,以往世论今世。他们最反感儒家言必称三代,论必援过去。韩非子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構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2] (《五蠹》),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际问题。对这些不同的实际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于今世的问题,只能用今世的方案来解决,而不可固守旧说,搬用过去的方案。在此,韩非子的现实主义是与他的历史发展论相一致的。与儒家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不同,法家注重的是历史的间断性。并且,儒家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遥远的三代,故儒家心目中的古史是价值化的古史,而不是事实上的古史。法家则要把儒家加给古史上的价值剥离,企图还原古史的事实。因此,儒家心目中的古史要比法家心目中的美妙得多。儒者以理想的过去来批判不理想的现世。尧、舜、禹等过去的圣王,承载着儒者的政治、社会理想,他们不是纯粹的历史人物。儒者以过去理想的君王来要求今天的人君。而法家则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来讨论过去的君王。韩非子指出,“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存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挈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2] (《五蠹》)作为现实主义者,韩非子以古今为官者物质利益上的差异来解释他们对官位的态度的差异。古代之让天下,并非出于高尚的动机,而是因为在当时为王并未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好处(他们过着跟平民一样的生活),反而是一件苦差事。但是,今天当官就很不一样了:即使做一个县官,也可以富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有车坐。因此,古代君王让天下,是由于物质上的原因,而今天一个小小的县官也不愿退出其位,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第四,法治论。如果说儒家的德治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话,法家的法治则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发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商鞅则在实践中极力实施以法治国,韩非子最后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但是,有人根据某种西方现代的法治观念,断定法家人士根本不主张法治。例如,梁治平指出:“法家之‘务法’、‘法治’……丝毫不具有法治精神。……法家之‘务法’乃是信奉法术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7] (P67)“以现在立场观之,法家之主张人治,决不亚于儒家。……法家的学说根本没有‘法治’色彩。”[8] (P98-99)梁治平的根据何在呢?似乎主要有两点:第一,法治的关键在于,“必须有一部维护公民权利,同时限制政府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宪法。”[8] (P95)第二,法家没有这样的宪法,也不会认同这样的宪法,因为他们是绝对君权论者,绝对不会想到以法限制君权。拙意以为,虽然梁治平对法治之关键点的看法,出自权威文献(德国《布洛克豪百科全书》),但是,以此来定义法治是很偏狭的。连梁治平自己也承认,在古希腊时代有法治思想。但是,当时并没有宪法。并且,该权威文献被他引用的部分谈的是“法治国家的要素”,而不是“法治的要素”。他似乎把法治国家的要素作为法治的要素。事实上,二者的差别相当大。
既然梁治平对法治的定义是偏狭的,那么,怎么样的定义才是恰当的呢?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比较好:“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9] (P199)这个定义避免了前述定义的偏狭,比较明了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内涵。依照这个定义,法家有无法治精神呢?显然是有的。普遍地服从法律,不因贵贱高低而有异,这正是法家的一种基本精神。商鞅要求统治者带头守法,而“法不阿贵”则是韩非子的名言。对法家的这种基本精神,拙作《法:公正与务实》已反复申说,[6] (P86-112)在此不赘。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二点(良法),法家是否也认同呢?答案不应该是否定的。法家主张法因时而变,以极力变法而名垂青史(他们所变之“法”内容非常广泛,但肯定包含了现代所说的法律),这正反映了他们对良法的追求。当然,肯定会有人反驳说,法家以严刑(重刑)论法,故其法为恶法、苛法。何谓区分良法与恶法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此不拟深论。我想指出的是,法家心目中的良法就是严法。根据他们的价值观,严法为良不为恶,而宽法却恶而不良。因此,我们可以指责他们的严法,却不能说法家主观上追求恶法。综上所述,虽然法家的法治与现代西方的法治有很多不同,但是,不能说法家根本没有法治精神。
众所周知,法家的法治是相对于儒家的德治来说的。关于德治,孔子曾有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 (《为政》)按照儒家的看法,法治的力量是暂时的、表面的、外在的,只有德治的力量才是长远的、深层的、内在的。因此,法治的效果总体上不如德治的效果好。他们以法治为权宜之计,不可以作为治国的根本。
与儒家强调德治的效力针锋相对,法家强调法治的威力。韩非子指出,对付一个屡教不改的顽童,父母怒之,乡人谯之、师长教之都不见效,但是,如果地方官派人捉他,准备对他绳之以法,他就会因恐惧而改其恶行。[2] (《五蠹》)德治具有理想性,而法治具有现实性。孔子希望以德去刑,希望通过人人都守德而达到“无讼”的境界。这种境界确实很好,但不容易实现,而法家的以法之威严来阻止犯罪的方法似乎更有实际效力。法治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但它起码是一种不坏的、实实在在的方法。
“个人主义”一词是从翻译英文的" individualism" 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只在西方世界中才有,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拙意以为,在古代中国,起码就存在三种类型的个人主义:道家的以追求个人精神自由为目标的个人主义(以下简称道家个人主义)、儒家的以追求个人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的个人主义(以下简称儒家个人主义)、法家的以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为目标的个人主义(以下简称法家个人主义)。
在这三种个人主义中,道家个人主义跟西方的个人主义最为接近。道家个人主义在庄子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为了个人的精神自由,庄子要打破一切外在的束缚,尤其是人为的、制度性的束缚。庄子把个人自然、质朴的天性强调到最高的程度。顺着这种天性生活,即可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希望,理想的个人应该像“相忘于江湖”的鱼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相互之间无牵无挂、各顺其性;或者像翩翩起舞的蝴蝶那样,翱翔各处,既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催促。道家个人主义是一种艺术家式的个人主义。
儒家个人主义在其“为己之学”中得到最明朗的显示。孔子和荀子都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0] (《宪问》);[11] (《劝学》)宋明儒者也很注重这句话。此处的“为己”是指“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而“为人”是指“炫耀自己,做给别人看”。用从英语“show”翻译过来的“作秀”来解释孔子和荀子说的“为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儒家的“为己之学”重己,但不轻人、不轻社会。因其重己,故它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有相通的地方;因其不轻人、不轻社会,故它又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正如杜维明所说的,“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并非指人本身是被孤立的或可孤立的‘个人’。他甚至也并不认为自我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自主实体,不认为自我经常与社会发生冲突。确实,其时其世还没有人持这样的观念。”[12] (P32)儒家个人主义是一种士者式的个人主义。
与道家的艺术家式的个人主义和儒家的士者式的个人主义不同,法家个人主义是商人式的个人主义。法家个人主义当然在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那里展示得最典型、最充分。他清醒地看到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个人本性、个人存在的意义都在一己求利活动中表现出来。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并不规定个人,相反,个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形成对他人的关系:与跟他利益相合者产生正的关系,而与跟他利益相逆者则产生负的关系。韩非子反复说,个人以计算之心看待他人。个人对有血亲关系的他人尚且有计算之心相待,至于对没有这种关系的他人,就更是如此了。韩非子心目中的个人,确实是赤裸裸的、纯粹的个人。
韩非子指出:“君臣之交,计也。”[2] (《饰邪》)以“计”来说明君臣关系,是韩非子的一大创举。在这里,君臣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君以“计”待臣,臣也会以“计”待君。于是,君尊臣卑的关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君臣一如合伙做生意的伙伴。这种关系意味着,君臣是平等的。仅以此即可看出,韩非子并不主张绝对君权论。
韩非子竟然还以买卖关系来说明君臣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2] (《难一》)君王是卖方,他出卖的东西就是官爵和俸禄。臣下是买方,他付出的就是力。买卖双方均自愿,强迫的买卖是做不成的。由此可见臣下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意志。韩非子把君臣关系看得太现实了。法家的个人主义是与其现实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人容易欣赏道家和儒家的个人主义,而比较反感法家的个人主义。其原因恐怕在于法家的个人主义过重己利而缺乏温情。但是,正是这种缺乏温情的个人主义含有平等意识。既然人人都是一个求利个体,人与人之间便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把君臣关系看作是做生意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在当时不是一种惊天动地的看法吗?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听到这个说法还是会感到吃惊的。
法家的这种个人,与西方个人主义意义下的个人很相似。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原子论,它对西方人的思想有很深远的影响。以原子论来看个人和社会,个人就被看作组成社会的原子。作为组成社会的原子的个人,就是个人主义意义下的个人。在这方面,法家跟西方的思想不谋而合。两者都把个人作为组成社会的原子,都把个人作为追求己利的主体。
法家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与韩非子所说的“不两立”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单独的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孤身奋斗,他必然会遇到很多其他也同样孤身奋斗的人,于是便难免发生碰撞,发生冲突,形成“不两立”的关系。因此,求一己之利的个人,是形成社会、政治上众多“不两立”关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法家人士觉察到人与人的分立、人与人的竞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竞争便会引向无休止的斗争。法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商鞅指出,“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13] (《开塞》)此处之“中正”、“无私”,当然就是指法律。法律一方面避免竞争导向暴乱,另一方面,又保证人们在公平的机会下竞争。由此可见个人主义与法家法律观的关系。
有人恐怕会问,法家不是主张国家主义吗?而国家主义不正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吗?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主张个人主义呢?这些问题提得很好。法家确实表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此一倾向与个人主义倾向形成一种紧张。不过,我们要看到,一般来说,法家的国家主义并不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恰恰相反,它利用刑赏二柄,以重赏来满足个人利益,以重刑来使人们权衡个人利益,从而鼓励他们为实现国家利益去耕、去战。法家人士信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则,而不相信民天生固有爱国、爱君之心。韩非子指出,“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2] (《饰邪》)从这里可以看出,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个人主义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主义并不必然处于不两立的状态。在韩非子看来,只要恰当地运用“二柄”,厉行法治,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就可以处于双赢的局面。
综观法家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不难发现它们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学研究的意义。研究政治学的人要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在研究政治现象时必须立足现实,保持冷静的头脑,以便寻找任何良好愿望所不能掩盖的真实。用价值中立的眼光观察人和社会,这是2000多年前的法家给后人的重要启示。根据这种启示从事政治学研究,容易得出新的成果。
注释:
①“法家政治思想”一词所指经常不容易确定。其关键原因在于,“法家”一词之所指不容易确定。有人把它定为“秦政”的执行者,而秦政又与暴政相连;有人把它定为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一个学派。本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法家”一词的。因此,本文所说的“法家政治思想”,主要是指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的政治思想。
标签:儒家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法家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五蠹论文; 韩非论文; 法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