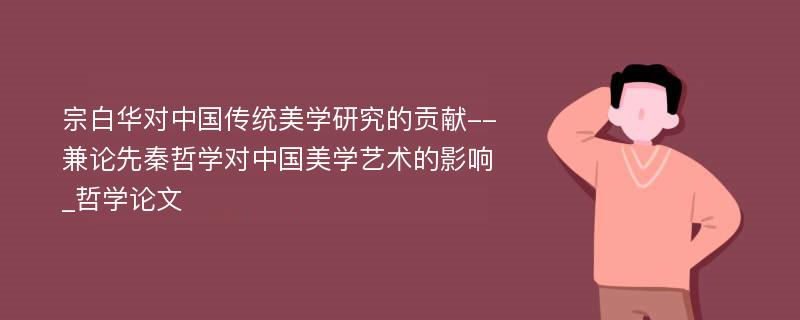
试论宗白华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贡献——兼评先秦哲学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先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3)01-0030-05
在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中,宗白华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探讨,他对艺术的精妙感悟,他的研究视角以及他的文章论述风格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我们看到,继宗白华之后,还有两位研究中国美学的大家,一位是李泽厚,一位是叶朗。但其实两人都与宗白华结下了不解的思想渊缘。叶朗可谓得其精髓,并使宗白华提出的许多见解和观念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特别是对某些重要的审美概念和范畴(如“意象”和“意境”)内涵作了更加明晰而深刻的阐发。而李泽厚,一方面在文风上承其华美,并更趋自由纵达;而另一方面,则从社会学和哲学的高度拓宽了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格局,以其思辩的理路展示出了一个恢宏的美的历程。但对中国艺术审美特性的深切体察上,却比宗白华终落一层。如果说,李、叶两人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必须直接面对的大家的话,那么,宗白华则是站在这两人背后的一代宗师。
应当说,考察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及其发展,远则可遥溯王国维,近则须以宗白华为基点。叶朗曾说:宗白华“在学术文化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1](P431)那么,他在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方面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之哲学底蕴的揭示上,而这又主要集中在对宇宙本体的审美探究上。宗白华认为,中国哲学构成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灵魂。所以他一再强调说:“文艺从它的右邻‘哲学’获得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2](P20)还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2](P110),而对中国美学和艺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乃是先秦哲学。因而我们看到,宗白华在讨论中国美学和艺术时总是反复引述老庄、《易传》等哲学观点。同样,对宇宙本体的探讨也是如此。可以说,先秦哲学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一个重要影响正体现在这一方面(当然不止于此)。这也就是叶朗先生后来所讲的中国艺术中所包含着的“宇宙感”。[3](P49-67)
宗白华认为,在中国哲人和艺术家看来,宇宙本体的一个基本品格就是“虚无”。先秦老子曾以“道”和“大象”等范畴来指称宇宙本体。宗白华说:“老子曰:‘大象无形’。诗人画家由纷纭万象的摹写以证悟到‘大象无形’。用太空、太虚、无、混茫,来暗示或象征这形而上的道,这永恒创化着的原理。”[2](P96)从这段论述可知,作为宇宙本体(“道”、“大象”)是不同于一般物象的,因为它是“无形”,或者说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十四章)[4](P31)。而一般物色则有形有状,具有某种确定的形态。正如后来庄子所说:“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达生》)[5](P271)在老子看来,人们感知一般物象,显然要依赖于某种感官经验,但对于宇宙本体(“道”)则不然,由于它是“无形”的,所以人们往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4](P31),无法以感官经验(视、听、搏)来直接把握之。不仅如此,老子进而指出,“道”还是“无名”的(“名”者,语言概念也),所谓“道常无名”、“道隐无名”,“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老子》十四章)[4](P31)。后来庄子也说:“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则阳》)[5](P403)这就是讲,一般物象往往呈现为某种实在形态(“物之居”),因而是“有名”的。而“道”乃为非实在的形态(“物之虚”),所以是“无名”的、“不可名”的,即无法以语言概念(“名”)来加以描述和界定。先秦哲人这些论述实际为后来中国艺术家在有形有状的实在世界中敞开了一个空灵通透的“无”的境界。
当然,作为艺术家(如画家)直接面对的乃是有形的物象,中国绘画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外师造化”,“以天地为师”。但是对中国艺术家而言,他在审美创造中往往不为某种确定的物象形态所拘,按照宗白华的说法,他们“由纷纭万象的摹写以证悟到‘大象无形’”,从而展示出“混茫”、“太虚”的宇宙境界。宗白华还说:“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到在一片无边的虚白上”,“在这一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2](P71)他又说:“书法的妙境通于绘画,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2](P71)应当说,在这里宗白华已然揭示出了中国艺术的“意境”的本质特征,即从有限(物象)通向无限,通向宇宙本体(“道”)。一切有形的,实在的物象在“境”的层面上如“光”笼照而显得虚灵晶莹而通透,彰显着宇宙的本相。所以宗白华常常将“意境”称之为“虚灵之境”、“晶莹真境”。中国艺术的“宇宙情调”、“宇宙意识”正是在这“意境”中流露出来。
宗白华还认为,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往往喜爱展示天地万物的整体景象。他说:“由于中国陆地广大深远,苍苍茫茫,中国人多喜欢登高望远”,“从高处把握全面。”[2](P48)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2](62)其实,这种审美倾向也与先秦哲学对于宇宙本体的探究密切相关。在老子哲学中,常用“大”这一词语来形容宇宙本体(“道”)。我们看到,除了“大象”之外,还有所谓“大道”、“大音”、“大方”、“大盈”、“大器”、“大白”、“大直”、“大巧”等等,“大”字触目皆是。我认为老子反复提到“大”字是极有深意的。“大”字意味着无限,意味着无限的“大象”(“道”)对有限物象的包容和宠统。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老子》三十五章)[4](P87)王弼注曰:“大象,天象之母也”,“故能包统万物”。[4](P88)在老子心目中,“天”、“地”已算是够大的了。所以他说:“天大”、“地大”。但天地毕竟还是一种有限的大,按照庄子的说法:“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则阳》)[5](P402)可见天地只是一种有形之大,而有形就会有限。只有大象(“道”)才是一种无限的大。所以老子又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老子》三十四章)[4](P86)这同样是讲“大道”(“大象”)可以上下左右,无所不至,从而将天地万物一概包容其中。因此人们要想从整体上把握和观照天地万物,就不能拘限于有限的物象,而应当从中腾跃出来,站在“道”的立场,执其大象。对此老子还有一般值得注意的论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大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老子》六十七章)[4](P170)这表明,“道”(“大象”之所以不同于(“不肖”)一般物象,不仅在于其“无形”、“无名”,而且在于其“大”,而不是“细”。《说文》曰:“细,微也。”可见所谓“细”,就是指物象的微小和有限,因此要想得到“大”(“道”),就不能局限于“细”,不能囿于有限的物象形态。后来庄子也一再强调:“不饰于物”,“不以身假物”(《天下》)[5](P499-500),而要“齐万物”,要“与物宛转”,要“官天地,府万物”,要“物物而不物于物”,要“浮游乎万物之祖”,“通乎物之所造”(《山木》)[5](P289)。一句话,就是要突破“细”,超越有限,这样才会拥有一种统摄天地万物的眼界和胸襟。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艺术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宗白华说,中国艺术家总是力图“在作品中把握天地境界”。他们总是“用心灵的眼,笼罩全景,从全体来看部分”[2](P81)。宋代沈括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正是这一思想的很好的美学概括。宗白华还以清代王夫之的话来进一步说明中国艺术家这种统摄万物,笼罩天地的眼界和胸襟,所谓“广摄四旁,圜中自显”,所谓“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并认为这些话“表出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2](P71)。后来叶朗发挥这一观点时指出,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注重展示宇宙的全幅天地乃是“意境”的一个最重要的审美特征。[6](P224)
宗白华进而认为,在中国哲人和艺术家的眼中,宇宙本体(“道”)的基本品格虽曰“虚无”,但绝不是“真空”,它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的创化过程乃是大气流行、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说:“中国人感到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都是万物的源泉,万动的根本,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老庄名之为道,为自然,为虚无”,“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虚中去”[2](P123)。这一论述是对老子(包括庄子)宇宙创化理论的极为深刻的阐发。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4](P117)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4](P110)其一个“生”字点明了宇宙本体(“道”)的创造伟力。老子还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4](P117)可见宇宙创化万物乃是一个气化(阴阳调和)的过程。“气”渗透于万物,充盈于虚空,而本源于“道”(“无”)。如果说,“无”乃是宇宙本体(“道”)的基本品格的话,那么,“气”则是这一本体的最重要的特质。有了“气”,天地万物才拥有了不竭的生机和生命。应当说,这种宇宙观为中国艺术创造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对此宗白华作了不少相关的精彩论述。他说:“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2](P110)而“艺术的创造追随真宰的创造。”[2](P24)“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2](P124)中国画“表象着全幅宇宙的絪緼的气韵,正符合中国心灵蓬松潇洒的意境。”[2](P111)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体系中,“气”这一范畴获得了极为重要而广泛的美学意义,它不仅用来说明审美创造的性质,而且还成为艺术品评的最高标准,进而还是揭示艺术才性和禀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大量文艺论著中,可能还没有任何其它概念可以取代“气”的思想地位,也没有其它概念像“气”一样与宇宙本体(“道”)如此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南朝谢赫所提出的“气韵生动”这一著名的美学命题才会影响深远而千古不朽。
与宇宙本体问题相联系,宗白华还考察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实际上,时空观说到底就是宇宙观。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宗白华将中西方时空观作了一番分析和比较。他认为在中国哲人和艺术家的意识中,所谓“空间”不像西方人那样是一个“堆叠穿斫”的机械空间,不是一个“测量推度”的几何空间,或者说不是一个“间架”、“顽空”,而是一个荡漾着节奏化的空间。因为中国人的空间感总是贯融和流动着时间意识。他说,对于中国人而言,“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率领着空间方位”,“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音乐化了!”[2](P89)正是这样,决定了我们中国艺术家在观照天地万物时,其视线是仰观俯察、流动宛转的,而不像西方人那样“集结于一个焦点”[2](P90)。也正是这样,我们中国艺术家在审美创造中不像西方人那样执著于“物象外表”,迷恋了“凹凸阴影”和“立体真景”[2](P110),而是力求“从刻画实体中解放出来”,而“取物象的骨气”,“以表示宇宙万相的变化节奏”[2](P95)。他还说:“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也阳同波(庄子语),我们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2](P89)因此“中国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2](P84)。中国人的山水画“好像空中的乐奏,表现一个音乐化的空间境界”[2](P83)。“中国书法艺术表达出来”的更是一个“节奏化的自然”[2](P105)。凡此种种,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的审美精神通向诗,通向音乐,通向舞蹈。从根本上讲,乃是通向那种将空间节奏化了的时间之流。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专列一节讨论“线的艺术”。其实是宗白华最先、也最深刻地从美学高度上阐发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绘画“特别注重线条”和“线条的组织”(更不用说书法艺术了);而中国的雕塑、戏曲、建筑艺术实质上也渗透了“线”的精神意趣。从早期的商周钟鼎镜盘上所雕绘的那些龙蛇虎豹、星云鸟兽,到东汉画象石和敦煌壁画;从顾恺之的“高左游丝”到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以至宋元明清的绘画,无一不贯穿着“线”之飞舞的韵律。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为什么注重“线条”?有不少学者从主观抒发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理解还必须联系到中国人的时空观。中国艺术的“线条”无疑最具有“时间”的品格,中国艺术家在表现空间对象时总是使其融化在“线条”的时间节奏中。所以宗白华说,中国画的“笔法是流动有律的线纹,不是静止立体的形相”[2](P133)。中国艺术家总是将“形体化成为飞动的线条”,“其笔法不暇作形体实象的描摹,而以表现动力气韵为主”,以“其线纹的动荡、自由超象而取势”。西方艺术当然也有线条之运用,但“西画线条是抚摩着肉体,显露着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暗示物象的骨格、气势与动向”[2](P132-133)。这也就是讲,西方艺术总是使线条服从于空间造型,而中国艺术则将空间形体隶属于时间化的线条组织,中西方艺术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时空观的不同。据此来看,中国艺术的“线条”就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技法问题,它和中国人的宇宙观(即时空观)紧密相关。所以宗白华说,中国艺术家“注重线条”,注重“笔墨的重要”,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代表了一种艺术境界”[2](P143)。宗白华这些论述使我们不禁想起清代大画家石涛的“一画”说。“一画”当然和“线条”(“笔墨”)运用相关。形象的但“一画”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在石涛看来,“一画”还是开辟混沌,为宇宙立法,贯穿天地万物的大法则。所谓“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所谓“一画”“可参天地之化育”,“能贯山川之形神”(石涛《画语录》)。而宗白华对此发挥说:“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是万物形象里节奏旋律的体现”[2](P29-38)。可见,“一画”乃是把中国艺术中的“线”的精神提升到宇宙创化的高度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美学总结。在这一问题的见识上,宗白华与石涛可谓灵犀相通,古今相照。
宗白华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例如,他对中国文艺所包含着的两种美感和理想曾作过精彩的分析。一种就是所谓“华丽繁富的美”(或曰“错采镂金、雕缋满眼”之美);一种则是“平淡素净的美”(或曰“自然可爱”之美)[2](P44)。宗白华推崇后一种美,认为只有这种平淡、朴素、自然本色的美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文艺较高的理想和境界。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一方面以中国历代文艺实例作为依据(如汉代的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水墨山水和园林等等);另一方面则以《易经》思想(所谓“白贲”的“无色”之美)为根由。其实从思想渊源上看,老庄哲学中也包含了更多的、同样的观念。老子认为,“道”本身就是“自然”(《老子》二十五章)[4](P65)的,其重要品格就是“恬淡”(《老子》三十一章)[4](P80)。庄子也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5](P227)“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5](P188)。可见先秦哲人早已为后世文艺提示和确立了这样一种审美境界和人格风范,而宗白华则进一步为我们考察美学史(包括艺术史)的风格划分和趣味判断提供出了一个宝贵的视角。
又如,他对中国美学史上许多重要的审美范畴和命题的阐发都是十分精辟的。他指出,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表达形象内部的生命”和“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2](P44)。所谓“骨法”,一方面是指“形象的‘骨’”、“形象内部的坚固的组织”[2](P45-46);另一方面就是指用笔要“全其骨气”。而所谓“风骨”则是“既重视思想”(“骨”),“又重视情感”(“风”);“骨”乃偏于“逻辑性”,而“风”则偏于“艺术性”[2](P183)。风骨相结合才是好文章,才能打动人。此外,他对顾恺之“迁想妙得”这一命题的分析,对宗炳《画山水序》的阐释,对荆浩“六要”的解读,如此等等,不仅精辟深刻,而且都是一些开创性的研究贡献。
宗白华还写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他在治“史”方面的非凡的美学眼力。中国历史到了魏晋南北朝,才真正开启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和艺术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先秦的哲学与秦汉的艺术都汇融到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格局中——这就是“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从而使中国人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2](P71)。它重个性、重哲学、重自然、重艺术、重风度、重情感、重友谊——所以宗白华将这一时期喻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说,中国后来美学思想的发展及中国艺术那种潇洒、优美而俊逸的身影皆可以在“晋人的美”中找到她的原型。宗白华虽然没有系统的美学史著作,但这一篇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短文,却能胜却他人若许著述,堪称为史家大手笔,美学大经典。
宗白华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在哲学(尤其是先秦哲学)上的深厚修养之外,有一点是不应该忽略的,这就是他对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深切体察。中国另一位美学巨匠朱光潜先生就曾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7](P553)的确,大凡在美学上卓有成就的中国美学家都是“通艺”的,都对具体的艺术部门作过深入的研究。如叶朗对中国小说艺术从情节结构到语言风格的考察,李泽厚对对陶潜、王维、苏轼等人诗歌境界的体味,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中国古代美学家中有很多人就是艺术家,他们的美学观点完全是从艺术实践中体验、提炼出来的。而宗白华同样如此。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没有对艺术实践经验的“真凭”“实感”,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如他对中国书画“用笔”的论述:“中国画的用笔,从空中直落,墨花飞舞,和画上虚白,溶成一片。”[2](P71)“中国书法家用中锋写的字,背阳光一照,正中间有道黑线,黑线周围是淡墨,叫作‘绵裹铁’”[2](P46)应该说,只有在对文艺实践经验体察的基础上孵化出来的概念和范畴才会富有美学意味,文字表述才会令人心动眼亮。当然,艺术家不一定能讲清美学道理,这是他们缺乏理论训练的缘故。但美学家却不仅要讲清道理,而且还必须讲得充满艺术情趣,因而他必须对艺术本身有很高的感悟能力。叶朗在评价庄子时曾说他的著作“充满了诗的意味”,“是哲学与诗的统一,智慧与深情的统一”[3](P96)。其实宗白华也是这样,读宗白华的文章,你不仅可以领略到美学的妙理,而且还会笼罩在一种诗情画意的氛围中,他的美学也是哲学与诗的融合和统一。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对传统美学的研究至今无人超过,而他的文章风格之美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极高的艺术感悟力也是人们无法比拟的。
〔收稿日期〕2002-08-28
标签:哲学论文; 艺术论文; 宗白华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老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