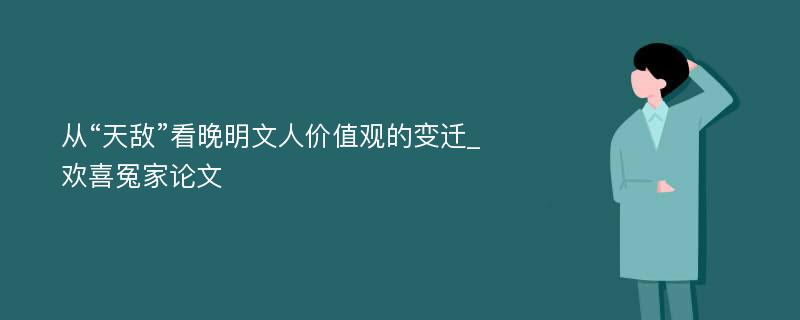
从《欢喜冤家》看晚明文人价值观念的变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欢喜冤家论文,明文论文,价值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众多的晚明通俗小说中,西湖渔隐主人编撰的拟话本专集《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艳镜》),尽管文笔略嫌粗糙,却以全新的价值取向而特别引人注目。表面上看,该书与“借通俗语言鼓吹经传”的劝善惩淫之作大相径庭,公然背弃了文人必须株守的传统理性原则,而在题材选择乃至某些细节描写等方面与晚明盛行的色情小说颇为相似,以致不无“诲淫”之嫌。换言之,真实地描绘生活中错乱的两性关系,进而揭示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对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表示极度的冷漠,构成了《欢喜冤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作者热衷于选择性爱题材,并非为了制造感官刺激以迎合市民阶层庸俗的娱乐要求,而是力图通过对颇为敏感的两性生活的深入剖析,寄寓自我对于个体生命的热情关注与严肃思考,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艺术品位。
(一)
《欢喜冤家》凡二十四回,其中二十回围绕性爱展开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占全书篇幅的5/6,足见作者本人“堪为风月文章”之说不诬。在这些故事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有过婚外性生活经历。若依据传统的女性价值标准衡量,即使不将她们一概视为“荡妇淫娃”,至少可以归入“妇德有亏”者一类。然而,对于这样一些道德意识异常淡薄的“失节”女性,作者不仅未予严厉指责,反而深切地同情她们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赞赏其中某些人果断泼辣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情感态度。
第一回中的花二娘,不仅“生得十分美貌”,而且胆识过人,是一位深得作者喜爱的女性。因丈夫花林整日酗酒赌博,“不在温柔乡里着脚”,二娘不甘虚度年华,义无反顾地与“年青俊雅,举止风流”的书生任龙相好,获得了向往已久却未曾有过的快乐的生命体验。偶闻任生未婚妻张氏“闺中不谨,腹中有了利钱”,二娘即主动设法替其排忧解难,挽救了另一位偷情者的生命。为了摆脱因奸情败露所面临的困境,不惜与素日憎恶的无耻小人李二白发生性关系,既躲过了杀身之祸,又严厉惩罚了居心不良的捉奸者。在该回小说中,花二娘的偷情、救人与自救,无不以背叛伦理道德为前提。即使是后来的“收心”,也并非自觉皈依理性原则,而应归功于丈夫的痛改前非。耐人寻味的是,渔隐主人不仅认定二娘的性放纵无可非议,更对其令人瞠目结舌的“自救”方式倍加赞赏,称之为“出奇制胜,智者不及”。相反,对于策划和参与捉奸者李二白、周裁缝的死于非命,作者却颇为兴灾乐祸,并从血淋淋的事实中引申出“杀人者还自杀”的结论,意在使视人命为儿戏的人们深自警醒。相对而言,李月仙(第三回)和犹氏(第七回)的生活经历更令人惊心动魄,她们所做的价值选择透露出更为强烈的生命意识。李月仙在丈夫王文甫出外经商不久,即与伙计章必英勾搭成奸,两人“就是夫妻一般,行则相陪,坐则交股”。章必英色迷心窍,与李禁子狼狈为奸,买通死囚宋七将王文甫扳入强盗一案,企图谋夫夺妻。月仙被骗改嫁章必英,虽然获得了极度的性满足,“爱得如鱼得水,如胶似漆”,但在知悉事情的原委后,即往官府首告,救出了在狱中苟延残喘的丈夫,使用心险恶的好色之徒落入法网。犹氏于丈夫潘璘落水身亡后改嫁富商陈彩,“朝欢暮乐,似水如鱼”,生活十分美满。就在案发当天,犹氏曾满怀深情地对陈彩道:“我与你十八年夫妻,情投意合,几曾有半句怨言?如今恨不得一口水吞你在肚里,两人并做一人方好。”当陈彩无意中泄露当年谋害潘璘的真相时,犹氏立即率领潘家儿子前往州衙叫屈,并断然拒绝去狱中与其诀别。如此急剧的情感变化,使陈彩至死不明所以。质言之,李月仙、犹氏令人肃然起敬的“割爱”之举,与其说是珍惜昔日的夫妻之情,不如理解为对于任意剥夺他人生命行为本能的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宁愿放弃令人歆羡的物质生活和销魂荡魄的两性交媾,无怨无悔地做出非常人能及的自我牺牲。
与上述三人相比,袁元娘(第五回)、方二姑(第九回)既毫无节制地放纵色欲,又不择手段地占有他人的财产,却没有“救人”、“割爱”之类的自赎,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失节”女性。对于此类女性,作者虽未旗帜鲜明地予以热情赞扬,但仍委婉含蓄地表示了理解和肯定。袁元娘被蒋青派人掳到船上时,曾因恐惧和羞愧一度萌发投水自尽的念头,也作过短暂的绝食尝试。但在蒋青甜言密语的央求下,旋即放弃保持清白之躯的努力,异常投入地与其交欢,“把那些假腔调一些也不做出来”。随蒋青到家后,见其“比刘家千倍之富”,便心安理得地做了“填房娘子”。六年后,刘玉前往蒋村认妻,元娘既未想到告官惩办蒋青,也不愿马上随丈夫返家,而是将房中的金银珠宝“一包一包的缚了半夜”,让其与小使一日几次地从衣服中夹带出去,搬运回家购置田地产业。后蒋青因奸被杀,元娘便采取暗度陈仓的方式将其百万家私占为己有,在胜利的欢乐中与丈夫团聚。方二姑慌乱中听信媒婆之言,误嫁“年纪足足五十岁”的小贩王小山,生活极不顺心。王小山为了改善日趋窘迫的经济状况,指使二姑卖弄风情勾引“极风流有钞”的未婚男子张二官合股开店,企图用美人局骗取其三百两银子的入伙股金。二姑不顾小山“与他调着,只不许到手”的叮嘱,与二官频频偷情,又助其夤夜盗窃店中货物,致使小山愤懑而死。殡葬小山后,二姑索性“明公正气”地与二官做了长久夫妻。在渔隐主人看来:袁元娘放弃徒劳无益的抗争以保全生命,刘玉不做于事无补的告官而获取财物,虽以牺牲名节和蒙受耻辱为代价,却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方二姑假戏真做乃事出有因,应予谅解;王小山“赔了夫人又折兵”则咎由自取,不必同情。
综上所述,在《欢喜冤家》执着深挚的女性关怀中,显然寄寓着渔隐主人具有反叛勇气和深刻内涵的生命意识。首先,个体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剥夺。众所周知,道学家们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将理性原则置于感性生命之上。与之针锋相对,渔隐主人在作品中暗含“失节事小,人命事大”的严肃命题,用大量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女性的“失节”由多方面的原因所致(诸如生理需要、迫于情势、上当受骗,等等),并不意味人性的堕落与毁灭,花二娘的主动“救人”、李月仙与犹氏的决绝“割爱”、莲姑的还子存祧(二十一回)、马玉贞的幡然悔悟(十五回)、蔡玉奴的知恩图报(十一回),表明“失节”女性依然有着明辨是非的“良知”。基于这种认识,渔隐主人对“失节”女性一概予以宽宥,并为其中某些因奸情而殒命者鸣不平。丫环爱莲参与主母通奸,御史张英将其推入池中淹死,被“有直臣风烈”的洪按院以“治家不正,无故杀婢”疏劾罢职(第四回);香娘既淫纵无度又思谋害亲夫,奸夫沈成激于义愤怒斩其首,亦由官府明正典刑(第八回)。在这里,渔隐主人更设想利用司法手段保障失节女性们的生存权力,其对个体生命的极端重视由此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黑壮男子怒诛情妇的故事,亦被写进《型世言》第五回,情节相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淫妇邓氏死有余辜,世人皆曰可杀;奸夫耿埴不仅蒙圣恩得宥,更成为万民景仰的“侠士”。在篇末评语中,作者更表达了对于冷酷奸夫的无限期盼:“安得耿埴者尽刃此不义妇,庶几令淫风少息。”透过同一题材的迥异处理,颇能见出生命意识与伦理意识之间的明晰分野。其次,个体生命存在于世,应在不危害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对于人类的自然本能,渔隐主人不仅充分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亦且主张乃至怂恿采取违背常规的方式释放“人欲”以确保生命质量。在具体操作上,渔隐主人选择失节女性这一独特的视角,不厌其烦地细腻描写她们在性爱过程中强烈的生理刺激和心灵震撼,以此作为实践自我生命意识的逻辑起点。书中大批主动放纵的女性,无不在性命相搏般的交欢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并由此发出惊喜至极的感叹。花二娘“不想此事这般有趣”的如梦初醒,李月仙“从来未有今朝这般快活”的今昔对比,莫氏“若得二年夜夜如此,死也甘心”的一往无前(第四回),香娘“早知嫁了他,倒是一生快活”的追悔莫及(第八回)……。这些裸露的内心感受,汇集成珍惜和赞美感性生命的大合唱。另一方面,渔隐主人在兴趣盎然地描绘混乱的两性世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写到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物质活动,其价值取向亦与传统的“义利之辨”背道而驰。《欢喜冤家》中的女性,不仅在性爱方面孜孜以求,对于物质财富同样颇为敏感,其获取方式往往具有掠夺性。举例而言:袁元娘侵吞蒋青财产陡然致富,方二姑唆使情人盗窃货物另开店面,马玉贞“穿一件大袖衫儿”倚门卖笑以救燃眉之急(十五回),莲姑“放出许多妖娆体态”向朱公子索取银两(二十一回),王氏以美色和满满八箱金宝珠玉为锈饵,将吝啬鬼汪监生三千余两银子席卷一空(十二回),巫娘伙同其弟梦花生卖弄色艺迷惑秀才王国卿,用鹅卵石暗中换走其六百两银子的考试盘缠(二十三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上述女性近乎掠夺的物质活动,渔隐主人明显地倾向于肯定,深情地赞许她们不让须眉的机智与胆识,而对于受害者们的损失财物,则不是归之于“天道好还”即嘲笑其“得便宜处失便宜”,兴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显而易见,渔隐主人不仅完全适应了现实生活中残酷的生存竞争,亦且认同了由此而来的损人利己的谋生手段。
(二)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裂变,传统的价值体系已濒临崩溃。人们怀疑乃至彻底否定传统的伦理道德,无所顾忌地放纵个人的自然欲望,形成积重难返的“好货”、“好色”的时代风气。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金钱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和崇拜对象,驱使人们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纵是至亲骨肉,关着财物面上,就换了一条肚肠,使了一番见识,当面来弄你、计算你。”〔1〕另一方面, 物质活动的社会化,打破了封闭的传统人际关系格局,促进异性之间的频繁交往,从而导致两性关系的极度紊乱。从充满原始性骚动的山歌,到“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的病态性观念,再到公开流传的春宫图册和淫秽小说,不难想见当时人们占有女色之欲望强烈、放纵到了何种程度。
面对“如沉疴积痿”的社会现状,王守仁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倡导积极的观念调整,力图以此帮助知识阶层摆脱心理困境并挽救世道人心。王守仁将超感性先验存在的“良知”作为心性之本体,用它去统一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天理”与“人心”的关系,从而奠定了否定程朱理学的本体论基石。他那“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价值判断,以及围绕该命题所展开的详尽论述,弥合了普通百姓与圣贤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蕴含着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为了引导知识阶层调整自我和客观环境的关系,王守仁不仅肯定“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辨明关注日常生活与“势利之心”的本质区别,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标准:“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2〕正是受着“做愚夫愚妇”思想的感召, 晚明相当多数的知识者放纵“心中贼”,理直气壮地与世俗社会和光同尘,走到王守仁主观愿望的反面。
王艮发展阳明“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的观点,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将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形而下的实际生活,变相肯定了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王艮深信:“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3 〕其子王襞将此观点具体发挥道:“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4〕在王艮父子看来, 人们为了生存所从事的各种物质活动,只要不是刻意损人利己和过于放纵,皆属合乎道德的行为,没有必要对其严加约束。用王襞本人的话说:“自朝至暮,动作施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与蛇画足。”〔5 〕王艮父子对于百姓日用的高度重视,为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同。在确认“百姓日用即道”的基础上,王艮首倡惊世骇俗的“安身说”,将个体的正常生存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王艮指出:“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欲齐、治、平,在于安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6 〕。所谓“安身”,包含两层意思:在主观方面,任何个体应该珍惜自我的生命价值,切勿为了贪图享受而胡作非为,以免招致各种灾祸;在客观方面,牧民者亦须尊重个体的生存要求,努力创造条件使其安居乐业,防止他们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从而彻底消除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先儒提倡杀身成仁,树立“烹身割股”、“饿死结缨”的人格典范,鼓励人们予以仿效。王艮则反其道而行之,严厉驳斥道:“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7〕诚然,“安身说”在实践中难免产生某些负面影响, 极易诱发丧失气节苟且偷生之弊,但其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却是值得重视的。李贽沿着泰州学派重视人的自然本能的思路向前推进,以“私心”为本体,对“人欲”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肯定。他深刻地认识到,生存竞争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与其强行禁欲“逆天道之常”,不如让人们“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8〕。为此, 李贽重新规定了“礼”的内涵:“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9 〕“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学者多执一定之见,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礼也。”〔10〕此处所言之“从民之欲”、“大同于俗”,显然脱胎于王守仁“与愚夫愚妇同”的提法,但更具有反理性意味。李贽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好货”、“好色”社会风气影响思想界的必然结果,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修正传统价值观的强烈愿望,虽然彻底否定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但也存在着鼓励纵欲的偏激。
稍后于王守仁的道学家吴廷翰愤怒地指出:“倡为‘致良知说’者,源头只是佛,假吾儒之学,改头换面出来。”〔11〕虽然王守仁提倡“在事上磨炼做工夫”,反对佛教徒式的独处静修,但他将“良知”比做释氏所言之“本来面目”,其竭力鼓吹的“学贵自得”亦颇类禅宗的“顿悟”,故极易被论敌目为“认贼作子”。龙溪、泰州紧随其后,“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使心学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王畿视心、意、知、物皆无善恶,直接将“良知”等同于佛性。王艮发扬光大师门宗旨,将个体感性生命置于理性原则之上,其“安身说”或多或少受到佛教“好生”观念的影响。泰州学派诸子皆强调“为人须求为真人,毋为假人”〔12〕,李贽更将“真”界定为“直心而动”、“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13〕,而这又与佛教的“不打诳语”颇为相似。万历后期,信奉心学的的知识者们愈益肆无忌惮地混淆儒释界限,“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形成使正统文人慨叹“经学几为榛莽”的狂禅世风〔14〕。梁维枢《玉剑尊闻》卷六引张元祯语云:“余自少登朝,见士大夫凡三变:初讲政事,后讲文章,今则专讲性命。”心学与佛教皆以关注个体生命作为逻辑起点,理所当然地激发了知识阶层联系实际生活思考和讨论“性命”问题的极大热情。据周晖《金陵琐事》“因果”载:王世贞与同僚聚会,极言佛氏因果之说,其驾轻就熟的讲论令众人折服。王性海身为宰官,公务之余经常去寺庙“担水斫柴,和众作务”,并作《戒杀文》以劝世,当上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俗家弟子〔15〕。随着“性命”讨论热潮的持续高涨,不少人因无法摆脱对于死亡的恐惧,相继走上了逃儒归释之路。邓豁渠曾从赵贞吉研习心学,后突然改变初衷,“以为性命甚重,非拖泥带水可以成就,遂落发为僧”〔16〕。李贽因“怖死”及“不肯受人管束”,乃坚心向佛,最初不过置名僧于公堂,“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17〕,后来索性弃官去麻城龙湖院做了和尚。袁中道大病之后“怖生死甚”,深悔“往日学禅,都是口头三昧”,决计“朝暮归依净土,作来生再会津梁”,于是购置一袭袈裟,每日支付米一升、蔬银二分,在二圣寺随众僧粥饭念佛〔18〕。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钱谦益在致黄宗羲的信中写道:“迩来则开堂和尚到处充塞……。士大夫挂名参禅者,无不入其牢笼〔19〕。此语虽未必尽实,却足以说明知识者迷恋佛教的狂热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入其牢笼”的士大夫中,掉弄机锋耽于禅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更多的却是象李贽、袁中道、邓豁渠那样坚定不移地“归依净土”。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宣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将“杀生”作为信徒们不可违犯的首戒,并通过寺院讲经和民间放生等活动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意识。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二《放生》云:“吾乡亦有放生会,每朔望输钱于柜,至期买羽、水二族放之。”渔隐主人在《欢喜冤家》第十三回亦写到杭州西湖盛况空前的放生会:“年年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满城士民皆买一切水族放于池中,比往日不同”。参与放生活动的人们,无论是日与诗书为伴的文人士大夫,还是挑葱卖菜的市井小民,无不在游玩消遣之余受到佛教净土观念的强烈感召。全社会一致皈依“净土”的文化心理,使知识阶层在个体生命价值判断方面与普通百姓形成共识,从而加速了自身的世俗化进程。
(三)
在嘉靖后期问世的《金瓶梅》中,已显露知识阶层价值观念变更的端倪。《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虽为“嘉靖间大名士”,但密切关注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对世俗社会的实际生存状态有着深刻而真切的认识,故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旷世“奇书”。作者将西门庆的物质活动与两性生活作为叙事焦点,从生理层面对人的自然欲望做全方位的展示。西门庆用各种令人不齿的方式获取物质财富,不仅出于满足个人奢糜生活需要之目的,更将之作为蔑视传统理性原则的精神支柱。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西门庆获得了前此商贾们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并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大批女性。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众多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向西门庆献出了肉体和灵魂。西门庆的不可一世,朝廷大臣的坦然受贿,应伯爵们的奉迎巴结,王六儿等人的投怀送抱,所有这些顺乎自然地引出结论:在人类生存过程中,物质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人们的物质欲望实际上不受理性原则控制。相对于物欲失控来说,色欲放纵更令人触目惊心。西门庆、潘金莲两位视男女交媾如生命的性爱顽主自不待言,他如陈敬济、李瓶儿、庞春梅、王六儿、林太太等人,亦皆有过不同程度的性放纵经历。在他们心目中,两性结合无须情感交流,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唯一只是从对方的肉体中获得生理满足和新奇刺激。李瓶儿由乖戾转变为温柔,潘金莲种种不安本分的变态行为,以及众多女性乐意接受西门庆疯狂的性榨取,其内在心理依据则是她们将生命价值定位于性欲满足。西门庆、潘金莲最终皆死于非命,前者更在冥间披枷带锁吃尽苦头。二人令人恐惧的毁灭,与其说是色欲放纵的必然结果,不如视为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报应。事实上,在有过性放纵行为的女性中,绝大多数并未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在《水浒传》中,潘巧云仅因与和尚裴如海通奸,被杨雄、石秀骗至翠屏山活体解剖式地残酷处决。相比之下,《金瓶梅》中的“荡妇淫娃”们要幸运得多,而这无疑应归功于作者对于人类生理需求的宽容理解。毋庸讳言,在性描写方面过于直露,生理剖析与理性思考成互相悖逆之势,使得《金瓶梅》的价值导向相当模糊,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产生“读者每至流荡”的负面效应。尽管如此,在文学创作中大胆引进前人讳莫如深的生理视角,描绘出真实的时代生活图景,仍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受《金瓶梅》影响产生的世情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极为明显。透过林林总总的世情小说,不仅能了解晚明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气,而且不难对当时知识阶层的世俗化程度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从纯生理视角描写已婚男女们出于动物本能的私通,堕落成为“着意所写,专在性交”〔20〕的淫秽小说。此类小说装帧、印刷、插图皆很精美,估计定价不菲却十分畅销。与此直接相关,编写一部色情小说无疑可获得相当丰厚的稿酬。从这个意义上说,色情小说作者反复申明的“以淫止淫”,其实可理解为“以淫换银”。必须指出,用淫秽笔墨轻松地解决生计问题固然是无耻文人们创作色情小说的直接动力,而在作品中间接地自我发泄亦为晚明知识阶层世俗化的必然选择。初始阶段色情小说中的男性主角,非历史人物即市井之徒,虽曾享受过极度性放纵的快感,但无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或此生遭杀身之祸,或来世妻妾淫人)。及至鼎盛时期的色情小说,男性主角的身份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文人们不再甘于潜伏幕后充当旁观者,于是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才子”作为自己的替身,以加倍的疯狂在作品中肆无忌惮地发泄肉欲。这些“才子”不仅有着令人羡慕不已的风流艳遇,应接不暇地享受美妇娇娘们主动送上门来的性服务,而且其非同寻常的美满结局亦令那些乐极生悲的前辈“浪子”们垂涎三尺。在色情小说泛滥成灾之际,某些“救世”心切的作家试图力挽狂澜,将通俗小说创作引上合乎传统理性原则的雅文化轨道。他们改变深受世俗社会欢迎的两性通奸的叙事焦点,再现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冲突,使读者获得真切的人生体验从而始终保持饱满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理性原则对各类事件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期待接受者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陆人龙编撰的《型世言》(包括其兄云龙的《清夜钟》)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为题材,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语言枯涩生硬,又喜发酸腐迂阔之论,显示出令人生厌的教化至上倾向。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虽皆“因贾人之请”而作,无疑受到过书商们“作肉麻秽口”之类的暗示,但自觉抵制狠求奇怪与大肆宣淫的媚俗恶习,高度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依靠娴熟的叙事技巧博得读者的喜爱。从整体上看,尽管《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什对于世俗社会追求物质利益和男欢女爱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却仍然较为明显地依附于传统的理性原则,以致无法克服作品中蕴藏着的内在矛盾。在《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撇开篇首那些与实际描写不符的堂皇说教不论,作者虽然对王三巧因丈夫长期不归而与陈大郎通奸的过失略施惩罚(所谓“妻还作妾亦堪羞”),但侧重于从生理需要和感情尚存的角度温和地看待女性失节问题,故最终仍让其在几经波折之后夫妇团圆。而在《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鸳鸯会》中,却出现了“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的恐怖场面,使人在毛骨悚然的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伦理道德的威严。这两篇作品虽非冯氏所作,后者更未对《清平山堂话本》中之《刎颈鸳鸯会》做只字片语的改动,但对于差距如此明显的价值取向莫衷一是,足以说明编撰者本人的茫然与彷徨。这种理性原则与感性生命之间的艰难选择,在《二拍》中同样明显地存在着,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将《欢喜冤家》置于晚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其全新的价值体系建立的必然性及其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历时性的角度说,《欢喜冤家》是自明代中期兴起的以反对禁欲主义为基本出发点的文化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以通俗小说的形式对人性的本质和个体感性生命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与全面总结,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发展了具有启蒙意义的时代文化精神。就共时性而言,在晚明的通俗小说中,《欢喜冤家》是唯一脱离传统雅文化轨道建立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体系的作品。如前所述,色情小说虽然彻底抛弃了传统的理性原则,但除了迎合和鼓励世俗社会放纵情欲,并未对感性生命进行过严肃认真的思考。以《型世言》为代表的教化至上类作品,固执地依附于脱离生活实际的传统理性原则,对人们普遍关注并力图作出新的理解的“人欲”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三言》、《二拍》试图在雅与俗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一个理想的结合点,但对于传统价值体系的过分依恋又使之选择了“脚踏两只船”的人生态度。《欢喜冤家》则不然,既毅然与传统文化告别,又没有放弃对于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新的理性原则的探寻,从而避免陷入纵欲主义的泥潭。从发生机制上看,渔隐主人将心学对于人性本质的思考与佛教“好生”观念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较为和谐地融为一体,用个体感性生命取代群体理性原则,从而真正建立起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体系。无可否认,《欢喜冤家》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认识并不全面,其生命意识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若假以时日,融入更多知识者的人生体验与理性思考,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当逐渐趋于完善。惜乎其问世不久即发生山河易主的鼎革之变,知识阶层惩于亡国之痛重新聚集在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地竭力抵制晚明盛行一时的世俗趣味,对于个体感性生命价值的探寻亦随之而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