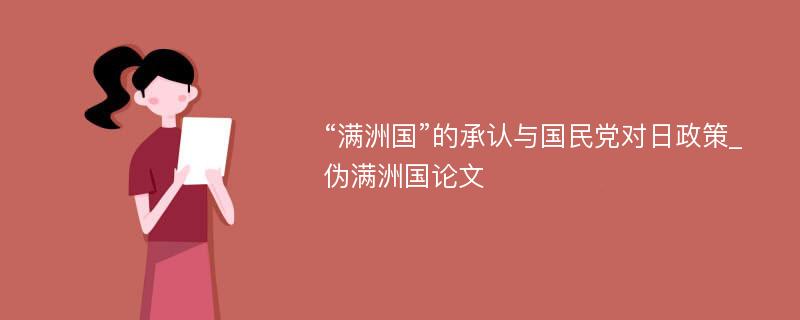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国论文,国民党论文,对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0)03-0014-06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建国宣言》在沈阳发表;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仪式在长春举行。伪满洲国正式建立了。“新”国家的成立,首先面临着国际上的承认问题。有关承认的国际法制度,在当时已日趋完善。关于国际承认的性质,向来有“宣告说”和“构成说”两种学说。现在的国际法教材或者对这两种学说进行折中,或者倾向于“宣告说”。比如,程晓霞主编的《国际法》就写到:“宣告说比较接近于事实而较为合理,现已获得大多数学者的支持。”[1]为什么支持“宣告说”的教材更多呢?这和新中国国际承认的实践有关。至1950年10月1日,世界上只有17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6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到1970年代初,世界上承认台湾当局的国家还是比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国家多。所以,大陆学者赞成“宣告说”,潜在的含义是:我国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不取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的数量,这一地位自1949年10月1日起已经牢固地确立。
然而,本文认为,“构成说”更为接近现实。所谓“构成说”,就是一个国家只有经过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倘若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了伪满,那么,中国东北就长期被分裂出去了,当然,这不可能成为现实。再就新中国的承认实践而言,如果长时期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一直很少,那么,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极大限制。
承认问题关乎国家生存发展,所以,近代以来,国际上的新国家与新政权成立之初,都积极争取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的傀儡政权也是如此。
1932年3月12日,伪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向17个国家发出“对外通告”,希望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包括:日、英、美、法、德、意、苏联、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荷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葡萄牙、捷克。通告的国家,除列强和苏联外,主要是欧洲新兴的独立国家。在通告中,谢介石阐述了伪满洲国的“对外交往的原则”,其中包括:“本政府将依据国际法及准则履行中华民国与外国缔结条约所规定应尽之义务及应忠实履行之义务;本政府决不侵犯满洲国范围内外国人民获得的权利并将充分保护外国人之人身财产安全;满洲国对外国人从事经济活动将奉行门户开放原则。”[2]第一项原则涉及到条约的继承。这三项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列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绝对不会因为伪满洲国的成立而受到损害,但所谓“门户开放”,实际上只是掩人耳目的说辞。
满铁调查部①作为日本侵略者的调查和政策咨询机构,在1932年7月提出:“母国中华民国如果承认分离团体满洲国,就等于放弃了各国承认满洲国时的抗议权,就等于承认了(满洲国的建立)与《九国公约》第一条尊重和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不抵触。在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上,帝国应采取如下政策:
一、努力使和满洲国有紧密利害关系的国家如苏联在事实上承认。
二、努力造成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的事态。
三、促成满洲国加盟国联。”[3]
日本为了使伪满洲国得到国际承认,的确是从上述三方面努力的。此外,还包括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和其他国家对伪满洲国的承认。按照上述政策,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是日本外交的努力方向。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对内长期军阀混战,对外依然受列强宰割。1928年底张学良政权的“东北易帜”,使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面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侵略,国民政府态度复杂,先是为避免和日本全面开战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而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虽然30年代初,国民政府内部有大量亲日派(汪精卫为核心)把持重要位置,但他们和蒋介石维持着合作关系,一度形成汪精卫主管行政,蒋介石主管军事的局面。在对外问题上,亲日派一边高唱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调子,一边“坚守”着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底线。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各派系和工农革命武装的挑战,基本上无暇顾及东北,最终采取了冻结东北问题的政策。
在当时,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是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
“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4]
在国际法上,《九国公约》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形成了约束,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上层都对此深以为意。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第一卷第二期刊登出来的《田中奏折》中谈到:“不幸帝国于对俄宣战时,误认该地之主权属于中国。其后华盛顿会议九国签字之际,复公开承认之,此不幸之尤者也。”②日本希望能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以彻底冲破《九国公约》的束缚。不过,其目的并未达到。
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后,1932年3月,《中华民国外交部工作报告》严正指出:“日军非法侵占东北各地,显系破坏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故在该项日军未撤退期间,中国政府对于在该处建立所谓独立或自主政府之举动,及令中国人民参加此种傀儡之组织,仍绝对不能承认,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云。”[5]
日方侵占东北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全境危险。1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作外交方针演说时宣称:热河省为满洲一部分,并且表示:“张学良麾下之正规军有越过国境而进入热河省之模样。根据《日满议定书》,属于满洲国领域之地方治安维持,固须两国共同负责,故所谓热河问题,乃纯然为满洲国内部问题。”[6]82为其侵略热河大造舆论。
1933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外交部长罗文干被解职,汪精卫接任,唐有壬任外交部次长。1934年,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担任亚洲司司长。这种外交人事布局和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在伪满洲国承认的问题上,包括亲日派在内的国民政府,态度非常坚决。因此,这一问题根本无法列入中日谈判的议程。于是,日方采取迂回战略,希望能够促成中国对伪满的间接承认。双方的外交战,主要围绕《塘沽协定》和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问题进行。
在热河全境沦陷,中日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的底线仍未动摇。亲日派的核心人物汪精卫致电负责与日本谈判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7]
1933年5月31日,中国军方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署《塘沽协定》。日方希望通过这个含混不清的文件,迫使国民政府间接承认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则希望通过派军方代表签字,来淡化这个协定的政治意义。《塘沽协定》规定: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队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8]。
《塘沽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对华北大片领土——冀东的主权。日方却可以采用包括飞机侦察在内的任何方式在该地区活动。《塘沽协定》的草案完全是由日方拟定的,中方几乎没有做任何修改。第三条使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的提法,意思是令中国方面认识到,长城线具有伪满同中国的“国境”意义;第四条强调中国方面只能负责维持“长城线以南”的治安,就是要取消中国方面对长城以北的主权,迫使中国间接承认满洲国。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开始了善后交涉。善后交涉主要包括“缓冲区”的接收以及山海关内外通车、通邮的问题,而伪满洲国的地位成为交涉中无法回避的部分。
1933年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喜多诚一自长春到达北平,向中方谈判代表黄郛提出《有关华北善后交涉商定案》,要求长城线各关口的警备权归属伪满,华北地方政权必须容忍伪满在山海关、古北口等处设置各种必要的机构,允许日军在《塘沽协定》的“缓冲区”使用土地和各类建筑物,并要求中国从速派遣人员与伪满洲国交涉通商贸易、交通等各类事项。
次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日方重申了外相内田康哉在1932年8月国会演说中确定的承认伪满的强硬政策,逼迫中国做出让步。黄郛随后表示,只要带有承认伪满洲国性质的和平方案,中方一概不可能接受。谈判性质属于局部善后问题,商谈问题应该局限于此,不能涉及政治、外交问题。中国代表强调长城各口的防务不应归属日本,应从速归还中国,但最后不得不屈服。日方《有关华北善后交涉商定案》的要求已经达到,于是就形成了关东军实际控制伪满与华北之间的“缓冲区”的局面。
除《塘沽协定》及其善后交涉外,日本还充分利用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问题。
1934年2月17日,日本有吉明公使直接会见汪精卫,再次要求解决“华北与满洲之通车通邮问题”。汪精卫答复说:“通邮、通车系技术问题,已授权与华北当局,如能筹得较好办法,而认为时机已到,即可办理。”[9]1934年,国民政府内部高级别的专门会议决定:“在不承认伪组织及否认伪政权存在原则之下,可与日本交涉关内外通行客车问题。”[10]
1934年6月,国民政府委托“中国旅行社”(1923年8月成立),与日方合组“东方旅行社”。中日双方在北平分别发表通告,自当年7月1日起恢复北平至辽宁的直达客车,每日北平、沈阳对开一列。中日双方随后制定了《东方旅行社组织章程》,共7章。在章程中,甲、乙方却不是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而是中日双方代表张水淇和平山贞斋。由于中日两国对外都宣称“东方旅行社”是中国旅行社和日本国际观光局合办,时人和后人都深信不疑。实际上,张水淇到山海关以后才知道,平山贞斋不是日本国际观光局的代表,而是满铁的成员。因此,在双方正式签署的文件上,不能写为日本国际观光总局的代表。国民政府不承认伪满洲国,极力避免和满铁直接交涉,因此也不能写平山贞斋为满铁代表。于是,日方就提出了这种以个人名义签署的方式。表面看,“东方旅行社”成了个人承办的机构,但是中国政府的命令一直是对中国旅行社发出。日方利用通车问题逼迫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目的并未达到。
尽管如此,中国旅行社依然因与日方合作,“涉嫌”承认伪满洲国而遭受指责。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的窗户被捣毁,其负责人对外宣布:
“中国旅行社原来不愿接受铁道部的提议。尽管如此,由于国民政府当局的坚持,并由于作为中国公民履行其职责,中国旅行社的董事会最终决定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在这件任务上与日方进行合作。尽管肯定东方旅行社将是一件蚀本生意……中国旅行社为了服务国家的缘故,仍没有对损失加以考虑。”[11]
国民政府不承认伪满洲国,因而在1932年7月23日全面中断东北邮政业务。这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东北人民与关内的通信完全中断;第二、经东北走西伯利亚铁路的国际邮路中断。日本想利用这个问题,在表面上解决通邮的同时,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1934年9月28日到12月14日,关东军方面的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进行了前后十五次的通邮谈判。
通邮谈判首先涉及邮票问题。邮票是经国家邮政机构发行的。邮票的使用区域,代表国家的有效统治范围。因此,关内外通邮采用哪种邮票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因为邮票对于双方而言,已经不是单纯的付费凭证,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和政治承认的问题。中方的基本立场是不承认伪满洲国,当然不能允许贴有伪满洲国邮票的信件公然进入关内。日方则希望直接使用伪满洲国的邮票,达到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目的。
会谈开始后,中方依照拟定好的方针提出使用中国通用的邮票,日方坚决反对,提出使用经过修改的伪满邮票,方案是取消票面上“满洲国”的“国”字与溥仪的头像,但在邮票用纸内制成“满洲邮政”四字的水印。中方见使用中国通用邮票很难获得日本同意,就提出另制作一种表示邮资已付的印花,但是印花中不能出现满洲字样及不适当的花纹,比如伪满国徽图案等。这种印花专用于东北进入关内的邮件。日方对中方的提案并不完全同意。
谈判过程中,“双方之上级决策单位察觉邮票在主权的承认上有超乎他们想象的效力,于是双边决策单位对此问题采取更保守与小心的策略,训令谈判代表依新的原则交涉。”[12]日方坚持必须承认伪满洲国的邮政机关,进而使用印有“满洲邮政厅”字样的邮票;中方除了坚持原来使用中国邮票之主张外,即使退让到必须使用专用印花的时候,也进一步主张此专用印花必须由作为第三者的商业机构发行,图案由中日双方协商确定。底线是委托日本邮政代办,总之不能由伪满洲国邮政方面发行。
1935年1月10日,中国关内和东北沦陷区之间的邮政业务恢复。信件的传递通过建立在山海关和古北口的一家机构进行。邮票和邮戳不使用“满洲国”的名称。伪满洲国发行了一种既无“满洲”字样,也没有溥仪肖像的特殊邮票,用于和中国关内的邮政业务。国民政府为避免承认伪满,对恢复以后的邮政业务非常谨慎,比如:拒绝发往“新京”的信件,而首先将其地址改为“长春”。
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问题“解决”以后,中日双方就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继续在外交领域进行较量。
1935年2月,国际常设法院法官王宠惠在赴荷兰就任的途中,顺道访日。王宠惠表面上没有承担任何外交使命,实际上是探询日方对华政策的进一步走向。就在王宠惠访日之前,蒋介石接受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公开的资料显示,采访并未涉及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但是,蒋介石在回答有关“中日提携”的问题时说:“东亚只有中日两个国家”[13],实际上间接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伪满洲国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5月7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将驻中国的日本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的提案。17日,中、日、英三国公使馆相互升级的消息在南京、东京、伦敦同时发表,随后美、德、法也仿效日本,和中国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于当年7月4日临时回国,回国前曾经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谈。会谈中,蒋作宾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广田弘毅则表示,希望中方采取实际措施,避免因为不承认伪满洲国而发生的中日纠纷。回国期间,蒋作宾可能接受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些指示。8月,他返回日本后,重申:中日双方应该尊重彼此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两国维持真正的友谊;两国一切事件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这是对王宠惠以私人身份访日期间谈到的原则的重申。蒋作宾表示:在日本同意并且实施上述原则的前提下,中方可以暂时冻结满洲问题,不要求回到“满洲事变”前的状况,但希望取消满洲事变后迫于日本军部压力而缔结的一切协定。关于“满洲国”问题,蒋介石的意见是:虽然不能承认满洲国的独立,但是可以暂时置之不问[14]244。目前能找到的关于蒋作宾和广田会谈的资料,均来自于日方。所以,蒋介石最终是否真的对伪满洲国采取置之不问的态度,尚存有疑问。但是,可以从后来蒋介石的言论以及国民党的正式文件中找到一些线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提出:“(调整中日邦交)的初步解决在于力使冀东、冀北、察北的匪伪军丧失依靠,以除去对我华北行政和主权之障碍。”[14]491并未涉及东北问题。1939年2月30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解释“抗战到底”就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6]313。在他的视野里,伪满洲国问题,也就是东北地区的光复问题,已经被冻结了起来。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日方并没有放弃“(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的要求。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日本至少秘密进行了三次重要的“和平工作”:1937年12月,德国大使陶德曼将日本的和平条件转达给蒋介石;1938年6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派代表秘密在香港与中方接触;1940年3月,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与中方代表宋子良、陈超霖在香港“和谈”。三次密谈,日方的和平条件都涉及了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提出“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声明:“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绝对无效。”[15]154到当时为止,日本扶植的所有傀儡政权都缺少政治分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明显是要分化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国民政府所说的“日军占领区域”并未明言是否包括东北,但应该是有针对性的防止出现新的叛变投敌者。1941年12月9日的对日《宣战公告》并未写到收复东北四省国土,但是同一天发表的对德意《宣战公告》中提到:“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已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5]472
参与对汪精卫诱降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到,1940年3月9日,秘密谈判的中日双方“通过”了所谓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恢复和平后),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3月10日,中方代表张治平送回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意见:“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16]对于这次谈判的真实性,国民党方面的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一直极力否认。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重新提起东北问题。他在书中说:“琉球、台湾、澎湖、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之要塞,这些地方之割裂,即为中国国防之撤除。”[17]然而,上述地区是否都要收复、采取怎么样的方式收复,蒋介石并没有提及。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收复东北,是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和罗斯福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和罗斯福一致同意:东北四省(伪满洲国)、台湾、澎湖列岛及大连、旅顺两港口应交还中国[18]。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中国收复失地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综观全面抗战开始到《开罗宣言》发表之前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没有明确地提出收复东北四省的主张,很少明确地否定伪满洲国。国民党当时在东北确实留有大量的地下工作人员,但是,关于这些工作人员的短期使命和长期目标的资料还有待于发掘和整理。目前也很难查阅1937年到1943年的《蒋介石日记》。但基本上可以肯定,蒋介石对伪满采取的是冻结策略:既不让步,也不谈收复。最大的原因是蒋介石认为:东北的收复有赖于盟国的援助。
注释:
①1906年,满铁成立,随后建立起下属的专门调查机构。满铁调查部的名称存在于1907-1908、1928-1943年,其他时间为调查课、经调会、产业部、调查局等。1939年起的大调查部时期,人员近2 500人,并拥有多个现地调查机关。1932-1936年称经调会。
②《田中奏折》的真伪是有争议的。但是,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考辨其真伪并无实际意义。因为《田中奏折》中的各项政策,日本军部和政府一直都在实施。
标签:伪满洲国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日开战论文; 历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蒋介石论文; 塘沽协定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