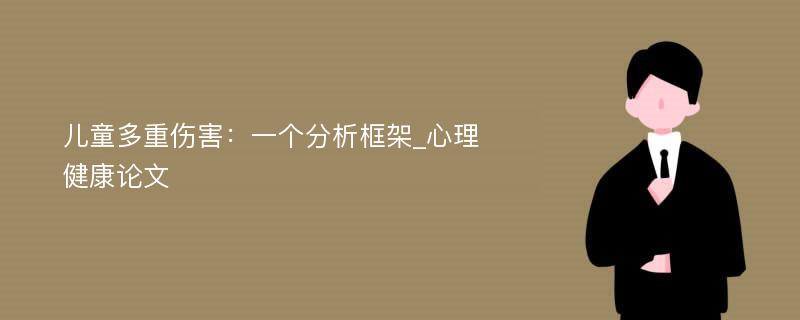
儿童多重伤害:一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5-0083-09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5.05.006 儿童伤害(child victimization)的类型有很多,例如儿童虐待、欺凌、目睹家庭暴力,目睹社区暴力或犯罪等。Finkelhor通过对2030名2~17岁的儿童进行调查发现,71%的儿童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遭受过一种伤害,如暴力、犯罪、虐待;22%的儿童遭受了多重伤害,其中15%的儿童遭受了4~6种伤害,7%的儿童遭受了7种及以上伤害(Finkelhor,2005,2007)。以往关于儿童伤害的研究多侧重于单一类型伤害对于儿童的影响,如性虐待(Jonzon,E.& Lindblad,2006;Davies,E.A.& Jones,2013)、儿童欺凌(Lee,S.T.& Wong,2009;Hinduja,S.& Patchin,2010)、目睹社区暴力(London.& M.J.,Lilly & M.M.& Pittman,2015)等,他们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某一种特定类型伤害的研究,容易导致高估个别伤害对儿童的影响,而忽视了与其他类型的伤害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此外,单一类型的儿童伤害研究不利于辨认处于多种伤害威胁的儿童,并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干预。为此,Finkelhor等学者在2005年发展了“多重伤害(poly-victimization)”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广泛、细化的调查,全面评估儿童遭受的不同类型的伤害,辨别遭遇多重伤害的儿童,了解并解释多重伤害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为实施有效的干预提供系统和科学的参考。 一、儿童多重伤害的概念及测量 多重伤害是指儿童在过去一年内经历多种不同类型的伤害(Finkelhor,D.Ormrod,R.K.,Turner,H.A.& Hamby,S.L.,2005),具体包括:身体攻击、财产伤害、虐待、儿童欺凌、性伤害、目睹/间接伤害。而多重伤害受害者则是指在一年中同时经历4种或4种以上伤害的个体。为了更准确、全面地测量儿童的伤害状况,Finkelhor发展了青少年伤害量表(Juvenile Victimization Questionnaire,JVQ)(Finkelhor,D.,Ormrod,R.K.,Turner,H.A.& Hamby,S.L.,2005)。JVQ适用于9岁及以上的儿童自行填写,同时针对9岁以下儿童则设计了家长版本。这套量表共有5个模块,共计34项问题:常见伤害,包括抢劫、偷窃、袭击行为等;儿童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情感虐待、被忽视等;来自同龄人或兄弟姐妹的伤害,包括群殴、约会暴力、欺凌等;性伤害,包括强奸、言语性骚扰等;直接目睹或间接伤害,包括目睹父母间暴力、父母对兄弟姐妹施暴等。量表以(0,1)的形式计分,1代表受到此种伤害,0代表未受到此种伤害,计算总得分。Finkelhor将JVQ总分≥4分(均分为3分)定义为多重伤害。4~6分为低水平多重伤害,总分≥7分为高水平多重伤害(Finkelhor,D.,Ormrod,R.K.& Turner,H.A.,2007)。各模块下均包括相关子问题,如侵害者的性格、是否使用的武器等。2011年Finkelhor对JVO进行修正,加入14项有关威胁、社区暴力、目睹家庭暴力、网络欺凌等新测量指标(Finkelhor,D.,Turner,H.A.,Hamby,S.L.& Ormrod,R.K.,2011)。经过检验,JVQ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信度方面,内部一致性检测结果显示,JVQ总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各模块间系数介于0.35~0.64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时隔3~4周后对100名儿童和100名儿童监护人再次测试,重测信度K均值为0.59,在可接受范围内;建构效度方面,JVQ与儿童创伤症状量表(TSCC/TSCYC)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间存在中度相关,具有良好的效度(Chan,K.L.,Fong,D.Y.T.,Yan,E.,Chow,C.B.,Ip,P.,2011)。 目前国内对于儿童多重伤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测量工具主要采用中文版青少年伤害量表(JVQ)。一项针对中国香港儿童的调查显示,JVQ的5维度与其子问题间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3、0.83、0.64、0.73、0.71,且不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经检验,JVQ与假设的社会心理学变量、压力变量、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变量具有相关性,对于反应儿童伤害状况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Chan,K.L.,Fong,D.Y.T.,Yan,E.,Chow,C.B.,Ip,P.,2011)。程培霞等运用JVQ中文版对中国山东省临沂市2419名高中生进行测评,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伤害量表中文版的维度结构与原问卷维度结构基本一致,问卷总分与维度分的相关系数为0.34~0.78,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5,重测信度为0.82,也证明了JVQ的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Cheng,P.,Cao,F.,Liu,J.,Chen,Q.,Dong,F.,Kong,Z.& Li,Y.,2011)。 二、儿童多重伤害的理论解释 (一)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该理论认为学习是个体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掌握社会知识、经验和行为规范以及技巧的过程。其核心思想在于阐述人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学习并形成和发展个性。班杜拉将学习分为直接学习和观察学习两种形式,直接学习是个体对刺激做出反应并受到强化而完成的过程,离开学习者本身对刺激的反应及其所受到的强化,学习就不能产生;观察学习是指个体通过观察榜样在处理刺激时的反应及其受到的强化而完成学习的过程。同时,社会学习理论注重对人的行为原因的考察,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内、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唐卫海、杨孟萍,1996)。儿童除通过直接学习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榜样的示范行为进行学习。家庭是儿童的首属群体,父母是儿童的直接模仿对象。父母作为榜样,对儿童的行为、言语都具有示范作用,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至关重要。研究表明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外部行为问题,如攻击、对抗和反社会行为(Lundy,M.,& Grossman,S.F.,2005;Bauer,N.S.,Herrenkohl,T.I.,Lozano,P.,Rivara,F.P.,Hill,K.G.& Hawkins,J.D.,2006)。此外,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可能会经历或表现出与内化行为相关的症状,如恐惧症、分离焦虑、寡言少语、低自尊及较低的社交能力(Huth-Bocks,A.C.,Levendosky,A.A.,&Semel,M.A.,2001;Kitzmann,K.M.,Gaylord,N.K.,Holt,A.R.& Kenny,E.D.,2003;Peled,E.,2000)。这些研究表明,多重伤害会增加儿童心理创伤的风险。 (二)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由鲍尔比(Bowlby)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认为母婴之间形成的亲密情感联结是情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依恋之所以贯穿生命全程且相对稳定,是因为早期依恋所形成的稳固的“内部工作模式”。该模式是婴儿在早期亲子互动中建构的关于自己、照顾者及双方互动的心理模型或者特征,这种内化的表征将对儿童的各种社会人际关系(如同伴关系)产生影响,更会对其成年以后的人际关系和婚恋关系产生长期的影响。艾斯沃斯将婴儿的类型分为三类:安全型、焦虑—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徐娜娜、段春媛,2010)。 依恋理论认为儿童早年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体验会影响到孩子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信任,并且形成探索、认识世界的固定模式,也会形成与他人交流的模式。孩子对父母产生的信任感将由此推及到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信任,能够很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反之,儿童期没有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儿童,缺乏自我认同感,较易产生恐惧、忧郁、愤怒、紧张等不良情绪,会对他人、周围环境产生不信任感,难以适应陌生的环境,从而影响他以后对待周围的人、事、物的方式,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增加儿童遭受多重伤害的风险。 (三)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由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于1979年提出,该理论指出环境对于个体行为和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外在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系统。 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微观系统是指儿童亲身接触并参与体验与儿童有紧密联系的环境,如家庭、学校、朋辈群体等,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要素都会对儿童的发展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中介系统是指儿童所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如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当儿童从一个系统进入另一个系统中时,两者就会发生相互关系,且儿童在一个系统中的作用受到在另外一个系统中关系的影响;外在系统是指对儿童发展起间接作用的环境,如父母的工作单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等;宏观环境是指儿童所处的大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等。同时,儿童所处的小系统、中间系统和外系统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车广吉、丁艳辉、徐明,2007)。系统间的相关性解释了多重伤害的不同来源,在家庭受到虐待的儿童在其他环境(如学校、朋辈群体)中也更加容易受到伤害,从而成为多重受害者。 (四)发展型受害者框架(Developmental Victimology Framework) 发展性受害者框架由Finkelhor提出,认为儿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的身材、力气、认知能力、性别意识、人际关系、社会环境都会发生巨大改变,且这些因素间相互影响都可能会令儿童遭遇伤害,因而需采用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儿童的伤害问题(Finkelhor,D.& Dziuba-Leatherman,J.,1994;Finkelhor,D.,Kendall-Tackett & K.,1997)。发展型受害者研究框架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1)风险因素的发展性。儿童受到的伤害随着年龄、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例如:蹒跚学步的儿童很少成为枪杀案的受害者,风险因素发展性又体现在儿童的性格及居住环境的发展性,它们的改变可能会使儿童成为伤害的对象,也可能会让其更懂得保护自己。(2)伤害对于儿童影响的发展性。儿童对伤害做出怎样的反应取决于儿童的发展阶段和脆弱程度。例如,青少年和蹒跚学步的儿童对于父母忽视和抛弃的反应有所不同。伤害除了会给儿童造成恐惧等常见性影响外,还有可能对儿童造成一系列发展性的影响,例如:自卑、侵略性行为、人际障碍、药品滥用、脱离群体、自残等。发展型受害者框架为立足于发展的视角,为儿童为什么遭遇多重伤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儿童多重伤害的影响因素 儿童遭遇多重伤害的因素可从社会人口特征、儿童自身、家庭以及外部环境来考察。研究发现,男孩更易遭受多重伤害,7岁和15岁是最可能遭受多重伤害的年龄节点,这是因为当儿童进入新环境时需要时间来认识新朋友和熟悉学校生活,因对潜在的威胁缺乏意识而增加受害的可能(Cuevas,C.A.,Finkelhor,D.,Ormrod,R.K.& Turner,H.A.,2009);相对于年幼的儿童,年长儿童(10~17岁)更易成为多重伤害者。 从儿童自身看,儿童某些特殊持久性的行为模式、情绪问题会让他们自己成为多重伤害的目标,例如暴躁易怒、消极沮丧、易哭泣、人格易分裂、感知力差等问题,会使得儿童在危险环境中难以形成自我保护(Bernstein,J.Y.& Watson,M.W.,1997;Hodges,E.V.E.& Perry,D.G.,1999)。其他一些人格特质在某些情境下也会使儿童成为受伤害的对象,如身体残疾(Finkelhor,D.,Ormrod,R.K.,Turner,H.A.& Holt,M.,2009)、性别特质不明显等(Williams,T.,Connolly,J.,Pepler,D.J.& Craig,W.,2003)。Finkelhor等人的研究发现,精神诊断也可能是导致儿童遭受多重伤害的风险因素。儿童有情绪问题,可能会增加风险行为、产生敌意、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有过精神诊断经历的儿童在五类伤害类型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例如受到精神诊断的儿童,49.3%受到了常见伤害,而未受过精神诊断的儿童受到一般伤害的比例为33.9%。还有研究表明,精神诊断与常见伤害、儿童虐待、受到来自同龄人或兄弟姐妹的伤害、目睹暴力有着重要联系(Berger,L.M.,2004)。 家庭方面,单亲、重组家庭的儿童更易成为多重伤害对象(Berger,L.M.,2004;Lauritsen,J.L.,2003;Turner,H.A.,Finkelhor,D.& Ormrod,R.K.,2007)。在家庭中遭遇儿童虐待和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也更容易成为受害者(Mohr,A.,2006)。儿童在家庭中受到虐待后会出现许多情绪、认知等方面的困扰,这些困扰会影响他/她与同龄人的交往及获得准确社会信息的能力,增加了被同辈欺凌的风险(Shields,A.& Cicchetti,2001)。Perry & Hodge(2001)进一步提出“家庭诱导伤害模式”,该模式发现受虐儿童在同龄人面前常常表现出脆弱、侵犯行为、逃避等特点,这些特点亦容易导致被同辈欺凌。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复杂而混乱的家庭环境,例如失业、婚姻危机、家庭财务危机等,会导致儿童缺乏监督,而增加他们遭遇多重伤害的可能性(Finkelhor,D.,Ormrod,R.K.,Turner,H.A.& Holt,M.,2009)。 外部高危环境也会导致儿童遭遇多重伤害的风险加大,例如邻里环境失衡、社会支持脆弱、社区监管缺失、犯罪率高等外部因素都会增加儿童遭受多重伤害的风险(Turner,H.A.,Finkelholr,D.& Ormrod,R.K.,2007)。Coulton等人(1999)发现混乱的邻里环境和社会支持的缺失会降低居民对虐待行为的干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活在高危环境中的儿童更易成为暴力、虐待、欺凌的对象。 由此分析得出,儿童多重伤害的成因与儿童所处的生态系统有密切的联系。微观系统——家庭、学校及同伴群体、社区,尤其是家庭作为首属群体,对儿童受到伤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儿童性格、行为的社会化具有启蒙和塑造作用,直接影响儿童进入到其他系统中的状态,具有延续性。同时,如果儿童身边的这些系统存在着高危险因素都将增加儿童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因而,需要对儿童遭遇多重伤害的原因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 四、多重伤害的影响 多重伤害经历会对儿童的身体、心理和行为造成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遭受多重伤害的儿童在创伤症状上的得分要明显高于单一类型伤害的儿童和没有伤害的儿童。在10~17岁遭受多重伤害的儿童中,80%和86%的儿童分别表现出了焦虑和抑郁的症状(Finkelhor,D.,Ormrod,R.K.& Turner,H.A.,2009)。陈高凌等人(1996)的研究发现,中国版JVQ得分与抑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陈倩倩和曹枫林(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遭遇多重伤害的儿童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组儿童的得分。此外,还有研究表明遭受多重伤害的儿童表现出了很多行为问题,例如吸烟、饮酒、网络成瘾、接触色情制品等(刘佳佳,2011)。 此外,多重伤害的负面影响具有持续性。已有的研究证实,多重伤害儿童继续遭受伤害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5.1倍。第一次调查显示遭受过伤害的儿童中有59%在第二次调查中仍遭受伤害,尤其是遭受性伤害、虐待的儿童(Finkelhor,D.,Ormrod,R.K.& Turner,H.A.,2007)。其次,多重伤害可能会导致更广范围的伤害。在第一次调查中受到虐待的儿童,再次遭受一般伤害的机率是未受到虐待儿童的1.9倍;遭受财产侵犯的机率是未受到虐待儿童的2.2倍(Finkelhor,D.,Ormrod,R.K.& Turner,H.A.,2007)。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伤害都可能增加遭受其他类型伤害的可能性。这些研究充分说明,遭受多重伤害的儿童处在一种伤害的环境中,是一种常态,而非一系列偶然事件。 五、多重伤害的预防和干预 针对儿童多重伤害问题,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预防和干预的建议。首先,需要准确、全面地评估多种伤害的类型。评估儿童伤害时需要综合考虑伤害类型,尤其当儿童遭受性虐待或欺凌,需要考虑到伤害症状间的相似性,专业人员有必要及时查明儿童是否有可能同时遭遇了其他类型的伤害及危险(Finkelhor,D.,Turner,H.A.,Hamby,S.L.& Ormrod,R.K.,2011)。第二,把握多重受害优先原则。考虑到多重伤害与精神健康、行为问题、学校表现等密切相关,且其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某一单一类型的伤害,专业人员应给予多重受害者重点关注,并综合考虑受害者的伤害史并对伤害进行正式的评估和归类。在采用心理健康干预时,专业人员应从旁观察儿童,鼓励儿童自行描述伤害经历及相关症状。这一建议强调儿童个人、关系网络在预测和保护儿童遭受伤害中的作用(Holt,M.K.,D.Finkelhor,and G.,Kaufman Kantor,2007)。第三,积极发展多重伤害的干预措施。治疗不能仅局限于单一伤害,尤其当伤害的风险因素存在共性时,应多角度、全方面地应对多种伤害,其中针对污名化及创伤回忆的策略同样适用于对多重伤害问题的处理。第四,积极应对潜在环境的风险。专业人员在实施干预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伤害给儿童带来的伤害,同时要关注总体环境或个体与环境互动之间产生的伤害。因此,专业的干预要在评估环境因素的同时,还应发展出相应措施,例如:教授育儿知识及监护技巧,培养父母、监护人与儿童间依恋关系,增加“儿童身边有能力的监护者”。第五,打破伤害的循环机制。基于多重伤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必要尽早发现并打破伤害循环机制。早期预防与干预十分重要,例如对危险、破裂家庭环境,危险邻里环境,儿童情绪问题等的及早识别,能够有效地预防现有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多重伤害。通过帮助家庭成员、法律监护人、照顾者、教师和其他可能给儿童提供帮助的成人提高监护及保护能力,以阻断伤害的恶性循环。 我国在应对儿童多重伤害的问题时,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政府、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儿童自身等方面开展预防和干预的工作: 第一,政府层面,健全并完善儿童保护法制。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责任主体,加强执法力度;成立儿童保护监管部门,出台专门的儿童保护法,切实保障儿童的权益。 第二,家庭层面,考虑到多重伤害产生的原因与儿童本身特质有关(例如:易恼怒、沮丧、比较消极),社会工作者需协助家长关注儿童的性格、行为方式;倡导父母与儿童友善的沟通交流,传授相应育儿知识和监护技巧;提升父母对儿童多重伤害的了解,建立家庭伤害预防机制;针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社会工作者应帮助家庭获取相关资源,提升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三,学校层面,教师要对新入学的儿童保持高度敏感性,尽早识别易受伤害的目标个体并传授伤害干预技能;学校社会工作者应特别关注具有情感困扰症状的儿童,除给予心理健康干预外,帮助其发展同辈关系,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关注儿童同辈群体,评估儿童的社会支持力量,避免儿童遭受伤害。 第四,社会层面,社会工作者需要以社区为依托,评估儿童所处的社区环境,降低社区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从而降低儿童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在全社会倡导儿童价值、儿童福利,推进相关儿童福利政策、组织的建立与完善,推动儿童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成立,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全面的儿童本位的福利体系;为青少年司法体系提供完善的伤害筛选、评估、安置和处理的标准,尽早识别,积极预防。 第五,儿童自身层面,通过开展个案管理、小组活动等方法帮助儿童学会情绪管理、提升社交技能;针对已经受到伤害的儿童,社会工作者需综合考虑其幼年经历与现在经历间的关系,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帮助儿童改变对于伤害的消极影响的看法,改变妥协、逃避行为,提升儿童的抗逆力,增强儿童应对风险的恢复力和抗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