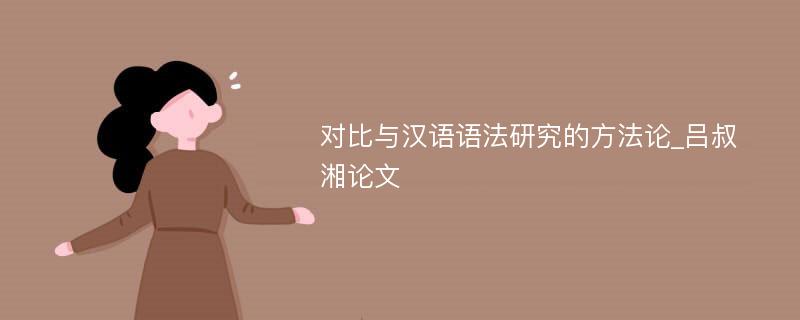
对比和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汉语论文,语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的语法研究从来都非常重视西方的语法理论和方法,但不大重视西方语言学家直接研究汉语时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这不免失之于片面。根据西方语言学的某一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建立起相应的语法理论体系,这自然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但不可否认也有它消极的影响,这就是为用“印欧语的眼光”观察汉语的结构提供了一种滋生的温床;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已为此作出了清楚的注释。至于国外语言学家对汉语的研究,其成果良莠不齐,但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的汉语研究,由于视角新颖,方法对路,往往会提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见解;我们只要能从中吸取它的精髓,定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其成效绝不会低于前一种研究途径。洪堡特就是这种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位理论语言学家,研究汉语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独树一帜,提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新途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本文以此为契机,联系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对比两种研究途径的成效,就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具体的讨论。
一 语言对比的研究和洪堡特的汉语观
洪堡特是理论语言学的开拓者,研究过很多语言,其中包括汉语。他的汉语论著有《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前者是1826年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后者是给阿贝尔-雷缪萨先生的信;两者基本上是繁简的差异。这封信是一篇有深邃内容的学术论文,很长,姚小平先生译成汉语,有三万余字①。在这些论著中,洪堡特对汉语语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提出了很多独特的看法,我们不妨名之为洪堡特的汉语观。他认为:“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区别可以归于一个根本的事实:在把词联结为句子时,汉语并不利用语法范畴,其语法并非建立在词的分类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思想中把语言要素的关系固定下来。其它语言的语法有词源和句法两个部分,而汉语只有句法部分。由此便决定了汉语句子结构的规律和特点,一旦我们进入语法范畴的领域,就会改变汉语句子的本性。”语法范畴是一些带有一定语法特征的词的类别,它与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有密切的关系,在词与句子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因为正是语法范畴起着说明词和命题统一性关系的作用”。这种统一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印欧语的语法是双轨制,一轨是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一轨是“主—谓—宾”的句法结构,二轨有内在的联系,即名、动、形的词类和句法结构成分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做谓语,形容词做定语,二轨合一才能造出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形成洪堡特所说的语法范畴与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统一性”联系。这是印欧语语法规则的核心。但是,如果要用这样的规则来分析汉语,“就会改变汉语句子的本性”,因为“汉语岂止是忽略语法范畴的标示,实际上它是不屑于使用范畴标记”。根据这一认识,洪堡特认为汉语中没有名、动、形的词类区别,“所有的词都用来直接表达概念,而不指明语法关系。所有的词,哪怕是在一个封闭的句子里,都处于纯粹状态,类似于梵语的根词。从语法上看,汉语确实没有屈折动词,严格说来也没有动词,而是只有动词性概念的表达;动词性概念以不定式的形式出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含混不清的一种形式”。这样,汉语的词不分名、动、形,而只有动词性概念的词,名词性概念的词;一个词往往既可以用作名词性概念的词,也可以用作动词性概念的词。这恐怕是汉语的实词无词类分别的最早论述。
没有语法范畴,不分词类,那如何造句?洪堡特认为这“完全取决于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词序在汉语语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严格说,在汉语里,词序只是指出,哪个词决定着哪个词。这种决定作用可从两个不同方面观察:一方面是一个概念的范围由另一个概念加以限定,又一方面是一个概念指向另一个概念。于是,起限定作用的词出现在受限定的词之前,被指向词跟在指向词的后面。整个汉语的语法就是建立在这两条基本的结构规律之上。”洪堡特还对这两条语序规则做了具体的解释:“在汉语里,词以非常确定的顺序排列为句子;这种词序所依据的根本原则在于,起修饰作用的词处在被修饰词之前,宾语处在支配它的词之后。当一个动词表达一个行为的概念时,本质上要求有一个它所针对的宾语;而当一个名词表示事物(属性或实体)时,本质上要求人们进一步限定其概念范围。所以,在汉语里识别名词要看它前面有没有限定语,识别动词要看它后面是不是跟着宾语。”
这几点恐怕就是洪堡特汉语观的核心,是他对汉语结构特点的认识。这一理论产生于《马氏文通》问世前七十余年,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过去对它的了解很少;而《马氏文通》以后影响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西方语法理论由于不是从汉语的研究中直接提炼出来的,因而也很少有人评述洪堡特的汉语研究。这一切使我们对洪堡特的汉语观既感到陌生,也感到新鲜,与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大相径庭。洪堡特的论述是否正确、全面、合适?人们见仁见智,评价可能会截然不同,但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这是在没有先入之见(即以某一种理论为依据)的情况下从具体语言材料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其精神比较接近于语言的直觉,或者说,接近于汉语结构的实际。这样的论断人们可能不同意,但希望不要因此而影响我们观察问题的方向,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完全是洪堡特的结论,而是他凭以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比较不同语言的结构差异,弄清楚每种语言的特点,进而对特点的成因作出理论的解释,我们不妨把它名之为“对比”。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语言特点的挖掘和认识,是值得推崇和提倡的。洪堡特正是比较了汉语和印欧语以及他所研究过的其它语言的差异之后才得出上述的结论,认为“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领域”,“在其它语言里具有联系的东西,在汉语里却往往分散、孤立地存在。因此,汉语的词语分量更重,迫使人们到词语本身之中寻索它们的关系。换言之,汉语让听者自己去添补一系列中介概念,而这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劳动:精神必须弥补语法所缺的部分”。这种特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模糊,需要人们自己根据语境和交谈双方的交际意图去补充,使之明确。“汉语有时显得有点模糊,但是,妙就妙在模糊上。”这是季羡林先生(1999)在总结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之后谈到汉语语法特点时说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洪堡特的论述的一个脚注。
对比的研究方法使洪堡特发现了汉语的特点,建立起独特的语法理论。这是我们从洪堡特的汉语观中得到的最大启发,说明对比是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语言间的共性,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语言的特性;要建立一种有特色的语言理论,必须以语言特性的研究为基础,洪堡特的汉语研究已为此作出了强有力的证明。汉语的研究如果要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离开这种对比的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史可以印证我们的论断。
二 “对比”的研究方法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
《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但这一“现代”,基本上是在仿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用印欧语的语法框架、理论、方法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为行文方便,我们不妨把这种方法论原则称之为“仿效”。用这种方法引入西方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论证方法,建立起汉语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个学术领域,使中国语言学进入转型期,其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但是也无法否认,它使汉语的语法研究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印欧语语法的阴影。在一个学科的初创时期,有这样一些弊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这里不是要评论谁的是非功过,而是要讨论方法论原则与汉语研究的关系,看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汉语结构的研究。
仿效和对比,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仿效论的着眼点是语言的共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的语法理论看成为语言共性的表现,因而认为它同样适用于汉语的研究,可以“依样画葫芦”地分析汉语的结构,而对语言事实与理论的矛盾则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比论着眼于语言的特点,想从对比中发现不同语言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语言结构的研究,对特点作出理论性的解释。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什么时候的语法研究就能取得比较大的实质性进展。四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就是广泛而深入地采用了对比研究的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三位先生。1936年,王力先生(1936,92)在《中国文法学初探》中明确提出,“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又过了几年,王力先生(1943,23)进一步指出,为了“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从语言事实出发才是研究语法的正确的道路”。吕叔湘、高名凯两位先生都同样强调对比研究的重要性,“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即对比——笔者)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是徒然”(吕叔湘,1942“上卷初版例言”);“和不同族的语言语法相比较可以看出一种语言语法和他族语言语法的不相同的地方”“汉语的语法系统和印欧语的语法系统是那么样的不同,为着明了本身的特点计,除了用普通的一般的比较外,我们应当细细的对于汉藏语系的语法作一比较的研究,同时更应当对汉语的方言加以比较的研究,因为方言的语族问题比较汉藏诸语的语族问题更来得明确”(高名凯,1948,55)。三位学者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起各有特点的三家语法理论体系。他们都探求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共性和特性,但把立脚点放在汉语特点的研究上,因而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称道。当时的对比研究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突破就是使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脱钩。前面说过,印欧语的语法结构是双轨制,词类和句法结构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词类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脱钩,就是二轨分离,各自进行独立的研究,这就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印欧语的语法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王力、吕叔湘接受叶斯丕森的“三品”说,认为“中国的词类可以从概念的观点上去区分”“词类是可以在字典中标明的,是就词的本身可以辨认,不必等它进了句子里才能决定的”,而词品则是在词入句以后就词与词的关系而言(王力,1944,19,29)。高名凯(1948)走的是另一条路子,认为汉语的实词没有形态变化,不能进行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但每一个词可以有名词的用法、动词的用法、形容词的用法,其说法与洪堡特相差无几。二轨分离,这就向摆脱印欧语语法阴影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以这一“脱钩”为基础的研究也提出和解决了汉语语法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王力先生根据汉语“与世界诸族语
相异之点”而提炼出来的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的句式分类和能愿式、处置式、使成式、被动式、递系式等的结构规则都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关于语法研究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的两种研究途径的论述和实践、有定性范畴在语法结构中的地位、动词的“系”的理论和关于汉语语法特点的论述,不仅揭示出汉语独特的结构规律,而且某些方面的理论还进入了语言学发展的前沿,如有关动词单系、双系、三系的“系”的理论就比国外相关的配价理论要早十余年。哈里斯、乔姆斯基的转换、变换(transformation)理论在五、六十年代曾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产生过重要影响,而这种思想也早已见之于我们四十年代的语法论著,吕叔湘先生关于句子和词组的转换、王力先生关于“把”“被”字句的转换等都已涉及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高名凯先生虽然在言辞上没有谈及转换或变换,但他的句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转换思想的表述,因为他明确指出,陈述、否定、命令、询问、传疑、反诘、感叹等不同的句式都是“同样语言材料的不同说法”“因为这些句子所用的词语和平面的造句法所用的完全一样,只是加些成分,或变更方式,而用另一种‘型’来说而已”(高名凯,1948,429)。这些情况都说明,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使我国的语法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既揭示出汉语独特的结构规律,对语言共性和特性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在理论上还有创新。当时的汉语语法研究已出现了不少接近于国外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闪光思想,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据此形成闪光的理论,因而人们的印象不是很深刻。这里最典型的是吕叔湘先生关于动词“系”的理论,无声无息,直到七、八十年代学习西方语言学的动词的“向”“价”理论之后才逐渐发现吕叔湘的开创性论述。形成这种讽刺性现象的原因恐怕与我们不重视语言理论建设有关。我们的传统研究不乏精彩的、有深邃意义的理论创见(如“因声求义”之类),但基本上只是进行例证,缺乏演绎论证的思辩,因而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吕先生的“系”理论也有此不足。这恐怕也是我们难以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汉语词类问题的辩论和“对比”研究方法论的挫折
五十年代,语言学界发生了多次学术争论,其中有两次争论,即主宾语问题的讨论和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相互间有内在的联系。从方法论的原则来说,这两次讨论是中国语言学想仿效结构语言学的新理论重建二“轨”联系(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句法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的反映,以便与四十年代所采用的方法论原则分道扬镳。这是方法论的对立和冲突,不可避免地会爆发激烈的论战,词类问题的讨论就是这种对立和冲突的集中表现。当时,语言学的主流思潮是结构语言学,认为在语言的共时分析中应该排除历时因素和外系统因素的干扰,只需要用分布分析法就可以研究汉语的结构。人们争相仿效这种理论和方法来解决汉语的语法结构问题。不过,这时候的仿效与《马氏文通》以后、四十年代以前的仿效分析不一样,它带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色彩,摆脱了机械模仿的痕迹,在词类问题讨论中的反映就是主张用词的结合能力来划分汉语实词的词类。这是结构语言学分布原则的具体化和汉语化。争论的另一方是高名凯先生(1953)。他单枪匹马,笔战群儒,主张汉语实词无词类的分别。高先生采用的方法就是对比法,认为汉语的词与印欧语不一样,没有形态变化,与句法结构成分没有规律性的联系,同一个词既可以做主宾语,也可以做谓语或定语,因而实词无词类的分别。他所运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与洪堡特是一样的。但这种方法当时无法抗拒结构语言学的思潮,因而沦为批判的对象。吕叔湘、王力两位先生是四十年代采用对比方法的旗帜性学者,他们的观点这时候也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吕先生(1946,97)认为汉语语法研究“所能凭藉的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而在论争之后他比较偏重于位置的分布研究,强调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讲语法(吕叔湘,1954),为重建二轨的联系开拓前进的道路。王力先生(1955,1956,1959)接受了苏联语言学家的词汇·语法范畴的概念,重新认识汉语的特点,并对他自己四十年代的语法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放弃了凭概念分词类的主张。他认为汉语有形态变化,“动词是诸词类中最富于形态变化的”,在划分汉语词类的时候“应该首先应用形态标准”“句法标准(包括词的结合能力)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准,在不能用形态标准的地方,句法标准是起决定作用的”“词义在汉语词类划分中是能起一定作用的,应该注意词的基本意义跟形态、句法统一起来”。王先生的汉语词类理论从概念论走向多标准的综合论,但从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的研究来看,不难发现,他仍然坚持着四十年代的研究方法。四十年代语法理论上的最大突破是二轨脱钩,而五十年代的两次大论辩批判了这种脱钩的理论,全力用结构分析法重建二轨的联系。王、吕两位先生的语法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向着这种联系倾斜。否定的否定,汉语语法研究又进入了一次新的螺旋式的发展。
辩论中坚持汉语实词无词类分别的高名凯先生陷入了极端的孤立。着眼于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这种孤立实质上就是对比方法的孤立。批评高名凯先生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他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分析汉语,而忽视汉语本身的特点。笔者(1994)过去也认为这是印欧语眼光的反映,只不过是一种浅层的印欧语眼光而已。这一看法不对,现在慎重修正。高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不是印欧语的眼光,而是对比方法的运用。要说印欧语的眼光,主张仿效分布分析法来研究汉语、划分词类的理论才是这种“眼光”的反映,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认为词类和句法结构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做谓语,形容词做定语,从而把汉语的结构纳入印欧语的双轨制语法框架中去研究,重建四十年代已经脱钩的二“轨”之间的联系。所以,高名凯先生与其他学者的论争实质上是两种方法论的论争,是对比法与仿效法的论争,论争的结果是对比法“寡不敌众”,遭受挫折。高名凯先生虽然仍坚持汉语实词无词类分别的主张,但论辩的尖锐性已大为减弱。这次讨论影响深远,涉及到此后几十年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方向,语法学界基本上形成了结构分析法的一统天下,对立的意见也随着高名凯先生的去世而销声匿迹。但是学术上是非的最高评判标准不是哪一种理论或哪一个权威,而是语言事实的检验,论争中一时的高下不一定是客观真理的真实反映,汉语词类问题的论争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张冠”难以“李戴”,结构语言学的语法理论无法解决汉语词类的划分问题,因而原来难以发表的一些意见又逐渐浮现出来,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同意和理解高先生意见的人越来越多;即使是那些顽强地坚持汉语有词类分别的学者,论述中也分出动名词、名动词之类的类别,要是高先生还活着,肯定还会就此发动一场大辩论。所以,这场影响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的大辩论应该有新的评价。一种正确的、有价值的方法论为什么会败下阵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我们过分迷信国外的语言理论,把它视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另一个原因恐怕是高先生自己对汉语的具体语言现象缺乏深入的研究,无法使对比的研究方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推敲的重大课题。我们这一评述的基本精神与二十余年前的评述(徐通锵、叶蜚声,1979)有重大的差异,说明我们自己也在语言事实面前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通过两次大辩论,结构分析法虽然取得了支配地位,对结构规则的形式化描写也取得了进展,但语法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并不大,除“层次”“分布”这些概念和方法之外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与四十年代的语法研究比较,内容相对贫乏;把汉语纳入双轨制的语法框架去研究,也是矛盾重重,仍然无法解决词类的划分和它们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排除历时因素和外系统因素的干扰,也无法对结构规律作出理论性的解释。吕叔湘先生(1977)感觉到这种单纯的分布分析法的局限性,不利于语言特点的研究,于是又重新提出对比研究法的重要性:“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比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等等,都是跟别的事物比较才认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这一倡议复活了对比研究法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从而使汉语的语法研究又发生了一次方法论的转折。首先应用这种对比的方法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朱德熙先生(1985a,1985b)。他通过方言间的横向比较和古今汉语间的纵向比较揭示出汉语反复问句的结构规律和分布区域;通过汉语和印欧语的对比,提出汉语的两大特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的词组本位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设法使词类和句法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脱钩,想在词组的框架内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脱钩尽管不彻底,对汉语特点的认识人们也有分歧,但无疑在向摆脱印欧语理论的束缚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徐通锵,1997)。同样是对比研究的方法,朱先生与洪堡特、与四十年代的王、吕、高三家的理论体系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差异?这恐怕与朱先生的观察视角和结构语言学分布分析的因袭负担过重有关。九十年代,对比研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路,这就是着眼于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它和语法结构的关系,一般简单地称之为“字”本位理论。它与以前的几种对比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差异。以前的对比都以“词”为基础,由于“汉语中没有词”,印欧语word这一级结构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赵元任,1975),因而对比的研究都无法完全摆脱印欧语理论框架的影响。以字为基础的对比研究想抓住中国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透过以语义为核心的汉语特点的分析揭示隐蔽于它背后的结构原理,建立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对比研究,或者说,是一种深层的对比,牵一发动全身,涉及整个理论体系的调整和改造。为什么?因为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两个,就是词和句;句不是指一个个具体的句子,而是指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框架。两个基本结构单位形成双轨制的语法结构,相互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二轨合一才能造出符合交际需要的句子。所以,词类和句法结构成分之间的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构成印欧语语法结构的核心,各种规律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形成,或者说,都需要接受这一根本性规则的支配。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只有一个,这就是字,根本不存在双轨制的语法规律;以仿效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一定要在汉语中建立双轨制式的语法体系,那无异是要在根本没有规律的地方找规律,自然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使二轨脱钩的努力,方向正确,成效显著,我们的语法研究如果能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那肯定是会取得比较理想的成效的。
四 对比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相互间也存在着某种共性。在具体语言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共性和特性的关系,这是每一种方法论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从洪堡特开始,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就其大的趋向而言,就是对比和仿效两种。这两种方法论的语言观基础,如前所述,是有差异的,对比论着眼于语言的特点,想通过对比重点研究语言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理论;仿效论着眼于语言的共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西方语言学的某一种理论是语言共性的反映,同样适用于汉语的研究。两种方法论从两个不同的立脚点出发处理语言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来看,对比的方法论成效比较好,因为它立足于语言特点的研究,能从对比中揭示出汉语的特点,使总结出来的规律具有比较深厚的语言基础。共性存在于特性之中,语言特点的发现和研究才能有助于语言共性的研究,因此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解决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四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和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汉语特点的研究以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为这一论断提供有说服力的佐证。要实现中国语言学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对比的研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开拓前进的道路。
仿效研究的方法论能不能揭示语言的特点,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理论上完全可以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问题是如何处理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汉语事实的关系:是用理论来框限语言事实的分析,还是根据语言事实与理论的矛盾去修正理论?从《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向来看,我们迁就西方的语言理论有余,而根据汉语的特点,即与理论相矛盾的汉语事实去修正理论的勇气不足,用吕叔湘先生(1986)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们在儿化之类的现象与音位理论的矛盾面前表现出来的裹足不前的情况就是这种“迁就有余,而修正理论的勇气不足”的一种具体表现。汉语儿化之类的变音是无法用线性的音位分布理论来分析的,但我们不敢怀疑音位理论本身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因而继续在音位、语素音位之类的概念上兜圈子,致使理论研究滞步不前,无法对汉语变音之类的现象作出切实的理论性解释。可以用来印证、对照的是美国语言学的生成学派,它根据音位理论难以解决英语、俄语等印欧系语言的重音而突破“音位发现程序”的框框而创建生成音系学、非线性音系学、词汇音系学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就使音系学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样是理论不适用,引出的结果却不相同。人家认为音位理论处理不了英语重音是有普遍意义的,因而对结构主义进行了‘革命’,建立起新的、普遍性的语言理论。我们则或者以为普遍理论不可更改,或者认为儿化韵是汉语独有的。一次很好的机会,根据汉语的特点来修正、补充、以至重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王洪君,1994,307-308)这恐怕就是中西语言学的差距的具体表现,是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思想障碍。现在碰到的汉语事实与流行理论的最大矛盾就是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印欧语的语法是双轨制,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的结构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我们用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发现语言事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名词可以做主宾语、定语和谓语,动词可以做主宾语和谓语,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谓语、定语和状语。这种矛盾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印欧语理论用于汉语的语法研究有严重的局限性,应该根据汉语的特点创建新的理论,以揭示隐蔽于汉语特点背后的普遍结构原理。着眼于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进而突破和修正理论,这从方法论上来说,已从仿效转向对比。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艰苦努力,设法使二轨脱钩,就是这种转化的标志。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根据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去修正理论,使汉语的语法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已经在语音的研究方面失去了一次“根据汉语的特点来修正、补充、以至重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机会”,希望在语法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不致再发出同样的感慨。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不管是采用对比论,还是仿效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揭示汉语的特点,并从特点的研究中去揭示隐蔽于它背后的结构原理,弄清楚它与语言共性的关系。从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史来看,对比研究的方法论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从洪堡特开始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对比分析法以及它的成效和局限,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以利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
①下面引述的译文均据姚小平。非常感谢姚先生提供他还没有来得及出版的洪堡特的译著。
